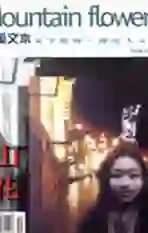遗失在眼中
2004-04-29刘建东
刘建东
顾小红的手机一直在响。这使得顾小丽的讲述不时地被打断,她烦躁地说:“你能不能把手机关掉!”
顾小红说:“不能,我还得靠男人们挣钱呢,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靠什么活?”
顾小红讲得有道理,顾小丽毫无办法,她的讲述只能是时断时续,她看着那个鲜红色的手机,觉得它像是一个发情的男人。
顾小丽来给姐姐讲妈妈的事情是迫不得已,因为那不是她—个人的妈妈,而是她们两个的。她觉得让自己一个人来承担那么大的压力不公平。虽然顾小红已经有五年时间和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瓜葛了,可是那个令人担忧的人毕竟还是她的亲生母亲。顾小丽说;“她是你妈妈这没错吧。所以你得听我把话说完。”
现在,像五年前的你一样,妈妈要逃离这个家。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妈妈的逃离跟你的情况完全不同。你是自愿的,而妈妈是迫不得已。你是去寻找你的幸福,虽然那种幸福我们不屑一顾。可妈妈要离开是不是能得到她的幸福就另说了。妈妈有这种想法已经很久了,但是她一直在犹豫,一直无法拿定主意。她想走是因为我们这个家太穷了,你知道我们的情况,自从爸爸死后我们的生活就一直往下滑,就像是坐滑梯。妈妈一个月只能从居委会领一百多块钱的救济。我和林刚一直和妈妈住在一起,我们没有钱去租房更别说去买房。我的腿你也清楚,作为一个残疾人我不想和别人攀比,只是想过得平静一些,可是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让人放心。对我们来说,生活就像是一条潜伏的蛇,它随时都可能窜出来咬我们一口。你当然想像不到,因为你早已经从我们身边逃走了。但是你的生活我可从来没有羡慕过。如果别人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姐姐。每次我都会断然否定的。你不要说我太绝情,我真的是看不起你做的那桩事。
好了,不要说你了,还是说说我们吧。我一直没有工作,而林刚也早就从单位下岗了。这几年他都是四处打工,别说是挣到钱了,就是简单的养家糊口也很困难。林刚的脾气就越来越坏。他时常打我。我并不怪他,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咬着牙不喊叫。我把疼痛都埋藏在心底了。他一个正常人,能够娶我我该知足了,而且他真的很爱我。我还能有什么要求?我知道他心里也苦呀。他打我两下能释放一下自己心中的痛苦,那我也值了。我尽量掩饰着身上被打的痕迹,可是天天在—起呆着,妈妈肯定能看出来,妈妈终于有一天就憋不住对林刚说:“你不能再打小丽了,你会把她打坏的。”
林刚当时就勃然大怒,他把饭桌掀翻在地。从那天起他们俩人的关系就十分紧张。他们之间好像有一张绷紧的弓,随时会把箭射出去。而我却无能为力。他们两人的紧张在半个月前达到了极致。
我们家不是住在一楼吗?林刚想结束那种四处打工的生活,也想使我们这个家能早点脱离贫困,他想把我们家那个邻街的房子改造成一个小门脸,他想开个小杂品店,可是妈妈和陈爽住在里面。于是他就琢磨着给妈妈介绍老伴,想把妈妈从这个家挤走。这一次妈妈没有生气,有一天她流着泪对我说:“小丽,我要离开这个家全是为了你。”妈妈没有让林刚给她找老伴,其实早就有一起的老人给妈妈介绍。妈妈一直以这个家离不了她为理由拒绝了,现在,妈妈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她去见了那个早就想和她谈谈的老头。那是个退休的干部。每个月有近两千块钱的退休金。老头看上去也。挺和蔼可亲的。两个人都很满意。但是老头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她不能带任何人。
对,该说到陈爽了。
陈爽是妈妈现在最大的障碍。你知道陈爽几岁了吗?对,三岁,亏你还能记得。说实话,你那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即使妈妈天天带着他,我想妈妈心里也是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就像当初你把他甩给妈妈时,你说的话倒很轻松,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你甩给妈妈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而是一块抹布。你说,妈妈可以把他扔掉,或者送人。你说,妈妈能忍心把他扔掉吗。好赖,他的身体里还流着我们家的血液呢。这三年来你几乎没有看过那孩子一眼,你当然不知道妈妈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妈妈叫他什么吗?野种。妈妈就天天这么叫他。这三年来,妈妈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她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是你干那些事情的后果,可是她又不能放弃对孩子的照顾和爱护。可是我和林刚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孩子一天。林刚背地里还打过他。这就是你的孩子的处境。你想想看,妈妈要想答应那个老头的要求有多难。她不可能把孩子给你。因为你早就说过你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她又不能把他扔给我们。她知道我们会像对待垃圾一样对待陈爽的。妈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我觉得这段日子的妈妈憔悴了许多。
与此同时,那个姓魏的老头频繁地来找妈妈,他可能是真的觉得妈妈对他很合适。他甚至把自己家门的钥匙交给妈妈一串,他对妈妈说,你随时都可以进那个家。但老头的条件也无法动摇。他说,我知道你那个小外孙的情况,我工作三十多年都没有让别人说闲话,到老了也不想给50人留下什么话柄。那一段时间,妈妈带着陈爽在外面玩,她口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她听着那悦耳的声音,看着无邪的陈爽,她真的有些为难。
后来妈妈想到了一个两全的办法。陈爽不能一直跟着她。总有一天她会死去。她只能给陈爽和她自己都安排—个好的归宿。她想到了把陈爽送人。当妈妈想通了这一点便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家。妈妈费尽了心思。她真的找到了理想中的人家,那一家本来有个孩子,在一次意外中死去了。他们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有一天那一对夫妻来了,看上去两个很有教养,也很有身份,两人的穿着都十分体面。两人看着陈爽就眼泪汪汪的,显然他们看到陈爽想到了自己的孩子。那女的还抱着陈爽死死的,都把陈爽吓哭了。是的,那一对夫妻看中了陈爽。几天之后妈妈给陈爽穿上了最干净漂亮的衣服,拿上他所有的玩具,两个人出发了。那一对夫妻本来是开了车来的。他们的汽车在我们院里还引起了一刹、小的轰动。但是妈妈坚持没有坐他们的车。她说她要自己把陈爽送到他的新家。陈爽看着那漂亮的汽车,真想坐上去玩玩,妈妈对他说:“孩子,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去坐汽车。”
妈妈蹬着她的破三轮车送的陈爽。没有人知道妈妈为什么非要蹬着三轮车去送陈爽,她也许是想把最后的回忆只留给他们两人,也许她是再给自己一点时间,看自己是不是会后悔。在那段不长的路程中,妈妈骑了整整一上午。这足以说明在那段路途中妈妈的思想斗争是多么复杂。那天妈妈把陈爽送到后并没有马上回家,整整一下午她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才听到她沉重的脚步。一天的时间妈妈好像过了有一年。回到家她就躲在自己房间里,也不吃饭。我去叫她时,看到她躺在床上像是一具僵尸。我就坐在她身边劝导她。我对她说:“陈爽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她是个野种。”
妈妈的声音轻飘飘的从床上飞过来:“他还是个孩子,那不是他的错。”
我接着说:“连他自己的妈妈都不喜欢他,你又何必呢。”
妈妈说:“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他一直以为我是他的妈妈。你说陈爽会不会恨我?”
我想妈妈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我能做到的只能是让她回到以前我们正常的岁月中。对,我说的正常的岁月是指没有陈爽的那些日子。如果你不给她甩这么大的包袱,妈妈会这么伤心吗?我说:“不会,孩子从来都不会仇恨。你选中那一家,也是因为那一家有钱,能给陈爽更好的未来,他能有个好的未来不是更好吗?”
我的话让妈妈的思维暂时脱离了伤心的海洋,她躺在床上,在一片黑暗之中畅想着陈爽的未来:“他会离你姐姐很远。他永远不会知道你姐姐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两个人会对他好。他们会供他上学,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研究生,也许他会出国。他永远不会记得你姐姐,可是他也永远不会记得我。”妈妈绕来绕去又回到了她伤心的起点。她真的无法摆脱陈爽的影子。她觉得在那小屋里的黑暗中到处都有陈爽的身影在飞。她倾听着屋外的动静,她在听汽车的声音。她说:“也许他们后悔了,他们不想要一个孩子了。”在刚刚失去陈爽的打击下的妈妈是个无法劝说的母亲。你只能任由她的思想一步步地向伤心的深处滑落。而那些此起彼伏的汽车声也加剧了她的伤感。对此我毫无办法。
没有人能说出妈妈从家里出去时的准确时间。因为我和林刚都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我们没有听到妈妈开门出去的声响。我们的梦里静悄悄的,连对方的呼吸都听不到。外面下雨了,那是一个让人拥有梦境的美妙时刻。而后来在冷嗖嗖的城市之夜中一个人的伤痛和兴奋是属于妈妈一个人的。
妈妈摸着黑走出了家。妈妈一直就没有脱去她的外衣。她无法睡眠。睡眠像是石头那样沉重。我们楼道里向来是没有电的,妈妈在走到楼洞口时崴了脚。所以在那个夜晚的后半程,妈妈走路时就一直一扭一扭的。好在夜色掩盖了这一切。妈妈狼狈的样子不会被任何人看到。连她自己也顾不上看自己同样狼狈的影子。那时间大概是在午夜或者更晚。时间对于妈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已经从伤心之中逃离出来,隔着浓重的夜色和迷蒙的雨雾,她仿佛听到了陈爽的笑声。她觉得小外孙的笑声就在她已经跳不动的心脏里。妈妈一路走得很快,她觉得在夜里走那条路并不十分漫长。这跟白天的感觉完全不同。妈妈赶到那对夫妻家时雨越下越大,妈妈的身上已经湿透。可是妈妈没有感到身体的份量在加重,相反她倒是觉得轻飘飘的。她站到了那对夫妻的门前。她听到了哭声。黑暗中的妈妈一下子笑了,她听到的陈爽的哭泣声简直比笑声还要动听。陈爽的哭声已经嘶哑了。而妈妈的样子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当那对夫妻打开门时,他们吓了一大跳,他们并没有立即认出妈妈。而还在痛哭的陈爽还没有看到妈妈就从门外飘过来的雨气中嗅到了妈妈的气息,他的哭泣戛然而止。
接下来的时间应该是属于他们两人的。他们在雨中的街道上快乐地走着。街道成了他们快乐的游乐场,那黑暗,那雨丝,仿佛都成了他们‘陕乐的道具。
是的,陈爽又回到了我们身边。陈爽的回来使妈妈的离去又投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妈妈不离开这个家,林刚的希望就又会无限期地拖下去。所以,在陈爽回来这件事上,遭到最大打击的就是林刚。他无法发泄他心中的郁闷,我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他打我时手更重了。次数也增加了,他仿佛是故意要做给妈妈看,要给妈妈示威似的。每次他动手打我时,我都咬着牙不吭声,我是怕被妈妈听到。可是那段日子林刚却喜欢上了我的叫声。他一边打我一边说:“你不喊叫我就一直打。”
我实在无法抵御挨打的痛苦了。我的喊叫其实是无意识的。而我的喊叫像是毒品一样令林刚上瘾。我的脸上肿得像是红色的南瓜。以前,林刚是从来不打我的脸的。到这种地步,林刚心中的苦闷是真的无法控制了。我不恨他,你别这样看我。我真的一点也不恨林刚。他爱我,他还像以前一样爱我。他打我是因为他心中有太多的伤痛。他想让我得到幸福,他想让我像一个正常女人那样过得好,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我脸上的红肿像是一面旗帜,是给妈妈看的一面旗帜,妈妈当然知道那面旗帜的意思。有一天她看着我脸上的红肿,她的眼里不像前一天那样眼泪汪汪,她说:“小区的南面,就是通向花园的那个道上,有一个井盖丢了。没有人管。我站在那里向下看了看,看不到底,只能听到下面传上来水流的声音。那声音并不大。”
接下来的一天,妈妈又对我说:“那是个深井。据说下面的水流得很急,能通向滏阳河。”
是的,那几天,妈妈的心思全在那个丢失了井盖的井上。她说:“那是污水井。人下去转眼间就会被淹死。即使不会淹死也会被臭味熏死的。”妈妈说这句话时,脸上竟然有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那笑容让我有点不寒而栗。
妈妈对那井的关注一直在持续。妈妈开始用数学的概念去理解那口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井。她说:“从我们家到那口井有两种走法。一条路是沿着那条肮脏的水泥小路,直角的时候才拐弯。一共要走一百零八步。我说的是在没有人挡你路的时候。如果有人挡路,那就另当别论。第二条路是不走那水泥路。而是走直线。直线的距离不是最短吗?当然路不好走。要越过一些泥沆,还有老王家种的一小片向日葵,再绕过那个门球场,才能到,但是这段距离短,只走八十步就够了。”
我没有去考虑妈妈突然对数学产生了这么浓厚的兴趣。我只是在想着我脸上什么时候船恢复到原形。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门了。我想出去到地摊买一个头绳,我的头绳都被林刚打断了。妈妈突然问:“我走哪条路好?”
我—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妈妈,我说;“随便,你想走哪条路都行。”
妈妈追问道:“那陈爽呢?”
我说:“也随便。”
等我脸上恢复了原样,我下楼去买头绳。我看到妈妈左手牵着陈爽,—遍遍地在走着通向那口井的路,她一会儿走那条水泥小道,一会儿走那条土路,嘴里还数着自己的脚步。她和陈爽都已经对那条路十分地熟悉了。我还看到她闭着眼拉着陈爽走。我远远地看着她们,我以为她宴走到井里边去了,我刚要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停了下来。他们正好停在井口。妈妈和陈爽。她低头向下看了看。然后抬头看了看天。
就是那个下午我才对妈妈的举动产生怀疑的。我觉得她之所以对那口井那么感兴趣,一定有她的目的。那口井并不漂亮,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唯一可以给人带来的就是危险。我特地跑到井沿向下看了看。那黑洞洞的井让我看得有些毛骨悚然。我甚至有一种向下跳的感觉。从那时起我的头脑中就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妈妈这样的举动不只是数学的问题。它只能预示着三个结果,一是妈妈想要跳下去,另一个是她想引导陈爽跳下去,三是她要带着陈爽一起跳下去。那几天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口井的样子,还有妈妈和陈爽跳下去的扑通声。那样子和声音都那么令人恐怖,它甚至比林刚打我还难受。那几天我简直成了一个哲学家,那三种可能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我想来想去,就推翻了其中的两个假设,—个是妈妈自己要跳下去,这不太可能,妈妈很坚强,她从来就没有轻生过,即使父亲的去世也投有击垮她。另—个就是妈妈和陈爽—起跳下去。既然第一条不成立,那就说明妈妈还想活下去,她不想给我们带来悲伤。所以这一点也基本上可以排除。只剩下了陈爽落井的一种可能。我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越大。陈爽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不速之客,他的到来只增添了我们家的混乱,其它的什么也没有带来,再说,他的突然消失不会影响我们任何人。它不会影响你,因为你从来也没有承认你有过那么一个孩子;它不会影响妈妈放心地去嫁给那个老头;它也不影响林刚想要开一个杂货店的希望。这是三全其美的事。为什么妈妈不选择这一条呢?我越想越害怕。我倒不是害怕陈爽一下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可是晚上我一躺下,一想到那个后果,我的后背就像是针扎似的痛疼。我觉得那是妈妈的目光。是她的目光让我感受到害怕的。她的目光不是一束,而是越来越多,是许多束,它们在我背上越聚越多。那目光是尖厉和坚硬的。我几乎都有些受不了了。
我知道,这是妈妈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可是我又不能阻止她。我不能天天跟在她的身后,即使我跟在她身后,她要是想做我也无法拦阻,所以我想到了你。因为只有你可以让那个后果不发生。
喂,你听着没有,你好像都睡着了。你这个混蛋。
劂、红揉揉眼睛说:“没有,我没有睡着,我听着呢。你说的一字一句都像是石头砸在我心里呢。”
顾小丽着急地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顾小红不耐烦地说:“我尽在这里听你说这些废话,得耽误我多少工夫,损失多少钱。你也听到了,这么一会就有十几个电话找我。”
顾小丽生气地说:“你那些臭男人重要,还是你儿子的性命重要?”
顾小红说:“你别跟我发那么大火,你跟我发那么大火干什么。这几年你和妈妈可从来没把我当成你们家的人。现在想起我来了是吧。我还懒得管你们那些咸淡事。我必须得走了。我再不走,今天的生意就泡汤了。你们爱谁跳井就谁跳。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完话,顾小红扬长而去。
顾小丽看着姐姐妖娆的背影,狠狠地向她吐了口痰。痰没有吐到顾小红的身上,而是无力地落在不远处。顾小丽骂道:“你这个贱人,良心果然让狗给吃了。”
顾小红听到了妹妹那句话。关于那个孩子,关于母亲和那个家,几年来她都没有来得及细细地想一想,是哪里出了什么差错。思想让她感到了沉重。而她现在的生活让她感到轻飘飘的,她喜欢这种感觉,这让她感到了生活的乐趣。既然她喜欢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不让它继续下去呢?她想。
顾小红在随后的时间里忙不停地接着电话。她嘱咐其中的一个男人。她在接电话的时候还想着那个姓赵的男人的模样,那人叫赵卫东,那是她见到的最诚实的一张嘴脸。她觉得把这件事交给他是最合适的。她叮嘱道:“你一定要看住那个老太太和那个孩子。我是说那口井,对,别让他们靠近那口井。”赵卫东说:“我不让任何人靠近它。”那男人同时得到了她的许诺,很兴奋地就答应了。然后她约好了属于另外一些男人的时间,便关掉了手机,打的向罗城头生活区奔去。
她让出租车在她妈妈家那个院里绕了一下,她看到赵卫东已经就位。他就站在那口井的旁边警惕地看着四周的人。她没有看到妈妈,也没有看到陈爽。她真的忘记了陈爽长什么样了。妈妈和陈爽都是她生活中沉重的东西,她不想记着。她想,也许过后可以考虑一下姓赵的建议,嫁给他。这个念头只是—瞬间便消失了。
就像顾小丽说的那样,老魏是个和善的老头。这是顾小红敲开老魏家门时的第一个感觉。老魏听她说是来给他送礼物的,便很热情地请她进了门,忙着给她沏茶,端水果。顾小红很从容地坐在老魏家的沙发里。她四下打量了一下,除了有点稍微的零乱外,家用电器等等一应俱全,肯定要比妈妈家好许多。她想,也许妈妈嫁过来是们艮好的归宿。老魏端详着顾小红。他疑惑地看着顾小红,问道:“我好像不认识你。”
顾小红嫣然一笑:“你是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可是有人认识你。正是那个人让我来给你送一个礼物。”
老魏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他显然在思考那个给他送来礼物的人,当他抬起头来时,眉头是舒展着的,有人送来礼物肯定是件好事,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刚刚退了休的老家伙,这说明还有人惦记着他,于是他试着问道:“是物资局的张处长?”
顾小红微笑着摇摇头。
老魏又问:“那是车队的老尚?”
顾小红依然微笑否认。老魏一连串问了有十几个人,顾小红都一一否定了。最后顾小红说:“你不要猜了,这个人不让我告诉你。但是礼物你总得收下吧。”
老魏点点头:“那当然,对于别人的好意我向来是不会拒绝的。那么,你替那个人带来的是什么礼物?”
顾小红笑了笑:“你不要那么心急。我先把茶水喝了,你有烟吗?”
老魏犹豫了一下,眉头皱了皱,他对于顾小红的这一个要求感到有些意外,但他还是拿出烟,递给顾小红。顾小红接过烟,很老道地点着烟抽了一口。顾小红平静地说:“我就是那个礼物。”
老魏张开嘴,诧异了半天,他更加地疑惑。顾小红站起身,在原地转了个圈,说道:“怎么,你对我这个礼物不满意吗?”
老魏张口结舌道:“我,我我我……”
顾小红说:“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吧。我在这里耽误了太长的时间了。”她说着就开始脱衣服。老魏有些紧张地看着她的举动,他突然向门外跑去。顾小红哈哈大笑,她没有去阻拦老魏。她知道他哪里也去不了。她若无其事地继续脱衣服。果然,老魏跑到门口,已经打开了门,一只脚踏到了门外,他猛然醒悟过来,又把门关上,回头自言自语道:“这是我家,我为什么要走。”他指着顾小红道:“走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我。”
顾小红已经脱得只剩下内衣内裤,她说:“我不走,我还没有把礼物交给你。”
老魏捂着自己的眼睛,声音发颤着说:“你会把我的名声毁掉的。你赶快走开。”
顾小红把自己的身体贴上去,嘴唇凑到他的耳朵边,她看到老魏的耳朵薄薄的,不像是一个有福之人,她说:“好名声值几个钱,好名声还不是做给别人看的。现在也没有别的人。你不用担心你的好名声。这对你的名声一点影响也没有。我只是做我的工作。你快点好不好。”
老魏闭着眼,他不知道这是谁送给他的礼物,他也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礼物。他说:“我可一辈子都没有做过这些事。”
顾小红不耐烦地说:“你装什么正经,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的时间。”
老魏不知所措,他感觉到了顾小红在脱他的衣服,他忧心忡忡地说:“我有心脏病……”
整个过程是在老魏半推半就之中草草结束的。
顾小红面对成了一滩泥的老魏亮出了她的底牌:“我现在告诉你吧,是谁让我来给你送这个礼物的。他是—个三岁的孩子。他不想离开—个人,那个人也不想离开他。他想和那个人—起来和你作伴。”顾小红说出了妈妈的名字。直到顾小红走,老魏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天花板。顾小红顺着他的眼睛向天花板上看了一眼,那上面除了一盏日光灯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顾小红从老魏家出来后还感到自己轻飘飘的生活仍在快乐地继续,这样游戏般的日子正是几年来她孜孜追求的。她喜欢随心所欲,她想那些让她感到沉重和忧伤的东西都离她远远的。随后她就去了那个井边。她看到赵卫东还老实地呆在井边,他不停地围着井边徘徊,脚下散落着烟头。他的样子—定让人们以为是区环卫处的工人,他像是个守护者,防止人们掉到井里。顾小红走上前去对赵卫东说:“走吧,你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跟我走吧,我会报答你的。”
赵卫东非常高兴这么快就能从这里解脱出来。他兴奋地对顾小红说:“这口井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顾小红说:“是的,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走吧。你想不想现在就得到快乐?”
两天之后,顾小红回了趟家,不过她并没有顺着那狭窄而昏暗的楼洞走进去,她在外面等着顾小丽出来。顾小丽果然出来了。顾小红便拦住她询问,顾小丽,妈妈是不是可以顺利地嫁给那个老魏了。她询问顾小丽时脸上露着笑容,她以为那已经是铁定的事情了。可是顾小丽却—脸的愁容。她说:“相反,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顾小红不相信会有另外的结果,她大声说:“这怎么可能?”
顾小丽白了她一眼,说道:“那个姓魏的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下午突然掉到了那个井里,对,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个丢失了盖子的下水井。据看到的人说,那天下午他一直在井边徘徊,看上去心事重重的。他还和妈妈在井边碰过面,他和妈妈还说了几句话。事后我问过妈妈,他在井边都说了些什么,妈妈说,他只是反复地说一句话,他说他对不起妈妈。后来妈妈领着陈爽走开了。这几天妈妈的心情一直不好。我每天都偷偷地跟在她身后,防止我担心的那件事情发生。妈妈带着陈爽越过那口井,去了小花园。等我跟在妈妈身后往回走时,我们看到井边已经挤满了人。有人说,老魏失足掉了下去。妈妈和我都挤进人群,我们向井下看了看,根本没有看到一丁点人影。有人说,早让水冲走了。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这个结果是大大出乎顾小红意料的。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突然间感到那些轻飘飘的生活瞬间就从她身边溜走了,她觉得心里沉甸甸的。这不是她想得到的,一股悲伤涌了上来。她还没有哭出来,就听到顾小丽说:“烦死人了。妈妈的事情更加复杂了。妈妈和林刚,我到底选择哪一个?”顾小丽说完这句话就匆匆走过去了,有一道刺眼的光反射到顾小红的眼睛里,她追着那道光,她看到那道光来自顾小丽的手里,她的手里拎着一把明亮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