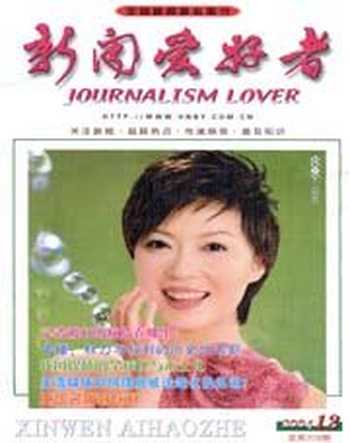美国报纸社论的写作特色
2004-04-29赵振宇蓝晖焰
赵振宇 蓝晖焰
美国报纸的评论体系大体上包括了Editorials(社论)、Op-Ed(社论版对页)、Columnists(专栏文章)、Readers'Opinions(读者来信)四种主要形式。其中,基于社论重要性之上,整个社论版被看作是报纸的灵魂和心脏。它在解释问题、引导舆论和提供信息并使读者得以就当下议题做出判断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国人对社论的重视程度从社论的发表数量上也可窥斑见豹:《纽约时报》几乎每天都会发表三四篇社论,《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每天也稳定在两三篇左右。同时,专门的Op-Eds(社论版对页)和Readers'Opinions(读者来信)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讨论空间。
相比我国社论直接代表党和国家发言,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美国的社论更多的只是一个论坛、一个自由表达的场所。为了能对美国社论的操作方式有所研究,本文特选取被公认为“重要的档案记录报”的《纽约时报》和“议员们每天必读”的《华盛顿邮报》为例,以期对他们的社论进行解读。
一、选题的开放性
社论是最重要的意见表达方式,所以在国人的印象中,社论所反映出来的新闻事件或者所讨论的问题也必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但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小见大的做法却经常被采用,大有中国人所谓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气势。以2004年8月的两报社论为例,首先是两报社论数量之多。单单一个8月,《纽约时报》就发表了131篇社论,平均每天发表的社论竟然有4篇之多!其中2004年8月8日和8月29日更是达到顶峰——每天都发了8篇社论;《华盛顿邮报》8月份发表的社论篇数略低于《纽约时报》,但也达到了92篇,基本上每天都稳定在3篇。这种数量和规模在我国报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其次,两报社论选题的范围都十分宽泛。以《纽约时报》为例,其内容就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说凡是具有一定关注度的事件和问题都有涉及。比如2004年8月7日发表的《乡村生活美妙的花园》就对当前纷繁的城市生活发表了评论,表达出评论员对美妙的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对城市某些恶习的批判。这些社论就分别涉及音乐、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领域,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而精彩的了!
再次,《纽约时报》社论的选题中社会类文章最多,《华盛顿邮报》的政治类文章最多(这与它的定位有关),但在比例上它的社会类文章与《纽约时报》的社会类文章占各报比例却差不多——《纽约时报》为27.5%,《华盛顿邮报》为25%。可见得它们都共同关注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
二、视角的下倾性
从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选题上,它们的社论不止在大事发生的时候表明立场、观点,更多还关注于平常日子里的社会生活现象;在写作角度上,它们更是注重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平行的视角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与受众一起探讨我们该怎样、不该怎样。
为了能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本文特意选取《纽约时报》对中国2003年10月16日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的评论来进行分析。在中国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的第3天——即10月19日《纽约时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 in Space》(《中国进入太空》)的社论。从写作方式上看,该文就是对“(社论)为读者提供信息并引导他们”的一个很好诠释。此篇社论从解释的角度说明中国进入太空并不会威胁美国,解开了在中国威胁论论调下的无稽之谈。文章涉及四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段点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成功是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的胜利,但“this modest first step should not reignite the global space race that died out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第一步并不会再次点燃随着冷战结束而结束的全球太空竞赛);第二段简单陈述事实,对中国此次飞行的详情以及随后还可能有的一系列登月计划进行较为客观的介绍;从第三段开始文章作出分析,指出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是美俄航天发展刺激下的产物,虽然它的成功使日本和欧洲感到恐惧,但日欧却并没有看到他们自身只是将这种实力转移到了其他方向上而已;第四段作者将自己置身于广大的美国人中,分析美国人应有的心态:Instead of fearing the nascent Chi-nese program,we should welcome it as an-other way to get crews and cargo into space at a time of crisis,like that which has grounded the entire American shuttle fleet.(我们不应当害怕中国的计划,反而应该欢迎它。因为它能够在危险的时候将人员和货物送进太空——它就好像变成了整个美国航天舰队的一部分一样。)排除由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差别,我们不得不承认该文一气呵成,亲切自然,有理有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将美国人对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浮躁心态引向了平和。
当然,视角下倾也并不是说非写“大白话”不可,无论多深奥的问题通过这种视角的处理也能写得引人入胜。譬如《华盛顿邮报》2004年4月16日所发表的《The Wrong Target》(错误的目标)。全文围绕Wally Wakefield(沃利·沃克菲尔德)宁愿被罚款也坚持不透露自己在新闻写作中的消息来源一事展开评论。由于评论所涉及的对象比较专业——在什么情况下记者即使与被采访者有匿名协议也必须提供新闻来源——因此,作者在处理时侧重从人出发,从Wally Wakefield 7年来一直坚持信守承诺、绝不说出消息来源的品格出发来质疑法院的审判结果。全文自然流畅,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从Wally Wakefield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在质疑法院判决的同时保护自己。
三、写作技法的多样性
传媒作为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必定会为政治服务,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社论仍然可以多样化,将所想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写得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就是写作技法的艺术了。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标准掌握在读者手中。而影响读者阅读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文章的写作是否有个性、有亲和力、含有较多的附加值。这几点恰恰是我们在社论写作中没有做好或注意到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到的地方。
1.社论语言形式的多样化
美国受启蒙思想的熏陶,几百年来确立起一个崇尚自由和个性的传统,反映到社论中来,他们的语言就要随意得多。具体到写作中,机敏的用词、震惊的方式、戏剧的效果、幽默的风格也就屡见不鲜了。2003年11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Can You Walk and Chew Pizza?》(你还走得动路,还嚼得动比萨吗?)的社论。文章主要指出当今社会里,在人们越来越忙的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社会对人的异化。在文章开头它这样写到:“纽约人发现任何活动都变得多样化了。当我在干洗衣服时,还要给我的祖母打电话;当我在杂货店外排队时,还要给煤气公司开张支票;我甚至还经常要一边吃饭一边为公事奔忙。”这样的语言就相当生动,读者会觉得“对呀,我也是这样啊”,然后继续往下读。
2.社论写作结构的多样化
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一书中将写作结构划分为以下几种:“马拉犁结构”、“瓶—颈结构”、“问题式结构”、“个性化的‘你结构”、“同我一起想象”结构和“我们都置身其中”结构。虽然这种划分方法在我们看来更多讲的是表达方式,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但却毫不妨碍我们对他们这种多样化的理解。只有不同的风格百花齐放了,“赢得读者”也才能成为可能。
《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2日发表的《试着测量人类创造的信息总量》是“问题式结构”和“我们都置身其中”模式的结合。文章从对一个最新的概念——exabyte(安百特,一种信息计量单位)的阐释开始,首先用提问的方法唤起人们的注意。然后详细介绍了专家们如何用exabyte来计量人类所创造的信息以及会遇到的问题。最后举我在回家路上看到的事物来说明“它们都是信息,但exabyte却不能测量出它们对于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从结构上看,文章一开始就问:“你知道ex-abyte是什么吗?我是直到开始读一个叫作‘2003年有多少数据?的报告时才知道的。”然后为了说明这种测量并不能代替一切,作者用了“我们都置身其中”的写作手法。比如:在第五段中写到:“相信,这些数字的使用和比较能让你感受到那些就是信息,也许说这些储存和计算的信息是被人类创造和消耗的会更明确些。所以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些:我们对于这些信息的创造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我们所生活的语言环境和数据环境都是在地球上其他组织的控制之下的……”
3.社论选题和语言的亲和力
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经验来看,将读者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写入社论,不仅不会破坏社论这一文体的权威性,反而还会全面提升人们对社论的关注。
在选题上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苏珊·拉赛蒂的看法。她在描述她从新闻报道转向社论写作时的情形时说:“最好的社论撰稿人是那些记者。不是前任记者,而是现任记者。像一名报道记者一样,我为社论做调查研究,但是写作却用建议或批评的方式。”她的阐述是对美国评论员注重采访的最好解释。《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应该得到更多》的社论,从文中充足的理由来看,评论员肯定是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了的,否则他不可能对出租车7年没调价、协会的观望态度了解得如此细致。
这种从采访中来的选题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贴近性,从而摆脱“闭门造车”时的某些不合实际并将问题引向深入,与此同时也不至于漏掉一些小的群众关注点。
在语言上,社会语言也必须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适应各种层次的读者,因为读者才是最终的落脚者。这里摘录2003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个下水道工人之死》的最后一段:“从Ralph Kramden”(拉弗·克拉丹)身上你可以了解到纽约是如何用野心来侵蚀你的,但从Ed Norton(爱蒂·诺敦)身上你却可以学习到我们必须直面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不管是在对高尔夫球搞演说还是在跳着hucklebuck(一种舞蹈),你在Ed Norton身上看到的始终是一个眼睛盯着自己的小孩。他热爱他自己,这是很酷的,甚至没人期望一个下水道工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种语言是很通俗、很自然的。也正是这种自然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除此之外,标题的亲和力同样也是社论亲和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在人们的视线停留其上的三秒钟内能不能吸引到读者,直接决定着这项传播是有效还是无效。
4.社论的附加值
附加值的多少也关乎着社论写作的成败。虽然社论的主要目的是就某一事件发表意见和看法,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但作为新闻文体,社论也传达着一定的信息。而且这种附加值越多,文章就会显得宽广,就越吸引人。如果无法提供“附加值”,单是讲一通道理、堆砌一堆华丽词藻,可以说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2004年4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Straight to DVD》(面对DVD)的文章,短短400来字的篇幅竟然容纳了三层意思:一是DVD给电影业造成了冲击;二是人们疯狂地爱上了DVD及其原因;三是提出问题:在数字技术更新如此之快的情形下,新的机器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又要重新制作已经看过了的老DVD?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增加附加值并不是说要把文章写得越长越好,而是在充分表达信息的前提下写得更简洁些。
(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蓝晖焰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