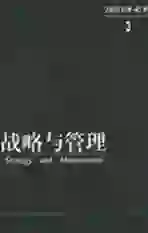信息产业里的民主观
2000-06-14吴冠军
吴冠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韩毓海先生用这一略作修改的诗句来表达作为一个技术门外汉的他对中关村的美好的祝福。但是作为读者同时也是技术“门内汉”的我,却是打心底泛起一丝丝的不寒而栗。韩先生的正气血性一向令我十分尊敬,但是若不对问题加以现实的理性分析,而一味地站在“门外汉”的角度呼唤“幽灵”,只怕韩先生心里那美好的愿望落笔成文字后便全部南辕北辙了。
韩毓海最重要的立论根基,即人类知识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本质”,无法私有化、“产权化”,所以计算机技术也不允许有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对于所有以“技术保密”来作为商业发展立足点的软件厂商,都必须受到“马克思的幽灵”的诅咒。
这一论述乍看上去相当言之有理,然而问题就出在韩先生将一对关键概念作了非常隐蔽的转换,即“知识”与“技术”的概念转换。韩毓海认为“科学和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和知识只有在平等的合作和交往中才能发展,科学和知识活动作为‘植根于人的兴趣、爱好之上的创造性活动,与建立在榨取剩余价值之上的‘工具性的异化活动是根本矛盾的。马克思对知识的公共性本质的论断完全适合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历史”。
如果“知识”与“技术”本质上是一回事,关于“知识的论断完全都适合于技术”的话,那么韩先生整篇文章的论点就毫无漏洞,臻乎完美了。只不过,我们从常识就可知道,适合“知识”的论述未必适合于“技术”,“知识”和“技术”是两个范畴绝然不同的概念。
严重混淆“知识”与“技术”这组概念的始作俑者并非韩先生,而是大洋彼岸发明“知识经济”这个名词的“学者们”。“知识经济”其实只是对技术专家的“经济”,与真正的学者和人文知识分子毫不相干。“知识经济”实际上应该叫做“技术经济”。同样的,“知识产权”更确切地也应该称做“技术产权”。这样才不至于混淆问题实质,从而有助于还原出问题的原貌。
知识研究者可以将自己的知识见解第一时间公开发表,使之成为人类的公共精神财富;而技术创新者则往往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尽可能快速地商业化,使之切实地深入社会改善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通过广大消费者的接受与选购来获得技术创新的报酬。掌握半导体技术的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也好、以葛洛夫为首的“八叛将”也好、以及微软帝国的“皇帝”盖茨也好,所有例子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技术创新者对技术商业化及技术保密的极度重视。韩先生大力赞扬了葛洛夫等当年的“叛逃行为”,但是如果葛洛夫不是与那位肖克利一样对自己的技术保密有加的话,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巨人Intel,早就被后来者AMD,或者Cyrix扫地出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专利保护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废除了技术专利保护,就等于扼杀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没有以专利形式存在的技术产权,世界上就不会有名扬四海的肖克利、葛洛夫和盖茨,甚至不会有当年的“发明大王”爱迪生,据统计爱迪生当年打专利官司耗用掉的律师费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试想如果那时候的专利法也像今天那样完善的话,很可能爱迪生也会像今天的盖茨那样富,难道我们就因为他富就诬赖爱迪生“垄断知识霸权”?废除技术产权、不准技术保密,那么人类不但要退回到没有个人电脑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甚至还得退回到没有电灯、电话的“蜡烛”时代。
与所有“IT民族主义者”(即方兴东、王俊秀、姜奇平等人)一样,韩先生对托瓦尔茨(Linus Torvalds)及他编写的被称为“自由软件”的Linux给予了高度赞赏,并认为“今天的自由软件运动正在成为盖茨们的‘幽灵,我想说,这个令盖茨辗转反侧的幽灵其实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一部分”。Linux的技术价值没人否认,但就此将其无限“拔高”到“马克思的幽灵”,也许托瓦尔茨本人闻之也会吓一跳。托氏当年编写软件时恐怕绝没有韩先生等人的觉悟——反抗微软霸权!作为高级程序员们的业余兴趣,自由软件的存在无疑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不能因为存在一定数量的自由软件就强迫要求所有的商业软件全部共享成为自由软件。正如不能因为有些歌手曾经举行过义演,就要求以后所有的歌手全部必须义演。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自由软件或者慈善义演都是人间美好的东西,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审美价值,但是其前提必须是自发的、自愿的,绝不是强迫的、逼使的。当年卢梭构创的“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的“道德理想国”经过二百多年的人间实践,结果如何?
一旦技术成果失去专利保护而被迫转为“自由软件”,人人皆可免费得之,那么只会使所有的技术开发转入业余兴趣状态。技术创新者本人既然拿不到技术成果商业化后的经济回报,他必然得寻找其他途径去维持生存,因此他不得不把大部分用来钻研技术的精力放在谋生的主业上,所以就同一个(组)技术人员来说,业余的水准必然低于作为专业工作的开发水准,即其业余的软件作品较之商业化的成熟作品必然有所差距。当然,永远都有善事,永远都有自由软件和热心人,但是从根本上大力推动行业进步的,是商业操作。正如恩惠互助在家庭、朋友、社区之间是普遍存在、甚至举足轻重,但它无法进一步扩展,成为无数陌生人竞争与协作的纽带。近代经济学奠基人斯密曾经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过日,那是一定不行的。”而诺思则更具体地就技术发展指出:“闲暇时好奇和实践会产生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见的某些变化,但是,就像我们在现代世界所见,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有恒产,始有恒心。如果所有的技术成果都没有产权,都是公共的,这才是阻碍技术发展最可怕的敌人。韩先生在道德立场和审美立场上赞美自由软件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对此人们没有很大异议,但是若就此更进一步地指责是商业软件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以为“企业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其源码秘而不宣,从而不利于软件技术的发展——这已经成为共识”,恐怕只是所谓“技术门外汉”的又一种脱离现实的臆想罢了。
商业化发展对推动技术的进步是有功而非有害的,不用说爱迪生时代,近十多年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成长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如果免费的“自由软件”已经是主流、是“共识”,韩先生及所有的“反知识霸权者”找来找去就不会只举出托瓦尔茨及其Linux等个别例子?韩毓海引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先生的一段话恰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计算机开发人员在为开放源码软件作贡献,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和兴趣工作,……”抽掉了“钱”的“工作”,那么那群“技术人员”吃什么喝什么,靠什么生存?抑或此刻世界上正有成千上万个比雷锋还有“雷锋精神”且不需要吃喝的“钢铁青年”在成长?自由软件永远只能是商业软件开发之余的一种副产品,我们大可看作是程序员的一种休闲活动,而决不能颠倒主副甚至要求把商业软件全盘封杀,否则就会出现以上这种违背经济学基本常识的话语。
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把市场分为初级市场和上层交换。初级市场就是集市贸易,通过集中性的交易活动,以一个相当低的制度费用达到交易的公开性和公平性。初级市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因而布氏认为实际上初级市场同资本主义并没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典型特征就是上层交换,即不断避开市场竞争的交换。不论盖茨还是其他企业家,任何一个商人打心底都不喜欢竞争,除非没有办法。实际上市场中的许多活动都是为了避免竞争。商人们的一种行为是投入竞争,另一类行为则是用各种方法不让别人参与自己领先的商业活动,而严守商业秘密则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项措施。布氏指出这种“反市场”的上层交换是真正的商业利润的源泉。在初级市场几乎透明的交易制度下不会有巨额的超额利润。而导致商人真正致富的,其实是那些避开竞争活动的成功的“反市场”动作。
布氏继而指出共有两种避开市场竞争的方式。一类“反市场”的方式是依靠官府权力的保护,一小部分商人获得特许权。有了官商结合之后的特许经营权,其他商人就无法轻易进入,于是形成没有竞争的超额利润以及原始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种避开竞争的方式是连续不断的创新。即不断地在技术上、组织上以及市场开拓上创新,从而在别人还来不及作反应之前“独占”市场机会。如果取消技术专利,盲目追求公共性的、开放性的“自由软件”,那就等于堵死了企业家走创新之路,迫使他们转而去动特许权的脑筋来实现避开竞争。
而放眼目前国内信息产业,在韩毓海及那些“IT民族主义者”高喊“起来挑战知识霸权”、必须共享技术成果的同时,一些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地插手进来,要为信息行业制定规范。一规范就等于为寻租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当韩先生的“马克思的幽灵”堵死了所有的技术创新者合理致富的道路,最终就只能迎来特许权经济的确立及寻租、腐败行为的泛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针对美国司法部控告微软一案表示:“我简直不敢相信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会如此短视,竟要求政府插手调查微软公司有无垄断。这样做不但需要大笔法律费用,还会促使政府制定某些限制行业发展的规定,结果将对这一行业造成远比微软能造成的大得多的危害。”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则说:“无论是法官还是立法者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断定一个企业到底是推动了竞争还是抑制了竞争。控制垄断的更有效的办法是鼓励竞争者进入行业,包括国外的竞争者。”
由自由竞争、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产生的自然垄断及基于其上的超额利润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自然垄断永远是即时性的,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马上会有其他商人跟进或者在技术上试图赶超,于是随即形成再一轮的竞争。因此自然垄断者必须时刻保持其旺盛的技术创新能力。Intel和AMD、Cyrix近十年来在技术创新及突破上真刀真枪的拼斗历史就是最好的例子。Intel一马当前的日子并不好过,它必须更快地创新,才有可能继续“当前”,一有疏忽就会有后来者“硬把皇帝拉下马”。伦敦学派的罗宾斯说得很精彩,“竞争性态势的实际上的重要性质,并不是存在着大量的实际的供应者,而是如果任何一个实际的供应者真的赚了很多钱,总合情合理地存在其他潜在的供应者,他们会涌进这个领域,分走超常的利润。”可见,自然垄断的地位总是不稳固的,时刻变化着的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需求和新的供应势必改变这种垄断地位。人们就在不断追逐新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彼特)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弗里德曼的老师)都曾经指出,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最近的《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为微软说几句话》一文中区分了四种垄断:“天赋垄断”(“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像邓丽君那样的歌星,或多或少有垄断权”)、“技术垄断”(即专利垄断)、“自然垄断”(即竞争中产生的优胜劣汰)以及“行政垄断”(“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分析得十分精彩。同时我还要在张教授的四种垄断之外再加一种垄断形式:金融垄断。集中大量社会资金的垄断金融机构拥有雄厚的金融实力,如果不对之有所限制的话,其就会排挤其他的金融融资方式而逐渐垄断整个金融市场,从而形成“肥水只流自家田”的金融垄断。任何创新都先要取得创新所必需的经济资源,创新者必须在金融市场中寻找条件适合的经济资源,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上的“劳动雇佣资本”现象。对此,熊彼特曾经总结为两句话:(1)“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2)“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一旦金融市场受到垄断,创新者无法在金融市场中自由选择合适的经济资源,这无疑意味着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将遭到毁灭性的压制。在美国,由于社会公众对于垄断金融机构的严重不信任,所以上个世纪以来的立法不断拆散了规模巨大的金融机构,强制隔离了各类金融机构的兼并空间,同时金融资本进入产业部门董事会也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正是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与立法保障,公开让广大市民自由参与的证券市场融资才成为美国企业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主要的融资方式。从而避免少数垄断金融机构霸占金融市场,并使得所有社会民众能够自由选择具有创新力的企业股票,分享其创新后的商业成果。
本文认为以法律强制形式存在的反垄断法只该反行政垄断和金融垄断,而不该反技术垄断。因为行政垄断和金融垄断只会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技术在本质上根本无法永久垄断。因为造物主赋予人类个体的智慧和潜质是“机会平等”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实现某种创新,并且依靠技术创新后的合理所得发家致富。这才是平等的真正涵义。行政垄断及金融垄断背离了机会平等这条现代性准则,并且恶性加大现实中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必须反对;而技术创新正是有效地维护了机会平等的空间,给弱者提供了一条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智慧攀升成为强者的道路(在如今“后工业时代”卓越的创新则更有可能使创新者一夜致富)。所以由技术专利形成的“技术垄断”绝不应该反对,相反必须加以法律形式的保护,以合理有效的专利法及产权法保障创新的技术在具体的期限内不被盗用。
弗里德曼对美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就极为不满,他批评道:“多年来,我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针对司法部控告微软的“反垄断”一案,他接着表示:“打这场官司劳民伤财。技术的进步,比法庭的步伐要快得多。到这宗官司了结时,谁会知道行业的局面是怎样?肯定不是今天这样。邀请政府的官僚来调停,你就请来了未来的管制。过去电子行业有幸免受政府插手,得以进步神速,但你会马上看到,以后轮到政府的管制增长神速了。”
“马克思的幽灵”在雅克·德里达这里还只是针对媒体帝国全球一体化政治幻想的“批判的武器”,目的是为了祛除媒体社会的新国家话语的同一性魔咒,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向所有霸权式的政治言说打入离心化的楔子。而到了韩毓海先生这里,“马克思的‘幽灵意味着更深入的东西,那就是为争取获得信息和参与系统程序的权利而斗争”。在以必然口吻宣示的“马克思的幽灵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光临中国,要来到我们身边”的壮阔宣言下,韩先生率领所有的“技术无产者”,唤醒“马克思的幽灵”,在“平等”、“自由”的旗号下重新拿起“武器的批判”,而遍寻不着“革命”的目标时,忽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韩毓海的这一宏篇巨制让我久久地不寒而栗,韩先生的确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因为一个民主化、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公路或高速列车,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但是,也甩下了另一些人,甚至拒绝让其他的人‘搭车……”而我要追问的是,究竟谁“一夜暴富”,而谁被“甩下”?
是那些技术创新者凭借其智慧及卓越的商业眼光“一夜暴富”;是那些无所创新者被“甩下了”时代的列车。而现在无所创新者却想不劳而获,竟要求开放技术,“利益均沾”,而且还振振有词,时不时地放出“马克思的幽灵”来助威。在我看来,这样的“马克思的幽灵”已经失去了其边缘批判与反思的作用,而成了数量庞大的“技术无产者”用来从技术创新者手中夺取利益的“攻击性武器”。
因而,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要的究竟是何种平等,哪类自由?是“无知的平等、瓜分的自由”,还是“机会的平等、创新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保护技术产权的法律,保护的不仅仅是盖茨、杨致远等已经“一夜暴富”的技术创新者,同样也保护所有其他拥有或可能拥有创新技术的人。只有那些认定自己将永远一无所有的人,才会起来反对保护产权。
我们都不愿意做一个教条化了的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对于正在降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也存在着内心的焦虑,对无限商业化带来的生产过剩及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泡沫同样深深地担忧不已。汪晖式的思考有合理性:“今天有几个人愿意仔细地去倾听阿族人和塞族人自己的声音,又有几个人去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遮盖了那些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当那些受难者的形象和声音偶尔裸露一点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和力量在控制他们的裸露和隐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便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置一个正常人基本的常识判断和知识分子起码的理性判断于不顾,以“庸俗的姿态”站在“底层无产者”立场上,向一切试图“全球化”的东西发起挑战,向一切“一夜暴富”的有产者挑战。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吉登斯就敢于揭“左派”的伤疤,“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悖理的结果。”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生产馒头的企业可以从慈善角度免费向老百姓发馒头,一次两次绝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便要求以后取消馒头的市场和价格,馒头生产企业全部公开向老百姓送馒头。长此以往企业靠什么去生产馒头?因此将馒头定位在“自由共享”,其实就扼杀了所有馒头生产企业的生路,也就从根本上扼杀了馒头的生产。“大家都能随便吃”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没的吃”。“按需分配”的“大锅饭”实践最终后果如何,这应该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吧!馒头的生产有成本,软件开发也一样,虽然拷贝的成本很低廉,但是开发的成本却十分昂贵(可以对比一下电影的制作),如果只许软件有试用版、共享版,而不许出商业版,使用者是舒服了,那么开发者何以为生,何以为继?还是一句老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至于韩先生呼唤的反抗“知识垄断”的“民主力量”,我就实在是感到不可理解了。以前韩先生呼吁加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扩大民主的范围,我还能够抱以同情性的理解与支持(不去探讨制度上的具体实现可能)。然而韩先生将这种吁求照般到技术领域,试图将广大民众一下子全部引入技术开发的领域,从而论证所谓的“知识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本质”,从而阐明技术开发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但是技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并不是“家族类似”的,试问技术开发怎样“民主”?难道怎样开发一个软件还要让所有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投票决策吗?技术开发而成的软件是一件商品,它的优劣好坏只接受市场中的购买者的“钞票投票”,而不接受来自类似政治领域的“公共空间”的民意投票。
民主是一样好东西,但它不是在人类生活的一切空间内都是这样。我们应该弄清的是,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好东西?民的对立面是官,民主对抗的应该是“官主”,所以其价值就在于在政治及其相关领域内同一切的专政独裁作斗争,而一旦超出这些领域,民主就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了。比方在私人领域,“人民”对于个人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以“人民”的力量剥夺个体的权利的“多数暴政”案例在历史上实在是此起彼伏、不胜枚举。民主同样也不适合任何的“专业领域”。广泛参与式的“大民主”只会破坏人类社会所有由专业精英组成的专业领域。民主与生俱来具有着强制性的力量,如果不加分析地将其施用在人类社会的任何空间,在“人民”、“公意”的名义下入侵人与人之间的所有领域,后果是可想可想而知的。 (作者单位:上海主旗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