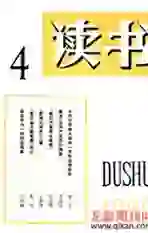传记文学的新镜鉴
1980-07-15黄克
黄 克
《梅尧臣传》读后
朱东润先生以八旬有余之高龄,完成了《梅尧臣诗编年笺证》、《梅尧臣诗选》、《梅尧臣传》三部著作,最近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这不只为梅尧臣这一宋代诗人增添了光彩,也可说是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一桩盛事。
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创作活动中,朱先生是开拓者之一。早在一九四三年便出版了《张居正大传》,以后又出版了《王守仁大传》,解放后还出版了《陆游传》(《陆游选集》亦随之问世)。《梅尧臣传》(以下简称《梅传》)则又是一部新的力作。在传记文学得到重视和提倡的今天,朱先生这一辛勤劳动的成果,足资我们镜鉴。
应该说,为梅尧臣作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官不过五品,大半辈子游宦于下层府衙。他先后受到叔父梅询的照料、挚友欧阳修的提携,虽然见过数次上层政治权力的角逐,但因没有亲身参与,所以宦途生涯也不曾有过什么大的沉浮蹭蹬。即便在诗歌创作上,虽然于当时已经享有“欧梅体”的美誉,但在文学史上依旧是个二流作家,影响远不及欧阳修。总之,作为传主,总感到形象似乎并不怎样突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连他自己也叹为“沉泥玉”的缺乏光彩的梅老夫子,竟以一个愤世嫉俗、耿介亮节、有血有肉、触摸可得的形象出现在《梅传》之中。毫无疑问,在梅尧臣的形象塑造上必然要有匠心独具的工夫,否则是难以达到这一境地的。笔者拜读之时,也曾对此加以揣摩,并随手记下点滴学习心得。尽管是瞎子摸象,却愿意提出来求教于朱先生和读者。
《梅传》序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诗人不是政治家,在历史记载里不会留下沉重的踪迹;他又不是哲学家,没有长篇发挥他的惊人的宏论。因此我们对于诗人的理解常常不够。”一方面存在着诗人不易理解的客观困难,一方面读者又要求通过传记得到对诗人的更为全面切实的理解,这确乎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于解决这一矛盾,朱先生做过多方尝试,也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几乎可以视作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的一点,是在指出历代“年谱”编著工作的不足时提出的:“他们只注意到诗人的升沉否泰,而没有把他放到时代里去。脱离了时代,我们怎样能理解诗人的生活呢?”这里,一句“把他放到时代里去”,已把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艺术特征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即同样离不开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然,传记文学的传主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管从文学角度看它够不够典型,作为客观存在,其自身就是一个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唯因如此,如实地展示这一特定的“典型性格”形成、发展的时代,即“典型环境”,对于传记文学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理解传主提供了可能。“把他放到时代里去”,无疑是符合这一艺术创作规律的。《梅传》的创作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的。
循着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道路,《梅传》展示了从真宗到仁宗几近半个世纪的时代风貌,这就为梅诗做了最为充分的注脚。比如,景
与此相呼应,以传主梅尧臣为中心,《梅传》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一代诗坛风貌。一般认为,宋诗真正形成自己的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格,是在王安石、苏轼一代,但那已是有宋建国百年左右的事了,而宋初以还几近半个世纪却是被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西昆势力所垄断。这股以“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为能的形式主义逆流,因其倡导者都是显赫的大官僚,一时间上行下效,竟闹到“倾动天下”的地步。既然如此,把诗歌创作从这种腐朽势力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创自己的道路,当非一人一时可以成功的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一代诗人涌现了。他们虽在西昆体的襁褓中诞生,却一意为新一代诗风鼓噪,是一批继往开来、有破有立的人物,梅尧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梅传》在如实地反映了梅尧臣这一过渡时期诗人的成长历程中,承上启下,实际涉及了从钱惟演到苏东坡这三代人的师承关系。刚刚步入仕途的梅尧臣,三十岁那年调任河南县主簿。妻兄谢绛是河南府通判,又是诗人,通过他结识了诗坛新秀欧阳修、尹洙等人。这群自称“洛下才子”的青年人,就是日后诗文革新运动的班底,而这个时候却是在西昆派的卵翼下从事诗歌创作的。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谢绎,颇得杨亿的推崇,而欧、尹、梅诸人更深受时任洛阳留守(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器重和关怀,他们之间交游唱和,自然仍脱不掉西昆体的巢臼。《梅传》也不回避梅尧臣早期诗作的西昆体痕迹,甚至照录了《无题》那样的柔靡之作。然而,一反西昆体的诗文革新也正是在这西昆体的巢臼中开始孕育的。梅尧臣基于他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遇,首先把农民的劳动生活引入诗中,以《田家》、《观理稼》等诗篇,大胆地突破了台阁体的狭小天地。这种对西昆体的明显背叛,也正发生在这个时期。此后,梅尧臣在与欧阳修、尹洙,还有苏舜钦的诗歌往还中,把这种离经叛道的行径更加发展、扩大,终而替代西昆体的盟主地位,把诗坛导向别开生面的新境地。
特别是梅尧臣与欧阳修之间,过从甚密,历三十年不衰。他们不仅于诗歌创作相互切磋、勉励,且于生活起居也相互关怀、照料。《梅传》把这种友谊表现得那样诚挚、深切,一地则同游,异地则相思,真是情投意合,几乎可以视作欧梅二人的合传。梅尧臣在赴湖州酒税任上时,欧阳修为之饯行,席间欧作《圣俞会饮》诗,梅答《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诗。《梅传》在照录之后,做了如下的描写,那是在欧阳修拿起梅尧臣诗稿的时候:
欧阳修朗诵着“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真感到有些唏嘘欲绝。他一边吟味自己(所作)“嗟余身贱不敢荐”一句,看看尧臣高高的个儿,满头白发,一领青衫,入宦十年多,到今只是一个不第的秀才,在封建社会里,这是一幅何等失意的图画。
既是文学,就不排斥虚构。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这一番端详和内心独白,自不必考其有无,不过他写过同情挚友“四十白发犹青衫”的诗句,这一虚构的真实性也便无可怀疑了。重要的是,借助欧阳修那一往情深的目光,勾勒出了梅尧臣那宦途失意、穷困潦倒的形象。此时的欧阳修也是在贬谪之后刚刚复任,同病而相怜,透过这一镜头,捕捉到的俨然是二人的合影。事实上,欧阳修一直为尧臣的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尧臣于五十五岁的暮年得以从监管仓库的小官升迁为国学直讲,继而汲引到唐书局,就多亏了欧氏的极力保荐。书中还记叙了这样一件轶事:嘉
是诗史发展的必然,抑或生活际遇的巧合,苏轼这位新一代的才子的颖现,也正出自欧、梅二人的擢拔。嘉
就这样,《梅传》以梅尧臣为中心,上串下联,展示了三代人的风貌,实际上揭示的是宋诗演变的流程,从而更突出了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作用。单就本身行状资料单薄而言,梅尧臣的形象实难塑造得丰满,但是借助政治斗争的时代背景,诗人的唱和交往,以及上下师承关系,把传主置于广阔的社会画面之中,这就不仅为其诗歌创作做了最为形象的注释,也为传主形象增添了异彩。这是《梅传》的特色,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
最后,想就梅尧臣诗的艺术特色问题和朱先生商榷。历来论诗,或宗唐、或宗宋,常走两个极端,对此,朱先生在《梅传》中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以唐诗的标准要求宋诗,那就只会看到宋诗和唐诗的距离,而不会看到宋诗的特点。我们必须认识唐诗的标准不是作诗的唯一的标准而后才能认识宋诗,尤其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诗。”这无疑是十分公允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它并不能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限制,因为后代自有后代的时代特点、社会风貌、创作甘苦。如果唐诗以外一无所见,那就否定了艺术的发展,也否定了自己;如果只是高山仰止,哀叹它的不可企及,一味在因循蹈袭中去钻营,就会走进艺术的死胡同,西昆体便是例证。艺术的发展规律表明,前代的高度艺术成就,势必迫使有为的后代另辟蹊径,奋力超越前人。诚然,超越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闯的精神总是可贵的,有别于唐诗的宋诗风格的形成不就是这样闯出来的吗?而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贡献亦正在于斯。那末,他的诗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和晏相公》)“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进士诗卷》)这是梅尧臣的自白。
“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这是欧阳修的认识。
“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苕溪渔隐丛话》)这是南宋胡仔的评价。
当然,把梅诗的风格全归于“平淡”是有失全面的,但是“平淡”构成梅诗一大特色却也应是事实。对此,《梅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朱先生于最近发表的《梅尧臣诗的评价》一文(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更力辩其非,认为“把尧臣作品归结为平淡,不但不符合梅诗的实际情况,也是违反尧臣的主观要求的”。因而这一问题便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提“平淡”,总要和“无奇”联系起来,其实并不尽然。“平淡”作为刻画形象的手法,犹如图画当中的“白描”,同样可以表现物象的千姿百态。这种表现手法的特点是平铺直演,不务奇嵬,不事雕砌,平平而入,淡淡而出,却也能收到有声有色、趣味盎然的艺术效果。我们读梅尧臣的诗也确实是这样的感受。即或是对皇
如果联系风靡于时的西昆体,甚至不妨说这种“平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昆体时称“艳体”,他们宗法李商隐,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