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尚”
2025-02-21周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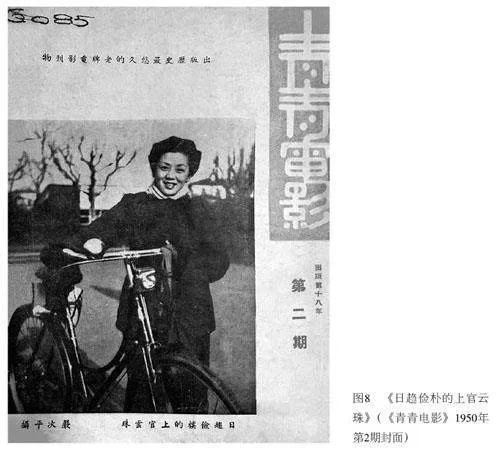










摘要 20世纪50年代,一场“美化服装”时尚风潮在中国银幕内外蔓延。电影与时尚的耦合培养了该时期中国女性超越实用主义价值的现代性经验,也引发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如何把握、女演员如何实现彻底改造、女性多元气质如何合理彰显等复杂又颇具风险的问题。这场风潮是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两种社会主义女性现代性经验的在地互动与碰撞。电影《黄宝妹》文本内外丰富的历史细节显示出,劳模黄宝妹既具备妇女高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力价值,又在日常生活领域释放着流行文化的魅力与经济效应,成为聚合两种经验的理想范本。其以“例外”姿态不仅指向中国女性的媒介再造,也指向对“十七年”在更高层面的重估。
1957年上映的电影《护士日记》里,女护士简素华轻声哼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翌年,以衣着时尚闻名的劳模黄宝妹出演的艺术性纪录片《黄宝妹》面世。“穿花衣”形象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登场时虽与主流意识形态语境格格不入,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演员王丹凤和黄宝妹成为大众争相效仿和爱慕的对象(图1)。但在当下对“十七年”的历史叙述中仍普遍套用“厌女情结”(misogyny),对这些由文本内部延伸至外部的意义场域语焉不详。华裔学者王玲珍在《重访女性电影: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Revisiting Women’s Cinema: Feminism,Socialism, and Mainstream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中指出:“针对‘十七年’女性及女性电影的研究无法走出预设好的政治宣传性质、父权文化等根深蒂固的研究范式,自然也无法对社会主义文化和妇女运动历史及相关遗产进行有效评估。”衣着时尚女性的被发掘可视为一种历史复调,为学界重估“十七年”女性文化提供独特参照。
通过钩沉史料会发现,简素华和黄宝妹两个角色虽共享着“时尚”标签,但两部电影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前者上映后遭到批判迅速沉寂,后者在四面楚歌的语境中创作出来并得到肯定,被选送为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片”。尽管“重写十七年”是当下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但研究者大都以1956年“双百方针”、1958年“拔白旗”以及“艺术性纪录片”运动为关键词概括这段历史,对繁多历史细节尚未充分发掘与客观评估。显然,“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生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电影、女性、时尚在该时期的互动是复杂的,并非简单跳出“政治-艺术”二元框架后就能完成重新概括,研究者必须释放更多历史细节并阐明其历史发生学意义。
除了《护士日记》和《黄宝妹》外,1957到1958年还短暂出现了具有相同特质的影片类聚:《青春的脚步》(1957)、《寻爱记》(1957)、《幸福》(1957)、《上海姑娘》(1958) 等。其中,《黄宝妹》是社会生活、产业工人等研究领域重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现场均无法绕开的典型样本。这不仅是因为影片携带着意义丰富的能指,还在于扮演者在文本之外参与了更广层面的文化生产,其事迹和时尚形象频频见诸广播、报刊、连环画等媒介,成为包含官方与民间多重诉求的文化符号。本文以《黄宝妹》为显性参照物与其他“时尚”影片并置,探析文本迥然不同的命运背后所关涉的物质消费、明星改造、女性气质等多重时代话语间相互交织的张力,并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这场时尚风潮做出更清晰的历史重估。
一、异军突起的“时尚”:“美化服装”与美好生活归属
若按前述路径,我们将“双百方针”等政治性因素暂时搁置,首先面临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1956年文艺政策松动后,为何是穿衣时尚现象在次年电影中异军突起?显然,这一文化诉求不属于此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内容。“着装统一的深蓝色、卡其绿或灰色代表了1949年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构成中国社会与民族时间和空间想象的同质性。没有阶级、年龄与性别的区分是标准共产主义的时尚形象。”自我牺牲的服装样式和色彩,对抗的是与政治话语、社会改造及经济建设等崇高历史需求相悖的、热衷于消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指出,一个头发夹子、一件皮大衣都可能变成诱惑女孩子走入歧途,甚至贪污犯罪的肇因。《上海姑娘》中,导演成荫设置的小插曲呼应了此说法。穿着时髦大衣的白玫上楼梯时,手里的皮箱不小心滑落,这一幕碰巧被下楼的陆野看到:
华丽的缎子的花围脖,各色各样的花手绢,带着丝绒套子的热水袋,绣花的毛线衣,彩色的辫结……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它哇地叫了一声,眨了眨那奇大的眼珠。
随后陆野“脸上浮起一丝嘲笑”,像是代表当时的主流价值做出评判,白玫的服饰、物件表现的时尚气质,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节俭朴素、集体主义极不相符。经济与社会学者安德鲁·魏昂德(Andrew Walder) 曾用“‘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asceti⁃cism) 概括中国1949—1976年政治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其关联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冷战的国际形势、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及物质贫乏的现实状况。因此,仅以惯常的政治规约来简单解读,认为时尚服饰等个体追求被抑制、社会主义政权反对生活消费,无疑稍显片面。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流叙事并不排斥对个人美丽装扮的表现。电影《高歌猛进》(1950) 中就有对人们在好日子到来后追求穿衣打扮的描述:
小孟:“妈呀,你看吧,再过几年,咱们的生活得从根儿变个样儿。”秀兰:“那时候把孟大娘好好打扮打扮。”众人附和道:“我送一身呢子衣服,我送一双皮鞋,我送一个大穿衣镜,我送梳头油和香水。”
众人的未来展望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对人民在物质进步上的承诺,但穿衣打扮所代表的美好生活与贫瘠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却是国家在建设初期难以有效调合的。影片中秀兰鼓励小孟的那句“咱们好好干”,是政治话语借用马克思“劳动创造历史”的价值逻辑对这种矛盾的弥合,穿衣打扮等生活消费问题暂时被悬置。但当国家顺利度过艰难的初创期,开启全面建设后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物质的丰裕让穿衣打扮、追求时尚的诉求需要被提上日程。《新中国妇女》的一篇文章焦虑地写道:“男女不分,老少不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诗人艾青也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环境的关系,老解放区大家穿制服是对的。但新中国成立已经五年了,不分男女老少还穿一样的衣服,就显得不合理了。……在大街上一看,全是一片蓝黑色,和两旁的建筑物、和生活的欢乐气息很不调和。”
1955至1956年的媒体舆论中,“时尚”“美丽”“服装改造”成为相当显眼的词汇。谈论的核心大都是如何用丰富多彩的装扮体现国家发展形势向好。上海《青年报》发文号召:“姑娘们,你们大胆的穿起花衣服吧……不但要把国家打扮的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的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主流媒体的宣传口径也出现松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速地发展着,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所改善和提高……相应地改进和美化服装……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随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国多座城市响应号召举办服装展览会。《人民画报》等杂志封面也出现了身着靓丽服装的女性,内页开始介绍苏联布拉吉、旗袍改良的短衫及不同款式的皮鞋和高跟鞋等(图2)。
1957年《青春的脚步》《寻爱记》等电影也对社会主义新时尚进行了全面展示:《青春的脚步》中林美兰共穿了九套衣服,王人美扮演的家庭主妇淑芳也系上鲜艳的丝巾、穿上旗袍(图3);《寻爱记》中出现了销售员马美娜帮助爱慕对象搭配、选购衣物的段落。对时尚衣着的渲染体现出朴素的民族自豪感与制度优越感,其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迅速推翻旧秩序、不平等现象后引起的乐观主义而出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兑现建立初期物质进步、人民生活提升的承诺,因而“从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来理解,服装话语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违背”。但影片上映后却饱受诟病,“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社会”“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舆论批判,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美化服装”运动偃旗息鼓的主要原因。
短短几年间,穿衣打扮议题在电影创作与现实生活中都陷入前后矛盾的境遇。一方面,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憧憬的对象,体现着制度优越性与物质文化进步;另一方面,穿衣打扮在“十七年”崇高美学观念中往往与资产阶级式的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等同,在物质文化进步后又成为需要克制的对象,这反映出该时期政治阐释体系的悖反困境。李玥阳将其概括为“生产话语的内在危机”,即“既要承认‘好日子’的优越性,又要随时警惕‘停留’在既有的‘好日子’之中”。在此之前,1954年前后工业题材电影的公式化创作曾受到质疑:“现在作品中有一种通病……不爱日常的生活,也没有日常的生活。”“难道工人的生活就只有劳动?”但此问题并未在之后的电影中改善,反而愈发严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一定程度上暂时脱离了物质匮乏的状态,原有以劳动为中心的审美样态与价值体系不得不回应“劳动之后”的一系列状况:未来美好生活该如何继续建构?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触碰到意识形态的边界,如若把握不好便有“越界”的可能。电影创作对表现美好生活的持续延宕与对穿衣时尚的公开追逐显然是两种极端,这意味着要在彼时的政治框架内做到恰到好处的把控是相当困难的。
黄宝妹的时尚劳模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登场,为这种“恰到好处”提供了一种可能。尽管她以劳模之姿进入大众视野,却因美丽时髦而闻名全国。她身着旗袍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形象曾引发巨大轰动 (图4)。苏联之行后,卷发和布拉吉成为黄宝妹的日常装扮,“女劳模都穿布拉吉了,布拉吉热潮一下子就给带动了起来”。她还利用全国劳模身份为广大女工人谋求生活上的福利,上海杨浦区政府应其建议“计划建立商业中心”,其中大型服装公司、理发店、洗染店、女子浴室应有尽有。与《青春的脚步》《护士日记》《寻爱记》等影片中的女性相比,黄宝妹的美丽时尚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引发的影响在电影上映后也招来了质疑,诸如“青年女工在生产时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平时互相讲究谁漂亮”“跟资产阶级学样,向往奢侈享受”等批评纷至沓来。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各文化部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未阻止黄宝妹的时髦形象进一步宣传扩散,这令时尚问题变得暧昧与模糊。拍摄《黄宝妹》时,面对工人阶级不能加白纱、“加了纱就不像工人”的言论,黄宝妹掷地有声地回应道:“今天我们拿自己的劳动来建设社会主义,过着社会主义的生活,为什么不能穿得漂亮一些呢?”该回答将时尚争议回置于社会主义推崇的价值逻辑中,时髦穿衣打扮成为“劳动光荣”之后的“消费合理”,时尚被转喻为一种革命先进性的表达,打着合理合法的旗号走向日常生活。劳模身份为黄宝妹时尚的不断发酵提供了合法的政治外衣,赋予她个人穿衣装扮的底气。在她的身上,时尚需求转变为服务劳动阶级、体现社会主义人民美好生活的正向话语。
但黄宝妹时尚的“媒介漫游”并不意味着国家公开倡导消费主义、推广消费品。相反,“劳动者”的含义优先于“时尚”,后者持续为前者的意义生产提供支持。其一,“时尚劳动者”表明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不能与国家物质进步脱节,要体现出物质激励,巩固“劳动之美”的既有价值体系;其二,导演谢晋利用黄宝妹广泛的时尚影响力拍摄电影,但影片重点却是对其先进的生产方法和工作精神的展现,个人时尚某种程度上就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宣扬工人阶级大搞生产建设与技术革命的“噱头”。
由此,《青春的脚步》《寻爱记》《护士日记》《上海姑娘》等影片遭到批判的原因显而易见,片中穿着时尚的女主角分别是建筑设计师、服装销售员、青年护士、检测工程师,皆不属于传统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范畴,她们的表现更像是在1956年对知识分子政策放宽后主动靠近工人阶级进行的自我改造。“美化服装”运动以及“时尚”影片的登场,标志着在新中国建设蓬勃发展的乐观主义氛围中,以创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美学界线的一次公开试探。但在彼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仍难以与劳动人民建立起等意关联,时尚议题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了官方话语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龃龉。就电影作品来说,这些影片选择表现非传统劳动阶级角色,这种做法并没有给出阶级改造如何与日渐凸显的消费主义、追求美好生活等问题耦合的理想解决方案,反而为这些问题蒙上一层现实焦虑。
二、脱下“花衣”后:“劳模演电影”与演员的焦虑
有别于一众“时尚知识分子”的劳模身份,成为黄宝妹能够独善其身的关键,但电影《黄宝妹》的叙事反而是由知识分子视角展开的。影片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拍摄片场开始,随后一旁观看的女编剧离开,独白带入:
我是一个编剧,为了反映祖国飞跃发展的面貌,我去访问一些先进的生产单位和模范人物,前些日子在报上,看到全国著名的纺织劳动模范黄宝妹又回到车间去了……我决定到国棉十七厂去访问她。
走出天马厂时,厂内横幅上写着“一心面向工农兵,多拍电影好快省”,相关时代含义呼之欲出——“访问黄宝妹”的行为勾描出国家推动的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劳动人民展开的持续自我改造。
“十七年”中以知识分子“访问”为线索串联叙事的电影并不鲜见,如《春满人间》(1959) 中记者对“全民拯救炼钢工人丁大刚”事迹的报道,《青年鲁班》(1964)里夜校女老师秦淑贞对李三辈钻研技术精神的探寻等,都将劳动阶级置于被观察的场景中。这一处理方式在增强工人阶级示范引导作用的同时,更突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反身性。《黄宝妹》则具体指向了编剧所代表的电影从业者。影片上映前后产生的效应,使电影从业者尤其电影演员在个人形象、生活方式与艺术观念等方面进行深度反思,对片中编剧的配音者、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张瑞芳来说,这种反思尤为深刻。
1957年9月,电影拍摄前发行的《上影画报》以部分版面介绍了张瑞芳夫妇、白杨夫妇等银幕伉俪的日常生活。在《银幕外的张瑞芳》专题中,三张图片引人瞩目,分别为:张瑞芳身穿旗袍和针织上衣同丈夫摆玩家中的艺术品、穿深色旗袍在书房中独坐阅读、穿当时流行的裙装陪孩子玩耍 (图5)。杂志本想以张瑞芳的靓丽打扮增加观赏性,却引发了轩然大波。《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编者不必如此有兴趣地宣扬这些个人远离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私生活,而更应该着重去宣传他们如何认真、严肃地从事艺术创作,以及他们深入生活、向劳动群众学习的作风,也只有这样才使观众更热爱和尊敬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明星”面临尴尬处境。“明星”具有彼时主流观念所警惕的负面含义——“堕落奢靡的生活方式、崇尚个性和自由,所有这些都源于‘资本主义’,迷人时尚的电影明星是商业消费文化中最性感的象征”。“女电影演员”“美丽服饰”符号的叠加,构成对资本主义式消费场景、好莱坞欲望观看机制的深度触及。画报上时尚的张瑞芳、《寻爱记》中马美娜对着橱窗里漂亮衣服翩翩起舞的场景(图6),以及《青春的脚步》里彭珂给林美兰拍照的桥段,都带有这样的负面性质。
《黄宝妹》片头场景也出现了王丹凤、上官云珠两位电影明星的身影。她们都脱胎于旧社会的艳丽女星,上官云珠曾以歌厅舞女、珠光宝气的富太太、艳丽风流女子等形象深入人心;王丹凤在一年多前刚扮演了“穿花衣”的年轻护士简素华。但在《黄宝妹》中她们却身穿朴素衣衫扮演劳动人民(图7),反而黄宝妹才是众人探寻效仿的“明星”。这隐喻着现实中时尚女性相反的命运轨迹:一边是劳动模范在“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被大众认定为靓丽的时代锋面;另一边是曾享有“时髦”光环的电影演员在阶级改造过程中抛弃自身旧有的一切,经历漫长又艰辛的转型阵痛。
陆小宁在《张瑞芳:塑造社会主义红色明星》(Zhang Ruifang: Model⁃ling the Socialist Red Star) 一文中,详细论述张瑞芳被逐步改造为新中国“红色明星”的过程,认为“李双双”是其改造完成的标志。李双双的质朴外形“重新定义了电影明星和观众之间的关系,鼓励明星和观众之间的亲密同志情谊,而不是对明星的狂热”。“劳动人民化”成为电影演员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而银幕内外散发着个人魅力与消费主义气息的华美服饰与妆容,成为首先被改造的对象。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女演员纷纷“丢掉高跟鞋和美丽衣裳”,穿上质朴服装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青青电影》曾连刊《影人们的服装》专题报道。“解放之前,所谓电影明星们的服装是日新月异,解放之后,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都趋向简朴。”上官云珠出现在其中,身穿人民装,推着自行车,微笑面对镜头(图8),生动展现了“明星”向“社会主义电影工作者”的蜕变。
相较于外形上的改变,女演员如何“学演工农兵”,在表演方式、阶级思想与精神气质上达到银幕内外的统一,才是长期困扰她们的难题。不少演员思想上陷入迷茫,“一时之间都搞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张瑞芳最初甚至表示不想再演戏了,“怕演真的工农兵,担心自己必然会失败”。不少演员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近过工人,从来不了解不熟悉工人……更不要说怎样来表达他们或她们的思想感情了……将来我们表现出来的绝不能是穿着工人的衣服而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说着知识分子语言的‘工人’。”虽然1949年后电影演员开展了多轮基层改造,20世纪50年代全面推广的苏联“斯坦尼”演剧体系也为这种深入劳动人民的日常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但“该怎样扮演工农兵”的问题却依然萦绕在她们心头。
探访叙事及观察式镜头正是对电影演员如何从行为气质到表演方式彻底劳动人民化的全面生动演示。《黄宝妹》中有一个女编剧观察黄宝妹擦玻璃的情节:她先是质疑黄宝妹,当看到黄宝妹把玻璃擦得透亮后受到触动。这一情节具象化了知识分子从深入劳动观察到自我反思的完整改造过程。此外,该片“劳模演电影”自然真实的效果,给电影演员带来更为剧烈的思想震颤,使他们产生严重的职业危机。电影上映后,不少人对比专业演员和《黄宝妹》中的演员的表演,认为后者“由于有雄厚的生活基础,表演得很有分寸,感情也真实,在她们熟练的劳动中,动作富有美感和诗意”。“如果让一个有经验的演员来演黄宝妹,可能在某些情节上表演得更细致、充分一些,但是整个人物气质很难赶得上现在影片中的黄宝妹……这不是某些表演技巧所能代替的。”《评影片“黄宝妹”的独特风格》更是认为:
影片显示出劳动人民一旦掌握文化,就可以大规模地参加艺术活动,从而可以打破对表演艺术的神秘主义……我们艺术活动发展的远景是无限蓬勃无限多彩的!
几乎所有评论都把黄宝妹和工人们描述成冉冉升起的文艺新星,舆论使经历多次劳动洗礼的职业演员不仅陷入始终“改造不充分”的自我否定,也对自己长久以来的表演方法产生反思,“在较多的演员身上,却进一步暴露了表演的虚假性”,“所谓艺术创造只能意味着是一些离开生活,技巧上的卖弄”。还有如蓝青的评论,“‘深入生活’,‘思想改造’,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这并没有在所有的创作人员的思想及实际行动中得到彻底的解决,思想障碍恐怕还不少”,“这些资产阶级美学观不改变,即使深入生活与群众同劳动,也不能改变气质,准确地刻画劳动人民形象”。职业演员对斯坦尼观察体验表演方式一直难以有触及灵魂的理解掌握,更加剧了她们思想气质转变不彻底的自我认定。
影片拍摄前,王丹凤、上官云珠、张瑞芳等演员刚经历过新一轮“到劳动中去”,农民模样的照片被刊登出来(图9)。但她们依旧因“骨子里还不像劳动人民”而受到指责:“两个月劳动结束回厂,我们几个皮肤黝黑,仿佛全身落满劳动人民气质,唯独王丹凤和上官尽管在小队里劳动带头,十分卖力,仍旧是脸色白嫩,声音娇软,有人批评她们没有从灵魂深处转变立场。”与黄宝妹首次表演就备受好评相比,上官云珠这样的旧时代明星虽然很快褪去了时尚装扮,完成外在“祛魅”,但她们在历经多次自我改造和学习后却依旧经受着漫长的转型阵痛,甚至遇到无戏可拍的局面。
黄宝妹与专业演员相反的生存轨迹既涉及对阶级改造问题的再思考,更关乎对造星机制的探讨。“造星”在“十七年”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它既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处于历史主体地位的劳动阶级自下而上的“制度神圣化”过程,又包括对不太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诉求的阶级群体自上而下的“去神圣化”改造。前者以劳动模范为具体表征,后者以转型成功的“社会主义电影工作者”为代表。两种轨迹皆为塑造社会主义理想公民形象的成功范式,因而广泛见于彼时的政治宣传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中。“十七年”时期,劳模和电影演员皆因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被纳入国家统一审美规范,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构与传播。二者在政治秉持、阶级属性及与意识形态的亲缘性上的相反特点,造成时尚要素在两种“理想公民”塑造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在电影演员身上,时尚的装扮、气质与行为是充满消费主义色彩和欲望张力的皮囊,身体样貌和思想观念都必须被祛魅与规训。但相较于穿衣打扮等外在标识来说,思想观念、个人气质与工作方式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加之主流意识形态对“明星”的天然提防,她们在脱下华丽花衣后,改造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电影工作者就变为一种持续进行时态,伴随着演员的职业焦虑贯穿于其银幕内外的角色扮演与个人形象建构中。
三、“纺织工就是仙女”:女性美的“第三种可能”
时尚既是阶级议题,更关乎性别彰显。上述社会主义造星机制的讨论有着鲜明的女性性别指向。在“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叙述下,女性群体虽属不同阶级,却都走上了成为“理想劳动者”的路径。特别在生产建设愈发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女性身份让位于政治身份,性别意识逐渐被阶级意识取代,也使得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在外在身体气质和内在审美观念上趋同。
对“十七年”“妇女解放”的历史评估,普遍的观点是女性在此过程中付出了自我性别意识和特质的代价,如各类媒介叙述中的“女战士”“铁姑娘”:“她们被判断为失去性别的一代,徒然只是革命父权话语支配下的意识形态符号。”历史学者刘亚娟在对1949—1963年间中国劳模的历史建构分析中指出:“大多数研究者习惯将阶级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形态对立,因而有意识地构建出一系列‘去性别化’的劳模形象,但既有结论无法解释黄宝妹形象的生成。”以阶级视角对女性“铁板一块”形象序列的概括,造成了对“十七年”女性问题的误解。
温柔、美丽、性感等女性特质并未完全湮没在该时期的公开叙事中,但“只有剥削阶级、敌对阶级才会拥有并使用性别化的视点”。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电影中以“温柔刀”“性感美”著称的女特务,如王晓棠在《英雄虎胆》(1958) 中饰演的阿兰(图10)。某种程度上说,她们以站在阶级意识中对立面的姿态,拓展了该时期单调的女性性别内涵与形象谱系。然而,如何在主流叙述中为主流阶级“女性美”找到恰当的现实落脚点,一直是萦绕在“十七年”文艺创作者心头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孟犁野、张弦等曾对《上海姑娘》等作品进行重释,指出以成荫为代表的一批导演已开始有目的地通过生活细节塑造真实、立体的女性形象。问题在于,工程设计师、护士、电影演员等时尚女性因来自劳动阶级外部而迅速销声匿迹,变成一种“无法指认的美”。显然,黄宝妹的美能被指认离不开她的劳模身份,但以此解释还不能充分说明影片对其女性美塑造的独特策略。
片中编剧跟着黄宝妹走进工人俱乐部,遇到上海越剧团排练节目,名角傅全香就在其中。在她的指导下,黄宝妹换上戏服学起了《织锦记》中“七仙女”的扮相(图11)。越剧扮相是解放前上海时髦女性钟爱的艺术照造型,洋溢着与革命话语与阶级意识疏离的女性气质。编剧也疑惑,“我想了解她生产模范事迹,她却请我看越剧”。片尾对此给出了答案,黄宝妹带领工人攻克了“白点”问题,在纺织机的高效运转和黄宝妹的熟练操作中,越剧里的“七仙女”叠化而出——“女工变成了织布的仙女”(图12),编剧眼含热泪,恍然大悟:
就在这些平凡的劳动中我找到了我原先要追寻的英雄的梦想……天上没有仙女,真正的仙女是我们纺织女工。我不是最脆弱的人,但是我眼角上浮起泪水;是的,她们就是仙女!
现实形象、政治愿景与中国传统民间神话意象的嫁接、杂糅,是“十七年”中常用的叙事策略,在夸大人的能力方面,“充分借用民众所熟悉的、喜爱的、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通过改造其中的形象……将其语系政治化,从而使民众产生亲切感并易于在无形中欣然接受”。时尚装扮是“七仙女”和黄宝妹的相似特征,各类文艺作品及民间想象中的“七仙女”同样不乏女性美特质:鲜艳妆容、飘飘欲仙的服饰、温婉的气质等。这种美具有勤劳创造生活及对抗强权阶级的寓意,因而被界定在劳动美的范畴。电影借用“扮演”的方式实现“女性美”内涵的迁移转化。“七仙女”形象在中国民间社会具备的庞大认知基础进一步增强了黄宝妹“女性美”的易读性与传播力。古今女性美形象的重合产生出巨大的叙事潜力,织女与现代纺织女工构成一组固定视觉符码,在日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政治宣传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图13)。
此外,“七仙女”和纺织女工还有着一致的职业属性。相较于其他行业,纺织业的女工比例一直比较高,“1957年底纺织女工人数增长到23.6万人,占纺织业职工总数的60%左右”。有研究者将纺织女劳模与其他行业女劳模的形象作对比,认为“重工业中的新女性的打扮气质都复制了男性工人,宣示‘男人能做什么,女人一样可以’”。与之对照,女纺织工有着鲜明的性别意识与柔美特质,漂亮的纺织女工“穿着雪白围裙,戴着雪白的帽子、再衬上红花衬衣,像一只快乐的燕子在织布机前来回穿梭”。纺织女工承载着那个时代大众对女性美丽的想象,她们拥有自然的女性职业美,也关联着“穿衣”“时尚”的话题,成为不少人的理想职业和爱慕对象。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后,银幕上女性意识的激活与女性魅力的释放就首先从纺织女工展开(图14)。
不少研究指出,20世纪50年代谢晋已敏锐地意识到女性的性别危机,再现黄宝妹“美丽的身体”就是他的有益尝试。纺织女工们并不像《寻爱记》《青春的脚步》中的角色以时尚打扮的明显动机试探性别之美。影片并未强调黄宝妹被熟知的时髦形象,她的女性魅力源于纺织女工的职业背景,绕过了“时尚”背后缠绕的复杂阶级议题。《黄宝妹》的海报及推广照上,她都是典型的纺织女工装扮——戴着雪白的帽子,身穿花衬衣,手里拿着纺纱,笑容甜美(图15)。这种朴素的美并未妨碍大众的认可,“黄宝妹手拿纺纱的海报出现在各个电影院门口之时,她也成为一个美丽而醒目的标签,从而在各个领域均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导演既借用黄宝妹“穿花衣”的时尚影响力,又在电影中将可能引发风险的“时尚”要素过滤掉,将其框定在职业女性朴素美的框架内。
但是,黄宝妹的职业美未免与其他纺织女性劳模类同,不足以成为其参演电影及影片大获成功的原因。对此,谢晋曾在导演札记中详细描述过拍摄动机:
黄宝妹人很活跃,非常喜欢看电影,据说还会唱越剧。很快,一个念头从我脑子里闪过,我想:要是她的事迹写成电影剧本后,让她自己来演自己,这该有多好,这对观众有多大的说服力啊!
由此看来,片中下班后学唱越剧、扮演“七仙女”的情节并非虚构想象,黄宝妹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和上海其他女青年一样的文娱方式与审美趣味。她经常听戏、唱越剧、参加工厂舞会,热爱跳舞,与周总理、贺龙、陈毅一起跳过舞。她跟傅全香学唱的桥段也是现实缩影——她和越剧演员徐玉兰交朋友,成了宣传“文艺界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文艺工作者和工人农民攀‘亲家’”的典型。以工作中的职业美来规避“时尚”的做法并不难实现,影片真正解决的难点在于对“八小时工作之外”女性美的真实塑造。黄宝妹不但有着纺织女工普遍的外形美,影片内外的文艺能手身份同样引领着女性在日常文艺娱乐方面的“时尚”,这无疑拓展了大众对于美丽内涵的认知,她的女性美既真实又立体,不仅局限在表面。
抛开关于时尚衣着的争议,前述《护士日记》《青春的脚步》等影片中对女性起居室展陈装潢、热爱跳舞观影等细节的展现,也跳出了外在形象的局限对女性美进行诠释。但受思维定势与认知经验的影响,“去性别化女性”的观点已内化为当代各类研究的普遍共识,这造成对“十七年”性别展演仅以正面或反面的标准进行指认,对女性气质的发掘也局限于穿衣打扮等外在表征。《黄宝妹》的成功,说明这一时期女性性别特质在要么“男性化”要么“魅惑美”的“非黑即白”标准外,的确还存在中间道路或“第三种可能”。相比于其他影片以“时尚知识分子”改写女性气质的路线,在纺织女工、“七仙女”组合衍生的叙事中,美的合法性是在劳动阶级内部重新建立的,并通过在政治安全界线内凸显女性魅力而获得的。她们身上既有一种符合劳动阶级的美,又部分游离于标准女性美范式之外,显现出非模式化的魅力,产生了更丰富的衍生文本与持久的社会效应。
余论:跨国性与处在“十七年”女性现代性经验间的“时尚”
需要指出,黄宝妹和她的姐妹们演绎的美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感。稍早时期,中国影院风靡的《卡塔琳的婚姻》(Kis Katalinházassága,1950)、《卡嘉》(Katka,1950) 等来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影片中出现了相似的纺织女工身影(图16)。《寻爱记》《上海姑娘》《青春的脚步》中衣着时髦的青年职业女性也与1955年前后受城市女性追捧的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Неоконч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1955)、《生活的一课》(Урок жизни,1955) 里的穆罗卓娃、娜塔莎有着同构的角色特质(图17)。当穿衣时尚经由电影等媒介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蔓延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通过大众媒介参与并推动了这场文化风潮。
有研究者已注意到“十七年”中国内部的地缘文化张力,他们以上海的独特地方文化切入,探讨电影中“穿花衣”女性形象的生成。这些女性形象更体现着超越国别的地缘文化张力,映射着冷战语境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跨国互动。此前,国内外学者通常围绕普遍存在于文艺作品及媒介叙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国家现代化建设”等意识形态话语,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文化交流的主体内容及历史经验。但这种“务实政治”(pragmatic politics) 式的看法,忽视了电影作为流行文化载体在社会主义大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若回看全球流行文化史,此时好莱坞一批“时尚影片”正带动战后女性流行文化与日常消费的跨国性风潮。那么社会主义阵营相似的情形是否说明,该时期苏联同样想借由时尚与电影这一现代媒介耦合所释放的流行文化意义与传播效力,构建一种女性主导的社会主义跨国文化结构与实践形式?
就像黄宝妹宣传布拉吉、鼓励大家“穿漂亮点”时强调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20世纪50年代“布拉吉”等时尚装扮对中国女性产生的深刻影响显示出苏联在国防军事、工农业建设、现代科学、意识形态工作等领域树立先进范式后更为宏大的战略谋求:利用一种类似消费主义、文化商品输出的思维打造跨国大众流行消费文化,以规范社会主义世界日常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诚如陈庭梅(Tina Mai Chen) 所指出的,苏联主导下社会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间有意通过电影等消费文化产品构筑“日常生活国际主义”(everyday internationalism),“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插入,将美学、政治、情感和现代性联系起来”,形成“另一种全球化”。显然,相较工业生产建设、现代科学等生产实践话语,作为生活内容与流行文化的“时尚”更易于女性理解和接受,在这一“国际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她们更容易发挥出远超在传统生产领域的性别价值,主体地位也得到彰显。尤其在“十七年”的“女性解放”主流政治动员中,女性因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主体而不断被“铁姑娘”化,在这一实用主义价值体系中,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电影的引入使各类时尚装扮进入中国女性观众的视野,不仅培养了她们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理解,激活了对美丽及流行文化的追求,更重要是获得了区别于实用主义价值的性别认知,建立起独特的现代性经验。
本文对社会主义女性跨国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视野的引入,揭示出“十七年”时期中国女性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由电影培养出的与西方女性观众类似的现代性经验。哈里·哈鲁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 认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现代性经验“并不仅源于新的社会制度与实践形式”,而且在“混合与互动中产生了一系列可能的暂时性及斗争状态”。我们不妨将20世纪50年代中国银幕内外这场短促的时尚风潮视为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两种社会主义女性现代性经验在地互动碰撞的具体表现。但无论繁多的“铁姑娘”式角色还是《青春的脚步》《寻爱记》中的时尚女性均顾此失彼,未将两种经验均衡统一,自然无法为解决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如何彻底改造女演员、如何合理彰显女性多元气质等一系列复杂又颇具风险的问题提供可行参照。《黄宝妹》文本内外丰富的历史细节,显示出其既具备妇女高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力价值,又在日常生活领域释放着大众流行文化魅力与经济效应,成为完美聚合两种经验的社会主义女性范本,有助于我们对“十七年”乃至更高层面的“革命中国”展开重估。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孙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