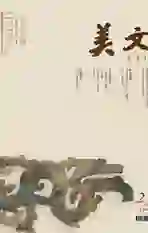塔尖之上
2025-02-18周倩羽
我的村庄生在云山上。这个村子不按姓氏聚落,许多人是外来到这里安居的。这里有河沟、田土,还有麻雀、蚂蚱和野山鸡。粮食有了,一簇一簇的人就来了。田野中的玉米、稻谷、蒿枝,也就沿着山路蔓延开来。
这些年里,云山上站立得最多的,除了毛茸茸的玉米秆子,就是四只脚的电塔。有了电塔,电灯电视电脑就有了。外面的世界透过铁塔的一根根电线,穿梭到村人眼前。这一切,可能都要归功于小瑜的爸爸哩。
十岁进城以前,我在云山村最好的玩伴是四家姐妹。“四姊妹”里,大姐是村长的女儿,最靠谱、最体贴,我们都叫她萍姐;二姐姓廖,一头短发,性格打扮都像男孩子,我们喊她廖哥。我属老三,小瑜只比我小两个月,排行老四。我俩除了年纪小不懂事没啥特点,因着年纪相近,也玩得最好。非要说区别的话,我家里人多,有时候灶头还算闹热,但她生来就没了妈,爸爸常年不在云山,怪惹人怜。
太阳落下又升起,黄澄澄的蜜蜂落在新生的玉米花粉上,露珠总挂在草叶间。日子是有脚的,这脚长在太阳身上,长在玉米秆身上,长在女娃娃身上。
小瑜打小就跟奶奶,她母亲生下她一个月后就得病不在了。爸爸在山那边的县城做塔建工作,两三年才回家一次。一天他打来电话说,等他在城里攒下钱,就要把小瑜的户口迁过去,供她在城里念书,将来还要读大学哩。
奶奶耳朵不好,小瑜每次传达完电话内容,奶奶总要噘着嘴,嘟囔很久:女娃娃家念啥子书,不如早点长大嫁个好人家。其实,小瑜才不想嫁人哩,每回看村里的女子嫁出去,个个都哭得厉害哩。我们姊妹四个私下约好了,今后谁都不离开云山。小瑜总要加一句,还不能离开高塔。
最初,云山的电塔只有一座,是小瑜爸爸带工人们修建的。尖利的塔尖下装着三扇钢铁翅膀,正好构成一个“上”字型。小瑜问过爸爸,为啥是“上”字,而不是对称的“土”“王”“干”?她爸说,因为人都要往上走,塔尖之上看得到重庆城哩,上面的风景最好看。但是,我们谁都不敢爬上塔尖,只能从下望见丝丝缕缕的细线,好像穿过天空的琴弦,一道道延伸到山外的天空,一直到大家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那个夏天,小瑜悄悄告诉我,她最近觉得胸膛和腰好酸好痛,睡觉时身上好像有虫子在爬。她说,那虫子从腰腹到胸膛,一口一口啃咬她的皮肤,咬出两颗硬硬的石头。我正惊讶着,谁料这话被奶奶听见。奶奶就立马吓唬起我们,凶神恶煞地说:“女崽子莫乱说,俺跟你一个床,虫子啷个不来咬我嘞!小姑娘家哪来腰杆子,怪你一天到晚在屋头坐太久了!走,跟我一路去给苞谷摇穗。”我晓得,小瑜奶奶又要找理由揪她去干活了。我反正在家无事,就也跟了上去。
太阳一步步从脚后跟挪到耳边,终于走到了小瑜家的玉米地。这片玉米地坐落在山顶旁的空地上,尽头处有一间半新不旧的红色瓦房。正午的阳光正慷慨地洒下,墨绿色的叶子顺着玉米秆舒展开来,朝向天空,张着手臂敞开怀抱。在这上下交错的怀里,每一根秆子上夹着两三个青叶包裹的玉米棒子。那些玉米须弯弯曲曲,从棒子的头顶一路垂下来。
“奶奶,啥子叫摇穗,是把苞谷上的须摇下来么?”小瑜捏了捏眼前鼓囊囊的玉米棒,又扯了扯它金黄的头发。奶奶把一根玉米秆从顶端拉下来,一簇扫帚般的穗子甩到我们眼前,上面有鹅黄色的小花。她说:“妹娃看,这就是苞米的穗子。苞谷棒上的须须也叫穗,不过那是雌穗,这秆子顶上会开花散粉的是雄穗。种苞谷要授粉嘞,把雄花粉摇到雌须上,长大的苞谷粒才齐整。”
小瑜挠了挠头,接着问:“为啥子要把粉摇下来呀,风一吹不就能自己掉下来吗?”我也追问。
奶奶开始不耐烦了:“俩背时女娃问得倒是多,谁家花粉落得均?刮风下雨,粉就被风刮跑了,被雨冲走了。”大概是奶奶骂得不解气,她又对着小瑜念叨起来:“你妈命也不好,生完你就死了!”
我们低下头,谁也没说话。因为村里都晓得,小瑜奶一看到男娃就要去捏人家的脸,老太太就是喜欢男娃不喜欢女娃。
沉默中,奶奶一边骂一边干活。我听见蝲蝲蛄还在土缝叫唤着,看见小瑜脸色耷拉着,就赶忙拉住她,钻进了密密麻麻的玉米地。
我俩一排一排摇动起玉米秆,看到顶上的花粉一点点落到玉米须上。太阳跑得快,从我们耳边滑到头顶。我俩一步步往前移,玉米叶沙沙作响,额头冒出了细汗,衣衫有些沁湿了,身上黏乎乎的。这时我听到小瑜嘴里叽叽咕咕念叨着,爸爸妈妈。
我笑她,莫听奶奶打胡乱扯,随便摇两下就成。她认真地摇着,边摇边说,那哪成,要好生摇。
从这头摇到那头,我们和奶奶越来越远了。高高的玉米秆将我们遮挡起来,飘散的花粉持续黏进流汗的肌肤里。玉米叶绒毛细嫩,玉米须纤长卷曲,挠得我浑身痒痒。不一会儿,小瑜突然抓紧玉米秆,说夜里那股酸痛劲又上来了,正从后背一直爬到心口两端,变成硬邦邦的两块。我吓坏了:“啷个回事呀,虫子在哪?我看看!”
“不是真有虫,就是像小蚕咬桑叶那个感觉,麻乌乌哩。”说着,她指着酸痛的地方让我去摸。我想到母亲给我讲的话,就只伸出指头按了按。我一按,小瑜那里真是硬硬的!怪了。后来到城里读初中,也开始感觉到那种酸痛。母亲告诉我,女孩子身体要发育,或早或晚,都是正常的。可惜,我还没来得及给小瑜解释缘由,她就越走越远了。
“哎呀,干啥子哟!”我见她这样,不好意思起来。
她背过身去,喘息着对我说:“玲玲,我觉得身上好痒哟,难受得很,让我挠一挠。”
天上的云凝滞了,蝲蝲蛄也不叫了,小瑜夹在玉米秆中间,脖子被汗液沁得润湿,玉米叶顺着她颈边的呼吸,窸窸窣窣地来回晃动。那一阵闷热过后,一阵凉风很快吹过来。她长舒了一口气,转过身来。
我们就又继续往前摇穗。一路摇到土地尽头时,突然传来一阵婴儿哭声。
扒开玉米秆,我俩探出头,看到那座红色瓦房门檐下,有一个女人在给孩子喂奶。她听到玉米地的窸窣声,看到了叶子后的我和小瑜,把我俩叫到了跟前。
“两个小妹,你们叫啥子呀?”问完话,她打量起小瑜,神色惊喜。“妹崽,你是山下赵哥家嘞娃娃吧!肯定是哩,眼睛跟你爸一模一样。”那女人矮墩墩胖乎乎的,面如满月,笑起来有两个桃花样的酒窝。
这女人看出了我们的好奇、害羞和拘谨,便让我们叫她莲姐,解释说家中原先的房子遭大水冲垮了才住到这里。她的男人前些年跟小瑜爸学过塔建,所以一眼就认出了她。听到女人一家认识爸爸,小瑜的眼睛亮了一下。
说着,女人大声喊起男人:“胜哥,给俩小妹冲点牛奶喝哟!”瓦房外的灶房传来一声“好”,音色雄浑厚实。我看莲姐面善敦厚,笑着对她说了声“谢谢”。但小瑜讷讷地,不敢开口。
莲姐夸奖我俩孝顺懂事。这时,在房里做饭的男人端着一个圆碗走了出来。莲姐的男人粗糙黝黑,端碗的手背上青筋爆出。
她抬头,正好对上胜哥的双眼。我看到她抖了一下,像有块石头砸进水坑。她颤抖地伸出双手,甚至连碗都没有端稳,牛奶就猛地顺着脖子淌进了她衣服里。那只碗哐当一下碎了满地,她吓得叫了起来,。
小瑜边跑边哭,我不晓得她啷个了,只好随她边跑边追,一点点撵到她面前:“你啷个啦,跑啥子呀?”
她不说话,一脚踩折好几根玉米秆,屁股坐到叶子上。她的两腿拱成一座桥,双臂交叠在上面,把脑袋埋进去。我一连问了好几声,她才开了口:“那个男的,眼尾也有一道疤,跟我爸一样。”
小瑜说,她是奶奶用米汤、乳糕混着蛋黄一勺一勺喂大的。三岁那年,爸爸从城里带回一罐白奶粉,开水冲泡后,味道浓郁绵软,好喝得很,奶奶每次只舍得给她泡一点点。而胜哥端来的奶,和小时候的奶粉一个味。
我纠正她,牛奶是牛奶,奶粉是奶粉,各有各的味道。
“玲玲,哪个好喝些?”她抬起头来问我,长睫毛湿润润的,像只小鹿。
“不好说,我偷吃过弟弟的奶粉,好香哩,但没味。要我说,最好喝的还是牛奶,又香又甜,刚刚胜哥端的那个就好喝,还冰冰凉哩!”
听我提到胜哥,小瑜又把头藏了起来。我坐到她身边疑惑地问她:“小瑜,刚才你啷个要跑呀?牛奶打翻了,我们应该要给人道歉呢。”
她不抬头,不说话。
我问她是不是想爸爸了,她摇摇头,压着嗓子。
奶奶从玉米地那头赶来,看我俩踩断了几根玉米秆,气得直跺脚。得知小瑜胸膛打湿的缘由后,奶奶赶忙把她从玉米地里拎出来,一路揪到胜哥家门口。我跟在后头,生怕小瑜要挨打。
“你个背时女娃子,点都不懂事理,快点给胜哥和嫂子道歉!”奶奶推搡着小瑜的后背,气喘吁吁地骂着。
莲姐仍坐在门槛前,看小瑜身上还是湿漉的,驮着背在低头擦眼泪,她着急地说:“哎哟,赵大娘,这个不怪小瑜,都怪胜哥碗没端稳,把小瑜衣裳都打湿了。”她转过头朝屋里喊了声胜哥,胜哥穿好一件灰黑色短袖跑出来,递给奶奶一条干毛巾。
“对哩,大娘你莫怪小瑜,两个女崽干活累了给她们端了碗凉牛奶,结果一下没端稳。你快给小瑜裹上,流完汗莫着感冒了。”见奶奶仍揪着小瑜,胜哥又赶忙说,“我下半年也要去县城找赵哥做活,小瑜要是感冒了我不好跟赵哥交代呀!”
小瑜奶奶这才伸手接过了毛巾。她边擦边看着胜哥:“胜儿啊,你眼角啷个也有道疤呀?”
“没得事哩大娘,修电塔遭电焊的火石烫到哩,再正常不过啦!小瑜爸带出来的我们这些塔工,个个都有这疤,成标志了哩!”胜哥爽朗地笑起来,像当时的日头,不偏不倚地落到小瑜身上。
她抬眼看了看胜哥,又扭头看看远处的电塔。塔身沐浴在光里,背后的穹苍蓝得纯净,蓝得透彻,没有一丝云彩。塔尖的光最炽烈,好似新长出一个太阳,还没有万丈光芒,但也耀眼闪亮。
小瑜奶奶在胜哥家一阵寒暄之后,带着我们往回走。一路上,她总是感叹,这胜哥就比小瑜爸小三岁,学得了建筑的手艺,讨了这么年轻壮实的媳妇儿,还生了个能吃能喝的大胖小子,真是有福气。小瑜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再像从前那样挺起胸膛,走路总是蔫耷耷的。
夏日的时光过得慢,我只顾着荡荡悠悠没心没肺找乐子,扭头就忘了小瑜身上不舒服的事,她也没再提了。有一天,萍姐的爸爸赶集带回来一盒水彩笔,我们“四姊妹”就围在一起画画。小瑜是手最巧的,不声不响地就画好了。画面里就是那座直插云霄的“上”字塔,凹凸分明、有棱有角,每一根电线都镀上了金色。正三角塔尖矗立在红太阳下,一个背影站在塔尖上。我们都晓得,那个背影,就是小瑜的爸爸。
如今,小瑜的爸爸回家了,却换作他每天呆望着铁塔,等待小瑜回来。
暑假过去,临近开学,玉米已经长好了,随时可以丰收。奶奶带着小瑜穿过玉米地,掰下几根长势最好的玉米棒子放进袋里。我帮着她们,拎着大包小包来到胜哥家。这些东西,她们想托胜哥给城里的小瑜爸捎过去。
小瑜奶奶给儿子准备了新缝制的衣裳和棉鞋,往年腌炕的香肠腊肉,还有一床自己做成的蚕丝被。小瑜则把那幅画装进了一个信封,想让胜哥帮忙转交给爸爸。
在胜哥家,奶奶和莲姐交谈的时候,胜哥去门外的树上抔来一把李子,清水洗净后,用水瓢装着递到我和小瑜跟前。胜哥蹲下身来,像一张平稳的桌子。他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嘴角扬起漂亮的皱纹。他特地挑选了几个红李,让我俩尝尝。我一向是自来熟,脸皮厚,咧着牙就抓了好几个往嘴里塞。小瑜看到他眼尾那道疤横在眼前,有点怯怯的,捏了捏手指,不敢去拿李子。
胜哥把水瓢放到地上,一只手抓起两个李子,另一只托起小瑜的手,并示意她摊开手掌。他的手沾了清水,湿漉漉的,轻柔地将她的手背整个包裹住。她垂下的眼睑抬了起来,在胜哥眼神的光亮里看到了自己的小小影子。
黄昏时分,胜哥要留我们在家吃完饭再走,小瑜奶奶拒绝了。庄稼人喜欢茶余饭后聊闲唠嗑,但绝不会轻易留在别家吃闲饭。我们与胜哥一家道别后,就顺着玉米地往山下走。离开的时候,胜哥往小瑜手里硬塞了一箱牛奶。
奶奶在前,我和小瑜排后,走在狭窄的小路上,两侧是望不到边的玉米秆。宽展展的叶子从摇穗时的青绿变得愈发褐黄,从拥抱天空的形状长成了低垂进土里的姿态,踩在上面有嗞拉拉的清脆声响。包裹严实的玉米棒被夏日阳光烘烤得绽开了皮,娇嫩的玉米须变为黄中带红的老成。
那时的我和小瑜,依然只有半根玉米秆子那么高。透过头顶苞米的尾巴,我们看到一头是夕晖渐渐弥散于夜色,一头是明月静寂初升于靛蓝天幕。好像在我们的肩上,一边担着日落,一边担着月升。高处的知了歇下了,地里的蚂蚁和甲壳虫开始忙活起来,它们在蓊郁的青草间吹拉弹唱、望月乘凉。
走出玉米地,小瑜感觉自己裤兜鼓鼓的,伸手一掏,摸出一个信封,才突然想起给爸爸画的画还在里边。奶奶骂小瑜不长记性,忘就算了,下次再寄吧。小瑜却不甘心,急得哭起来,坚持要把画给爸爸。眼看奶奶又要发怒了,我赶紧站出来劝,说我陪她去。
小瑜攥着信封在风里飞奔着,我都有点跟不上。她的双手双脚挥甩起来,橘黄色的云霞和罩着红晕的山峦都落在了她身后。
跑到胜哥家,我们看到房檐下和堂屋里都没人,就来到窗边,见着胜哥和莲姐正在灶房筹备晚饭。莲姐弓着身子在灶台上切丝瓜,胜哥怀抱着儿子,摇晃着手中的拨浪鼓,眉眼笑成两轮弯月,嘴里念着那曲古老的摇篮曲: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爸爸、妈妈, 永远陪着你!
唱完后,胜哥俯身亲吻了儿子的脸颊,又哼起了新的歌。听着歌谣,小瑜的眼眶早已湿润。那一刻我知道,她多希望自己是胜哥怀里那个安睡的小孩啊,可惜她不是男孩,也不是胜哥的孩子。
见小瑜迟迟不行动,我开始催促她,她的眼泪却越掉越长。
担心小瑜的哭声被屋内的胜哥和莲姐听到,我急忙把她拉到了屋后。
“小瑜,你在哭啥子呀?”我一边问一边给她擦眼泪,“瑜妹你莫哭了,你爸就要看到你的画了,看到他肯定就要回来哩,你哭啥子嘛。”
小瑜听到我的话,反倒失声痛哭起来:“他肯定不得回来了,村里人都说他在外面有了媳妇和儿子,不得要我勒个扫把星了!”
我手足无措,不懂小瑜为什么临了又退缩了,不就一幅画么。我从她手里夺过信封,气冲冲地说:“你不敢,那我去送!”
她却狠劲拽住我,使出浑身力气抢回信封,把我手臂都掐青了。她眉头紧锁,红眼睛恶狠狠瞪得滚圆,冷冷对我说了一句:“不要你管。”
说完,小瑜就绕过红房子,拼命向玉米地方向跑去了。我呆愣在原地,还回想着小瑜刚才的神情。她像是一片被酸雨腐蚀后裸露的土地,贫瘠而萧瑟,弥漫起腾腾冷气,令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只得一个人穿过玉米地。那条路,我走得很慢,很慢,始终没有等到小瑜回来。未曾想到,那竟是我和她的最后一面。
薄暮的最后一丝霞光从头顶闪过,细碎的叶片在耳边呢喃,眼前的靛蓝一点一点变成深蓝,而后消失于天际。天空中的月亮朗润起来,星星发着光,远处那座高塔插入云端。云雾中,我恍惚看到一个人站在塔尖上面,是小瑜的爸爸。他将星星摘下来安装在塔顶,照亮了整片田野,有铁线般的道路从四面八方铺展开来……
随着云山的路越建越宽,电塔和高架桥一座座涌入,我也顺着这些道路蜿蜒到了城市。童年转瞬即逝,晃荡的玩性渐渐褪去,我走向了云山之外的世界。
那几年春节,我回过云山两次。第一次没看到小瑜,只见得她奶奶。团转的人问小瑜去哪里了,奶奶说,小瑜进城和她爸过年了。第二次再回去,是我高三的寒假,只见得小瑜的奶奶和爸爸。团转的人又问小瑜去哪里了,她爸说,在城头进厂打工,过年假期少,就不回来了。
上大学后,听母亲闲聊说,小瑜嫁人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哪个小瑜?还有哪个小瑜,你赵叔家的小瑜。啷个可能啊?我惊得下巴都要掉到地上。那时我刚入大学不久,正感受着学府书院的古色古香,吹拂着湘江水畔年轻的风。嫁人,多么遥远的两个字……小瑜说不想嫁人的,怎么会这么早?母亲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
我难以置信:“胜哥的表弟?岂不是都三十好几了?小瑜不是在城头打工么,啷个回去了?”
“是,估计比小瑜大十几岁吧?娃娃都两个了,屋头还有一个疯子媳妇。哎,天晓得她啷个就回来了,听说是在城头工作不顺,老和她爸吵。几个月后,你赵叔才晓得这事,气得半死。我心头一阵唏嘘,给久未联系的萍姐打去电话。她告诉我,胜哥一家人心头愧疚,曾带着赵叔去找过他表弟。赵叔想拉小瑜回去,但她不肯,怕回村子里被说闲话。赵叔拗不过,大病之后辞了工作,拿了钱回云山村等她。赵叔说了,只要他在,小瑜受委屈了还有个去处,他就在电塔下把她守着。
听到这些,我心头下了场大雨,酸楚绵延了好几宿。小瑜离开云山的时候,有没有像别人一样黯然神伤呢?最后分别的那个夏日黄昏,她潜藏着什么秘密?而此后的岁月,我怎就飞也似的匆匆掠过云山的塔顶,未曾给予她片刻的念想与回望。
今年春节,我回村途中路过小瑜的家,满山上只有这家门上没有贴春联,才晓得小瑜奶奶去年冬天过世了。大年三十的傍晚,“上”字电塔便开始沉默工作了,不时闪烁出滋滋的电流。村中户户亮起屋灯,点燃鞭炮,放起烟花。全村人都领着孙孙崽崽到山坡祭祖,端着饺子互相串门,绕着云山游来逛去,热闹好似赶庙会。
暮野四合,山中人烟渐渐稀少,云山天色慢慢黯淡。下山时,我看见赵叔一人在坝子上静静坐着,似乎在望着远处。因为背对着大山,我看不清楚他的模样,只看到他瘦削的轮廓,头上爬满了白发。
夜幕中,他像座没有电线的铁塔一样沉默。周倩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