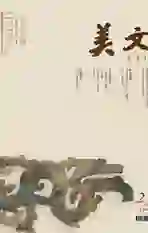风中的父亲,雨中的车
2025-02-18周倩羽
北方冬天的室内总被暖气充盈,晚间一条薄被的拥抱便足够暖和松软。我正酣睡着,南国的风雨却从手机里飘飞过来,猛地将我淋湿。
电话是父亲拨来的。那头风声很大,父亲嗓音沙哑。他说,大卡车昨天夜里在高速上追尾了,他前头那辆货车被撞翻倒,连着自己的车都报废了。说到这里,他语气满是自责,怪自己瞌睡,一年辛苦钱全赔了。不知怎的,我感觉南方的潮湿雨水混着汽油味,一点点顺着电话线漫进床沿。
父亲发来一张照片,那辆他心爱的红卡车已然破碎坍圮,面目狰狞地立在雨中。它失去了铜墙铁壁,就那么凹陷着脸,露出凌乱的血管,显出断折的骨架,龇牙咧嘴地好像在哭。平日里,它总是刚健威武、沉默寡言。在这最后一刻,它却哭得那么大声,把之前淋过的所有雨水都倾倒,哭成了一条浑浊的长河。
父亲没有哭,只是在我和母亲打去视频电话的时候很快挂断了。平日里,父亲总是咋咋呼呼,乐呵呵的,喜欢唱歌讲笑话,天不怕地不怕哩。这一次,我知道,他还是哭了,只是不想让我们看见。打记事起,父亲就在开车,摩托车、小货车、大卡车……父亲像风,总停不下来。他每一次换车,都是因为车祸。这次劝他,看开点,人没事就好,今后不要再开车了。他回复我,你老汉没文化没力气,不开车啷个养活一家人?我明白,他仍不打算停下。
人间的车,形形色色,载着故事不说。车对父亲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职业是开车。不是出租小哥,不是公交师傅,更不是专职司机。这份工作没有那么体面。无数个夜里,黑黝黝的山洞一口接一口地吞噬他和车。还有无数的他们,一齐吞吐在群山的盲肠里,以明亮的车灯照见石壁的脉络,用轰鸣的汽笛撼动大山的心脏,作为他们呼啸过人间的证据。
一开始,父亲有辆嘉陵摩托车,是在重庆打工挣的。摩托车的车身像个红色大蚂蚱,脚蹬子撑起时,后轮会悬在空中。五岁暑假那年,父亲骑着它载我和母亲进城。起先,父亲把我放在最前面,车前胸口处有一个圆鼓鼓的油箱,我立刻抱怨油箱坚硬硌人还烫屁股,就被换到了父母亲中间。其实,油箱一点不硌,只是我有一点自己的小小私心:妹妹还很小,坐车不便,我难得进城,就想坐在爸妈中间。
那时候,年轻的父亲还是平头,穿着条纹衫,身形瘦削,一米八的个子只有一百来斤。他爱干净,买了摩托后便在城里拉客,母亲则摆摊做点小生意。这年夏天,爸妈专程回云山村,想带我去见见世面。父母亲的前后怀抱里,我不觉拥挤,一路上欢欣雀跃。摩托随山路一起盘绕,两岸田埂的水稻苗已挺直了腰,夏日熏风把稻田摇曳成一片翠绿的远海。偶有白鹭往来,不时惊飞一地麻雀。
我的少年时代尽在这无图索骥却又其乐无穷的山野度过。吹着云中掉落的风,看阳光一闪而过。我将脸蛋贴到爸爸的背上,嘴里的儿歌换了一首又一首。终于唱累了,我便靠在父亲背上休息,嗅到他衣衫里有淡淡的草味,是被阳光晒透的干草气。
“咦?玲玲妹楞个快就睡戳(方言,睡着)了嗦。”听我停止了歌唱,父亲问。母亲赶紧两手搂住我,并让他开慢一点,生怕把我吵醒。我根本没睡着呢,于是将计就计,用上牙齿咬住下嘴唇,努力不让嘴角上扬,就那么憋着笑装睡。过了一会儿,我嘴里开始胀气,实在是憋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接着是连绵不断的哈哈大笑,像滚动的玻璃珠乒乒乓乓地洒落,父母也跟着咯咯笑了。
“玲玲勒个娃儿,以后肯定精灵得很哟。”飞驰的摩托车上,父亲大声说父亲大声说笑着,还发誓以后不开“敞篷”车,要开那“有盖子”不着凉的好车。当时我不明白,“敞篷”摩托车也很好呀,父母亲都可以贴在我身边,风儿凉悠悠,一路美景尽收眼底,有哪里不好呢。想着想着,我就真的在风声、谈话声、引擎声中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到了高楼遍地的山城——一座令我眼花缭乱的水泥森林。
但我们的家不在高楼上,而在巷子深处两座居民楼交界的地底,得从干涸的排水沟里走下去,路面上的人一般看不到那里。地下十平小屋的墙上有几个方形小洞,连接着外面的石板路。我在屋里就能听到路人走过的脚步,每个人穿了什么鞋都看得一清二楚。
阳光透过方孔钻进来,又被路人的脚步踩碎。父母亲不在家,我无聊时就会趴在床上,干瞪着眼睛,数外面路过的鞋子数。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从早上醒来到爸妈回家,窗前走过了73双脚。
晚上,父母亲回来后,时常会带我到隔壁小区玩。那有很多游乐设施,滑滑梯、沙坑、大转轮,但我总是不安分,喜欢玩最大最危险的铁秋千。秋千有一股铁锈味,晃动起来是重金属尖锐刺耳的响声。我喜欢让父亲推着我,荡得多了,我开始嫌弃父亲推得不够快,就把他赶走,自己荡了起来。
一天傍晚,我将双脚悬空,用力踢蹬着,恨不得飞到天上去。再高点,再快点!我兴奋地叫喊着,甚至尝试站到座板上,感受更烈的气流。突然,我的身子因为重心不稳失去了平衡,出汗的双手抓不紧铁链,整个人从侧面歪斜。秋千还在晃动,大链子已经把我的手腕擦破了,是火辣辣的疼。我知道自己即将被秋千甩出去,重重摔到地上,座板会撞向我的脑袋,恐怕得磕掉一颗牙,满嘴流出鲜红的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不知从哪里变了出来,闪电般冲到我身边,用他精瘦的臂膀紧紧地接住我,避免了一场意外。我惊魂未定,心跳如鼓,吓得脸色苍白。父亲的短袖被铁索钩穿了,薄肩头砸得淤青。一时间,他怒目圆睁训斥起我:“死龟女儿,荡楞个快摔死你!”
我能看到,父亲的眼神里其实满是惊恐。他骂我的声音很大,吓得我哇哇大哭起来。当时我在想,父亲是神仙吗?从哪里变出来的?怎么就能接住我呢?要是没有父亲,我真的差点摔死了!我哭啊,好害怕地哭,飞在秋千上有多么飒爽,哭的时候就有多么后怕。现在想来,父亲在每一次车祸幸存之后,总是一个人面对一堆废墟,况且从没有人接住他,他是不是也这样害怕过呢。他的害怕,应该是我当时的千倍万倍吧。
我第一个城里的夏天,就这么在无聊和惶恐中过去了。回到云山村,我继续到云山小学读书,每天呼朋唤友没心没肺地爬山路,追逐着蹚过一条条河,偷了好多人家田埂里的菱角和玉米。这期间,妹妹落水里去了,没得了。屋头就我一个娃娃,我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荡着,不服软,也荡成了一架铁秋千。
我在云山荡,父亲在山城荡,看来这不安分的基因是遗传的。三年级的一天,我在放学路上遇到了屋后的马二婆,她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以为她是来逮我的,紧忙扭头就跑。因为那天早上,我偷了她地里仅剩的一根黄瓜。她追我不上,喘着粗气大喊道:“背时闺女哟,还跑楞个快!快回去看你老汉,出事了!”
我霎时愣住,拔腿就往家跑。回到家,我看到父亲捂着肚子,身下都是血。乡医在一旁忙活,母亲和奶奶抹着泪。马二婆说,我父亲这趟是专程送母亲回来养身子的,怀上了。“你老汉呀,点都不像个老汉,简直是个小汉!几十大岁了,还手痒痒要去耍刘幺毛的摩托车。别个刘幺毛那个车,又不是普通拉人的摩的,别个是飙车的那种赛车,开起来比马儿还要快,他哪里开得来嘛!哦豁,一不注意就栽到柚子林去了,肚皮都遭树枝剐破了!哎……”马二婆一边摇头一边说。
后来我跑到柚子地去看了,刘幺毛那辆车确实好看得很,车型饱满,像头金色狮子,每个角度看都是闪着光的。爱车的父亲一遇到漂亮车子就挪不动脚,跟小娃遇到泥巴似的,哪能不手痒痒呢。
幸运的是,树枝没有插中要害,父亲被抢救过来了。养伤那段时间,母亲大着肚子,花光了打工挣的所有积蓄,还找亲戚借了好些钱。等到父亲伤愈,我看着他的身影,总觉得他似乎矮了一些,腿不直挺,背也弯了。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外出,总是一个人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沉默不语。我放学后也会立刻回家给母亲帮忙,不再去山野间疯跑。
弟弟出生后,父亲松了口气,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又变得像原先那般开朗,不过多了几分沉稳。没多久,他同姨父到涪陵城区做水果生意,姨父负责进货管账,父亲负责开小货车吆喝。
离家前,父亲把摩托卖了,钱全给了母亲。他说,一个家就是这样,喜喜恼恼,哀哀怨怨,总有不顺的时候。一家人齐齐整整,比啥子都好。说完,他抬脚向落日的方向下山去。夕阳像一锅刚蒸好的糯米饭,热气腾腾。父亲弯曲的双腿在山路上架成一个圆拱形,黄昏的风往来穿梭,他却好像挎着一个暗沉沉的月亮在行走。
父亲的第二辆车是一辆白色轻卡。它身着素衣,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却是泥泞中摸爬滚打的高手。父亲和姨父铆足劲干了两年,总算攒了些钱,够把母亲和小弟接到城里了。我依然一个人在云山里晃荡,想读几页书就读几页,哪里有好玩的就蹭上去,没有小尾巴跟,也没有大老虎盯,自由自在,但寂寞无聊。
父母亲和弟弟不在身边,家里突然变得好安静,冬季更是漫长。天犹犹豫豫地亮,夜干干脆脆地黑。云山没有暖气,奶奶怕我着凉,总把我强制性按进被窝里。我哪里睡得着呢,总是趁奶奶打起呼噜后伸出手指头去戳床帐上的小洞,慢慢地,小洞被我戳成了大洞,土墙上的泥巴也抠出一个凹凼。看到凹凼越来越大,我才不抠了,因为再弄下去就要挨骂了。我只得在床帐上打了个结,无奈地翻身睡去。
后来,我翻来覆去的时候总听到床铺下沙沙作响,掀开被单一看,才知是奶奶铺了层厚厚的穰草。那草就是脱粒后的稻草,蓬松柔软,铺到床上一下子就比灶头里那些野茅草高贵多了。我喜欢闻穰草的味道,那是一种干爽的清香,是农人大汗淋漓地劳作后洗完澡躺下的踏实,是摩托车后座上闻到的父亲旧汗衫的草气。之后的每天夜里,我就趁奶奶不注意把被单撩起来,将脸贴到穰草上,大口嗅着那清香,就好像躺在一片金黄干脆的稻田上。穰草张开它长长的耳朵,听我讲了一夜又一夜的梦话。
寒冬腊月,我还不舍从梦里出来的时候,奶奶就把我拽出被窝,换上干净的衣服,说要迎接父母回来过年。但我哪能不去灶头猪圈攀爬呢?衣服不到半天就黢黑了。那天下午,父亲把他的白色轻卡开回来了,好多人来我家坝子围观。村子里开摩托的多,偶有两家挣钱买了长安车,没见人开过卡车回来哩。他们仨穿得鲜艳齐整,大方板正,一看就是温馨的一家人。再一看我,指甲盖里满是泥,鼻涕都在嘴角结痂了,还凑上去喊什么爸爸妈妈呢。
我瑟缩在奶奶身后,没有主动和父母亲打招呼。一年不见的小弟已经会走路了,他穿着能发出声响的小鞋,踮起脚尖,生怕踩到地上的鸡屎呢。彼时我已大了,不再像吃妹妹的醋般为难弟弟了,只觉得眼前这白白胖胖的小娃娃着实厉害,可爱得让每个人脸上都春光灿烂。父亲看到我的时候,先是愣了几秒,然后才让我走到他跟前。他抽出纸巾给我擦鼻涕,又去烧了一壶热水,一厘一厘地给我擦脸、擦手。许是水蒸气的缘故,我感觉父亲的眼睛湿漉漉的。
过完年那几天,父亲每天都在给人打电话,听着低声下气的,打听些读书求学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筹划把我也接到城里,去读完剩下的半年小学,然后再看能不能在城里找个好点的中学。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当时那个决心下得不容易。两个娃娃读书开销大,外面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团转人和云山小学的老师们都说玲玲妹崽精灵得很,不好生读书可惜了。
听到这,我心头的疑惑簇簇冒上来。我问父亲,我天天在云山天不管地不管长着,从没听人说我精灵,老师也未曾夸过我什么,啷个突然间就聪明了?他笑嘻嘻地说,我的女儿我晓得,就是精灵得很!还有就是,要读书,要好生攒劲,才能像城头娃娃一样,越来越精灵。
原来啊,天下父母都是魔术师,只要攒劲,就可以把娃娃变精灵哩。后来我还听到过另一个版本的缘由,是母亲告诉我的。她说:“那年景,你老汉其实心头没得底。把你也带到城头,一家人吃不起饭啷个办哟。但是他看到你满脸是锅灰,衣服黢黑,他心头就像被刀割了,剌一场哟。我们没啷个读过书,到城头,看到那些读了书的人过的啥子样的生活就想着你和弟弟不能落下。不管男娃还是女娃,都要带在身边,一碗水端平才亲热。静妹没得后,我们就只你一个丫头精了,哪能不心疼。”说起这些,母亲就要落下泪来。我才明白,父亲在我身上的好,是连带着妹妹那一份的。
又一次到城里时,我惊讶地发现,父母居然仍住在那个十平米的出租屋。屋子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而我的小床只是一块架空的废弃门板铺成的。我气鼓鼓地问他们啷个不换个地方,母亲说,找来找去还是这儿房租便宜,而且我读书的事还是房东老板给解决的。父亲说,走到哪点黑就到哪点歇,一家人齐齐整整的比啥子都重要。
但我并不喜欢那里。现在的我自然懂得,要是没有父亲当年咬牙把我带到城里,我估计会在某个山沟重复着老一辈的生活。在经济的重压下,那十平米的空间已是他们能给我的最温暖的世界了。但对于一个十来岁青春懵懂的女孩而言,从广阔的山野一下子被关到狭小空间,从简陋的乡村小学到琳琅满目的城市课堂,要怎么故作豁达呢?
有一次,我在学校好不容易交到一个放学顺路的朋友,她随我一起走到了排水沟的上方,正站在落满阳光的方孔处。我停下来告诉她,我到家了。她当时笑着抬手指了指台阶上面那栋单元楼问:“你家就在这上面吗?你住几楼呀?我家小区就在前面,你下次可以来我家玩,直接坐电梯到16楼哟!”那时,我不晓得啥子是电梯,只想告诉她,我们脚踩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家里仅有的阳光此刻正在被我们踩碎。
但我没说出实情。自尊在心底泛滥,我担忧内心小小的尊严微光一样被踩碎。我点了点头,和她说了再见。然后,我往转角的台阶走上去,爬进了那栋从未进过的高楼。仰望那栋楼的时候我看不到尽头,像是登上升入云端的天梯。在天梯上,我呆坐了很久,估摸着她已经走远了,才胆战心惊地跑回自己地下的家。如果生命是层叠的落叶,年复一年,季复一季,那最下面的一层,该是我藏匿的敏感,像蚊子叮咬后留下的小鼓包,让人总想去挠它。
等我上了初二,父亲终于带我们搬离地下室,到了个一室一厅的小楼房。他们仨住“一室”,我住“一厅”。因为当时姨父身体不好,打算去租一个门面休养着,父亲就决定自己单干,既管账又管货还要开车。
夏天的长途水果容易坏,父亲便在城内开着轻卡到人多的地方停车摆摊,母亲偶尔去帮帮忙。摆摊摆着,父亲就摆到了我的中学附近,因为那里住户多,生意更好做。我开始每天战战兢兢,和父亲打个照面就假装作业太多,连忙跑回家去了。后来,我索性躲在角落里装作没看见父亲,趁他忙碌时加速跑开。
直到有一天——“幺儿,来吃西瓜!”父亲的一声呼喊让我不得不停住脚步。白色货车上传出“来来来,西瓜西瓜,甜得很哟”的喇叭吆喝声,如同无数钢针刺破我的鼓膜,仿佛向全世界宣告:快来看看吧,这个人假装体面,其实她的父亲就是个开车摆摊卖水果的!父亲的热情烫红了我的脖颈和脸颊,被蚊子叮咬的小鼓包不断扩散,变成心里的千千结,怎么顺都捋不清。我的眼泪几乎是从眼眶里飙出来的。我气急败坏、面红耳赤地拒绝了父亲:“哎呀我不吃!你能不能莫来学校门口卖瓜了!”
父亲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他收起西瓜,继续摆摊,关闭了喇叭里他录的吆喝。那天之后,他就真的再没去过我学校门口。父亲一向是家庭关系中主动的一方,但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就这件事展开任何交流和讨论。就像他松开紧握铁秋千的手,默默看着我飞荡起来,又时刻准备着将我接住。但年轻的我那么自信,从不回头看他,相信自己不会轻易摔落。
后面的光阴忽地转动得快了。我气喘吁吁地跑向高中,莽莽撞进青春期的怀抱,心事都沉甸甸的,却又一无所获。父亲车里的世界早被我抛在背后了,他去做生意,他去跑车,都随他去吧,不要干扰我的一方天地就好。
岁月悠悠,奈何世事难测。一个冬夜,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卡车在积雪的山路上打滑,踩不住刹车,翻到崖沟去了。母亲焦急地问他有没有事,他声音颤抖着说,没得事,还是命大,抓着崖边的树杈爬出来了。我才意识到,那几年里,父亲都是一个人开车到山区卖水果,既要装货又要卸货,耳根子都爬满了冻疮。
当天,父亲一个人在高速紧急救援站待了一整晚。寒风击打着窗户,我梦到父亲的白色货车在蜿蜒山路上翻滚,无尽的深渊将他吞没。我伸出手去,想要接住他,但他就那么直勾勾地坠落下去,消失了。我没能接住他。
我从梦魇里惊醒,汗水浸湿衣襟。刚才的梦似乎还在眼前,我惊吓得蒙进被子大哭起来,夜色被我的哭声震得四分五裂。
但父亲总能重整旗鼓。白色轻卡宣布“退休”后,爱车的他意欲换一辆更大的货车,这是我和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事情。在他们的争吵声中,父亲的眉宇间蹙起了一座山峰,千斤重般压着他的眼。忽地,他就像个孩子哽咽住了:“幺妹哟,我不开车还能干啥子呢,我这辈子就只会开车啊。”母亲知道,在开车这件事上拗不过的,只得作罢。
父亲换了辆大红色解放牌卡车,成了专职的水果运输司机。母亲时常担心父亲在车上打瞌睡,便央求父亲让她同去,好相互有个照应。父亲总是一口回绝:“两个娃儿在屋头读书,你去了娃儿啷个办?”在父亲一口一个娃的挂念中,我跨过高考和十八岁的关口,就要坐着长长的绿皮火车离开山城。
父亲的车轮辗转于地理版图上,不知疲倦地行进着,在山河大地碾压出深深浅浅的轨迹。高考结束那一年,我主动提出想随父亲出省看看的愿望。父亲担心我身体吃不消,特地带我去了四川宜宾的富荣镇李子园,行车时间不超过十二个小时。那会儿,我还没离开过山城,第一次出省很是欣喜。父亲则像一名勤恳的导游,移步换景地向我介绍着哪边是乐山大佛,哪里又是金沙江。看得出来,在我配合的惊呼声中,父亲相当满足。坐在大红车高高的副座上,天空离我只有咫尺,夏日黄昏的流云聚集在头顶,红车一晕染就变成了火烧云。
到果园时已是亥时,四五十个戴着白手套穿着麻布衣的工人已经将百来吨李子分箱装好,只等父亲的车来运送回城。我才得知,这趟“旅程”,以及父亲之前所有的“旅程”,都是只“程”不“旅”的。天亮之前,他还得把水果运回去,开个通宵。
路转峰回,大红车呜呜然从高速上驶过。隔着车窗,我感觉山色越来越深,天和地似乎连到了一起,空空茫茫只这一点红。车厢里的空气更是阴冷逼人,脚下轻飘飘的,让我有些心悸。父亲打开车载音乐,都是快节奏的热闹DJ,歌到高潮他还会跟着唱,全然不顾大山和暗夜的吞吐舔舐。他呀,绝不让日子死气沉沉哩。
“幺儿,上大学要好生读书哟!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才不得像你老汉勒着熬更守夜。”父亲在音乐声里扯起嗓门跟我聊天。
“我老汉勒种啷个了嘛,有歌唱有果吃,多欢愉!”我晓得父亲又要开始抒情了,便提前打断了他。那会儿我觉得,是他自己要选择开车的,几次三番都要开,由不得人。那么,所有的“熬”,都得他一个人咬牙熬着。
后来的事情你我都知道了。父亲和大红车相伴了六年,风里来,雨里去。卡车的漆面光泽早已黯淡,父亲鬓角的白发也日益增多。他们共同经历了无数个日升月落,他是看着它沧桑的,而它亦是他的见证。它留存着父亲半生的脚印和指纹,见证着他的信心和恐惧,光荣和空寂。
最后大红车还是被拖走了。它太破败了,修不好了,父亲不得不放弃它。它替他挡下了最后一次风雨,一如父亲这些年对家里的竭力而为。他录下了大红车离开的视频,沉重地叹了口气,作最后的告别。风雨中,父亲一个人靠在残损的它身边,同这位并肩作战的老朋友说了许多话。
北风呼啸中,我走出门去,站到天桥上看车水马龙的北京。无论天晴落雨,路上总是有很多车。车周围是车,车里面是人,车和人周围是人和车,是无数的高楼和房间,房里是更多的人。如果有一辆车突然从人海里消失了,恐怕也激不起什么水花。但我想到父亲,攒了半辈子的劲,还没有一个踏实的房间,大多时候只能孤零零躲在一辆车里。人生四十载,父亲都以车谋生。对他来说,车仿佛是通往世界的一扇大门。只要车在,他就得一个人在路上。岂料,外面的路毕竟不好走,风声雨声鱼贯而入,他不得不一边颠簸屏息一边踩紧油门。
于是,那晚我梦见,一条长长的公路上,一辆又一辆车驶过去。旷野上,清风自在,阳光温暖。车队走得很慢,很慢。其中有一辆父亲的车,车内坐的,是我和年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