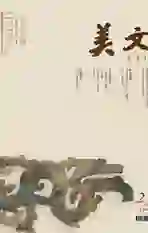云山寂静
2025-02-18周倩羽
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父亲肩扛锄头走在前边,母亲拎着一筐新摘的香椿,我和弟弟沾泥的手拤着两把野蒜,一齐朝家中老屋走去。
又一个清明,回云山村扫完墓,天上飘着点毛毛雨,大青山藏在雾霭中。弟弟喊着要打伞,父亲扭头道:“雨淋坟头钱,春苗出齐全。大雨不得停,好雨要多淋哟。”说完,他微笑着望了望远处,又将目光收回,落到母亲身上。
拢屋后,父母进灶房做饭,我接过弟弟手里的野蒜。他就坐在石门槛上耍,两腿优哉游哉摆动着。待我从灶房出来,他突然兴冲冲地对我说:“姐姐,勒个(方言,那个)桃子是不是你画的,教哈(方言,下)我嘛!”
见我一脸疑惑,他趴下身子,伸手指着门槛内壁说:“你看,勒个门槛上有个桃子!”
内壁背光,门槛才到我小腿高,我站着只看见一片黑。弟弟拉我蹲下,眼前果真出现了桃子的轮廓:一个倒立的爱心。
我惊奇小弟的观察力,打开手机电筒细看起来。这是一个信笔涂鸦的红桃,底下还带有两片绿叶子。整体画得比较粗糙,线条有些凌乱,在年深岁久的土灰色石壁上显得更为稚嫩。
弟弟问我桃子是谁画的,我十分确定地告诉他:是你二姐画哩。他反倒很惊奇地说:“是静静姐姐呀!妈妈给我说,静姐姐是她最乖的女儿,原来静姐姐也喜欢画画呀。”
我知道小弟的话是童言无忌,自己也长大了许多,不再为这样的话伤心。但再次看到那火红的桃子,我还是心头一颤,不敢多看。逝去的时光便去了,未曾想过竟留下了刺眼的证物。于是,我跨出门槛朝屋后走去,走到原来桃树生长的地方。
以前,老屋后有方小池塘,池塘边有棵桃树,我们都亲切地叫它桃花池。现在,我站在没有水也没有桃树的池塘边,看到里面堆满了土灰砾石,簇簇野草从石缝里往外冒。
这方小池塘,曾经是爷爷专门挖来供耕地的黄牛喝水打滚儿的。六岁那年,爷爷把牛卖了,池子的水就变得静悠悠的,越发清亮。水边的桃树长得结实,我和小两岁的妹妹喜欢去树下玩。
我的小名叫玲玲,妹妹的小名叫静静。母亲说,我出生那天哭了一整晚,铃铛一样吵得她没睡好觉。但妹妹出来的时候,静悄悄哩,不哭不闹,比我好养活。
我爱疯玩她爱画画,我吃麻辣她喜清淡,我爱扯谎她太老实。我俩基本耍不到一块儿去。她比我听话,大人们都更喜欢她。唯独相同的是,我们都喜欢吃桃子,一到热天就好趴在池塘边巴望着桃子长出来。
当树上的果子从绿油油的青变成毛茸茸的粉,沉甸甸地压在枝头,也压在我和妹妹垂涎已久的心头。但桃子基本都悬在我们碰不到的池中央,推谷子的刮板也够不着,我俩就捣鼓着怎么把桃子弄下来。
往事一幕半景,交叠错杂,和眼前的杂草一样乱,我理不清。桃花池水若还在,现在顶多只能打湿我的大腿。但当年小小的我们,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深的地方。十多年过去后,当我再度站在这里,它已经是云山村最浅最浅的所在了,浅到没有人记起它曾经装满了水,结满了桃儿。
无感,似乎是所有人的感受。哪怕因为小弟的一句话我来到这里,也不是为了缅怀什么,而是因为骨子里的强势和占有欲再一次被刺痛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改变得很彻底了,到头来发现,很多事根本没那么轻易放弃。
“你主动点嘛。”在外求学的岁月里,这是身边人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但小时候每次挨骂,家人都会说:“你莫占强很了。”
那时候,为了摘到树上的桃子,我会主动脱了鞋爬上树杈,让妹妹回坝子边去拿竹竿来。哪怕坑坑洼洼的树皮硌得屁股疼,水面的飞虫和树上的蚊子盯得我胳膊腿上满是鼓包,我都不怕,但最后妹妹却叫来了爷爷。爷爷一边抱着她,一边凶神恶煞地呵斥我:你个死龟女儿,爬楞个高拽个阔转落到水头去淹死你,马上给老子滚下来!我不信邪地回嘴:这点水算啥子哟,还不够给我洗脚呢。妹妹却眨巴眨巴着那双无辜的大眼睛,跟我说爷爷是来帮我们摘桃子哩,还提醒我好生下树注意安全。她那种天真无邪的笑意,我是永远学不来的。
下了树,我穿上那双引以为傲、独一无二的水晶凉鞋,却看到妹妹的脚上也有了一双迷你版。当时的我很气愤,鞋子是母亲给我一年级期末考了双百分的奖励,她连学堂都没进过,居然轻而易举地也得到了奖励。其实后来我问过母亲那双鞋怎么回事,她只说,看我穿着好看,没多想就给妹妹买了,她以为我不会在意,便没跟我多说。
大人哪里知道小孩的心思呢。那天,我盯着眼前比我矮一个头的妹妹,趁爷爷不注意,狠狠地踩了一下她鞋边的那朵花,把花芯都踩黑了。但她并没有生气,两颊提拉起来,仍然笑盈盈的。事实是,她越是懂事地微笑,不争不抢,我就越是生气。当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嫉妒,只想要霸占独一份的好,总觉得她是我完整世界里的入侵者。
爷爷骂骂咧咧地给我们摘了很多桃子,当然,全都是在骂我做事冒失。到家后,他挑了个最大的桃子一切两半,让我们自己拿。我老想着要大的,辨认半天也看不出哪块更大,就随便拿了一块,坐到堂屋的凳子上开始啃。妹妹穿着那双晃眼的凉鞋从跟前走过,拿着剩下的桃子爬到了门槛上。
她从小就喜欢爬门槛,那块比她腿还高的石头被她磨得光滑冰凉。妹妹和小弟一样,是岔着双腿坐的,一条腿在门内,一条腿在门外,背靠着画满彩色星星的木门。我只记得,当时她门内的那条腿在黑暗里来回晃动,鞋上的花也复活了,飘来飘去闪着光,直刺我的眼。再一看,她手上那半个桃子还滴着清水,感觉比我的大得多。我甚至疑猜是爷爷给她换了更大的。愤怒达到极点,我起身走上前去,二话没说就把她手上的桃子夺掉,还说着“我不准你吃”,接着就放进自己嘴里大啃了一口。妹妹着急了——她终于急了——立马抓住我的手准备抢回桃子。看着她无助的样子,我有些兴奋。后来的拉扯过程中,她的另一条腿来不及翻动,被我一拽就从门槛上重重地摔了下来。
她的一颗门牙磕到门槛缺了大半,嘴皮被石边划烂了,向外翻展着流了很多血,清口水混着鲜血不断从牙床里渗出。用于擦拭的白色棉絮一次次被血水浸染成红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血,第一次听到妹妹歇斯底里的哭声。没有人知道,六岁的我心里其实有一股报复后的快感。
如今我不那么喜欢吃桃了,觉得扎手、麻烦,还硌牙,但小时候就是觉得好吃,看着她哭,嘴里的桃子更好吃。本以为她会好几天不理我,但妹妹仍没有记仇,只是安静地跟在我身后。我去小伙伴家玩,她都跟着,我们笑,她也一起笑。跟在我身后的时候,她始终像颗沉默的种子,默默地笑,默默地走路,默默地吃饭,哪怕玩捉迷藏、踢毽子、过家家,她也是默默的,让我感受不到她的存在,也习惯了她的静默。
面对眼前的荒芜,我突然意识到,大家很久没有称其为桃花池了,都只说那是后檐沟。一条下雨天会积水发臭的水沟罢了,谁还记得里面游弋的小鱼呢。
六岁的夏天,我和妹妹路过桃花池,发现池塘里长出了几条小鱼。野生的鱼儿像手指头大小,在阳光照耀下活灵活现地游动着,池底晃着鱼儿和云朵的影子。我们便趴在桃树边的石头上,呆呆地看着这些新奇的小玩意儿。
水面上倒映着两个女孩脑袋的轮廓,那是两颗留着一样的短发和狗啃刘海的脑袋。两人的发丝在风里飘扬到一起,不过我的更长,她的短些,头发比我们先一步牵了手。在凝望中我发现,靠近石头的池壁边有两个洞,洞里不停地有鱼儿游进又游出。我给妹妹说,这些鱼就是从这两个洞里长出来哩!她抬起亮亮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脸上沾了灰,傻乎乎地问我,真哩呀?姐姐,你啷个晓得呀。我迫不及待地想向她证明姐姐的不可置疑,便站起来挪到离桃花池更近的篱笆边,双腿跪地,一手抓住近水的石头,另一只手往水中的洞口伸。
然而,那洞口远比肉眼看到的要深,我使劲向下掏,身子也往下压。突然之间,我重心再难平稳,一个扑楞反身摔进水里。落水后我才发现,桃花池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浅,再加上是脑袋先扎入水中,我根本无法感知到岸在何方,只觉得水底有千万个黑洞在将我吸进去,面目狰狞的水怪在咬我的脚。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水呛死的时候,忽地被一只手拽了起来。原来,是妹妹跑回家叫来了爷爷,我才捡回一条命。
从水里出来后,爷爷奶奶严厉地训斥了我,不允许我俩再去池边玩水,还在桃花池上用柴禾与树干铺了一层,水底的鱼儿也不知去向。我知道被水吞没的滋味不好受,不再喜欢去桃花池,但在爷爷奶奶的斥骂中,我也没有因此而对妹妹心怀感激。之后,每次路过桃花池,我的心都拴着一根麻绳,总是拧紧的。
热天过后,我就自顾自地和小伙伴去上学了。妹妹因为在冬天出生,还没能读上学前班。我不断地在外面结交新朋友,她永远都在老屋里、在田坎上,浸泡在我的旧教材和画本里。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远远地就发现她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笔在门上画着。她穿着一身天蓝色的长裙,裙子长得都快要拖到地面。但她用手拉着裙摆,生怕沾到一点灰。那是我不要的旧裙子,因为长胖了穿不下,但她穿着很合身,甚至更好看。不过,妹妹依旧留着小男孩般及耳的短发,我的头发已经蓄长了。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有点期待她上学后留长发的样子,想象着她的未来。
我走近门槛,看见她拇指的指甲盖里都是铅笔的灰。妹妹的手小而多肉,铅笔在她手上就像是一棵浑圆的树站在软糯的土里。木门上,她画的是我们一家人的简笔画。画面里的太阳公公有笑脸,绿色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形状的鲜花,火柴样的爷爷奶奶在地里干活,父母牵着我和她在草地上放风筝。除此之外,天边蝴蝶状的风筝旁还有一棵树,树上结着爱心形的桃子,树下的波浪线里有几条小鱼和数不清的星星。
看到画,我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我对她说:你也太傻了吧,竟然将桃花池和鱼儿画在了天上,让星星落到了水中。
在画面的空白处,她歪歪扭扭地写上了几个大字,分别是“天”“地”“人”。“天”字有云朵一样的小尾巴,“地”字的竖弯钩是圆圆的,如同被水草包围的桃花池,而“人”字的一撇落笔很高,像倒立着的桃树枝桠,在“天”“地”之下向上生长。我诧异地问她识不识得那几个字。妹妹转过头来,歪着她的小脑袋朝我笑了笑,说她不认得,只是抄了我本子上第一页的作业。
我长吁了一口气,骄傲地进了屋,心里暗自庆幸,还好她不认识,不然爷爷奶奶又得夸她了。在我小小的世界里,得到她没有的东西,是最满足的一种奖励。妹妹继续兴致勃勃地举着彩笔,我却偷偷把我的书画本子都藏了起来,不想让她学。她依旧在墙上门上桌子腿上瞎写瞎画,净是些四不像,我也懒得去搭理,觉得她是闲得慌。
后来我才懂得,她的那份闲,其实是怎样一种寂寞。
那年冬天,在外打工的父亲母亲照例回家过年。许是太久未见,我见着他们的第一眼怯怯地不敢靠近,只是低着头踢脚下的碎石子。但妹妹就不一样了,她一下子冲到爸妈面前,声音像奶糖一样黏在他们身上。父亲迅速将她抱起来,她开心得甚至亲吻了父亲的脸颊。
父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边感叹幺女黏人,一边捏了捏妹妹的鼻子,之后才注意到我。他让我帮妈妈提一下东西,说完又空出另一只手来牵我。
父亲的手掌很大,拇指上的茧厚厚的,硌得我的手心痒痒的。回忆起来,我自相矛盾的性格其实从那时候就有了。虽然我多么希望被父亲抱在怀里的人是我,但牵着父亲的手,我又觉得不习惯,想挣脱。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看来,只有妹妹才算是保暖贴身的那一件。
除夕夜,一大家子围坐起来架着炉子吃火锅,我和妹妹随便吃了两口就忙着把玩爸妈买的各式各样的烟花。父亲和爷爷轮流给我俩点火,我们站在坝子边的石板上,举起冲天炮对着面前的水田比赛,比谁的烟花冲得更远,看火药绽放在水面映照出无数炸裂的星光。妹妹若比我远一些,她就会笑着欢呼,我又哼哼不服气地将烟花举得更高。大人们哇哇啦啦地看了会儿姐妹俩的比拼,就热乎着打起了夜麻将。
凌晨十二点,父亲准时点燃了桶装的烟花,我和妹妹屏住呼吸,等待着火焰从纸筒里冲入云霄的时刻。一阵簌簌的引线燃烧声后,烟火表演正式开始。妹妹不知何时拉住了我的手,在焰火下蹦着跳着,发出一声声快活的惊叹。她的手心温热,如同在灶火里焖烤红薯,待到火焰熄灭后,余下的炭火冒着星点,四周的冷空气都被烤熟了,变得暖烘烘的。那是我印象中妹妹的身体最暖和的时刻。或许有更暖和的时候,只是我没有贴近过。
到了年初三,姑姑一家回来看望爷爷奶奶。爷爷一大早就把桃花池上的干柴抱进了灶房,说是把火烧旺好炖肉。十来岁的洪明表哥最喜欢逗我们,特地把家里的四五个小孩子召集到一起,举起一个金闪闪的红包,和我们玩猜手指游戏,谁猜对的次数多谁就能得到红包。那会儿,云山村里没有商店,我们不在乎红包里的钱,只在乎那上边闪耀的金粉。
连猜了好几轮,强烈好胜心的驱使下,我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猜中的。表哥挑逗着举起红包问谁想要时,我跳起来大声高呼,恨不得跳到房顶上。而那时候,只有妹妹没吭声。表哥注意到了安静的她,问她怎么不说自己也想要,她说,自己游戏输了不能要。但我看到她分明抿了抿嘴唇,抬眼看了看那个红包,就是想要,还装作不要。
然而,表哥把红包送给了妹妹,还教育我们要学会谦让。我自然是气不过,但是又不敢挑战表哥的威严,狠狠地瞪了一眼妹妹,忿忿地跑开了。
想要的东西我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呢?我时常思考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些人事后才明白,欲望像一棵洋葱,显露得太旺盛是会把人熏走的。这样看来,小小的妹妹竟然有点大智若愚的度量。
我怀着一肚子气来到灶房,看奶奶和姑姑在灌香肠。肉泥里的辣椒和八角在空中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我很快就看得入了迷。不一会儿,妹妹也循着香气进来了,嘟囔着要去找爸爸妈妈。
爸妈在屋后杜姨婆家打麻将,奶奶让我带妹妹去找他们。但她衣兜里的那抹金色在我的余光中挥之不去,又想到她被父亲抱起来脸贴脸的场景,我断然拒绝了。
一阵风吹过,桃花池边的石头有些冰凉,我晃了晃神,看到脚踝上爬着两只蚂蚁。前边那只蚂蚁爬得快,后面那只慢。前面的既然不愿意等,后面的又追不上,何必一直追着呢。我想着,随之跺了跺脚,两只蚂蚁都摔了下去。
那天,我拒绝妹妹之后,她第一次对我有了逆反的举动,自己去找爸妈了。以前我曾想,生性乖顺,真的好么?后来我总想,乖顺的人逆反一次,代价如此深重么?
那天上午,她和爸妈都迟迟没有回来,奶奶就催我去看看。我极不情愿地将手擦干,换上棉鞋,啃着一截刚煮好的香肠出了门。正月的空气依然冰冷,太阳没有出来,土地上结着一层厚厚的霜,齿钉棉鞋踩在上面都滑滑的。
从屋门口到杜姨婆家必须路过桃花池。池边的凹凼里都是水凝的冰霜,桃树只剩个光秃秃的脑袋,树枝裸露着,树边百草枯黄。
那天,我挪着步子从池边走过,看到遮盖水面的圆木已被搬走一大半,剩下稀松的缝隙间填满了红。那是一抹盖着薄冰的红,像桃花池的一张红面纱,遮住了池水的喧嚣,只留下寂静与深邃。
那会儿,我对死亡还没有概念,一直在想冬天的水面怎么会是红色的,甚至以为是秋天落到水中的桃红花瓣。我又仔细地瞧了瞧,发现是一件大红色的衣服漂浮在池面,下边一双蓝色的棉拖鞋倒转着。
是妹妹的衣服。我的第一反应是,衣服在水里,那她人呢?
我又蹲在池边,定睛一看,看到了一只白色的手背和五根展开的手指,旁边还有一个散着金粉的红包。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人落水后会漂到水面上,还天真地以为妹妹在故意和我玩捉迷藏,我还想趁她不注意,把水里的红包捡起来。
没有回应,她始终沉默着。我看不到她朝下的脸,只见着黑色的头发笼罩在一圈若隐若现的脖子上,池水从弯钩样的耳朵里漫进又滑出。
那一秒,我才知道,妹妹落水了,不是在和我玩捉迷藏。我愣在了原地。
这时候,同村的李二叔刚好路过,他见状,大喊了几声父亲的名字。李二叔的声音大得几乎要掀翻屋顶、震碎云山,我被他的喊叫吓到了。父亲闻声而来,从屋后的斜坡跑下,一个踉跄滚到了桃花池边。他伸出大手一把将妹妹从池子里抓起来,深呼一口气,跪在地上用力按压她的胸腹。
我这才看到黑色头发缠绕下妹妹那张苍白的脸。她的嘴唇发紫,嘴巴是张开的,仿佛要大喊什么。她的眼球被水泡得鼓鼓的,眼皮半闭着,像鱼的肚皮露出一小半白色,长长的睫毛粘在眼睑上。妹妹全身湿漉,棉服里都是厚厚的积水。父亲按压的时候,有池水不停从妹妹的嘴巴、耳朵、鼻子里冒出,但她始终没有再睁开眼睛。
父亲把妹妹抱进屋里,我还想去把水里的红包拾起来,但那里很快就又被大人用圆木堵死了。接着,云山村的人都来到了家里帮忙。新年是一趟辞旧迎新的列车,大家本应是喜气洋洋的乘客,一下子全都变得垂头丧气了。
母亲知道事情原委后,对我骂了一句:死龟女儿,你啷个楞个占强。我记得她看向我的时候,眼睛射出冷冽的光芒,让人无法直视。母亲在狭窄的卧房巷道里躺着,翻来覆去哭了两天,衣裳裤子都磨破了,还裹着地上发臭的鸡屎和米糠。别人都去拉她,我不过去,怕看到她冰冷的眼睛。母亲的哭声一开始很大,后来就只是瞪着眼低声啜泣,任由泪水从破水龙头般的眼眶里流出。父亲则一边招待客人,一边往自己脸上扇巴掌,然后整宿地坐在光滑的门槛上,守着屋檐下那具小棺材。父亲和妹妹一样喜欢两腿岔开坐,头倚靠着门,只是不时地将自己的后脑勺用力砸向门板,在冬夜里发出轰隆的响声。奶奶每次听到这个声音,都会捂住我的耳朵抱紧我。奶奶也在被窝里全身颤抖着哭,只是没有哭出声来。
那具棺材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棺材。村里的老木匠将柏树制成的厚木板砍成五块,三长两短,再长对长、短对短地用榔头钉子固定住。青黄的棺木上,松柏纵切面的年轮留下淡淡的纹路,松散又凌乱,用手一摸会沾上粉末般的木屑,是棵新木。
下葬之前,母亲终于从地上爬起来。她跑到桃花池边,把那株桃树仅剩的几根枯枝撇下来,在妹妹的棺材前狠狠拍打了两下,嘴里念着“死龟女儿,让你不听话,让你不听话”,又把桃枝扔进了棺材。
至此,棺盖合上。妹妹被特意葬在了田野对面一个隐蔽的山谷土堆里,任谁都不能一眼看见。没过几天,爷爷把桃树砍了,又一个人默默地抄起扁担,来回挑了三四天泥巴,将桃花池填平了,还把门板上的画刷上了油漆。我和爷爷一起刷油漆,尽管有点不习惯,但心里想的是,挺好的,她的痕迹终于要全部没得了。后来老家修了路,人们可以从水泥路直接通往大公路,不再从桃花池边走过。
而现在,想起年幼的自己,我仍觉羞愧。火红火红的桃子,在日起月落春风秋雨之后,还紧紧抓着旧日的门槛,抓着我想要忘却的记忆。桃花池边的风轻轻地吹过,似乎生了一只手,正抚摸我沁凉的脸,抚摸我的傲慢,抚摸我的自私。
我耐不住这份寒凉,站起身准备回屋。我的脚踩在池子的泥土里,差点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用鞋撇开杂草,我看到一个发霉潮湿的圆木切面,侧边新长出一个坚硬的枝干,绿色的叶子悬挂着,像桃树叶。它们轻轻舒展,探出小小的身躯,仿佛带着一种对世界的好奇与期待,叶片上的露水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我蹲下身子,发现被我甩开的两只蚂蚁钻进了圆木的洞里。它们一个触须长些,一个骨节圆些,但始终共处于一个树洞里,经受同样的风霜,路过同样的石子,形成一段共同的小小岁月。
回到屋里,母亲正带着小弟在门槛上玩。她问我:“玲玲,你去后檐沟干啥子?”
“哪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地问。
母亲嗓音突变,有点哽咽地说:“桃花池。”
“哦,没啥子。”我强装镇定。我没有告诉她,下次路过后檐沟,会立着一棵新的桃树。可以确定的是,后来母亲再也没用那种眼神瞪过我,我也没把她那个无意识的眼神放在心上,只是自己收敛了团转的刺头,将尖利一方扎向了自己。
进屋后,我爬上二楼阳台,望向田野尽头被草木掩映的那方小坟地。早晨,父亲带我们去那里烧了些纸钱,除了弟弟稚气的叫嚷,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说话。斜风包裹细雨,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一位亭亭的姑娘立在田埂上,拿着画笔笑着向我招手。她穿着一袭皎洁的长裙,柔顺的长发扎成两束乌黑发亮的辫子,头上戴着粉色花环,双眸盛满闪亮的春水,纤细的睫毛在风中轻扇。
但她始终不说话。这个女孩有点太静,静得有点像山。一边是风声、雨燕、绿色秧田和起伏的云雾,另一边,仅仅是她。她与云山并肩。她就静静地守在那里,让我一直以来飘着的心忽然找到了定点落锚。十来年未见了,她不但长大了,而且长高了那么多,头发变长了,更漂亮了。我不敢认她,她,还认得我么?
我知道自己又在幻想,回过神来,云山依然寂静地矗立。白雾缭绕,雨水飘飞,在我眼前闪闪逝去的,是水光还是时光?山色在雾里还是在梦里?四十五度角的山脊斜斜垂落,好似放了一道时光之梯下来,迎我上去。此后,我将一级一级地攀爬,走出云山,走到更高更开阔的地方。一切都是未知数,只有最深最深的桃花池,永远为我准备着。它为我准备了多少果实,云山就为我准备了多少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