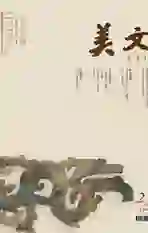杨桃公园四时观鸟小记
2025-02-18赵艳华
1月22日:今天的不急之务
今天上午读《古文观止》,有些篇章甚有趣,略记之。
《臧僖伯谏观鱼》篇中,鲁隐公想去“棠”这个地方看人捕鱼(书中曰“观鱼”,这两个字让我想起了“观鸟”,不禁一笑),臧僖伯反对鲁隐公此举,理由是“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臧僖伯又讲到鸟兽用处不大,国君不应该将宝贵的时间浪费于此,这些屑小之务如“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是“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读到此,不仅有点赧然,觉得自己沉溺观鸟,不务正业,也有似于此。但鱼、鸟中乐趣,又岂是忧心忡忡的臧僖伯所能了解的?臧僖伯一生中,想必不曾浪费时间沉溺于“不急之务”,但鲁隐公一定有过此种经历,他一定知道“沉溺”的个中趣味。所以尽管臧僖伯讲了一箩筐的人君之道,鲁隐公的“恶趣味”最终还是战胜了人君的责任感——他找了个堂皇的“略地”的理由,去棠地“陈鱼而观之”,哈哈。
下午,去瓦壶岗公园一小时。
这个小公园有两座小山,山上多高树,游人少去,想来会有一些鸟吧。这么想着,就赶紧收拾东西,出门去也。
山把中山大道的车流关在了外面。一入山,外面的世界仿佛装了消音器,全变成了远远的微微的背景音。满山的人加起来也不超过10个,真是又清静又荒芜。
山上高树那么多,树荫又浓密,来来回回只听到小鸟叫,却很难看到鸟影。我4点到山里,5点钟山就阴了下来。散步的人一个一个下山去,默默地,一点声音也没有。山上原本就有抗日时期的碉堡残迹,现在,更森森然。我虽然心里微微有些怯意,但仍不舍得走,强撑着在山路上走走停停,期望有那么一点斩获。
在半山的亭子旁,有人在练很奇怪的功,一遍一遍大喘着绕着亭子游走。有咕咕哝哝的细碎叫声,就在亭子旁边的小叶榕上。我瞪大眼睛看了良久,才看到一树的小东西在叶子间蹦跳。瞄准了一个,认真看时,它却又跳走了。在望远镜里,只看到它并不长的尾巴,和腰间的一抹白斑。我跟这些莺们纠缠良久,眼酸之极。
微微失望着,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有高亢婉转的优美鸟声传来,听声音,鸟应该就在不高的树上。
我想:这野山中莫非也有乌鸫?寻了半晌,只看到白头鹎一只,那大嗓门的歌唱家也静默下来,但却没有扑棱翅膀,呀地一声飞走。它是聪明的,拿沉默当了最好的隐身衣。我转身想走,眼睛的余光却看到一人高的树杈上,就在我鼻尖前,有大鸟一只,望时——哇,一只硕大的画眉!它白色的眼圈清晰如画,也正定定地看我。
对视片刻,它不飞,却一跳,跳到略高的树枝上;再一跳,跳到树叶后;再三走两走,它就不见了。
林子暗下来,天却仍旧明亮。我等待良久,只好下山。走了不远,就听到它在半山放开喉咙大叫,一时满山都是它。一山无人,高树寂寂,相思树阴阴凉凉的气息满山,如此高亢悠扬婉转乃至热情得要燃烧的声音,如烟花般满山迸溅。
我一个月前才初识画眉,直到今天,听到空山里的画眉鸣声,才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在山林中”,对一只画眉鸟是多么重要。这山林要足够大,足够野,足够空,足够自由,才容得下也散得了如此高分贝的美声。
又转一个坡,一只褐色的鸟突然从草丛中窜出,急速跃过石子小路,又隐身在草丛里。这是另一只画眉。
我驻足细听,山上的画眉鸣叫已经变成了二重唱。显然,这座山里有一个画眉的族群。
华师苗圃中也有画眉鸟,它们被人捉了,养在笼子里,青布蒙着。某个时刻,它们也叫——一只叫,两只叫,乃至几只蒙着眼睛一起大叫,小小的苗圃里只听到它们不由分说的大嗓门,几近于聒噪——对比这瓦壶岗中的同类,它们着实可怜之极。
这小小的瓦壶岗,在游人散去的空寂傍晚,该有多热闹!这小小的山林,其树上树下,每一片树叶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秘密,我不得而知,也无法想象。
这座山,一直就在我家附近,我也一直以为它是一座小小的荒山。现在,我终于认识到,它内中的丘壑,大得很呐。
5月30日:端午节,春色无边
我的观鸟记录,是从端午节开始的。现在回看,觉得也是必然:端午节,既是春天盛极之时,万物生机勃发,也是鸟儿繁衍盛季。在这个节日前后,确实最容易“感受”到鸟儿的存在。
端午节早晨,七点钟。杨桃公园。
太阳已经很热,跑步的人很多。胖的瘦的男的女的,气喘吁吁地掠过你。荔枝树上,碧莹莹的荔枝,红了脸的荔枝,累累垂垂,一树都是。头顶上都是鸟鸣,仿佛一树林子都是鸟。有人在很大力地拍手掌,那么长的时间,只有一个节奏,亏他的手受得了。
昨天听到一种鸟叫,其鸣如蛙,声震四野。我长久地蹲守,端着望远镜瞄来瞄去,却不能在浓密的树荫中找到它。旁边的老伯经过,给我指点:“那里,那里!在那里啊!它的脚很长,这边叫过之后就走到那边去了!这是我们说的田公鸡啦!”我看他描绘得如此真实,自己却连片鸟毛都看不到,不禁恨恨。录音之后,惆怅而回。问于通家,曰:白胸苦恶鸟。正因为鸣叫声是“kue——kue——kue”,所以才有此名。这厮生长在水边,这是在求偶呢。
于是今早再来。
明显今早又来晚了。细细碎碎的,婉转的,柔媚的,短促的,各种鸟声,上上下下,飘飘忽忽,仿佛到处都是,然而我认真看时,却只看到几只暗绿绣眼鸟调皮的影子。端起望远镜,兜了半天,还没有锁定呢,那厮又“忒儿——”,一翘屁股,飞啦。
没关系,菜鸟遭遇历来如此,更何况还是一个自娱自乐才观鸟第二天的菜鸟。我不急。我今天一点都不急。
我钻进杨桃公园的大杨桃树下,一棵一棵,一直钻到最深处去。大树。水沟。遮天蔽日的大树枝子。人声渐稀,树荫清凉。猫着腰认真听鸟叫的我,突然看到水沟里有个大东西一掠而过,搅得满池老水风起云涌,各种潜藏的活物都吃了一惊,稀里哗啦乱动一气,一条小水沟仿佛刮起了龙卷风。
难道这浅浅的水中也有大事情搞?
水定了,不过几条小毛鱼,两只老螺,优哉游哉,岁月千年静好。
那些被惊扰的野物一眨眼间,都缩回去了。
我惊魂未定,心中明白:就是这小小浅水,也绝不能小觑。
一路搜寻无果。
我总是不能窥得真身。有黄鹂在鸣叫,有布谷鸟在鸣叫,有发条一样的鸟叫,有饱腹之后满意的喉音,有一唱一和的惬意,我却只能听音,急煞人也。偶尔在树荫间有暗灰或黑色的身影闪过,再找时,就芳踪渺渺,再无可得。
最终,兜兜转转,到得荷花池来。池中,新荷冉冉,一朵一朵开得正美。绕着荷花池,种了一圈水蒲桃树,树下,红色的蒲桃果子落了一地。有人在池边看花,有人在树下练功,有蝴蝶在荷池中间翩然而过。
突然,对面的水蒲桃树顶上,飞来了一只鸟。就在高高的树顶上!
我赶紧举起望远镜。因为太激动,手还有点抖。
那是一只白头鹎。它又愉快又警惕,站在全公园的制高点,志得意满地俯视高高低低的树。站了片刻,它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愉快地叫了一声,突然发现了什么,于是拍拍翅膀,一下子投进附近的树丛中,不见了。它的身后,另外一只白头鹎也跟着投了进去。
投,鸟儿真的是“投”林啊,那种敏捷,那种无所畏惧,非“投”字不能名状,古人诚不我欺。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将自己的目光长久地投向天空,投向高高的树尖,投向树尖的一只陌生傲娇的鸟儿。
这个领域在我的世界里,又获得了新的意义。
一只翠鸟掠过,停在旁边的小河边上,我追逐着它,将自己隐身在铁栅栏后面,窥向那片平凡的水域。
翠鸟一瞬间不见了。
可是水面上却飞来了一只长腿白胸的中等鸟儿,白胸,黄腿,黑褐色的背羽——这正是我要等的白胸苦恶鸟!
它淡淡然地飞到水边那一丛三角梅上,小小试了下音,kue——kue,就静了下来。然后,它高高地站着,快速移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向里走,向上走,再向里走。它的腿果然是好长啊!在三角梅丛中如履平地。
我先是裸眼看,后来才想起来调望远镜。等望远镜调好,那只鸟果然就不见了,镜头里只有一树红艳艳的三角梅。
我放下来,静静等着。
河水无声。红花寂寂。几片叶子和花静静地从高处飘下,落到河里。我盯着那簌簌的落花,心中若有所动,觉得安宁平和,又隐隐然似乎有大惊喜。一秒钟之后,我突然清醒过来——这一定是那苦恶鸟踩踏摇落下的花叶!果然,循着那花叶,我又看到了它!它已经走到三角梅的最高端,并且显然已经找到了一个它很满意的藏身地,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它热烈的、不顾一切的大叫:kue——kue——kue!kue——kue——kue!叫到情浓处,还要来几句绚丽的花腔。即使我不是一只母苦恶鸟,我也能感觉到这鸣声中超越一切的热忱,对爱情的无比的渴望,以及必须要到达对岸的决心。一只鸟儿无穷的决心、勇气,以及生命力,都包含在这叫声中了。
我听了很久很久。
我想,如果周围有母鸟的话,它一定会循声而来,看看这执着的王子到底长什么样。
很久很久之后,在三角梅下面,真的飞来了另一只苦恶鸟!它扇动翅膀,立定,隐身。我大为惊讶,心想,这可真是童话世界了——上面那只鸟,该作何打算?它心中该有多狂喜?
哪知道,调一下望远镜的工夫,就听得苦恶鸟们一阵大叫,这是什么信息?不可遏制的动情的大喊?
等我抬起头,却看到一只翩然而去。是第一只,还是第二只?为什么走?是一地不容二鸟,还是互相看不上眼?
只有它们自己知道。
苦恶鸟走了,却又看到一只翠鸟,在三角梅下晒太阳,弄翅膀,左弄右弄,搔首弄姿,做尽姿态。我尽情欣赏,却不知道这鸟为什么不走,不去捉鱼,却只在这里梳妆。等再看去,却又在这只翠鸟背后,看到另一只翠鸟,没有这只颜色美,只静静地立在这只背后,不“说”也不动,只看。
哎,我明白了。
最后,拍一张荷花图,题字曰“新荷袅袅,春色无边”——虽是初夏,我却看到花在开,蝶在飞,蛤蟆在抱对——这不是无边春色又是什么呢?
8月15日,观鸟盘点:白胸苦恶鸟、黄眉姬鹟和白眉姬鹟
今天想对自己的观鸟过程做个盘点。
我的观鸟,有一些里程碑般的记录。
这个历程,首先以白胸苦恶鸟始。每到春天,杨桃公园里总有奇怪的叫声传出来。这声音近在咫尺,却总让你看不到发声者是谁。越看不到我就越好奇,越好奇却越看不到,那声音也越大得疯狂,一个杨桃园子都是它。我被撩拨得如痴如醉,几经追寻,在一棵荔枝树上,我终于看清楚了那只终日发出“阔——阔——阔”声的大鸟:它长颈,白胸,红褐色的尾部总在一点一点,整个形象与我从小认识的那些鸟极不一样。更有趣的是,这厮一边引颈充满渴求地“阔——阔——阔”大叫,想吸引同类;一边却又轻捷地踏枝而上,尽量想把自己藏得严实些,再严实些,以躲开我的目光。总之,它既狡黠,却又按捺不住自己大肆鸣叫。我兴致勃勃地看着,解开谜底的快乐充溢了整个身心。
白胸苦恶鸟是一个代表,一扇门。它代表着的,是广州本地容易看到的留鸟;由它而打开的,则是鸟类世界生机勃勃的大门。从白胸苦恶鸟始,我一发不可收拾,一只接一只,渐渐认识了乌鸫、鹊鸲、白头鹎、红耳鹎、长尾缝叶莺、暗绿绣眼鸟等“菜鸟”们。
大概积累了40种左右时,普通的菜鸟已经被我认识得差不多了。我开始进化到第二个心理阶段——极度渴望刷到“新鸟”。希望见到不认识的鸟,
辨认之,在自己的记录上增加一个数
字——这大概是观鸟者入门时候的必经阶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上下班必穿杨桃公园,有空就去华师晃悠,有更大的空就到各个公园晃悠,也蹭了不少拍鸟大爷的光。可以说,那个时候,一日不观鸟,我就若有所失。
某个春日,我又到杨桃公园里报到。看遍老朋友,没有新收获,于是悻悻地准备回家。就在这时,仿佛梦一般,一只亮黄色的鸟突然飞过,落在芭蕉树上。凭借我对杨桃公园的熟悉,这绝对是一只新来的鸟儿。我于是屏气凝神,追踪良久,终于拍摄到了一只黄眉姬鹟。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对观鸟者来说,发现、追踪并最终确认并拍到一种鸟类,并且是自己事先不认识的鸟类,其喜悦,是无可比拟的。黄眉姬鹟颜色艳丽,行动警惕,杨桃公园树又多,很难在偌大的公园里追踪到它。第一次邂逅,我仅看到了它两次,确认了它的存在。第二次,我扛了相机去,在第一次发现它的地方整整逡巡了一天。我不喝水,不看风景,只坐在那里睁大了眼睛,警惕地四处张望,任荔枝花落了我一头一身。可以说,我一连维持了几个小时的高度警觉,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朝外界睁大了眼睛,寻找那只黄眉姬鹟。所以,当我偶尔转身,看到它愣愣地站在我左边树上的一条绳子上时,真有踏破铁鞋后的大惊喜。那一刻,心脏几乎就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看到是一喜,把它拍到相机里是另一喜。这是我观鸟里程碑的大事——我自己发现了杨桃公园里的一只美丽的过境鸟。其实,它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只鸟,喉及腹黄红色,覆羽黑色,有白斑,有美丽的黄色眉纹,体型跟麻雀差不多——但是,在这么多的事物里,我却唯独能看到它,发现它,记录它,知道它的一点来龙去脉,它千里奔袭的旅途,有我偶然的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件太值得庆贺的事情。
自黄眉姬鹟,我才知道,初春是观鸟好时节,过境鸟,候鸟,都可以在一些地方看到。过了这个村,再找这个店,估计要到下一年了。
自黄眉姬鹟,我也才知道,观鸟人们要么是到专门的地点去找鸟,要么是在特定的时间去找鸟,在每一座幽深的大山里,在每一个草长莺飞的春天,都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比如,你会偶然看到一只黄眉姬鹟。
下一次,再见到另一只类似的鹟,是在盛夏,河南董寨的一个小村子里。七月中旬的小村平淡无奇,跟我见到的任何一个河南小村子差不多:屋后有粪坑,杨树绕着房子,是红砖砌的平房,只是树有点多。在一个比我高不了多少的小柳树旁,鸟导说,这里有寿带的巢。那树很伶仃,那巢也比一个酒杯大不了多少——这环境,这树,这巢,跟我们想象中的寿带仙风飘飘的样子,似乎并不是很相称。鸡们就在寿带巢下啄食,寿带巢下就是个粪坑。我不大相信这里有名字如此诗意飞扬的鸟——寿带。
但它们确实在这里。我钻到林子里,走了几下,就看到小小的寿带雌鸟。就在一伙人认真追踪寿带的时候,鸟导突然惊喜地喊了一声:“鸭蛋黄儿!白眉姬鹟!”我循声看去,就在一秒钟之内,我就看到了槐树上停留的那只黄黄的可爱的小鸟。它看到我们,走走跳跳,并不远飞,似乎不太怕人,也似乎是有所牵挂,不能远走。
我终于可以认认真真地、好好地看一下这只鹟了。春天,我在那只黄眉姬鹟身上,倾注了多少心力啊。现在,它在我的视野里眉目清晰如画,触手可及,再也不像在杨桃公园里它的兄弟那样芳踪渺渺,遥不可期——那一刻,我很感慨。这感慨里,既有故友相逢的惊喜,还有一点不可名状的苍凉。在彼处千呼万唤不出来、神仙一样的鸟儿,在此地,却是仿佛邻家之子,随处可见,怎地不叫我感喟!
作为一个文艺女中年,我酸兮兮地在河南的一只白眉姬鹟身上,投射了对另一只途经广州的黄眉姬鹟的感情。我在它们的身上,不仅看到了美,也看到了世界之大,之复杂,之新鲜,之生机勃勃。
这么大的世界,就在这两只这么小的姬鹟羽翼之下。这两只姬鹟所拥有的世界,可比我大得多呢。
看到白眉姬鹟,也许算是我观鸟的第三个阶段。对比于第二个阶段的痴迷,疯狂,投入,和对刷到一只新鸟的贪念,第三个阶段的我变得喜悦,平和而深沉。
这种喜悦感来自于董寨。这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充分满足了我对鸟类的好奇心。到处都是鸟,到处都是新鸟——天上,电线上,河沟里,稻田里,树上,石头边,公路边,竹子底下,人家的窗户缝里——都是鸟,像鸟的鸟,不像真鸟的鸟,大的鸟,小的鸟,雏鸟,喂雏的亲鸟,哎呀!这三天里,我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到了一个宴席上,那种匮乏感不足感被一扫而光。
当内心的渴求被满足了之后,人会自然而然产生出幸福和喜悦感。我温和平静地看那些鸟,看山斑鸠互相喂食,看两只巨傻的斑文鸟平静地在巢里孵蛋,看三宝鸟淡定地俯视众生。当一只陌生的鸟从我的镜头里逃逸而去,我也并不十分懊丧。鸟反正是看不完的。某一天,我终归还会听到这熟悉的叫声,它会一再地自动跳到我面前来,任我看个够。这个规律我已经屡试不爽。
除了白眉姬鹟,在董寨,我还看到了两个老朋友:北红尾鸲,比之杨桃公园,它现在更忙碌,它叼着虫不停地进进出出,为儿女操碎了心;乌灰鸫,它仍旧在地上翻来翻去,走走停停,这习性一点都没改。它们在南方过冬,在河南生儿育女——在这里能看到它们,我油然生出了一种探亲的喜悦感。
我期待着,在未来几个月后的广东,能再看到风尘仆仆的它们。
我也知道,在未来风尘仆仆的岁月里,我将会不断地看到这些精灵般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鸟儿。我静静地愉快地看着它们,看世界的未知、神秘和各种美好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地展开。这乐趣是任何东西也夺不走的。
9月17日:台风过后,我看到了一只黄鹂屁股
台风之夜,九楼之上。
我一边是身子滚烫的娃,一边是呼啸不止的风。史诗级的台风过境,孩子也发烧,呕吐,生病了。吃了药后,这一晚很安宁,我甚至做了很甜美的梦。在梦里伸手摸摸孩子,他身子仍旧热,却有汗,呼吸虽然略微急促,却不躁。早上醒来,他爬起来上厕所,我问:“感觉怎么样?”他愉快地答:“好了!”
既然好了,我就赶紧爬起来,挎上
望远镜和相机,去公园。这个大风大雨
之后的早上,杨桃公园会是什么样子?鸟们过得怎么样?会不会给我一点惊喜?
小区的树被拔倒折断了很多棵。尤其是网球场那几棵洋紫荆,一律倒向东边,肃杀得很——但昨天刮的却是东风呀,照理它们该倒向西才对。难道风是回旋了一下,折返吹倒了它们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公园的树还好,杨桃树和荔枝树都不甚高,且是老树,根深厚,所以能风吹雨打一日一夜而屹立不倒。唯一一棵折断的,是一棵中空的小杨桃树,可能是被虫蛀了,才如此脆弱。
然而,水却弥漫了整个公园。除了大路,其他的小径全是水,路灯柱也泡在水里,让人望而生畏。于是我只能沿着大路走,一直走到大榕树和棕榈树下去。
落羽杉湿漉漉的,很绿。杉树下的河涌昏黄而急湍。杉树上面有奇怪的声音。我刚一走过去,就看到一只喜鹊冲进树丛。那奇怪的声音是什么?我默默地等,看到它从对面冲向我的头顶,又从我的头顶飞到身后的大榕树树冠里,不见了。
这是早上八点钟,台风“山竹”过后的早上。公园里只有忙碌的工人,一地的落叶,满公园的水。和我。我仍旧在等那奇怪的鸟叫声。
对面树上有影子一闪,我用望远镜望去,仅仅看到了半个身子,黄色的身子,一级飞羽羽尖黑色——怎么会有这么鲜黄的鸟?难道是黑枕黄鹂?前天中大的观鸟人们才说,他们观测到了黑枕黄鹂。我可不大相信,这么美丽这么鲜艳的鸟,居然也会降落到杨桃公园这么平淡庸常的地方。
然而我是真的看到它了。虽然没有拍到。我按捺住内心的狂喜,默默地在树下走来走去。看了看自己,穿得不适合,是鲜艳的白T恤,在绿叶丛中太显然了。然而没办法,就等吧。
我又去公园深处走了走。公园的中门开了,公园小河涌正开了闸在泄水。出了中门,一棵榕树成熟了,一大堆白头鹎和红耳鹎在上下觅食。它们应该是饿了好久。一个亮蓝色的影子唧地一声飞过,我知道是翠鸟。我都知道。然而我却不知道那只黄鹂鸟现在在哪里。于是我又回去,在水杉树下默默地等。
另一棵水杉树上突然落了三只鸟,叽叽喳喳大叫。我小心翼翼地看,待看清楚了,终于认出是今年才出生的那三只黑领椋鸟。它们虽然羽翼未丰,却已经习得了父母巨大的嗓门。它们一出声,整个公园都热闹起来了。
突然,水杉树叶丛里有影子一闪。我举起来望远镜看,啊,正是它!它在细碎的叶子上面,朦朦胧胧的,一只黄色的鸟!我看得更清楚些,甚至能看到它喉咙周围灰黑色的纹斑。我举起相机,却怎么也对不准焦。终于对准了,却只拍了半个屁股。再认真看时,又把目标给丢了!
正在这个时候,孩子打电话来,问我看到了什么鸟。我回答完毕,他啧啧称奇,我再看时,那黄鹂已经是芳踪缥缈,无迹可寻了。我很不厚道地在树下放了很久的黄鹂叫声,仅仅有一次,看到水杉树上有鸟影一闪,却怎么也等不到它了。
虽然只有半个屁股。但我也知道,这么黄的,这个季节的,翅膀上有黑斑的,这么大体型的,只能是黑枕黄鹂了。它当然不可能是金黄鹂。它只能是一只黑枕黄鹂的亚成鸟。
以前,我一直觉得黄鹂这种小清新小文艺的鸟,只能活在书里,诗歌里,“阴阴夏木啭黄鹂”啊,“两个黄鹂鸣翠柳”啊——可我没想到,它就生活在中原农村,生活在瓦屋后猪舍上的大杨树里,整个夏天就一直在我家屋后啼啭着。而现在,我也没想到,它繁衍完子孙,又千里迢迢(直线距离1470公里),从中原飞到岭南,居然一直飞到我的身边来了!
所以,我得这么说:注意,注意,注意!你的身边,很可能有一只黄鹂出没!如果你有一个望远镜,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耐心,再加上一点点安静,你就有可能看到那只活在古诗里的鸟。当然,你也有可能,在某一瞬间,把平淡的生活,一不小心,就过成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