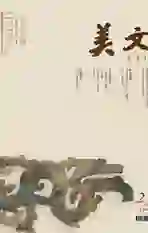路遥的两位文学导师
2025-02-18王刚
“文学教父”——柳青
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当中,柳青对路遥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分别出生在陕北吴堡与清涧,都讲着陕北口音的方言。几经辗转后又在西安长期生活并创作,对文学有着至高的信仰,这种共同的追求让他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路遥把柳青称为他的“文学教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柳青作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是路遥在做人和创作上的可见可触、可亲可爱的楷模,更称得上是路遥的精神导师。他们都信奉现实主义文学,路遥对柳青的敬重便源自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
路遥曾多次提到,在《平凡的世界》准备创作前,自己曾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七次通读《创业史》,每次阅读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准备阶段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由此可见路遥对柳青这位同乡,可谓是一种极高的致敬与义无反顾的追随。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写道:“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
路遥生前曾多次见过柳青。
1974年6月,柳青受邀到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西大街的招待所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讲话,这是路遥第一次见到柳青。此时的路遥已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据路遥大学同学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是路遥床头的必读书。路遥胞弟王天乐生前曾在《〈平凡的世界〉诞生记》中回忆:“我第一次向柳青坦白说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时,柳青拍了一下我的背说,娃娃,这是一个非常的选择,是好事,但你以后受罪呀!”
1977年10月31日,柳青出席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的发言。路遥作为青年作者和《延河》的编辑,参加了本次创作会议,又一次见到柳青,并聆听了他对文艺创作的看法。就在这一年的7月,《陕西文艺》恢复《延河》刊名。其间,柳青在医院坚持撰写、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下卷已敲定将在1978年2月号的《延河》上连载,路遥作为《延河》年轻的小说编辑,和老编辑经常去医院看望柳青。路遥在《病危中的柳青》中写道:“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地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创造的奇迹——啊!我们这些体格健壮的人又能做出些什么呢?”此时的路遥,作为同乡后辈的文学青年,作为《延河》杂志的一名编辑,在与晚年柳青最后的交往中,精神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他后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
其间,路遥与柳青有过一次重要的对话,路遥又将这番对话转述给了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你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人自己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
1978年春,《延河》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柳青因病住院,“路遥去柳青病房录下柳青对陕西青年作者的录音教诲。在省作协小会议室播放……小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却悄无人声,都安静地听着柳青那浓重的陕北口音讲述的文学真谛”。根据这次录音内容,后来以《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为题在1978年《延河》第5期刊发了。在路遥看来,柳青完全有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骄傲的理由,他在《病危中的柳青》中写道:“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
打开小说《人生》,第一眼便可看见柳青在《创业史》中谈论人生的两段话。路遥说柳青对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在构思、表述上, 是《创业史》的“延续”,也是对柳青精神的坚守和继承。由此可见,柳青的文学经验对路遥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柳青在小说集《恨透铁》印刷之前,反复叮咛编辑,无论如何不能省略掉《恨透铁》书名下的“一九五七年纪事”这几个字。路遥早年的一本小说集《当代纪事》,其中有两篇小说的副标题采用××××年纪事的方式:《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纪事》。“史诗”的宏大叙事不只是向前辈柳青学习致敬,更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继承,这种史诗情结的创作不仅客观显示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成为时代的一面放大镜。有评论者说,路遥在继承柳青文学传统的前提下,对柳青的超越是显而易见的。路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战胜前人,不管能否达到这一点。否则, 就没有文学的发展。”
路遥曾坦言:“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他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也刷新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面临的是生命危机与完成作品之间的艰难选择,如果停笔调养,可能像柳青一样会留下一部残缺的《创业史》而死不瞑目;如果选择继续完成创作,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路遥最后选择了继续完成创作,在关键的时刻,他冲到了终点,但也留下了无限的悲怆与遗憾。
1983年4月9日,路遥在上海写下了《柳青的遗产》,文末有这样一句话:“他一生辛劳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由此我们看到,路遥接受并感激柳青馈赠的这份遗产,像一汪永不干涸的泉水,供路遥解渴、吸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滋养并成就了“路遥”。
今天,我们注意到,“新时期”以来,标举写“个人”的“新启蒙”文学在摆脱束缚的同时,逐渐远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注定了对路遥的创作有一种集体的排斥与忽视。路遥曾不平地说:“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有必要再次重申,那些被称为重要的文学史拒绝或远离“路遥”,这种态度与读者对其的接受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在弟弟王天乐的陪伴下,他专程去长安柳青墓祭拜,并在柳青墓前独自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是路遥在向他的“文学教父”柳青汇报自己的文学成果。
生前为楷模,逝后是丰碑——从某种程度上说,柳青和路遥都做到了这一点。
“文坛伯乐”——秦兆阳
1978年9月,路遥在西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满怀着希望把稿子寄出去以后,得到的却是一封封退稿信,两年时间内全国大刊走过了一圈,没有一家刊物愿意刊发。就在路遥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时,妻子林达托母亲袁惠慈想办法,转机出现了。袁惠慈当时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工作,她找到时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作家黄秋耘。黄秋耘1976年起由国家出版局借调到北京负责修订大型汉语词典《辞源》工作。根据程文《陕北的博大 生命的光辉——路遥生命里程中的二十位扶助者(二)》显示,当黄秋耘读完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后很是赞赏,于是便把小说直接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的秦兆阳。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代表。
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路遥好友海波在《人生路遥》里有过这样的叙述:
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还有另外一种更具体的说法,这事路遥没给我说过,是我和路遥在城关小学时的老师、《山花》的创办人之一白军民,在事过四十年后即2017年对我说的。他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屡投不受,就在路遥已经差不多绝望的时候,林达的母亲出面帮忙了。林达的母亲和著名作家、时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的黄秋耘熟识,当时黄正被国家出版局借调到北京,参与主持修订《辞源》的工作,林母就提起这个事,看能不能帮忙看看。黄了解了大致内容后,很感兴趣,就把小说推荐给秦兆阳。
据厚夫《路遥传》披露,路遥便接到《当代》杂志社邀请到北京改稿的通知:
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果真出现了,命运之神终于把幸运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日,《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编辑部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
路遥来到北京后,拜见了秦兆阳,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述了这次难忘的拜会: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
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与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重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路遥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在秦兆阳的指导下,修改了20多天,将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路遥为此感慨:“改稿比写稿还难。”之后,《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在1980年《当代》第3期上刊发,标题字是秦兆阳以隶书体写的。只有他认为是好作品才会主动为其题写篇名。在1980年《当代》第3期《编后小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本刊一直遵循创刊时公之于众的一个重要宗旨,即:注意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要大繁荣,没有大群的新战士是不可设想的。这一期,我们很高兴地再向读者介绍几位大家尚不够熟悉的青年和中年作家,这就是张俟、刘亚洲、张林、路遥、周冀南等。
由此可见,秦兆阳主持下的《当代》明确了刊物对于新人的关注和扶持。在他的主张下,编辑部也一直坚持扶植文学新人的方针,并且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在1994年《当代》第6期(《当代》的15年)《永远纪念我们的主编兆阳同志》中写道:“强调刊物要办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力戒‘跑野马’,不要跟着‘风’跑,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秦兆阳同志提倡文学刊物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要多样化,但他更看重那些朴实厚重的作品,反对在刊物上发表那些过分缺乏思想内容,单纯在形式上耍花架子的浮华之作。”经常在家中接待新的年轻作者,他同他们交流创作问题。假设,如果没有秦兆阳这样开放的办刊精神的指引,没有对新人的发现和扶持,路遥或许会遭到埋没或者更长时间地沉寂。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发表后,秦兆阳还为路遥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一篇评论《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对路遥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于个人命运的作品……朴素自然,写得很有真实感,能够捕捉生活里感动人的事物;别具匠心的结构,生动的语言……
得到秦兆阳的充分肯定,为《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1981年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1 年《文艺报》中篇小说奖、1979—1981 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路遥成为陕西文学界第一位获此三项荣誉的青年作家,一时受到强大的精神鼓舞,成了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新星。
路遥延川时期的好友、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诗人闻频,见证了路遥得知获奖消息的情景,据梁向阳《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显示:“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一大早我在办公室写东西,他从前院急促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高兴地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路遥这种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我只见过这一次。这是他《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全国获奖,也是他第一次获奖。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茅盾文学奖,他再没激动过。”
此后,秦兆阳与路遥之间不仅是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更是心灵上相知相通的忘年交。秦兆阳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官气,也没有迂腐气。他在编辑岗位上付出的辛勤劳动大大超过了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所花的心血。对于路遥来说,秦兆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的人生导师和文学教父,而秦兆阳与路遥、蒋子龙等一批作家的交往,足以说明无愧于“文坛伯乐”这个雅称。他是路遥心中的“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一生确实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的缩影。
1985 年冬天,正当路遥在铜川的大山里埋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得知秦兆阳夫妇来陕,路遥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当即联系赶回西安的车。车到半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又联系坐上了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这使路遥痛感愧疚和难过。直到临终之前,路遥还牢记这件事,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向这位尊敬的老人深深致歉,祈求得到秦老的谅解: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
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
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