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批评的“难”和“易”
2025-02-15林路
早些年,我在《中国摄影需要什么?》的长文中,提到一个话题:中国摄影需要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然而,说到摄影批评,它在中国的这片土壤上既“难”也“易”,原因很复杂,也值得深入思考。
我们先来看看摄影史上的一段“公案”,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摄影家米诺·怀特。当年的怀特是美国摄影的信仰人物,有很多追随他的学生。他的教学方法也颇具特色,包括禅宗练习或运动练习等。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怀特的传奇性剧增,他自己也成为一些人的批评目标,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来自 A.D. 考尔曼,一位为《乡村之声》写作的年轻的摄影评论家,哪怕怀特帮助了他的展览。考尔曼在几点上竭尽全力地攻击怀特,他的文章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如“主要的极权主义者”“滥用权力”“神秘主义精神食粮”“不可思议的极端”“反智力的和自我夸大的主题”“自动神化”。考尔曼甚至说,怀特的“自尊自大,权力的滥用以及不负责任”是极端的。
考尔曼对怀特的批评的确直接影响了怀特的声誉。然而,怀特虚怀若谷,依旧像以往一样没有停下精神寻觅者的脚步,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人“现在只有向上提升,再提升,带着燃烧的精益求精的火炬,去点燃旅途中每一个路边的位置。我们可以追随他的进程沿着排列着的篝火上山,直到他消失在山顶积雪的落日中。”
这样的批评(考尔曼)和这样的宽容(怀特),在中国摄影界也许是难以想象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向来被人们比喻为艺术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任何一门艺术样式的成熟提高,都是和相关的艺术批评紧密结合的。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艺术创造就将成为“独轮车”,难以维系起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因为离开了批评的监督,或者离开了批评的导向,一方面,艺术创造很容易成为“一言堂”,成为某种观念甚至是某一个权威的“家天下”,很容易扼杀艺术创造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批评的缺位,很可能使艺术创作庸俗化,失去原本应有的活力。就国内艺术创作的领域来说,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是文学界和美术界,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批评氛围,一直是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多么具有权威性的“大家”,都无法逃脱随时被点名批评的“幸运”,从而也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十批判书”,批评者的锋芒直指王蒙、王朔等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又比如美术界的泰斗吴冠中在数年前引发的关于中国画的“笔墨”之争,也引来许多尖锐的批评。这样的例子在文学界和美术界不胜枚举,尽管在一些场合中也不乏商业炒作的成分,但是对于提升整个艺术观念的变革力度,无疑是利大于弊的。
反观中国摄影界,不是说这样锋芒毕露的批评没有,而是实在少得可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批评的氛围越来越稀薄,几乎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静下心来想想,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为过。
首先我们缺少的是宽容的批评环境。整个大环境没有对批评的“纵容”,也就很难形成让人说话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批评的出现。当今的摄影界热衷于说恭维话,习惯于好话连篇,这不完全是批评家之过,而是批评环境的缺失和批评氛围的无法形成之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早些年,一位中国摄影界德高望重的老摄影家冷评“商业性人体摄影热”,在专业的摄影报刊头版对近年的中国人体摄影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不仅老套,没有说中要害,反而会对中国人体摄影形成一定的误导。于是笔者写了一篇千字的短文,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令人失望的是,编辑的回答颇具玄机:文章很好,立论准确,也有足够的批评力度,但是不适宜刊登。因为被批评者是一位摄影界的老前辈,就可以被当作佛像一样被供养起来,来不得半点“不恭”?不久以后,这位老前辈因年事已高“仙逝”,我从此失去了原本可以对话请教的机会。我理解编辑的最终决定也是言不由衷的,这是中国摄影批评缺位的典型写照。长此以往,中国摄影要想保持新鲜的活力,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批评的缺位同时也是中国摄影本身就缺乏批评的力量,缺乏真正对摄影批评有责任感的专家和名家所导致的。我不是说中国摄影界没有这样勇于直面人生的批评者,但是像鲍昆、胡武功、王瑞这样一批敢于狠狠揭开摄影界的伤疤、大胆鞭挞现实的批评者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不能不说又是中国摄影的一大悲哀所在。
其实,摄影批评的“难”和“易”,还涉及一个品位问题。在中国,摄影的品位是什么,很难评说,也不敢评说。因为主导的话语权不在我手里,因此说了也白说。但是如果一个欣欣向荣的摄影大国失去了摄影的品位,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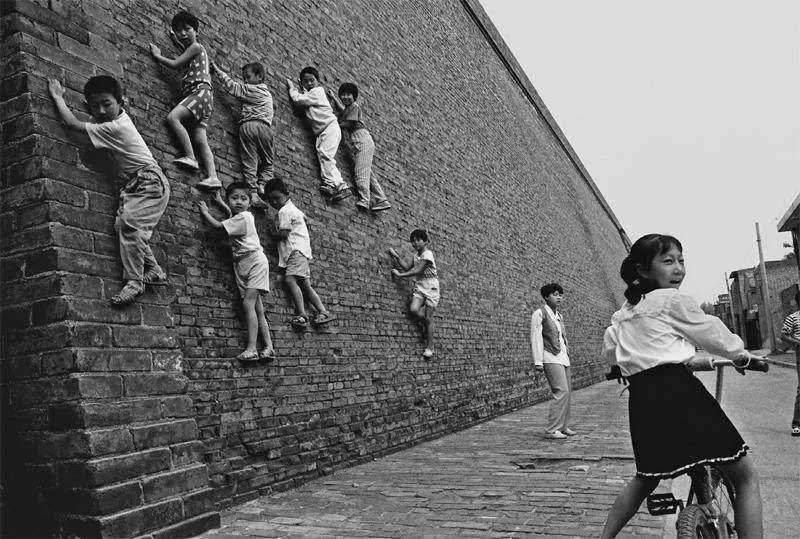
早些年曾经以批评著作扬威文坛的女作家,也是摄影人熟知的摄影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第四部小说《在美国》获得了全国图书奖。但是她对得奖很矛盾,尤其是不看关于她的书评。但是害怕批评的桑塔格一定很痛苦,因为批评的文章还真不少。除了《纽约时报》角谷美智子对她的小说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之外,《新共和》杂志也有一篇文章把她放上了“手术台”。文章的导语是“桑塔格赢了,文学品位输了”。其实文章也不是单单冲着桑塔格而来的,因为文章还说到,其他被提名的小说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么是平庸、乏味、毫不含糊地逗人发噱,要么是很好但不太令人难忘。因此, 桑塔格也算是实至名归”,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其实,在中国如今最高级别的各种摄影评奖,其平庸之态也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表面看上去“很好”但是却“不太令人难忘”,这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像前面的文章批评美国的文学品位一样:“……对那些体面但技巧平平无奇的书,则一而再地当成发育不良的陌生国王和王后吹捧之。”其实,中国的摄影不乏真正的精彩之作,不乏“十年磨一剑”的潜心体验生活的心得,但是偏偏进不了主流话语的“慧眼”,被毫无良心地扔在一边,这究竟是谁的过错?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身故后才被主流话语沉痛悼念的摄影家如侯登科、赵铁林等等,似乎都没有得过中国摄影的最高奖,这是不是中国摄影品位的缺失?我们要那么多的风花雪月装点门面,却把那么重要的天地良心弃之不顾,这合理吗?
再回到关于对美国文学趣味的批评,文章最后说:“在美国,有价值的文学,已越来越难找到,终有一天会彻底消失,而平庸作品正把这种有价值的文学遮蔽得黯然失色,进而把它覆盖得不见踪影。”看来整个世界大同,文学和艺术的遭遇也是一样的。让摄影保持它的品位其实不难。哪一天摄影界的主流做到三顾茅庐、躬身民间,真正以求贤若渴的态度面对中国摄影最为广大的群体,不拘一格展现中国摄影真正的辉煌,实事求是,中国摄影才真的有救了,摄影的品位也就有救了。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了当年黄一璜的文章《中国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人们一直想说但又一时无从说起的问题,对中国摄影界中的种种“自恋”情结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让人感到很是痛快。
这里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摄影评论人的问题。文章认为“评论人不应自比执法判官,以为可以操纵摄坛”“抢注××理论、××观点或××提法”的现象“已出现过太多次, 无需一一枚举”。然而我恰恰以为,中国的摄影评论人在摄坛上的炒作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中国摄影的发展之所以还远远未达到人们所认可的程度,在某些方面和摄影评论人的不成气候相关。据我所知,在摄影和其他艺术样式相当发达的法国,摄影评论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摄影发展的导向有着绝对的权威。然而这种权威的建立,正是需要这样的一种不断炒作的氛围和大环境,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理论、新观点的前提下得以完成的。当然,正如黄一璜在文章中所说,“摄影批评中任何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需要摄影实践的检验,需要一定量的摄影作品的支撑,需要逻辑思考的演绎,缺乏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判断而仅凭感性的欲望是难以做好评论的”。但是如果在中国摄影评论还如此薄弱的今天,连一点感性的欲望都不能生存,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中国摄影的理论发展的。从感性的初步认识到理性的逐步成熟,这是任何一种理论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双重自恋”的话,那就不妨宽容些,让摄影评论在自恋的情结中自我成熟,真正实现对中国摄影发展有利的批评环境。中国的摄影评论人已经不太活跃了,与其一潭死水,还不如提出些新理论、新观点,或是将某种摄影现象多点些火,炒作一番,这样总比冷冷清清的好吧。
早在近30年前,著名摄影家张新民就在给王瑞的信中说到了摄影批评:长期以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摄影批评的现状,让人感到有些东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们做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摄影,却做不到摄影的自我批判,只要话题引入图像批评,就很容易陷入人际陷阱,扯到个人的其他关系。其实一片赞扬未必就天下太平,该争名夺利还争名夺利,那是人性的弱点。而缺乏严肃的学术批评,确实是摄影的悲哀。
总而言之,中国摄影批评既“难”也“易”。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让人说话而不仅仅是让人说好话,这是中国摄影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让整个文化界对中国摄影能够刮目相看的唯一可能。没有批评的艺术创造固然可以营造一时间的“花好月圆”,但是一定经不起“吹落黄花满地金”的一夜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