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还给时代
2025-02-15翟墨
一
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华北地区,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时统治华北地区的是金朝。此前,女真人曾在这片土地上迎来过短暂的鼎盛,而今则来到了盛世的尾声。特别是当十三世纪初,铁木真接受“成吉思汗”的尊号、建立大蒙古国,近在咫尺的金朝,也就无可避免地落入了这位未来征服者的视野,时代巨变的序幕就这样被缓缓拉开了。
元好问(一一九〇至一二五七)出生在这一时代剧变的前夜。他出生的这一年,恰逢金章宗登基称帝。或许是因为这个命定般的巧合,所以抛开社会现实危机不谈,我们会发现,在元好问后来写下的文字中,章宗一朝常常被他描述成士人的黄金时代。出生七个月后,元好问被过继给了叔父元格,在陪同元格前往各地赴任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元好问二十一岁时,元格病逝,他护送灵柩回乡。次年,成吉思汗发兵攻金。不出几年,战火就蔓延至元好问的家乡,包括他的胞兄元好古在内的大批士人和百姓在战乱中丧生,金朝被迫迁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迁”。元好问偕家避难、寓居河南,很快就在文坛扬名,总算进士及第。此后又经历了仕隐间的几度反复,最终调任尚书省掾,进入朝廷。没承想,两年之后,蒙军围攻汴京,金哀宗出奔。次年正月,守城将领崔立发动叛乱,以城投降,汴京沦陷。元好问被俘,由蒙军押往今天的山东聊城,拘禁解除后又辗转于今天的山西、河北、北京、山东等地,最终在河北鹿泉走完了自己六十七年的一生。
金朝灭亡这一年,元好问四十三岁。也就是说,他在金朝亡国之后又生活了二十四年。如果把时间线向后拉长: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发生在元好问去世后的第三年;而其正式以“大元”为国号,则又是十一年后的事了。换言之,元好问的后半生,恰好处于政权更迭的过程中。
这段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动荡岁月,往往被笼统地概括为“金元之际”。与精确的系年相比,“之际”更像是一种对时间的模糊化处理策略。在这个略显混沌的时间尺度下,人们容易陷入某种概念化的认知陷阱,缺乏拨开混沌、直面历史现场的热情。于是,一些明明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却被轻轻带过了。比如,同样是王朝更迭,元好问所经历的“金元之际”,究竟还伴生着哪些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特殊现象?这些具体的情状,又怎样影响并塑造了他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日本学者高桥文治的新著《元好问和他的时代》的追问,正是围绕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金元交替这个大时代里的种种面向,从而真正走进并理解元好问和他的时代。
二
金朝灭亡之后,华北地区并没有立刻被蒙古或者南宋纳入版图,而是经历了一段罕见的王朝空白。在本书第一章《危机时代》中,作者就敏锐地指出了这个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事实:“在中国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除去金元交替的这二十六年,年号从‘中原地区’消失的现象绝无仅有。”(6 页)自汉武帝以来,年号就被视作历史和文明秩序的象征。它的消失,会给浸润在儒家文明中的金朝士人带来怎样的冲击?正是带着这样的关怀,作者尝试走进元好问的精神世界。
高桥文治是日本中国文学,特别是金元文学研究的大家。在他的笔下,通往元好问精神世界的路径首先当然是文学。为了呈现“王朝空白”之下元好问的心路历程,高桥文治选择了其在此一时期创作的七言律诗《镇州与文举百一饮》来进行解说。诗的首联是:
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双阙记神州。
这首诗在现行诸家元好问集的整理本中都有收录。或许是出于母语的习熟,中国研究者对于“神州”一词往往不会额外出注。而高桥文治的分析,则显露出了有别于中国研究者的“异域之眼”。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解读元好问这首作品的关键在首联的‘记神州’这一文字表现上。”(8 页)他认为,这里的“神州”具有强烈的文化指向,代表着中华文明的中心;而元好问刻意强调的“记神州”,也应该从文明变迁的层面去理解。
有赖于这一特殊的观察角度,高桥文治在文本释读中,往往又有超越语词层面的发明:如果说看到元好问“翁仲遗墟草棘秋”对柳宗元“翁仲遗墟草树平”的承袭,是一般研究者的普遍认识;高桥文治则更进一步注意到,元、柳二诗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元好问的作品中,‘翁仲遗墟’是对文明本身的一种毁誉褒贬”(12 页)。也正是基于对时代大关节的把握,作者才没有把金朝的灭亡仅仅理解成元好问个人抑或是某个王朝或政权的悲剧,而是中原文明消失的悲哀。也正因如此,作者的解说才能最大限度地去还原元好问创作时的心境。
不只是元好问,和他同时代的金朝士人在这段王朝空白、年号消失的历史时期,都有着类似的困惑与焦虑。对于这批普遍生长于世宗、章宗朝的汉族士人来说,金朝是他们亲历的儒家治世。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传统的“夷夏”语境下,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其正统性问题更容易遭受质疑和挑战。更重要的是,眼下的“王朝空白”,恰恰就暗示着金朝历史评价问题中的不确定因素。蒙古和南宋,究竟谁会掌握未来历史记载的话语权?他们又将怎样书写金朝的历史?金朝如何才能跻身文化正统的序列?这是前金士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在金亡不久的一次前金士人的聚会上,有人就提出,金朝是否会被作为宋朝的“载记”之一,沦为不被承认的非正统王朝?一位名叫修端的参与者,当即对此予以反驳,并详细阐发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当以辽、金为“北史”,以北宋为“宋史”,以南宋为“南宋史”。这一观点的本质在于将辽、宋、金作为地位对等的政权来看待。
修端的这篇议论,后来以《辩辽宋金正统》为题,被收入了王恽的《玉堂嘉话》和苏天爵的《国朝文类》中。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高桥文治对这篇长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翻译和解说,继而指出:“灭掉金王朝政权的是蒙古铁骑,并不是南宋,但能够抹杀‘金朝历史’的却是南宋而不是蒙古”,“《辩辽宋金正统》文中之所以将金朝定位为‘辽王朝的后继者’,就是为了与灭金的征服王朝蒙古站在同一立场,以便为新提议的‘北朝’的存在造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名正言顺地跻身于胜利者的王统阵营中来”(35 页)。这些精当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作者本人深厚的史学积累,更能反复提示读者,元好问和他的同时代人,其文学文化活动乃至种种人生选择背后,关系着怎样错综复杂的脉络。
三
时代变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酝酿和发生的过程中,以元好问为代表的这批深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金代士人有过怎样的思考和表达?这是书中继续讨论的话题。
《辗转仕途》一章以元好问的仕途经历为线索,回溯了时代剧变来临之前金代的社会状况,以及官员身份下元好问的时代观察与心路历程。元好问曾有过三次担任县令的经历,《宛丘叹》是他在南阳令任上的作品。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是通行文学史对这首诗的普遍评价,但作者却在深入解析诗歌内容结构后发现,这首诗的主旨并不是流民的悲剧,“而是元好问自己身为县令目睹流民悲剧的发生却无能为力的懊恼”(59 页)。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作者又将元好问的《宛丘叹》与辛愿、雷琯反映金朝末年社会现实的诗作进行对读,指出后者诗中的视线一直聚焦在难民身上,而元好问的视线“最终却是落在了自己面对人民的水深火热却束手无策的身影上”(62 页),从而呈现出官员元好问在现实和理想间的苦恼、挣扎与无奈。而这一观察角度,也体现在作者对于“崔立碑”事件的梳理中。参与为导致汴京陷落的叛臣崔立撰写功德碑,是元好问生平最受争议的部分。但作者在这里既不纠缠于陈旧的道德审判,也无意去故作翻案文章,而是同样着重去呈现事件各个相关方的身份、立场,及其各自秉持的伦理观,最终以元好问“屈己循物”的自我剖析作结。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物研究的“理解之同情”,也即将“人”本身作为价值的学术关怀。
除了表达某种复杂心绪外,元好问又是如何通过文学,去有意识地回应时代、定义自身的呢?《丧乱诗的创作》一章给出了一些线索。“丧乱诗”是元好问最负盛名的文学创作类型,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此类诗歌风格、内容的讨论上。本书则秉持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特别关注了元好问是如何通过用典等传统修辞手法,在诗中融入了对金朝正统性的塑造。
一二三一年,金军在与蒙军的交战中败北,凤翔陷落。元好问得知这一消息后,创作了《岐阳三首》。高桥文治从诗题中的“岐阳”出发,指出这组描写金、蒙实际战况的作品中,没有出现“凤翔”这样当时具体的地名,而是“在利用过去的战役典故进行‘影射’”(110页)。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对唐代杜甫《喜达行在所三首》的祖述。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曾从被叛军占领的长安逃至肃宗的行在所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描述的就是这段经历,诗的首句“西忆岐阳信”中的“岐阳”指的正是凤翔。高桥文治认为,这是杜甫刻意使用西周成王岐阳会盟的典故,来显示唐肃宗受命于天的正统性;同杜甫一样,元好问在诗题中也将凤翔称为“岐阳”,除了强调了这一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更是“向人们暗示了这场战役掺杂着历史王朝‘天命所归’的重大性。这一描写视角,显露了元好问欲将自身的诗作置于中国文学正统之地的意图”(113 页)。
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别关注到元好问丧乱诗中典故运用、诗体选择,与当时中国南、北正统问题的互动,指出“把金朝定位为正统王朝,对它的覆灭进行描述的时候,元好问多选择‘近体诗’诗体,利用众多的历史典故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绘卷”,“但是在将国家灭亡以死别、流离这样的着眼点进行描写的时候,元好问会有意识地选择‘乐府’‘曲子词’这样的诗体,通过类似俗谣的‘闺怨’来歌咏丧失的悲哀”(139 页)。这些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观察。
四
随着金朝的灭亡,华北的战事逐渐告一段落。此时的前金士人,既有前文所述“王朝真空”下的思想焦虑,又不得不面向眼下的社会现实,在支离破碎中探索重建的可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元好问们又将如何自处呢?《战后的元好问》这章,就将目光从单纯的文学文本转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呈现了金亡之后华北地方社会的新体制。其中,作者特别关注到,此时因获得免税特权而急速扩张的佛教、道教团体,挤压了儒士群体的生存空间;而儒士群体的领袖、孔子后裔孔元措的去世,又使得士人的待遇问题更加悬而未决。在作者看来,元好问为忽必烈上“儒教大宗师”名号,也必须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中来理解,才能避免落入名节之争的窠臼。
元好问既是时代的亲历者,更是历史的记述者。但作者从元好问的作品中发现,他似乎少有“正确观察蒙古新体制的热情和积极性”(249 页)。也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本书在最后的三章里,开始着意去观察那些元好问笔下“故意的遗漏”,以及其中所展现的元好问的精神世界。比如,在第五章《归乡与复兴》中,作者原本试图去揭示元好问对于金亡之后蒙古支配下的地方社会复兴的观察,然而却发现,尽管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关系着元好问的实际生活,但他“却几乎都没有做过正面记述”(253 页)。第六章《史传与挽歌》以元好问写给同乡友人白华的书信为线索,考证了他在忻州的思想、交游以及与修史相关的诸多活动。第七章《空白的国家论》则继续讨论了和白华有关的话题。白华的经历比较特殊,他是金末的进士,颇受哀宗器重,又在金亡后降宋并出仕,后又随宋将降蒙。作者认为,《金史·白华传》的原始资料来自元好问。这篇长传记的详略安排背后,遍布着元好问的“曲笔”,是“元好问怀着最大限度的意图执笔的‘辩亡’,是他竭尽全力的‘君主论’”(393 页)。
在高桥文治笔下,元好问始终无法对于金朝皇帝进行直接的批判,也无法做到什么也不留下,最终形成了一种敏感而又克制的记述者意识。事实上,正如元好问需要谨慎行使记述者的权利那样,本书的作者同样需要去巧妙地处理历史中的记忆与遗忘。就“有”谈有未必容易,但就“无”谈有一定更难,在这里,作者就显示出了高超的“无中生有”功夫,带领读者不断从空白处寻找答案。
那么,为什么作者就笃信空白处一定藏有答案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高桥文治在文学研究之外,对金元时期的政治、社会、制度、思想等领域同样造诣颇深。他的《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研究》《蒙古时代道教文书研究》,对于蒙古初期如何处理原本金朝治下的地区、金元时期的宗教团体与政治文化等问题,也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此外,作者在书的序言中也曾提到,自己完整参加过本田实信、杉山正明主持的《元史·本纪》研读会,这段经历对他的元好问研究同样启发颇多。因此,在与元好问的反复相遇中,高桥文治看到的也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人物。也只有在这一宏阔的学术视野下,他才得以完成序言中“尝试阐明‘元好问写了什么,而他不想写也没有写的又是什么’”的写作目标,为读者奉上一部内容充实、脉络丰富的佳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诸多核心文本,均进行了注释和详细的翻译和解说,这也是日本汉学家常用的文本细读法。这种方法不仅为日本读者提供了阅读的便利,也有利于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主张。譬如《岐阳三首》的写作时间,此前诸家普遍认为是作于一二三一年四月。而作者通过对诗歌内容的细致梳理,认为这组诗“实际上描写的是一二三一年正月到五月,这几个月之间金朝与蒙古之间的实际战况的变化”(109 页),“按照时间序列将千里以外的战局变化做了明了的记叙”(107 页)。再如,对于元好问诗歌中出现的“吴”,作者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指出它何时指代的是金朝、何时指代的是南宋。这些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同样深有启发。
诚然,书中也存在着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编纂元好问年谱的缪荃孙”(188 页)疑应为“缪钺”,想来可能是作者的笔误。另外,在个别语句上,中文译本的准确性似乎可再做斟酌。比如,作者在言及金亡之后的元好问时,并非一概以“遗民”称之,但中文译本中却有超出作者本意的表达。例如,作者用日文的“亡命者”来形容元好问晚年的状态,中文译本直接将其译为“亡国遗民”(6 页);作者用“士大夫の法を越えて”来描述元好问的立身处世抉择,中文译本则在“违背了士大夫的准则”之后又衍生出“选择遗民苟活的态度”云云(48 页)。事实上,即便日文称“遗民”处,恐怕也并非全然能与今天最常见到的、强调政治立场的“遗民”之意等同,作者本人在书中更无意对元好问的出处问题做扩大化的评价。至于没能准确把握元好问《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以“河朔”代指“蒙古”的表达,错以“河朔”为“金朝”,从而把作者“その投降を「河朔」に帰順した〈大夫〉と〈士〉たち”的解说,错译成“将文人们对金朝的投降称为‘归河朔’”(154 页),则是中文译本的误解了。
总而言之,近年来,“某某和他的时代”似乎正在成为街头巷尾的量产标题。在其流行的同时,也很容易陷入“人归人、时代归时代”两不相干的窠臼。如何“把人还给时代”,既从宏观处把握住时代的大关节,又从细微处在大时代中定位出“人”的坐标系,考验的是研究者的眼界、笔力和智慧。在这些方面,本书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范本。
(《元好问和他的时代》,[ 日] 高桥文治著,陈文辉译,中华书局二〇二四年版)
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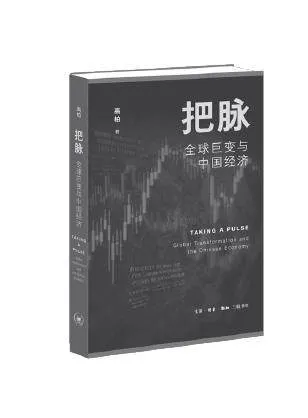
高柏 著 79.00 元
高柏近十年思考与写作的结晶,本书以高度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揭示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的两次同频共振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历史同时代性和共同特征,从历史的纵深与比较的视野分析中国经验,为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十分独特的视角。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