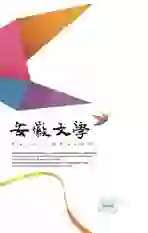猛兽
2025-02-11冉也
我喜欢坐在屋顶。天晴的时候,天山上的雪白得清晰可见。
那天下午,沙很泰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他已经跟萨菲娜说好了,暑假坐同一趟飞机回来。
“好兄弟!”我说,“我到机场去接你们,咱们在乌鲁木齐吃个饭,赶在天黑前回吐虎玛克镇呗。”
当时,我正在屋顶上铺平昨晚被大风卷起的防水油毡。即使是夏天,吐虎玛克镇也多是大风天气,尤其是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白天被晒得脱胶的防水油毡很容易被风吹起来。这会儿,蒙根布哈村的人都在午睡,我家的小狗正躲在后院的向日葵下乘凉,时不时支起脑袋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村道电线上的麻雀抖动翅膀,警觉地看着我打电话,前院浓密的海棠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李约哥,你不会真的喜欢萨菲娜吧?”沙很泰顿了顿,继续说,“你们汉族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吗?人家拿你当兄弟,你对人家图谋不轨呀?”
我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话听过没有?”
沙很泰说得没错,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吐虎玛克镇长大,太熟悉了!按理说,我跟萨菲娜当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不可能有这种超越普通朋友的想法。可是,上大学后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我总是想她。
沙很泰问我:“那是为啥呢?”
我说:“大概是爱情吧?”沙很泰挂断电话。
我把屋顶的油毡全都铺平展,用提前拿到房顶的碎砖压好,避免大风再卷起来。做完这些,我脱下短袖上衣,趴在被炙烤得热烘烘的防水油毡上面,后背朝着太阳。网上的养生博主说,晒背可以调理脏腑气血。萨菲娜有次在微信里说,她和她的同学们都热衷于晒背养生,为此还专门买了瑜伽垫和露背运动衣。
我说:“那你赶紧回新疆啊,把你的瑜伽垫和露背运动衣带到我家屋顶上来。”
她说:“我家没有屋顶吗?我干吗非得去你家屋顶上晒。”
我说:“随便你,新疆的太阳在等你。”
我爸从屋里出来了,喊我的名字,说:“铺好了赶紧下来,待在上面不怕中暑吗?”
我双手扶上木梯,看到他正在发动车子。那是一辆有些年头的五菱宏光,车身的外漆斑驳,发动机的嘶鸣像得了肺炎的病人。这种车承载能力强,用我爸的话说就是“耐造”,很受吐虎玛克镇农牧民的欢迎。
我问:“爸,你的车明天借我下可以吗?我去趟乌鲁木齐。”
我爸说:“你刚放假回来,帮你妈在家干活不行吗?心都玩野掉了。”
我妈跟着出来了,穿着她最喜欢的那条绿底花点的裙子。她拉开副驾驶的门,朝屋顶上的我抿着嘴笑,说:“李约长大了,有人家自己的事情呢。”
我爸黑着脸,发动车子,说:“你最好心里有点数,要是人家爸妈再找上门,我可丢不起那人。”
我问:“你们到哪儿去呀?”
我妈说:“我们去县上买个收割机的零件,晚上回来晚的话,你记得把鸡和狗喂了。”我爸是镇上唯一开收割机的庄稼人,眼看着就要秋收了,很多村民找他收麦子。
爸妈出门后,我坐回书桌前写一个关于青春期的小说,心里乱糟糟的,总是进入不了状态。我从书桌的夹层里摸出藏在下面的钥匙,打开柜子,里面飘出樟脑丸淡淡的气味。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从巴扎上买来这张旧办公桌。桌子是实木的,深咖色。我自己装了锁。柜子里有我高中时的校服,有朋友送我的各种小礼物,还有十几本我在高中时写的日记。
我拿出校服,铺在桌面上。高三毕业那天,萨菲娜用黑色记号笔在我的校服上写下我俩的名字。校服里面还夹着一件白色短袖衫,前胸用红色丝线绣着两颗紧挨一起的心。
萨菲娜的高一是在甘肃天水老家借读的。高二下学期,她转回奇台县就读。高考像压在高三学生心头的乌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做题,让人闷得喘不过气。她跟沙很泰都是理科生。我是文科,和他俩几乎见不上面,只有放月假的时候,我们才相约一起回家。
傍晚八点,回吐虎玛克镇的小巴车已经停运。我们只能约着一起租车回家,平摊下来每人需要支付20块钱的车费。有时候,萨菲娜的爸爸来城里买他家饭馆里用的食材,我们会一起坐她爸爸的车回去。
萨菲娜的爸爸叫萨金山,镇上的人都叫他“老萨”。萨菲娜说她家在镇上开了几十年的饭馆了。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她爸妈好像一直在镇卫生院对面开饭馆,就连门头上的招牌好像也从来没换过。饭馆里主要卖的是奇台的特色美食黄面凉皮。原先,他们家饭店旁边还有一家维吾尔族大叔的烤肉摊,后来大叔跟着儿子搬去城里生活,老萨就把烤肉摊接了过来。
小学的时候,我跟沙很泰经常去萨菲娜家,在老萨那里混吃混喝。老萨会准备我们三个人的饭。我们吃完饭后就在萨菲娜家后院的葡萄架下写作业、打羊髀石玩儿。直到天色暗下来,我跟沙很泰才骑着他的小马“闪电”回家。
我跟萨菲娜是同一天在镇卫生院出生的。老萨跟我们说,萨菲娜出生那天,她的妈妈正在后厨忙呢,突然腹部疼痛难忍,恰巧沙很泰的爸爸在外面等着吃烤肉,用牛板车把她的妈妈送到了镇卫生所。
老萨说:“那天多亏了沙很泰的爸爸。”他回头看着我笑:“我们把你阿姨送到镇卫生所门口的时候,你正在里面哭。”
萨菲娜在旁边笑,说:“爸爸,我妈怀着我呢,你咋还让她干活呀?”
“为啥?为了养活你,为了给你挣钱读书啊!”老萨故意严肃地说。
这时候,萨菲娜的妈妈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啊,以后的社会,没文化是不行的。”
萨菲娜放下手里的笔,挺直腰杆保证:“妈,你放心吧,我到时候给你考个好大学!”
老萨正要说话,来客人了。萨菲娜的妈妈看着我和沙很泰说:“你俩给阿姨做个见证人啊,萨菲娜说要给阿姨考个大学呢,到时候阿姨去上大学,让萨菲娜给人烤肉、做黄面凉皮。”
这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沙很泰纠正萨菲娜的话:“是给你自己考个好大学,不是给叔叔阿姨考个好大学。”
沙很泰说这话的时候一脸认真。我跟萨菲娜相互看了一眼,撇撇嘴,继续低头写作业。
沙很泰是哈萨克族人,上小学的时候才从山上的宽沟草场下来,定居在吐虎玛克镇。我的很多哈萨克族朋友都很幽默,能说会道。沙很泰是个例外,不管是学习还是平常聊天,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把衣服重新叠好,放到柜子的最深处,翻开日记:
2010年5月19日 晴
昨天,收到了萨菲娜从甘肃寄来的信。我并不觉得意外,她早在QQ里说了要给我写信的事情。意外的是,她还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穿着牛仔裤,水粉色的短袖,剪了短发。希望我们尽快见面。
翻开另一本日记:
2012年9月24日" 雨
天气突然就转冷了。沙很泰昨天跟我说,山上已经下雪了。马上放国庆节假了,跟他约好去宽沟的草场上看看。萨菲娜说下学期要回新疆上学了。期待!
日记本上写的都是些在学校的日常,萨菲娜的名字却频繁出现。合上日记本的时候,我心里悄然涌出一阵失落。青春里的情绪像列车穿过时间长长的隧道,在开出隧道口的那一刻碾压过仍在洞口徘徊的我。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切好像都变了,又好像还在原地。不管怎么说,日记里的萨菲娜和沙很泰依然在我的生命里存在,这已经足够让我感到幸运。
我早早起床,洗了头,换上干净的衣裳,开着我爸的车向地窝堡机场出发。车子开出蒙根布哈村的村道后,我抄近道往228省道上开。这是一段土路,除了镇上的农民少有人走。路两边的麦子已经染上了金黄,后视镜里,朝霞把半边天都染红了。
在进入省道的岔路口,我停车下来。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不远处的蒙根布哈村,一排排房子的黄色外墙被染上淡红色的光,静静地立在荒凉的戈壁上。农民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向麦地里走去。
蒙根布哈村在吐虎玛克镇的北边,整个村庄坐落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散布在戈壁上的深井把地下水抽出来,用一道道浅浅的渠浇灌出规则的庄稼地。农民们习惯在通往地里的路边和浅渠旁边种树。这些树可以减少太阳对灌溉水的蒸发,可以防止土壤沙化。虽然也会汲取一部分的地下水,但长远来看总归是好事儿。
萨菲娜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张登机前检票的照片。我回复她:“我在停车场等你们。”
过了一会儿,她回复了个“可爱”的表情,眉眼弯弯,嘴角像个波浪号。我摁灭手机屏幕,想到这个暑假我们要一起在吐虎玛克镇度过,对接下来的日子有些期待。
我们三个人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去年放寒假的时候,萨菲娜跟着自己的导师做课题,沙很泰也在实习,俩人都没有回来。说来惭愧,高三那年,我们商量好一起考到北京去,可我报的第一志愿没录取上,最后他俩考到了北京,我在西安一所高校读林学。当时,萨菲娜在送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安慰我:“虽然不能一起去北京,但这个专业也是你喜欢的啊。”
车子穿过奇台县,上了乌奇高速,速度就快了起来。我关掉车里的空调,打开车窗,烈日炙烤沥青路面的味道有些呛人。风灌进车窗里,吹动车里的挂饰,噼里啪啦,像在下雨。
我到机场的停车场时,已经是下午两点。这会儿正是午饭时间,肚子咕咕叫。距离他们落地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想去机场附近吃个拌面,又想到万一他们提前到达呢?最后还是决定等他们。我点根烟,从后面的座位上拿了瓶矿泉水打开,把座位放平躺下,等他们出来。
这是新疆最大的机场,每天有人在这里出发,有人抵达。飞机的每一次起飞都牵挂着两端的亲朋好友。坐在飞机上的人会想什么呢?沙很泰这会应该睡着了,他总是上车就睡,下车就尿,坐飞机应该也是。萨菲娜呢?我猜她正拿手机俯拍着雪山、沙漠、薄薄的云层。
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我睡了过去,直到有人拉开车门。
我一睁眼就看到了萨菲娜那双明亮亮的眸子,几乎贴上我的眉毛了。我不禁吓一跳,猛地坐起来。耳边是他俩恶作剧的笑声。
沙很泰说:“你的那个手机是板砖吗,打电话给你不会响的吗?我俩把停车场的车找了一个遍。”
萨菲娜嘻嘻笑着,她嘴里的热气像鱼的嘴巴一样碰触着我的皮肤。我抹了一把自己的脸,有些发烫,说:“早晨起太早了,不小心睡着了。”
萨菲娜说:“要不你再睡会儿?”
我说:“我先带你们吃饭去。”
沙很泰说:“李约哥,这会儿市里肯定堵车,要不咱们直接回奇台再吃吧?”
“沙很泰着急回奇台见他的小情人呢。”萨菲娜笑着说。
“小情人?”我回头看看沙很泰,他的脸唰地红了。
萨菲娜从她的包里翻出一盒牛奶,一个面包,说:“你应该没吃饭吧?我俩吃了飞机餐,你先吃点儿面包垫垫。”
“什么小情人啊……”沙很泰不好意思地推了下萨菲娜,“是木丽德尔,她在古城商业街订了饭,等我们呢。”
木丽德尔呀,我怎么把她给忘了。我从萨菲娜的手里接过牛奶和面包,说:“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拉着她一起来接你们了。”
沙很泰说:“她在奇台等我们呢。”
我把车发动起来,扭过头对萨菲娜说:“那你坐前面来,回去得三个小时呢,让沙很泰在后面睡觉去。”
萨菲娜把自己的背包扔到副驾驶的座位上,揶揄我:“哎哟哟,你比木丽德尔还贴心呢。”
我侧身过去帮萨菲娜系安全带,她把两只手朝半空里伸,嘴里说:“你可以呀,李约,跟电视上学的吗?”
我笑着说:“叫哥,没大没小的。”
车子穿过停车场,绕上高架,桥两边的高楼迅速向后倒退。沙很泰果然很快就睡着了,后面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呼噜声。
我说:“萨菲娜,你看沙很泰睡着的样子,像不像那个啥?”
萨菲娜瞪我一眼,说:“像啥?你想说啥?”
我说:“像佩奇。”
萨菲娜狠狠掐我的大腿:“还说,你还说?”
我连连讨饶:“不说了不说了。开车呢,别闹。”
萨菲娜松了手,突然叹口气,问:“你还记得陈甜吗?”
“陈甜?”我把这个名字快速地在大脑里过了一遍,没什么印象。
“我高三时的同桌,理科班第一名。”萨菲娜说,“她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个动画片。”
我想起来了。我说:“太可惜了,当时老师都觉得她可以上清华的。”
“我想去看看她……”萨菲娜说。
路上,我跟萨菲娜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路过阜康服务区的时候,我问她要不要休息下,上个卫生间。她说:“你要是不去的话就赶紧走吧,木丽德尔还在奇台等着呢。”
过了会儿,她压低声音问我:“哎,他跟木丽德尔真谈恋爱了吗?”
我反问:“你觉得沙很泰像会开玩笑的人吗?”
她笑了,看向车前方:“真好。”
我从后视镜里看她,问:“你在北京……没谈一个吗?”
“废话。”她说,“我每天忙得要死。我要找个新疆的,我太想吃奇台的饭了,我在北京天天就想着新疆的大盘鸡、拌面、炒米粉、擀面皮……”
我说:“怪不得呢,你看上去瘦了很多。”
她就笑了,两只手在她的腿上比出一个圈儿,又在我的大腿上比了比,笑着说:“是吧?我真的瘦了吗?瘦了好!”
我紧盯着路面,接着说:“你看上去变化挺大的。”
“有吗?”萨菲娜朝后座看了看正在熟睡的沙很泰,凑过来低声问,“那你说说,我哪里变了?”
我说:“更漂亮了。”
萨菲娜“切”了一声,撇着嘴:“你真油腻啊!”
我能感觉到,她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高兴着呢。
我想说,要不咱俩试试,忍住了。
接下来的路程,几乎就是她在说单口相声,导师催论文如何残酷啦,舍友同时谈了几个对象啦,去出差的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啦……
车子开到奇台商业街,沙很泰在后面打了个哈欠,问:“到了吗?李约哥。”
我说:“你是闻到木丽德尔的味道了吗?睡了一路,到地儿就醒。”
萨菲娜又笑。沙很泰上初中的时候跟木丽德尔是同桌,因为说木丽德尔身上有味道被她“记恨”了好些年。直到沙很泰上大学后,两个人谈了恋爱,木丽德尔提起这事儿还要掐着沙很泰的耳朵让他道歉。
沙很泰摆摆手,说:“哎呀,你们不要笑,木丽德尔身上只有香水味。”
我跟萨菲娜连忙摆手:“不知道不知道,到底是啥味道,只有你知道,我们哪里知道呢。”
沙很泰气得不说话了。下车的时候,憋出一个词儿:“猥琐!”
木丽德尔已经在店门口等着了。她热情地跟我和萨菲娜问好,把我们迎进饭店,又把沙很泰的背包接在手里,用哈萨克语跟沙很泰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话。两个人这么久没见,有些拘谨,礼貌得像是刚认识的朋友。
这是沙很泰和萨菲娜回到奇台的第一顿饭,木丽德尔点了大份的大盘鸡、烤肉、洋芋鱼鱼子和一些素菜,桌子上摆得满满的。
沙很泰跟木丽德尔坐在那有说不完的话,我跟萨菲娜只是闷着头吃饭。
我说:“沙很泰,你们俩这么久没见了,一会儿吃完饭在县城里先转转吧,八点左右我来接你们。”
沙很泰正要说话,木丽德尔开心地直点头,说:“行呢,李约哥。那你带姐姐逛一逛,咱们赶天黑回去。”
吃完饭,我跟萨菲娜去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些水果和纸钱,开车去奇台喇嘛湖公墓。
路上,萨菲娜的情绪有些低落,右手扶着额头朝车窗外看。
我说:“萨菲娜,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她是你高中时期的好朋友……”
萨菲娜突然问:“你说,要是陈甜还在世上的话……”
我说:“那可能,可能跟你们一样,在北京上学呢。”
过了半天,她说:“是啊,要是她还在的话……她学习那么好,人也很好。”
高三年级成绩第一的女生陈甜投河自尽,传言是因为早恋。她的对象我们见过,是校外一家KTV的服务生,长得高高帅帅的,经常骑着摩托车来接陈甜放学。那个男孩在冬天出了车祸,当场死亡。同学见到陈甜都绕着走,私下议论她不检点。没多久,学校里又传陈甜殉情。
萨菲娜说:“放屁!陈甜是被那些家伙的流言蜚语逼死的。”
我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探进裤兜摸出一支烟,衔到嘴里,说:“马上到了。”
车窗外,新栽的林带急速后退。不远处的那块高台就是喇嘛湖梁了。萨菲娜突然问:“你说,为啥这个地方叫这么个名字呀?”
我想了想,说:“这个地方可有历史了,以前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会儿,人要进古城子,就在这儿卸驮子,也算是个大的巴扎呢。”
萨菲娜说:“是吗?看不出来啊。”
我说:“这个世界一天一个样子,那都是多久远的事情了,哪能让你看出来呢。”
萨菲娜说:“这个地方离蒙古很近了。”
我说:“就是,据说以前这梁上还有个喇嘛昭呢,蒙古人还在这个地方办‘那达慕大会’,可热闹了。”
萨菲娜望着车窗外面,过了一会儿,说:“现在,这个地方建公墓了。”
气氛有点沉闷。我开玩笑:“说明这个地方风水好啊,政府在这个地方修路、搞绿化,估计以后要大力发展这个地方了。”
萨菲娜点点头。我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摇下车窗,想把烟头扔出去。风猛地吹进来,烟灰被吹得到处都是,有几点火星掉在我的裤裆上,我急忙低头拍打。
“李约——”我听到萨菲娜喊我的名字,那声音是尖厉的。车身剧烈晃动。我猛打方向盘,看到夕阳在车窗外急速旋转。
我什么都听不到了,耳朵周围的空气像被抽干。我看到红色的太阳光闪过萨菲娜的眼角,钻进她张大的嘴巴。
我喊她的名字,但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我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
这个场景似乎出现过。我努力回想,看见我的身体回到了高三那年。对,就是那一年,陈甜出事后,全校整顿校风。萨菲娜因为经常跟我一起坐车回家,被同学举报说我俩谈恋爱。在年级主任的办公室门外,她面向老师站着,潮湿的目光偶尔掠过老师的头顶,看向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我,就像现在这样。我张大嘴巴叫她的名字,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早恋,在高中校园里是禁忌。无论你心里的爱多么真挚,在老师和家人的眼里都如洪水猛兽,好像会立刻吞噬掉一个人全部的人生。十六七岁的我,无力对抗尖刺样的窥视,也不敢耽误她可预期的璀璨人生。
昏迷的一周时间,我躺在云做的床上,发着白光的圆形灯在头顶昼夜不熄。每一朵云床上都躺着人,没有具体样貌,也没有性别和年龄的分别。我们都不说话,一次次朝云下张望。昏迷后的第三天,我听到云床下有很多人喊我的名字。我的云床被那些喊声拽着,像被渐渐收回地面的风筝。在我的周围,有些云床迅速升高,最后融进白色圆形灯发出的光束里。我的云床缓缓降低。第六天的时候,几乎已经紧贴到地面。晚上,白色的圆形灯熄灭,天空像黑色的布幔展开。紧接着,星辰渐次出现,那是一双双焦急的眼睛。我醒来的时候,先是看到了萨菲娜,然后是我爸妈,还有沙很泰和木丽德尔。
我试着张了张嘴,想要说话,脑袋疼得厉害,下巴也是。我想问他们:“你们在和我做最后的告别吗?”
萨菲娜撇了撇嘴角,她好像要哭,强忍住了。
“李约哥,你真是把人吓死了!”沙很泰说。
我看着沙很泰和木丽德尔,心里对我这个好兄弟生出一些羡慕的情绪。
后半夜,大家都去休息,萨菲娜坚持留下来陪我。我跟萨菲娜说:“这个暑假,我可能没法爬到屋顶上陪你晒太阳了。”
萨菲娜好像在笑,我听到气流从她唇齿间轻轻擦过的声音。她小声说:“我带了瑜伽垫和露背运动衣。”
噢,我的心飞到我家屋顶上去了。
萨菲娜的暑假只有四十二天,半个多月都在医院陪我。她喂我喝水、吃饭,扶着我去卫生间,完全照顾起我的饮食起居。
萨菲娜用暖水瓶从开水房接水,把开水倒进白色的塑料盆,掺进凉水,搓洗毛巾,为我擦拭全身。我有点不好意思。她说:“你别磨磨叽叽的,搞得我占你便宜了似的。”
她去卫生间倒水回来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阿姨说:“你媳妇儿对你真好呀!”
萨菲娜站在床头,看看阿姨,又看看我。我们相视一笑,谁都没有解释。萨菲娜走过来,帮我盖上被子。
我压低声音,说:“我的身体对你没有秘密了。”
她瞪我一眼,坐下来,端起放在床头的一次性饭盒,舀了一勺稀饭,吹走上面看不见的热气,说:“你可闭嘴吧。”
我睁大眼睛看她,她说:“张嘴。”
出院那天,沙很泰开着他爸的车来接我们。他用轮椅推着我去停车场,吃力地把我抱到后排座位,说:“别人出院瘦好多,你咋好像更胖了?”
我看到萨菲娜的脸上闪过笑意,很得意的样子。好像把我这个住院的病人喂胖,就是她取得的好成绩。
回去的路上,我叮嘱沙很泰开车慢一点。萨菲娜说:“你现在知道怕了?”
我说:“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等我好了……”萨菲娜的手穿过我的后脑勺,轻轻捏紧我的肩膀。
我不敢再说话,我怕那小小一掌的温暖从身上消失。我喜欢她手掌渗出的细汗渗进我的皮肤,我的血会带着那温暖游走周身,抵达我的心脏。
“有点晕车。”我靠着她,额头抵上她的下巴。
“真难伺候的,你。”她说。
每天下午六点,萨菲娜都会准时到我家来。出院一周后,我尝试着下地走路,但萨菲娜不肯。她在院子里打开轮椅,搀扶着我坐上去。她推着轮椅,我们在蒙根布哈村的巷道间漫步。妈妈说:“萨菲娜对你真真可以呢!要是他爸……”
爸爸打断她的话:“娃娃嘛,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路上,我问萨菲娜:“你爸爸知道你来看我吗?”
她说:“知道。”
我问:“他没说啥?”
她说:“你是因为我才这样的,他能说啥?”
我说:“我心里愧疚得很。”
她说:“你现在跟大爷似的,会愧疚?”
我说:“我愧疚的不只是这一件事情。”
她问:“还愧疚啥?”
我说:“我这个人得很,你没发现吗?”
她说:“你本来就是个人。”
我说:“你这是骂人的话。”
她说:“骂你咋了?”
我说:“你想骂就骂吧,我现在想勇敢一次。”
她没有说话,推着我继续往前走。
我继续说:“萨菲娜,我喜欢你。咱们上高中那会儿,我就喜欢你,你心里肯定知道吧?”
她说:“我不信。”
我说:“我发誓。真的,要是这句话是假的,我就出车祸死掉!”
萨菲娜停下来。我昂起头看她,她的眼泪聚在眼窝里,像草梢上颤抖的露珠。
我相信眼泪。
柏油路在朝北最后一栋黄色房子后面突然消失,沿着马来戈壁的边缘向东西方向散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T字。戈壁上嶙峋而立的碎石像海上的浪花,风把碎石间孱弱的矮草吹得发抖。
傍晚,她搀着我站起来,往戈壁深处走了几步后停下。我们朝向西边,看着蛋黄似的太阳滑进天山。夕阳全部跌入山中后,留下通红的云彩和金色边角的雪山。余留的光从天山上淌下来,为生长在马来戈壁上的梭梭树、骆驼刺镀上金汤。这片土地如此荒芜,又如此富贵。
我看到不远处那栋被牧民废弃的土屋。上小学那会儿,我们经常去树下玩。现在,门前的老榆树已经长成一围粗,树冠分成两枝,一侧的分枝干枯,另一侧却生机勃勃。
我们横穿碎石铺的小路,绕过屋侧用木桩围成圆形的区域。以前,这儿是屋子的主人圈羊的地方。屋后的馕坑早已塌陷,露出烧黑的炉壁。我们站在老榆树下,看到树上结满大大小小的鸟巢。窗玻璃是破碎的,上面有泥水晾干后留下的污痕。
萨菲娜走到树下的矮墙边,朝墙外张望。我走进屋内,里面一片狼藉。屋子的主人离开后,这里成了流浪猫、老鼠和夜鸟的乐园。我不担心有蛇,我从来没有在马来戈壁上见过蛇。板床上的羊毛毡被随意卷成一团堆在角落,旁边是一副损坏了的马鞍。我挪到板床上,扯开毡子坐在上面,顺手拿过马鞍,吹去上面的灰尘。
萨菲娜喊我的名字。透过窗户,我看到她正往这边走过来。她穿着黄泥色宽松牛仔裤和黑色V领针织长袖,松软的头发从耳前垂下来。她责怪我不该一个人跑到屋子里来。她扶着门框,探头进来,让我不要待在里面。
她说:“李约,你啥时候能改掉乱爬别人床的习惯?”
我反问她:“我啥时候有这个习惯了?”
她说:“换个脑子吧,你这破玩意儿多半是废了。”
我看着窗外,夕阳透过榆树的叶子,流进屋里。我说:“真好看。”
“什么?”她走进来,踩上板床,一屁股坐在我的左肩上。
“你把我当牲口骑呢?我是个病人哎。”我轻晃肩膀,像小时候试图摇落藏在树叶下成熟的杏子。
“哎哟,”萨菲娜抽走我手里的马鞍,“您还真别说嘿,这不一水儿齐了吗?”
“嗨,”我也学她的京腔,“您这真是够讲究的!”
我想起出院那天回家的车上,萨菲娜用她小小的手掌捏紧我的肩膀。她给过我小小一掌的温暖,她手心里的细汗流入我的心脏,到这会儿终于沸腾不止。
我把她扯进怀里,抱着她,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太想你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忍不住哭,“萨菲娜。”
萨菲娜趴在窗台上,一直到残阳落尽。她穿着露背的运动衣。马来戈壁上开始下雨,风把雨水吹进破碎的窗户,落在她平滑的脊背上。我们彼此紧扣的手伸出窗外,想让时间停下。
雨不会一直下,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雨水会渗进沙子,但不会平白消失,只是藏进很深的地方。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