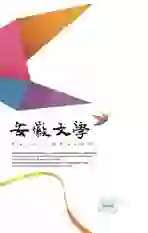推开悲伤的记忆窄门
2025-02-11彭正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说:“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由此视点观之,短篇小说《软壳城堡》中主人公老六“当前”的身世命运里自然包蕴着过去不同时代“时间的选择累积”。尽管只是一篇短制,文本的“故事时间”却从改革开放的9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历时30年之久,这赋予了短篇小说难得的历史感。不仅仅是历史感的获得,《软壳城堡》承载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图绘了过去年代的精神谱系,并深度勘测特定生存境遇下的人性渊薮。小说推开了悲伤的记忆窄门,呈现了丰富的时代表情。表情的背后则是时代的心理、精神和广阔社会生活的深层肌理。
小说从当下的同学会开始,自然触及往昔同学的当下生活状况。于是,记忆的窄门经由“我”打开,老六过往时代的种种生存图景被一帧帧地翻出。按照沃尔特·本雅明的说法,具有一定历史感或历史意味的文本,重要的不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描绘过去,而在于“捕获一种记忆”。因此,对老六大学时代及其后来生活的记忆自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小说叙述反复申明,由于年代的久远、记忆的模糊或酒精的挥发,很多往事“在回忆里绕来绕去,像迷了路,找不到现在或将来”。这自然是作家的叙事策略,或者说作家深谙本雅明的记忆诗学观:一切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是记忆主体对记忆客体有目的的捕获,在此过程中,有很多放大、凸显甚至虚构,也必然会有很多遮蔽、化约甚或舍弃,原生态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小说中老六“本来的样子”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叙述者/记忆者试图呈现给读者怎样的主人公命运及其幽微的人性隐秘。
老六的大学时代,刚刚明确大学不包分配,大概是1996年前后。作者蒋诗经是1970年代生人,刚好大学时代是在1990年代,因此他这篇小说的叙事经验应该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是相契合的。1990年代改革开放已到了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乡下人进城已然成为一种潮流,但城乡区隔、二元对立的壁垒仍然森严。老六的大学生活、他的贫困遭际深刻反映了城乡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带来的生存状貌与历史境遇。为了能在大学里生存下去,老六翻捡垃圾、到工地打零工、贩卖磁带与碟片、遭受屈辱与不公,所有的这一切源于城乡的结构性对峙,并造成了他对贫穷的敏感与异样的自尊,他无处消化自己悲苦的生存感受,只能在长年不撤下的蚊帐里暗自疗伤,蚊帐成了他赖以生存、抵抗外界侵袭、疗愈身心的“软壳城堡”。来自“我”的记忆,陈红的记忆,阿毛的记忆无不选择性地呈现老六贫穷、憋闷、屈辱的那些细节与场景,尤其是深夜他在翻捡垃圾时被看完电影回来的同学们撞见的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为何文本推开记忆之门都毫不迟疑地指向老六的悲伤与贫穷?一方面,作家试图通过选择性的记忆诗学,揭开市场化改革“半张脸的神话”另一半的精神面影——伴随着风起云涌、朝气蓬勃的改革神话构建,阵痛、悲伤、喑哑甚至不公也如影随形。一方面,小说也借此记忆叙事,一步步强化老六在内心对“城市”和“乡村”之间对抗关系的想象与认知,这也为后文他因为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极度地自尊与敏感,报复性地强奸了自己喜欢的大学生林幺妹做足了铺垫。原来大学生林幺妹不是出生于乡村,而是冒名顶替了乡村的林幺妹才上了大学,并凭借顶替来的贫困县学生身份顺利申请到了助学金,而真实的林幺妹则沦落为美容院的小姐。余华有一部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部作品试图“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余华以杂文的形式直陈“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生存和命运的巨大差距,在1990年代尤为触目惊心,这篇小说由此触及了深邃的时代主题,它将个体的命运故事经过转喻或者转换,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总体命运,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表情。因此,小说里关于老六因为真假林幺妹的命运所激起的对于社会不公的极大愤慨,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一个偶发的事件,他对林幺妹的强奸报复,不是爱而不得的结果,而是以此极端的行为对冲命运的不公,即便为此被捕入狱,也无法消解这样的冲动。此间的报复,生理/身体力比多冲动被置换为阶层/阶级力比多冲动,生物学意义上的行为上升至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层面,小说主题意蕴的厚度遂由此得以大幅度增加了。
出狱后老六的命运逐渐走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故事框架,在“城乡一体化”的时代浪潮中,他不说混得风生水起,也算游刃有余。他开上了奥迪Q7,成了建筑公司的老板,可以说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红利的一杯羹。然而,这个阶段,社会阶层生活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但那是资本时代的不公,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不能再全部归咎于城乡之间的对立与阻隔了。只是,老六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些悲伤的记忆、过往的生命经历与心理症候已经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当下即历史的延长线,无论是个人抑或集体与社会。此后,出狱归来的老六一系列看似不合情理的行为,如果放在其心理逻辑与创伤记忆的纹理中去观察,就合情合理了。比如他对婚姻看似十分随便和草率的态度,实则暗含了他对当初自己鲁莽、暴虐行为的赎罪,他主动去找沉沦风尘的真实的林幺妹,他对小姐陈红的婚姻承诺以及之后的婚姻状况,无不掩藏着自己内心无边的悲伤与愧疚。他已经无法摆脱往昔的旧伤和精神暗疾,无法轻松无碍地投入没有历史记忆负重的当下生活。他就是自己的历史、记忆、悲痛、忧伤与当下糅合的产物,曾经的时代与生存境遇已经在其灵魂深处烙上了难以抚平的疤痕。心灵已然破碎,当前的生活让其重新粘连在一起,实则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灵魂。他之所以不愿让“我”在同学们面前提及他,不愿让同学们谈论他,就是因为他无法直面记忆中不堪的自我,往昔生活与尊严的破碎。小说的文本叙述打通了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当下,在彼此互文的叙述中,展示了时代的沿革以及丰富表情背后的人性真相。
小说的艺术表现亦可圈可点,个体的故事与命运融入了深广的时代内涵。老六、林幺妹、“我”、陈红等个体的生命时间负载着足量的时代文化内涵与精神符码。个体生命时间的流逝折射出时代与历史的沿革与流变。三个人物的回忆性视角和日记的视角共同拼贴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生命故事。不同视角的选择体现出作家不俗的艺术构思:“我”作为老六的同学,负责选择性地回忆他大学时代的生活以及后续的交往,直至参加完老六的葬礼,这是一个见证者、知情者的视角;陈红作为老六的妻子,她以对老六的不理解从另一面揭示了老六真实的精神世界,她的不理解恰好是对老六生存真实的反证,这说明老六并没有把自己的内心交给陈红,或者说老六不认为陈红会理解他的境遇、懂得他的情感世界;阿毛作为老六的弟弟,通过他的补充性记忆,填补了老六上大学之前的家庭状况以及出狱后的种种现实,为完整勾画老六的生命轨迹起到了必要补充;日记则可以视为老六自己的记忆与视角,它虽然凌乱、潦草,甚至语言不够连贯,有时像梦呓一般,可它是一个内部的灵魂视角,为我们揭开老六真实的内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这几个视角的选择是相互补充的,共同描画了老六的生命图景,不同的记忆性叙述明显带有倾向性、选择性或者说捕获性,它们共同完成了别具特色的回忆叙事与记忆诗学。有意味的是,小说多次写到老六遗体的笑容,写他“嘴角的一丝笑意,反而比平时的笑更坚固”,写他“依然顽固地笑着”,直至小说的结尾也是这样收束的:“我甚至看到他躲在蚊帐后对我露出个模糊的笑。那份笑意,竟然和他离世时脸上的笑容一模一样。”小说为何反复摹写老六离世的笑容?我想,这也许是作家想以此让其笔下的主人公不再被现世的悲伤、痛苦所折磨,他终于走出了自身的禁锢与枷锁,终于实现了对既往所有不堪、欲望、愧疚、罪孽的超脱,可以安详地走了。
由上述分析不难判定,这是一篇质量令人满意的作品。
(本评论为安徽省 “江淮文化名家”领军人才培育工程项目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