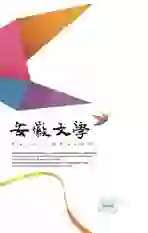形式的“完备”难掩内在逻辑的失洽
2025-02-11陈振华
从表面上看,短篇小说《软壳城堡》似乎还说得过去:小说中的“我”既是叙述者,也是见证人,还是小说中串联故事的线索人物,在“我”的串联之下,主人公老六的故事从依稀模糊到逐渐清晰,较为完整地浮现在读者面前,“我”的叙事功能算得上合格;多个人物视角再现了老六悲戚而喑哑的人生图景,其中“我”的视角,陈红的视角,以及阿毛的视角起到了主要的复盘作用,各个视角之间的切换与交织也算得上自然;小说中多个视角还原的老六的人物形象、性格和命运也令人印象较为深刻,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而言,尽管达不到典型的高度,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老六的蚊帐作为“软壳城堡”的隐喻,对揭示人物的命运尤其是心理症候也颇有意味;小说对改革开放1990年代的社会生存景况有较深入的刻绘,尤其是对大学生活的描摹比较真实具体;此外,小说的叙述调性、语言以及小说故意抖落的元叙述技巧也略见功力……由此可以认定这是一篇颇具水准或新意的佳作吗?
且慢!小说经不起认真的细读和推敲,尽管表面上小说形式比较“完备”,文本看似成熟,其背后,实则有着内在叙事逻辑在关键节点的失洽,这给小说带来了致命伤。小说并没有抵达众妙毕备的境界,而是主要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与情感的设置明显背离正常的事理和生活逻辑。
首先,叙述者“我”(也就是文本中的三哥)和老六之间的关系状态、情感深度、交往铺垫远未充分。小说选中“我”作为叙述者,从情节的发展到结构的设计自然合情合理,“我”是“软壳城堡”主人公老六的同学、室友,见证甚至部分参与了老六大学时代的生活,是其大学生活的历史在场者,也是其生活、心灵真相的后期知情者。然而小说中的老六,因为家庭、个人、贫穷、时代等各种窘迫情况的叠加,他在大学时代有过屈辱的经历,最终还因为强奸罪被捕入狱。出狱之后他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更是在同学圈中杳无音讯长达20多年之久。突兀的是,毕业20年之后,他突然之间主动联系了“我”。“我”尽管知道老六老家的地址,但毕业后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主动寻找他的愿望与冲动,可见,“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是普通和一般的。那么问题来了:老六为何在20多年后主动联络“我”?并多次告诫“我”,不要将他和“我”之间的交往告诉任何其他同学。由此看来,他在心理上是拒斥和往昔大学同学交往的,甚至不愿让大学同学知晓他的任何讯息。既然他选择了“我”,这说明“我”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惜的是,小说中关于“我”和他之间关系的描写仅限于室友关系,远未达到他向“我”倾诉生命中最隐秘的情感,甚至告知其命运真相的程度。作家在编织故事的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叙述中找补:“我和老六大学时的关系算不上亲密无间。老六和谁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好,他总喜欢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酒后和我说过,之所以20年后还会找到我,就是喜欢我和人相处的边界感。”在我看来,仅仅这一句叙述上的找补,很难匹配后文中“我”对他故事、情感与命运的深度介入。文本欠缺的是“我”和老六在大学时代情感、命运甚或秘密交织的“前史”,如若添加充分的二人特殊关系的书写,那么小说在设置“我”的角色和功能的时候,就不会显得牵强,叙事逻辑也会自洽很多。
其次,小说中老六和林幺妹之间的关系及其纠葛的设置也有些匪夷所思。老六和林幺妹并非一个班,只是因为老六翻垃圾捡到了林幺妹的钱包上交给保卫科的马干事,后因为钱包里面200元的去向问题,林幺妹才闯入了老六的生活。故事一波三折,老六的被冤枉与受辱,寝室众兄弟的义愤填膺以及老六艰难的生存处境,直至后来摆地摊卖磁带和碟片维持生计。卖碟片的生意遭遇到了滑铁卢,这个时候林幺妹挺身而出,买了老六地摊上所有的碟片。这个时候老六对林幺妹出现了若隐若现的情感上的暧昧。叙述至此,并没有违背那个年代的实际生活状况与情感逻辑。问题出在随后的情节设计及老六的人生命运走向上。老六托阿毛转交给“我”的日记,最终揭示了老六为何强奸林幺妹并致使她羞愤难当下自杀,老六自首并锒铛入狱。从小说布局谋篇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结构设计确能体现作家的艺术匠心,但这不是艺术营构的问题,而是人物本身的行为动机、行动逻辑出现了与现实可能性的巨大偏差。在美容院,老六遇到了另一个林幺妹,她和大学生林幺妹来自同一个县,之后才获知真相:大学生林幺妹原来是冒名顶替才有机会上大学,而真正的林幺妹则沦落风尘。于是小说有了下面的情节:老六把大学生林幺妹单独约到后山,在黑暗与残暴中完成了对林幺妹的奸污。显然,这样的情节设计是作家刻意的安排,以这种极端的处理方式或命运反转来强化小说的冲突性与悲剧性,没有顾及情节的合逻辑性与人物命运的可能。我试图以各种阐释给予这个结局以逻辑自洽的合理性,然而发现很难。如果说老六单恋大学生林幺妹,文本中确有相关的叙述与心理描写,但凭借着老六的正义与善良,他不可能有如此下作的行为;如果是因为大学生林幺妹冒名顶替了农村的林幺妹,导致了真实的林幺妹凄楚的命运,他的施暴行为是一种报复,然而这样的报复完全背离了方向,只能解释为老六的丧心病狂;如果仅从主人公对贫穷的敏感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看,他的强奸行为更是与合目的性的诉求南辕北辙。质言之,这个所谓的强奸施暴的行为及其后续故事,无论从情感、人性、阶层、正义还是从人物的性格、处境来看,都有点匪夷所思。而恰当的、符合主人公性格逻辑的情节应该可以考虑:主人公尽管暗地喜欢大学生林幺妹,但他还是克服自身的情感藩篱,勇敢地、不顾私情地揭示出事情的真相。随后,再有相应的故事后续及人物的命运起伏,如此,可能逻辑上更为合理和自然。
再次,小说中老六与陈红之间的关系也令人诧异莫名。出狱后的老六,执意要去娱乐场所找寻真正的林幺妹。其真实动机或许是为了死去的大学生林幺妹赎罪,或许是对现实的林幺妹的补偿与拯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作主观的猜测。顺此理,叙述也算符合人物的心理症候与情感逻辑。可惜的是没有了后文,老六寻林幺妹未果,遇到了作为小姐的陈红。令人诧异的是,简单接触,老六竟然乐意娶陈红为妻。这不是浑不吝的玩笑,而是付诸了真实的行动,难道就是因为陈红的身份是小姐?或者不是陈红,任何一个小姐都可以?那么找寻真正的林幺妹的意义何在呢?老六不是救世主,不可能解救所有深陷风尘中的女子。因此,小说的这一情节设计再一次出离了我的认知逻辑。文本叙述一方面在不辞辛苦地建构老六的生存意义与情感心理,一方面又在情节的编织中无形地解构了他性格逻辑的完整性。为何林幺妹就轻易地置换为陈红?而且没有前后的铺垫与说明,仅仅是因为这一次没有遇到?如此随意,对塑造特定境遇与时代情境下的人物形象,显然是欠缺整体性考虑的。这不仅仅消解了故事的悲剧性意蕴,也明显违背了主人公性格的统一性。从通篇的叙述看,老六是敏感的、自尊的,甚至充满正义感的,尽管贫穷导致了人生的悲剧,但他也是有自赎的动机和行动的。只是,一些不合逻辑的情节与人物关系设定破坏了小说总体性审美价值的生成。
罗兰·巴特曾经在《写作的零度》中说:“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 短篇小说《软壳城堡》确实把个体的生命(老六的、林幺妹的)变成了一种命运,在“我”的、陈红的、阿毛的记忆叙述中,文本还算清晰地呈现了老六的命运走向。在长达3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家试图给我们解码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性真相、生存状貌、心理现实与情感真实,可谓用心良苦,想赋予流动的时间以意义与向度,赋予时代以丰富的内涵。巴特告诫我们的是,文本不仅仅是形式的搭建与字词的游戏,它必须有充沛的社会内容的嵌入,才能赋予文本以真实的意义。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文本嵌入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还不够,还必须是合逻辑的鲜活的人、事、物的生活世界,而不能为了拍案惊奇,为了故事的传奇性、读者的猎奇心理而牺牲生活本身的内在逻辑。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