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声乐比赛:如何准备国际声乐大赛
2025-01-31曾震宇
我曾在《四大声乐比赛:中国选手做错了什么?——与声乐师生恳谈》一文中谈到,世界上的重大声乐比赛都有自己的个性。但由于语言障碍,国内对这些显著的不同缺乏敏感,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不同的评价标准没有足够的讨论,更缺乏如何赢得比赛的路线图。这样的备赛可谓挂一漏万。
如今,音乐比赛的激烈程度不啻体育比赛,很难想象短跑或举重运动员不进行系统训练就贸然参赛,而这往往是中国选手参加音乐比赛的常态。所以,我希望就此文,仅就各大声乐比赛的曲目要求举例,谈谈如何理解各大赛事,并对不同比赛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

米里亚姆·海林声乐比赛
米里亚姆·海林声乐比赛(The Mirjam Helin Competition)是著名的声乐比赛,以标准高、曲目要求高、奖金高(第一名奖金50000欧元)、评审团有分量而闻名。许多如今世界一线的歌唱家,如巴尔(Olaf B?r)、嘉兰莎(Elīna Garan?a)、帕佩(RenéPape)都曾是该大赛的获奖者。中国选手方面,梁宁(1984)、袁晨野(1994)曾获该赛事的第一名,迪里拜尔(1984)曾获第二名,傅海静(1984)曾获第三名。2024年,25岁的女中音徐晶晶犹如一匹黑马,在众多强手中夺冠。这也是袁晨野夺冠30年后,中国选手再次问鼎米里亚姆·海林声乐比赛。
大赛的组织者是芬兰文化基金会(Finnish Cultural Foundation),以芬兰最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米尔亚姆·海林(1911—2006)的名字命名。米尔亚姆·海林没有孩子,决定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芬兰文化基金会,用于创立声乐比赛。大赛自1984年来,每5年举办一次;从2024年起,该大赛将每3年举办一次。

以2024年的米里亚姆·海林声乐比赛为例。比赛的选手年龄限制为32岁以下。首先参赛者需要向赛事组委会发送简历和视频,组委会从来自57个国家的485份申请中选择56名选手(韩国选手13名)进入现场比赛。初赛阶段,每位选手演唱20分钟,其中至少演唱1760年以前的作品1首(受难曲、神剧、弥撒或康塔塔选段),歌曲2首(德语艺术歌曲至少1首),歌剧或音乐会咏叹调1首;16至20名选手进入复赛,复赛阶段选手演唱不超过30分钟,须演唱芬兰作曲家创作的歌曲1首,时长15至20分钟的艺术歌曲1组(可以是同一作曲家,也可以是不同作曲家),咏叹调(歌剧或音乐会)1首;6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选手演唱不超过20分钟,演唱咏叹调(歌剧、神剧、康塔塔或音乐会)至少1首。在比赛中,所选曲目必须包含3种语言,且同一曲目只能演唱1次。米里亚姆·海林声乐比赛考察选手把握各个时期、各个语种的作品的基本功,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家的金钟奖,但曲目量远大于金钟奖。
也许有人会觉得演唱芬兰作曲家的作品是备赛的难点,其实不然。芬兰作曲家的作品既可以用芬兰语、瑞典语演唱,也可以用英语、德语的译文演唱,而且组委会还提供了推荐曲目列表。

真正难的是演唱一组15至20分钟的艺术歌曲,这非常考察选手的策划能力。什么样的曲目最能够展示选手的水平?评委和观众希望听到的是什么?诚然,可以演唱一组声乐套曲,但这样可能并非最佳选择。法国高男高音冈萨雷斯(Logan Lopez Gonzalez)的选择令人印象深刻:他选择了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的一组诗串起主题,而作曲家分别是德彪西、福雷、哈恩(Reynaldo Hahn)和瓦雷兹(Edgard Varèse)。遗憾的是,由于连日比赛的疲劳,他在半决赛最后阶段的演唱明显力不从心。我问他为什么做这一选择。他告诉我,这是他正在策划的一个项目,因为他真的很喜欢魏尔伦的诗,很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他的态度让我深深记住了他,并更加期待在剧场里可以看到他的表演。
徐晶晶是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比赛,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她直到不断进入下一轮、了解了其他选手的实力时才感到害怕,甚至时时刻刻略显莽撞和笨拙。首次参赛即获得第一名,徐晶晶做对了什么?她的经历为什么能对中国选手的备赛有所启发?

徐晶晶来自十分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贫穷的家庭。在南京艺术学院读本科的时候,她的专业老师是周洁副教授。周洁对她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培养,一次暑期带她去美国学习,更让她见识到向音乐大师学习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情。自此以后她更用功,攻克了英语并拿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奖学金。她不断地努力学习,并不清楚自己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因为她的生活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父母的想象,而父母也无法给她任何经验来借鉴。像徐晶晶这样的平民儿女的故事不断发生,这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如果她缺乏对未来的想象,仅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就永远都看不到窗外的风景。徐晶晶在音乐中钻研,她的单纯和决心散发着了不起的光芒。她在众多选手中显得异常可爱,极具观众缘。米里亚姆·海林曾说的“一抹微笑、甜美的外表和自然的气质足以营造出一种魅力。明星不是靠后天培养出来的。明星的魅力来自歌手自己的意志和决心”,这个描述用在徐晶晶身上非常贴切。

日内瓦音乐比赛
日内瓦音乐比赛(Concours de Genève)创立于1939年,是世界最早、影响最大的国际音乐比赛之一。德·洛斯·安赫莱斯(Victoria De Los Angeles)、阿美林(Elly Ameling)、凡·戴姆(José Van Dam)、米莉齐欧(Nelly Miricioiu)等人只是获奖者中的一部分。中国女高音姜咏曾获得日内瓦音乐比赛“歌剧大奖”(1989),亦是迄今唯一在声乐领域获得该奖的中国选手。

2024年度的日内瓦音乐比赛有31名选手入围初赛,包括5名中国选手。在完成视频选拔之后,2024年的首轮比赛在网上进行,所有选手自行录制25至30分钟视频,其中包括歌剧咏叹调2首、清唱剧及宗教音乐类咏叹调1首,艺术歌曲2首,要求至少包括3种不同语言、3个不同时代,且其中1首必须是1950年以后的创作。淘汰堪称残酷,只有8名选手入围现场半决赛,3名选手入围决赛。我向赛事的秘书长施诺克(Didier Schnorhk)请教:“众所周知录音和现场听感有极大区别,那以视频的形式完成初赛,且淘汰率这么高,遴选结果是否令人满意?”他的回答是:“现在全世界对环境非常关注,邀请全世界30多名歌手坐飞机来日内瓦就只唱几首歌便淘汰的这种模式不再能继续。而且除了声音以外,还有很多评判重点,譬如语言、音乐能力、对作品的理解、表演等等。”的确,无论是对环境问题的敏感,还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暂时萎靡,大概越来越多的比赛将会缩减现场环节。中国选手也应准备好应对这一变化。
日内瓦音乐比赛的半决赛,要求十分庞杂。若中国选手进入此轮,也会面临极大的挑战。选手须演唱1场30分钟以内的歌剧独唱音乐会,1场30分钟以内的艺术歌曲演唱会,以及准备1场个人艺术项目的展示和答辩,且此3项的得分以45%、 35%、20%的比例计入总成绩。在歌剧咏叹调方面,选手需要准备3种不同语言、3种不同风格的4至6首歌剧、轻歌剧或萨苏埃拉(Zarzuela)咏叹调,并且组委会强烈鼓励选手演唱尽可能多的种类;在艺术歌曲方面,选手需准备30分钟节目,包括1900—1940年间的女性作曲家的作品1首、当代风格的作品1首——并且演绎这首当代作品的时候,必须使用扩展的声乐技巧,采用非常规的发声方式,例如微分音、吟诵、音色变化、声音噪音等等;而个人艺术项目的展示必须是原创的,且与选手的个人艺术个性密切相关,他们陈述这一项目,并接受记者的采访。我问施诺克:“比赛的战线必须拉得如此之长吗?”他的回答是,时间足够长才有可能真正有时间去了解每个选手,并为他们提供帮助。这也是他从2000年开始倡导的一种新的比赛模式;而对现当代作品和女性作品的要求,也在于培养选手对业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敏感性,而且在这些领域,的确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我对施诺克说,从日内瓦比赛的比赛方式来看,其很显然选的是全面的“音乐能力”而非“潜力”,因为太年轻的选手可能连曲目的要求都无法达到。施诺克表示赞同:“既然是5年才举办一次声乐比赛,那就希望选出毫无争议的、非常成熟的、能够立刻被业界欢迎的人才。”声乐比赛与器乐比赛有着一定的区别,学习器乐的学生可能十几岁就能够举办独奏音乐会,而声乐演员需要加入不同的剧组与不同的人合作,没有足够的能力很可能会拖剧组的后腿。所以日内瓦比赛是选拔年轻音乐家,而非选拔音乐学生。
在本年度的日内瓦音乐比赛中,韩国选手的表现足以作为参照。有几个唱得很好的韩国选手,在歌曲独唱音乐会环节中,由于曲目储备不够,唱了20分钟左右就草草结束;在个人艺术项目环节,一名已经在耶鲁大学学习的选手,语言能力仍不够好,只能念稿陈述。与之相对比的是最终获得第一名的女高音祖尔弗吕(Chelsea Marilyn Zurflüh),她的嗓音条件毫无疑问不是最好的,但是她极为全面,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她演唱的贝尔贝里安(Cathy Berberian)作曲的《脱衣舞》(Stripsody)充满想象力,可以说她时而代言、时而评述,一个人就演出了一出小戏,观众反应极为热烈。在个人艺术项目环节,她又谈到了自己有塞舌尔的“根”,那里的海存在于她的血脉中,于是她选择与海和记忆有关的声乐作品策划了这场演出,并且她还邀请一名舞者跟她一起,把这场演出奉献给孩子们,激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同时她希望以音乐为媒介,与更广泛的观众建立情感联系、进行智力互动。她从容自信,而且项目可操作性强、易于落地,很明显是具有基层经验、并对自己的项目进行了深入思考,得到评委的认可在情在理。

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
1985年,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居特斯洛市(Gütersloh)举办了一场纪念贝塔斯曼传媒集团成立150周年的音乐会。活动期间,卡拉扬与利兹·莫恩(Liz Mohn)谈到了歌剧新秀培养计划的缺乏,并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德国很难找到合适的年轻歌唱家。1987年,莫恩发起了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Neue Stimmen International Singing Competition)。这个比赛现在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发现年轻歌唱家的比赛。获奖者包括女中音斯图茨曼(Nathalie Stutzmann)、男低音盖伊(Paul Gay)、高男高音法吉奥利(Franco Fagioli)、女高音茜耶拉(Nadine Sierra)等。中国男高音张龙(2019)曾获该赛事的第一名,男中音刘嵩虎(2003)、男高音夏侯金旭(2011)、男高音雷明杰(2017)获第三名。



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目前为两年一届,每届大约会收到1500份申请。自2013年起,音乐会按男女分组授奖。比赛流程为:选手首先向组委会提出申请,然后参加在世界多个城市举办的现场试唱;本届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有39名选手进入总决赛,并进行三轮演唱。曲目方面,申请人须从必唱曲目中选择5首咏叹调,并符合以下要求:来自4个时期中的3个时期(1600—1750、1750—1830、1830—20世纪初、20世纪)的咏叹调3首,以及不同歌剧的咏叹调(时期不限,且其中1首亦可从轻歌剧中选择)2首。而在每轮现场演唱时,则选手自选1首、评委选择1首。
媒体办比赛的思路,跟音乐人办比赛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音乐人注重音乐方面的专业性,注意选手技术的完善程度、耐力、对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等等,譬如米里亚姆·海林比赛既要求演唱歌剧咏叹调又要求演唱艺术歌曲,而且曲目量要求很大;而新声音比赛则只要求唱歌剧咏叹调5首,每一轮也只演唱2首,而且打分方面考虑的因素也细化到四项,供评委斟酌。这四项因素分别为:技能、音乐诠释(节奏、乐句、表达)、声音质量、艺术个性。打分后若出现平局,则评委根据年龄和发展潜力决定进入下一轮的人选。新声音作为一个赛事“外来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不仅召集了以各大剧院选角经理为主的评委团队,在舞台设计上流光溢彩,电视转播方面也毫无瑕疵,提供了另一种办赛模式。时至今日,新声音已成了最受关注的声乐比赛之一。
新声音的参赛者年龄限制是30岁,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是26岁左右。坦白说,这种年龄的选手并不完全成熟。加上在选手进入居特斯洛总决赛之后,终身只能参加一次的规定,必然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比赛结果:完美的歌手并不那么多,但那些具备一定实力、外表又美好的选手,展现出年轻人的非凡光芒。我与一名我在专业上非常信任的声乐老师一起观赛,很快就发现了我与她在评判选手方面的分歧。于是我跟她展开了一场比赛预测:预测进入半决赛的16名选手中,有哪8名能够进入决赛。结果,我猜中了7名,她只猜中了3名——长期的思维习惯容易让声乐老师过多考虑声乐技术,而忽略了其他。如果在场有其他声乐老师,预测成绩也不见得会好多少。新声音寻找的是有“星光”的人,联系到这一比赛对选手的长期赋能机制,从赛程设置到评价体系再到评选结果,逻辑完整,非常合理。

我与本次比赛的主要评委之一、萨尔茨堡艺术节选角经理维瑟(Evamaria Wieser)讨论比赛,她跟我说,中国选手近年来表现越来越好了,譬如这次就有6名选手进入居特斯洛的现场比赛。以往的中国选手不掌握任何外语,根本无法沟通、无法合作,所以很难以比赛为契机开始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很多在海外的中国歌者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情况。
其实中国选手已经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内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高水平的选手,另一类是已经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选手。在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Operalia)中获奖的卜乐就属于这一类。他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完成了本科,又进入了大都会歌剧院的青年艺术家计划。在他获奖之前的几天,重要的艺术经纪人、选角经理摩尔(P?l Moe)与我交流时提到了卜乐。当我告诉他卜乐进了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决赛时,他便预测卜乐可能会得奖。这说明,歌剧这个圈子,哪怕横跨五大洲,仍然很小。只要唱得好,业内人都会有所耳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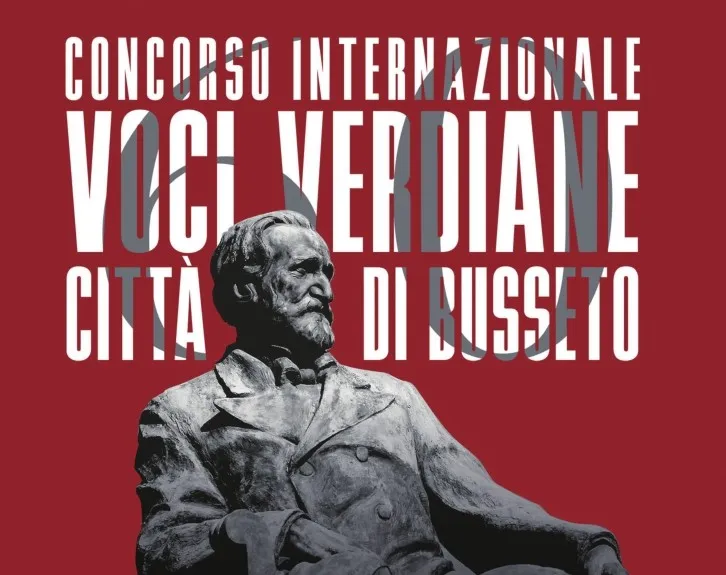

“威尔第之声”声乐比赛
“威尔第之声”声乐比赛(Concorso Internazionale Voci Verdiane Città di Busseto,又名“威尔第国际声乐比赛”),是意大利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声乐比赛,也是世界重要的声乐赛事。“威尔第之声”素以寻找能够胜任威尔第作品的歌唱家为使命,又由于曲目限制在威尔第作品范围内,且要求数量多,故被认为难度极大,亦被中国的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均认定为“国际一类艺术赛事”。“威尔第之声”的另一特点是评委会中有重要歌剧院的院长和艺术总监,因此候选人不仅有机会参加比赛,还能进行高水平的面试。参加“威尔第之声”国际声乐比赛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都取得了辉煌的职业成就,如拉斯皮纳(Rita Orlandi Malaspina)、古林(Angeles Gulin)、隆古(Irina Lungu)、阿拉加尔(Giacomo Aragall)、库比多(Alberto Cupido)等。“威尔第之声”声乐比赛历史上获奖的中国选手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和慧(2002)曾获第一名,程达(1993)、周凡(2018)、顾文梦(2019)曾获第二名,李环宏(2022)曾获第三名。2024年“威尔第之声”声乐比赛主要由帕尔马皇家歌剧院组织。剧院对赛事进行了改革,以往接受选手自由报名、几百人赴现场比赛,而今年增加了视频预选环节,将初赛选手限制在50名以内,这样就更加提高了比赛的竞技水平,同时评委的层次也继续提高,美欧两地重要剧院的艺术总监或选角经理担任了比赛评委。我深度参与了“威尔第之声”的组织工作,包括在中国设立“威尔第之声”中国选拔赛暨首届中国威尔第声乐比赛,因此对比赛要求更为熟悉:选手需要申报威尔第曲目5首。在初赛中,选手先自选1首演唱,评委也可以选择多听1首,曲目由评委选择;不超过24名选手进入半决赛;在半决赛中,评委指定1—2首曲目;不超过12名选手进入决赛;在决赛中,评委指定1首曲目。抽查的比赛形式对选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选手的比赛策略往往较为保守:在演唱了较难较长的曲目之后,他们希望能够演唱短小、唱起来比较轻松的曲目,因此在提交的5首曲目中含有篇幅较小的曲目。结果在决赛中,评委恰恰指定了他们演唱那首篇幅更短的曲目。选手们对此哭笑不得,也认为评委的选择客观上阻碍了他们的发挥,让他们表现得不够充分;但该曲目确实也是自己选择申报的,选手们有苦难言。

一谈到威尔第的作品,很多人的印象是必须是大而浑厚的声音才能驾驭,所以师生经常对威尔第的作品充满畏难情绪。其实不然,威尔第的前期、中期、后期作品有不同的风格,几乎可以说威尔第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非一个作曲家。甚至有人说,前期的威尔第作品要唱得像莫扎特,所以一些撑大的声音在演唱威尔第的前期作品时,就会有把握困难、风格不当的风险。“威尔第之声”评委、威尔第学院(Accademia Verdiana)学术总监伊佐(Francesco Izzo)亦认为:无论声音型号大小,都可以从威尔第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曲目参赛。他也在威尔第学院的教学中不断倡导这一理念。经我观察,目前中国男中音选手基本建立了相应的曲目,而男高音、女高音则应大力扩展曲目。
韩国选手崔芝银(Jieun CHOI)问鼎本届“威尔第之声”冠军没有争议。她声音条件出色,演唱连贯性极好,表演也非常成熟。中国选手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共有中国选手10名入围现场比赛,其中5名为中国威尔第比赛的3—5名,其他4名为威尔第学院的往届或在读学员。进入决赛轮次的11人中,有5名中国选手,最终男中音闫石获得第3名。
世界上较为重大的十几个国际声乐比赛,虽然都以发掘声乐后起之秀为使命,但各有各的不同。有的注重演唱,有的唱演并重;有的要求“成熟”,有的更喜“潜力”;有的寻找“星光”,也有的与经纪公司紧密合作。与此同时,所有比赛又都在以“可持续性”为目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比赛之时,不能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尤其不能武断地评判对错,而是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够利用好规则,获得更好的成绩。毕竟在比赛中获胜仍然是走上职业生涯最快捷的方式,我们也倚仗这些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的年轻人把中国音乐唱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