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电影到室内歌剧
2025-01-31张宝华

2018年,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三年级学生的胡一轩,凭借室内歌剧《调音师》,入选了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世界新音乐节(ISCM)暨北京现代音乐节(BMMF)。该剧根据奥利维耶·特雷内(Olivier Treiner)导演、编剧的微电影《调音师》故事情节改编,编剧为作曲家本人。当年5月23日,著名音乐家许忠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厅首演了该作品。2019年,室内歌剧《调音师》在汉堡由指挥家Bar Avni、歌唱家Pia Davila、Florian Wugk以及Symphoniker Hamburg Symphonieorchester der HfMT Hamburg 再次演出①。
在反复对比微电影剧情与室内歌剧脚本时笔者发现,虽然电影剧情与歌剧脚本的核心内容基本相同。但由于室内歌剧在舞台布景、时间、空间和演员人数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剧情处理上,室内歌剧的脚本应该比微电影更加凝练,这首先表现在精简剧本结构并合理规划戏剧性动作上。另外,在音乐不变、歌剧脚本不变的前提下,中、德两版室内歌剧在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和戏剧矛盾处理上竟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甚至二者的戏剧核心人物——主角都发生了偏移。如果说从微电影到室内歌剧的改编,体现了胡一轩的智慧,那么中、德两版室内歌剧所产生的诸多变化则主要体现了导演、演员对于相同歌剧脚本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
一、微电影《调音师》与同名室内歌剧之戏剧脚本比较
提到法国电影,大家往往会想到浪漫、自由、奔放,苏菲·玛索的美丽与优雅,阿兰·德龙的风流与潇洒,仿佛成为法国电影的不朽名片。但在微电影《调音师》(2011)②中却充斥着无奈、凄凉、矛盾、隐喻与讽刺。由格雷戈瓦·勒普兰斯-林盖所饰演的调音师阿德里安(Adrien),将人性的脆弱、自以为是和自欺欺人演绎得淋漓尽致。
影片采用倒叙手法,将结尾作为开场序幕。钢琴声响起,一位白发老人睁着眼睛呆坐在沙发上,阿德里安仅穿着内裤和袜子,坐在钢琴前假装淡定地弹琴,他身后站着一个人,画外音说道:“我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除非是为特殊的场合或者观众,就像今晚这种。这个男人是谁?我不认识他,我甚至没有见过他,我是盲人。况且,我也不是为了他而演奏,我在为我身后的人演奏。”从画外音中可以感知到,其陈述的是阿德里安内心独白,其中暗藏以下玄机,白发老人是谁?是死是活?阿德里安为何穿着内裤弹琴?他身后站着的人是谁?是男是女?他们三个人是什么关系?

随着开门声,钢琴音乐戛然而止,序幕与电影第一幕在黑屏闪现过后丝滑地连接在一起,大全景下的压抑舞台,好似人眼睛的形状,将镜头切换至“伯恩斯坦钢琴比赛”现场,这也隐喻了影片的叙事主题——眼睛。随后的近景直接对准坐在钢琴前焦虑、惶恐、无助、额头冒汗的阿德里安。画外音再次陈述:“去年,我还被视作一个天才,我也自认为前途无量。15年来,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伯恩斯坦音乐大赛。”此时的阿德里安紧张地把手放在琴键上,按下了一个键,此镜头结束。其实,之前序幕中的画外音提到的“我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已经为阿德里安比赛失败埋下伏笔。学习过音乐的人都知道,钢琴天才需要在众多大型演出现场得到公众和专业人士的认可,而不是自我吹嘘的、一位学琴十五年的“钢琴天才”,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这注定他不是天才,也必然会在钢琴比赛中失败。
电影第三幕围绕阿德里安比赛失败后,女友弃他而去,为了生存,他假装盲人免于客人投诉,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赚取更多小费,并堂而皇之地偷窥客户隐私。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阿德里安不仅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甚至还乐在其中,自以为很聪明。这一虚伪、自欺欺人的人性阴暗面被胡一轩敏锐捕捉到,也由此处入手作为室内歌剧的开始。
在歌剧第一幕开场中,男主人公安德里的戏谑性唱词,显示其已经从比赛失利、女友出走、钢琴家梦想破灭的阴霾中走出,他仿佛还在以一种“佛系”视角,审视并嘲笑着身边人为了生计疲于奔命的窘态。“路上的行人,行色匆匆,为了生计而奔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一成不变。而我,哈哈,悠闲的调音师。愁眉不展,垂头丧气,仿佛与我毫不相干。(戏剧动作:摘下墨镜)作为一个‘盲人’,人们对我嘘寒问暖,人们对我无微不至。对我推心置腹,对我无话不说。置身于众人之外的世外桃源,获得这世间唯一的宁静。远离喧嚣,远离暗流。我满足,我充实,我怡然自得,我心满意足。”虽然安德里的唱词尽显轻松,但作曲家在开场音乐所营造的音响氛围却异常紧张,弦乐组渐次进入的密集小二度高频泛音,与调音师轻松的心态形成鲜明反差,预示着危机即将到来。在歌剧中,作曲家是以无调性现代风格的音色音响,将戏剧人物的轻松感与乐队营造的紧张感造成鲜明的对比,以此达到暗示或隐喻效果。而在微电影中,经纪人劝说阿德里安不要把糖当饭吃,隐喻调音师假扮盲人虽然在当下尝到了一些“甜头”,但日后终将自食恶果,会走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电影中,男主人公在毫无顾忌地一次次得逞后乐在其中,甚至说服他的经纪人对他装瞎不要过多干涉,毕竟装瞎后的工作订单翻了一倍,顾客出于怜悯会多给小费,还没人投诉。经纪人于是也默许了阿德里安的这种行径。在一次上门调琴服务时,年轻的女舞者以为阿德里安是盲人,所以毫不避讳地脱去衣服,仅穿着内衣在他面前跳舞,舞蹈结束后还送上香吻,这种重新寻回激情的感觉,也将这一幕推向了高潮。这些意想不到的美妙体验,完全得益于他的谎言。为精简剧情,室内歌剧改编脚本中将此处剧情删除。
当调音师沾沾自喜,以为可以从此享受装瞎伪装所带来的“红利”时,殊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电影也进入危机四伏的第三幕。调音师站在客户门口,多次按门铃无人应答,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记事本,确认并核实预约记录和地址无误,将记事本放入衣服口袋并再次按响门铃。屋内女主人询问来者何人何事时,调音师表明自己身份,女主人拒绝开门,称其丈夫并不在家,自己独自一人,让调音师改日再来。调音师强调调钢琴不需要她的丈夫在家。在女主人表示可以支付上门费但仍不开门后,调音师进一步强调自己是盲人,到客户家需要费很大力气,不是钱的问题,由于没有取消预约,至少需要开门解释一下。女主人没有回应,调音师等待了几秒后再次按响门铃,门依旧没开,他气愤地将拐杖碰地之后,门终于打开,一个老妪用手抵住房门,上下打量着调音师。此时,对面一位身穿粉红睡衣的老妇人打开门,探出半个身子 ,疑惑地看着他们,老妪也终于同意让调音师踏入“死亡之门”。
在室内歌剧中,胡一轩基本保留了此处和随后的剧情,但也有改变戏剧结构和矛盾冲突的重要变化。胡一轩将不给调音师开门的老妪调整为年轻女性汉娜,在此基础上,还将汉娜设定为遭受家庭暴力,不堪忍受折磨、决心与丈夫同归于尽的弱势一方。这一增加的强烈戏剧矛盾冲突,使得汉娜的戏剧角色地位几乎与调音师“平起平坐”。较为巧妙的是,胡一轩在歌剧前半部分采用平行空间叙事。在开场,安德里戴着墨镜,拄着盲杖上场,戏谑地嘲讽路人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命时,安娜同时在舞台的另一侧平行空间中叙述着自己被家暴的遭遇,二者在各自的时空内,完成了一段二重唱。
汉娜:几经何时的我,曾经享受那样的美好。
安德里:美妙的音乐从我的手指迸发,
汉:美丽的爱情好像只属于我和他,
安:就在那一天,
汉:不知什么时候,
安:世界变了模样,
汉:世界变了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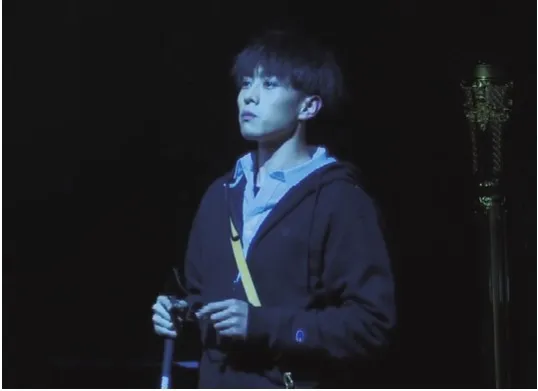
安:我梦寐以求的那座奖杯!却变成了无法忘怀的梦魇。
汉:我心心念念的那个爱人!却成为张牙舞爪的魔鬼。
安:这世界充满了陷阱,名次早已板上钉钉。
汉:这世界充满了暴力,生活只剩拳打脚踢。
安:可我又能怎样?
汉:可我又能怎样?
安:人难道不都是自私的吗?
汉:人难道不都是无耻的吗?
安:就这样隐姓埋名,
汉:就这样同归于尽,
安:我只想独自一个人,
汉:我只想让你下地狱。
(戏剧动作:安德里看向自己的手表 )
安: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去林荫大街了!
在安德里赶往林荫大街客户家的时候,两个平行叙事时空会合在一起,此部分的歌剧剧情相较于电影剧情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明显改动。例如电影中并没有交代老妪从门后猫眼看向门外;而歌剧中,则明确交代了汉娜听到敲门声后受到惊吓,匆忙走到门后猫眼位置观察门外。安德里一再按门铃后,看到邻居开门查看,尽管怀疑“这个盲人有问题”,但汉娜担心引起怀疑,还是将安德里请进屋内。
随后的剧情发展,歌剧与电影剧情基本吻合,歌剧相较于电影更加简练紧凑。安德里摸索着进门,询问钢琴在哪,汉娜要给他带路,安德里踩到地上的血迹滑倒,此时剧场灯光全部点亮,观众会看到汉娜的丈夫死在了沙发上,安德里惊恐地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和坐在沙发上的死人强装镇定,却浑身颤抖。汉娜解释说家里在装修,油漆洒了一地!汉娜尝试将安德里扶起来,但安德里的身体仿佛凝固一般,一动也不动。汉娜的手在安德里面前晃了又晃,过了许久,安德里才回过神来一个激灵。安德里忙解释:“没事儿没事儿,我眼睛不太舒服。”随后的两个戏剧动作重在突出安娜试探安德里是不是真正的盲人。
动作一:安娜抓住安德里的手,拉起来扶到钢琴面前,并故意用力推了一下,安德里本能地扶住钢琴,忘记自己是一位盲人。
动作二:汉娜以眼镜脏了为由,粗鲁地从安德里脸上强行摘下,她并没有擦眼镜,死盯着安德里的眼睛仔细观察,安德里屏住呼吸,安娜顺手将眼镜放在了钢琴上,走到舞台左侧进入衣帽间。调音师如释重负地坐在钢琴前,而此时达到戏剧矛盾的高潮点:安德里希望继续装瞎,蒙混过关不被安娜发现;安娜则怀疑安德里不是盲人,知道了她杀死丈夫的罪行。
二人在戏剧的最后互相猜忌,恐惧、紧张、忐忑不安一触即发。当汉娜拿着射钉枪重新走回安德里身后对准他的后脑时,安德里假装淡定,用沾满血的手开始弹奏钢琴。至此,电影结束,但室内歌剧脚本中增加了乐队演奏员的旁白:“杀死他!杀死他!否则你的所作所为都将被他发现。快住手!快住手!他只是个无辜的调音师……”总谱中,此时乐队静止,标注着“时间过了很久……传来了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即乐队旁白所描述的汉娜内心的情境,挣扎、犹豫与痛苦。安德里在舞台上弹奏着德彪西的《月光》,时断时续,灯光忽明忽暗。类似于此类具体的戏剧动作,胡一轩在剧本和总谱中都有着极其细致的标注,这一点是可取的。一些第一次创作室内歌剧的年轻作曲家,无论剧本还是总谱,从头至尾只有台词、没有任何戏剧动作的标注,这会对导演、指挥和演员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或不必要的麻烦。
二、中德两版室内歌剧的叙事变迁
微电影《调音师》虽然很短,只有13分30秒,但无论从倒叙的陈述手法、环环相扣的剧情,主人公戏剧化的身份转变,还是其开放性戏剧结构,都使影片成为当代电影史上毫无争议的经典;也正因此,该片还荣获2011年卢纹(Leuven)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奖、2012年法国恺撒奖最佳短片奖。胡一轩选择一部如此成功的微电影改编为歌剧脚本,既有一定优势,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优势在于,一部公认的微电影杰作,其剧本一定不会差,无论从戏剧体量还是相对集中的主线人物叙事线索来看,它与室内歌剧的小舞台、小乐队、小人物、小事件等方面的要求都有着相似之处,如果经过认真打磨、反复推敲,一定会成为一部优秀的室内歌剧脚本。单从剧本上来看,胡一轩的改编是成功的,且有一定的可圈可点之处。

但是在参照胡一轩的歌剧脚本及总谱,对比观看许忠指挥的北京版本与德国的汉堡版本之后,我曾一度怀疑两部作品的戏剧脚本是否都相同,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在确定音乐与脚本完全相同,仅仅是中、英文唱词的转换后,我又与作曲、编剧胡一轩进一步确定了北京版本的室内歌剧是没有导演的,基本由胡一轩本人负责与演员和歌唱家沟通。这其中还有极具创意的安排,使得该剧是我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部唱演分离形式的室内歌剧,相关论述笔者会另外撰文详述,此处不加以展开。
正因为北京版的导演相当于作曲家本人,所以基本与室内歌剧《调音师》脚本中的人物和戏剧动作相吻合。但德国版室内歌剧《调音师》的导演是特蕾莎·冯·哈勒(Theresa von Halle)③,她是一位音乐剧导演,在排演德国版室内歌剧《调音师》的过程中,胡一轩与哈勒在对待汉娜这一角色,以及戏剧结构的延展方面出现了分歧,有些地方甚至难以调和。最后胡一轩做出了让步,她认为尝试一下相同歌剧的不同排演方式也未尝不可,所以最终选择尊重哈勒导演的意见,这也就导致北京版和汉堡版歌剧大相径庭的舞台呈现。
作曲家和哈勒导演针对《调音师》意见不统一的地方可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哈勒认为汉娜的角色不够丰满,为了增加戏剧的紧张性,并考虑到剧情的连贯性,哈勒在歌剧开始补充了与汉娜相关的剧情,让汉娜与丈夫活生生地上演“爱恨情仇”的桥段,还原了汉娜的婚姻从幸福到不幸,直至最后杀死丈夫的过程。歌剧音乐开始前,汉娜有将近两分钟没有台词的独角戏,她坐在沙发上愁眉不展,思索片刻后起身,打开钢琴上独立设计的拉门,把手伸进去,拨弄出酒杯碰撞的叮叮当当声,这种舞台声响应该是导演的有意设计,暗示安娜与丈夫在生活中不断产生摩擦与碰撞。汉娜从中拿出一瓶红酒和高脚杯,在倒入满满一杯红酒后一饮而尽,这一戏剧动作在原作剧本中也没有,导演不仅是想以此来暗示汉娜压抑、惆怅的心情,更是想为之后的戏剧情节中,汉娜对丈夫的家暴进行反抗并杀死丈夫埋下伏笔。这一系列的戏剧动作过后,汉娜的丈夫在舞台后侧楼梯上缓缓走下来,与汉娜上演了拥吻、温存的画面。此时乐队演奏进入,安德里独唱开始。
按照胡一轩本人的解释,此时的舞台布景依旧是平行叙事空间,安德里开始的自叙式演唱段落与汉娜和丈夫“温存”的剧情同时发生,但各自独立。当安德里和汉娜的唱词进入到“(安):我梦寐以求的那座奖杯!却变成了无法忘怀的梦魇。(汉):我心心念念的那个爱人!却成为张牙舞爪的魔鬼。”同时,汉娜与丈夫在舞台上开始增加互相推搡、谩骂、殴打的戏剧动作。汉娜丈夫的扮演者是戏剧演员,而非歌剧演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汉娜的丈夫在表演过程中,戏剧动作“发力过猛”,导致了正常歌剧的“主角”光环发生了偏移,戏剧结构在最后无法形成闭环效应。例如,汉娜的丈夫为了强调其作为施暴者的残忍无情,不仅推搡汉娜,冲着汉娜做各种夸张的戏剧动作,甚至把钢琴的琴键全部拆卸下来,散落在地上同时又砸向汉娜。尽管以各种变态手段对汉娜实施残忍的家暴的戏剧动作,会使当时的戏剧情境十分吸引人,甚至让观者感觉到不可思议和意外,但这种为了一时的戏剧冲突效果,而增加汉娜丈夫拆琴、毁琴的戏剧动作,却让整个戏剧结构产生了本质性变化,尤其会让戏剧的后半部分付出惨痛代价。
哈勒导演与胡一轩的第二点矛盾正在于此。歌剧结尾,汉娜用射钉枪在安德里脑后瞄准时,光着身子的调音师原本应该一边坐在钢琴前弹奏德彪西《月光》,一边在内心祈祷汉娜不要杀死他,与此同时,汉娜也在《月光》中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犹豫要不要杀死无辜的调音师。由此可见,整体的戏剧结构需要在歌剧结尾保持钢琴的“完整性”,因为无论在微电影剧本,还是室内歌剧的脚本中,“钢琴”不仅仅是道具,更是一种戏剧“象征”④,钢琴对于整个戏剧结构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在歌剧结尾,调音师演奏钢琴一方面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在抚慰焦躁、恐惧的汉娜,为开放性结局埋下伏笔,让观众想象汉娜是否会射死调音师留有充足的回味空间。但可惜的是,钢琴已经被汉娜的丈夫在过分的家暴戏剧动作中拆得七零八落,在德国版本中,歌剧最后,调音师只能光着身子呆坐在没有琴键的钢琴旁,汉娜举着射钉枪站在身后,《月光》被换成了与歌剧毫不相干的其他作品……
结 语
无论对于一部电影还是一部歌剧来说,“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的意韵,是一种潜在的意义、隐含的意味。它是对读者、观众的审美体验和联想的某种定向,但这种定向不是一种具体的限定。它是开放的、无限的,诱发对美的创造性再发现。因此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又具有某种模糊性或半透明性。”⑤
对于微电影《调音师》来说,其“象征意味的意象”是眼睛。无论是电影第一幕类似于眼睛形状的远景舞台;还是比赛失败后,躺在床上以超近景显示的调音师的眼睛,在玻璃球状鱼缸后绝望、呆滞、凝固的眼神死死盯着狭小空间里的金鱼;再或是影片最后,调音师呆坐在钢琴前,无助且装瞎的眼神被镜头再一次拉近。这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潜在意义,隐含的意味,令人回味无穷的内在意蕴。此时,无论那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拨弄着何种音乐,似乎也无法让观众从调音师那双装瞎的眼睛上离开。这就足以证明,微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对戏剧核心的“意象”要素——眼睛,把控得十分精准、到位且贯穿始终。

受舞台空间及布景的限制,室内歌剧与电影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缺乏对某些局部意象的关照和“特写”功能,但室内歌剧对于某些戏剧“象征”或舞台“意象”的把控却并不输于电影版。北京版《调音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歌剧结尾所运用德彪西的《月光》,可谓是该剧的神来之笔,可圈可点,令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但完好无损的钢琴这一不可或缺的“象征”,以及由此产生的舞台意向——“月光”,却在汉堡被一个“死人”——汉娜的老公,拆得七零八落。我想作曲家本人对汉堡版本的结尾并不满意,所以当我打趣地问胡一轩,为什么现在网上看到的德国汉堡版《调音师》结尾,是调音师尴尬地坐在凳子上发呆,却依旧还有《月光》的背景音乐?胡一轩笑着说,这是她后“贴”上去的音乐。她还是认为北京版的结尾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张宝华,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本文为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室内歌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3BD064)
① 德国汉堡演出的室内歌剧《调音师》视频链接:[《调音师》室内歌剧 The piano tuner *完整-哔哩哔哩] https://b23.tv/QnA49hs
② 微电影的视频链接:[短片《调音师》14分钟版本无水印-哔哩哔哩] https://b23.tv/SweeGq0
③ 特蕾莎·冯·哈勒(Theresa von Halle)曾在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和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学习双簧管,并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她的作品包括在科隆歌剧院上演的《不来梅的音乐家》(Bremen Mizikacilari )。此外,哈勒还在汉诺威国家歌剧院执导了《儿童会议》(Konferenz der Kinder ),她的作品曾在柏林音乐厅、汉堡Kampnagel和汉堡青年剧院等地上演。
④ “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往往出现在布景、道具系统中,在观众进入剧场或大幕拉开之后,就以独特的语汇异常醒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有时则以舞蹈、歌曲、形体表演等形式出现。但都与剧情的进站无关,仿佛超出叙述之外,只隐隐地对题旨做某些提示、阐发,起到提擎全剧的作用。”引自《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林克欢著,北京联合出版社,第161页
⑤ 引自《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林克欢著,北京联合出版社,第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