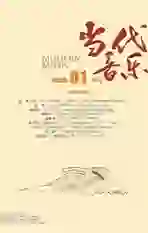浅析《大江东去》音乐性与文学性的交融
2025-01-18戴传明
[摘 要] 《大江东去》是我国音乐家青主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被认为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开山之作”。这首作品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代表作,它既借鉴了西方作曲技法,又表现出了苏轼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情感。不仅如此,这部作品也是音乐与文学成功交融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依据音乐要素综合分析艺术歌曲《大江东去》的音乐性,再根据歌词和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分析作品中存在的文学性,最终探索这部作品中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
[关键词] 《大江东去》;音乐性;文学性;交融
[中图分类号] J605"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136-03
一、作品简介
《大江东去》是我国现代音乐家青主根据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被贬至黄州游览赤壁时有感而发,借赤壁之战时周瑜雄姿英发名传千古却依然随着历史长河消散,感慨人生短暂以及人的生命在历史面前的渺小。这部作品是青主于1920年在德国创作的。[1]此时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混战,青主也想为国内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他将自己比喻为当年的苏轼,同苏轼一样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怀,却不料命途多舛,无法实现报国之志。
二、作品的音乐性与文学性
(一)音乐分析
这首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为带尾声的单二部曲式,根据苏轼词作上下阕的结构而来,上阕旋律采用了宣叙调的形式,庄重严肃,大气豪放;下阕则是以咏叹调的形式抒发情感,形成鲜明对比。曲式结构如下(以调式d-D-d为例)。
首先歌曲A段为非方整形乐段,调式以d小调为主。开头a乐句的音乐材料直接以属音到主音向上的跳进开始,然后整体级进向下进行到小字一组的la,隔半拍休止后级进上行又急转直下到小字一组的mi,旋律线条上下波动呈波浪形。乐句前后强弱对比鲜明,伴奏以柱式和弦为主,一个字对一个和弦,铿锵有力,气势磅礴。3、4小节的材料是对前两小节的陈述做进一步补充,材料级进下行到小字一组的降mi上;钢琴伴奏右手同旋律一样共同进行,左手为柱式和弦;调式进入降A大调,和声停留在降A大调的Ⅰ级上。a乐句短短四个小节就能够使听众身临其境,仿佛站立在长江边,望着波涛滚滚的江水一路向东,为全曲的氛围奠定了基调。
随后b乐句以级进向上的均八分音符为主,中间各穿插一拍的休止,不断由弱到强。伴奏织体右手是随着旋律向上的柱式和弦,左手为向下跳音进行的四分音符,形成右手与人声同步进行,左手与人声一呼一应的效果,调式在第6小节转入f和声小调,和声停留在Ⅰ级和弦上。b乐句7、8小节旋律材料和钢琴伴奏都是根据a乐句后半部分的材料发展而来,和声停留在Ⅰ级上。B乐句结合歌词欣赏能感觉到刚刚被拉到长江边上的听众似乎还不清楚身处何地,然后蒙眬地看见赤壁场景,逐渐会想起三国时期火烧赤壁的历史故事。
间奏部分9—12小节的伴奏旋律材料由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四分音符按照特定的排列方式进行,旋律线条呈波浪形,全程由弱到强反复进行,而且每个音符都有重音记号,情绪极为激烈,好像长江水流翻涌不断,调式在第12小节转入d小调。13、14小节的材料为间奏前半部分材料的简化,只有一条旋律线进行,而且都为弱奏,仿佛是汹涌江水的回声,也为歌曲后面的内容进行过渡。
c乐句的材料为b乐句材料的变化发展,伴奏织体为间奏13、14小节伴奏织体的延续,都是固定的和声在Ⅰ级上的和声音程,给人意犹未尽之感。17—20小节的旋律材料和伴奏织体依然是b乐句的变化发展,19、20小节是17、18小节的变化重复,二者相差五度,一强一弱,衔接紧凑,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增强情感。
20—22小节d乐句的旋律材料在a、b乐句都能找到类似的材料。分析到此不难发现,八分休止加八分音符连着两个平八,再以四分或二分音符结束(例如“江山如画”这四个字的节奏型),这个特定的节奏型是这个作品最具有特征的符号。上阕的ab两个乐句的“尾巴”、间奏、尾声,都是以这个节奏型进行发展创作,运用这个节奏型时,钢琴伴奏也会演奏同样的旋律,进一步强调这个节奏特征,因此不难窥探出青主在进行创作时的构思。
B乐段音乐风格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旋律、节奏,还是伴奏织体、调式调性等都与A段形成对比。调式由d小调转入同名大调D大调,旋律从宣叙调的风格转为咏叹调的风格。旋律以主和弦的三音开始,上下起伏,节奏大多以一个二分音符带两个四分音符进行发展,钢琴伴奏右手部分是主旋律,左手部分是连续的反复上下波动的三连音节奏型,和声以Ⅰ、Ⅵ为主,28、29小节短暂的转入降G大调后又回到D大调,在41小节乐段临结束时调性转回了主调d小调,最终和声结束在Ⅰ级。
43—53小节是作品的尾声部分。旋律整体是休止的,只有“人生““如梦”二词以单音出现,风格回到宣叙调的形式。伴奏是以Ⅰ级分解和弦用大附点的节奏形式进行排列,与主旋律部分形成巧妙的搭配。这部分以钢琴伴奏作为情绪的渲染,给人以思考沉静人生的空间氛围。
最后,第51—53小节再次出现A段的特征性节奏型,旋律和伴奏都以主和弦的根音一路向上,音乐由弱渐强,以表达作品从对人生的思考到豁然开朗,从音乐性上形成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完美配合。
(二)文学分析
《大江东去》的歌词直接借鉴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2]词中描绘的赤壁景观,以山、浪等客观存在暗喻现实世界与历史浪潮,既描绘出了事物的客观形象,又写出了事物的精神。开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描绘出长江流水磅礴的气势,展现出庞大的意境美。短短一句话直接表现词作行文豪放的特点。“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则是借赤壁江水的场景联想到赤壁之战的史实,从而具体展开对“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对赤壁宽阔凶险的场景进行更加细致夸张的描写,充分展现苏轼豪放不羁的创作风格。同时,这一句也是歌词改动的主要部分,“乱石穿空”改为“乱石崩云”“惊涛拍岸”改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做了一次重复。“穿空”改为“崩云”,“拍岸”改为“裂岸”,从文学的角度上看,他们之间所表达出的效果是接近的,都能够表现出恶劣凶险的环境,后者表现得更为夸张。从音乐的角度分析,我们分别将苏轼原版的歌词和青主改过后的歌词代入旋律试唱能够明显发现,青主改版过后的歌词更加适合代入音乐旋律。“乱石穿空”这四个字在诵读时是连贯的,而在歌曲中这四个字中间穿插了一个四分的休止,它并不是连贯的。“穿空”改为“崩云”运用被动句式将四个字分开,完美契合了音乐的旋律。从歌唱咬字的角度来考量,“崩”的声母“b”和韵母“enɡ”咬字相比“穿”的声母“ch”、韵母“uɑn”更加适合歌唱的咬字,而且“崩”字具有力量感,能够更加夸张地表现出环境的凶险。“惊涛拍岸”改为“惊涛裂岸”也是同样的道理。“卷起千堆雪”重复一次从文学的角度看是有着些许加强语气的作用,从音乐的角度看,重复的两者之间旋律节奏相同,但在音区和强弱上形成对比,着重表达了环境的险恶。这一句歌词的改编能够使人感受到青主在进行创作时对歌曲整体表现的考究。“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一句是上阕的结尾句,“江山如画”是对上文赤壁场景的总结,“一时多少豪杰”是为下文回忆周瑜火烧赤壁铺垫,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两句是对火烧赤壁史实的细致描写,但是其中存在部分歧义。[3]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与曹军对抗,吴军的主帅是孙权,孙权“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周瑜并不是赤壁之战的主要贡献者。火烧赤壁无论是看出曹军不善水还是草船借箭,大多是诸葛亮所提的计策,文中“羽扇纶巾”的形象也明显是指诸葛亮。但是根据苏轼描绘的内容,仿佛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料事如神的谋士,很容易让人误解。不过,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都崇尚写意而非写形的美学态度,苏轼对词的考量应当是更偏向于意境和感受,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他并没有刻意地描绘赤壁之战谁是胜利者,谁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做出最多的贡献,苏轼对这段史实的描绘只是做了简写,这首词的中心内容在于风流人物都随着历史消散,无论是周瑜还是诸葛亮。因此对这一句的深入解读能够进一步感悟到苏轼豪放不羁的人格魅力。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对苏轼内心的直观描写,苏轼被贬至黄州,空有一身报国志,内心的愤懑无处可泄,他羡慕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然而时光易逝,未壮志报国就已年迈,词句中充满了对自己的嘲讽和遗憾。“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一句简短有力,充分展现了苏轼洒脱的人生态度。[4]人生就像一场梦,不要对人生中所遇到的事物过于执着,不如享受当下,举杯与江水明月共饮。这一句既是全词的结尾也是中心主旨,一句话就拉高了苏轼的人生的境界与格局拉高。即使苏轼的身体随着历史的长河消散,但他的人格会依然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三、作品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结合
(一)音乐进行与音调的结合
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赤壁之战的缅怀,表达出作者在历经人生世事无常后依然展现出了对人生豁达乐观的态度。[5]青主的曲其旋律贴合歌词的声调格律,如“大江东去”四个字,其平仄规律为“仄平平仄”,这一句的音乐旋律整体呈现出一个拱形,基本符合了词的平仄规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平仄规律为“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其旋律在“平平”的字上进行时以级进为主,在“平仄”的字上则是为跳进。
(二)诗词结构与音乐结构结合
词的结构分为上下阕,上阕绘景并引出下阕,下阕回忆抒情,而歌曲的结构同词一样分为两段,A段宣叙调,B段咏叹调,尾声是对B段抒情感慨人生无常后的自我解脱。从结构上看,歌曲的上下两段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苏轼的词上下阕之间没有明显的对比,但仔细品味词的内容不难发现上下阕的风格是存在一定对比的。上阕以赤壁的险恶环境引出周瑜火烧赤壁的故事,以叙述为主;下阕借周瑜火烧赤壁大败曹军雄姿英发,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消散而去,借此抒发自己命途多舛、胸怀壮志却不能实现的感慨,以抒发情感为主。所以,词作的上下阕具有一定的对比特征,青主用音乐的形式将词作上下阕的对比放大,使听众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地体会作品中的情感。
(三)音乐动机的创作与诗词的联系
慢慢诵读苏轼的词作,细细体会诗词中蕴含的抑扬顿挫,不难发现,我们在诵读“千古风流人物”时通常会把“千古”二字连读,“千古”与“风流人物”断开,将“风流人物”四个字一字一顿。不仅如此,“三国周郎赤壁”中“三国”是连读,“三国”与“周郎赤壁”断开,“周郎赤壁”是一字一顿;“一时多少豪杰”中“一时”是连读,“一时”与“多少豪杰”断开,“多少豪杰”也是一字一顿。在诵读词作的过程中能明显感受到这种独有的抑扬顿挫的规律,如果用音乐节奏的形式来展现这种规律,可以表示为两个八分音符带三个四分音符(■)。这种特点与前文所说的A段中常出现的特征性节奏型具有一定的关联。只要在这个节奏型的前面加上一个八分休止符和一个八分音符,就变成A段中出现的特征性节奏型。所以,在进行歌曲旋律创作的过程中,青主必然也曾无数次地诵读苏轼的词,然后以词的抑扬顿挫的规律进行音乐的创作。
总" "结
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探究《大江东去》这首作品,我们不难感受到青主在创作这首音乐作品时的考究程度。青主娴熟的西方作曲技术与苏轼流传千古的诗词相得益彰,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青主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及其风格和形式成为中国近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开辟了现代音乐与中国古诗词相结合的创作形式,为现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风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于洋.歌曲《大江东去》音乐分析与歌唱演绎[D].南京师范大学,2017.
[2] 杨生善.浅谈苏轼词作及《念奴娇·赤壁怀古》[J].文学教育(上),2020(11):62-63.
[3] 钱玉趾,陈思同.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正解[J].文史杂志,2018(03):37-44.
[4] 尹飞扬.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意境分析[J].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2018(11):11.
[5] 周茂文.青主《大江东去》钢琴伴奏的艺术特点[D].青岛大学,2022.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