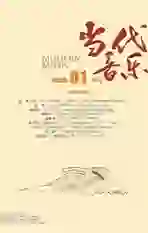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中的“意象空间”
2025-01-18李瑾靳竞
[摘 要] 本文以中国青年作曲家李肖昀的长笛独奏作品《凝望原野的片刻》作为研究对象,以如何构建属于演奏家独有的“意象空间”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作品中所使用的现代作曲技法,如结构、音响的设计,结合笔者的“二度创作”经验,深入阐述了作曲家的创作理念,即,以演奏家的视角诠释当代音乐创作中是如何将长笛的现代演奏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
[关键词] 长笛;意象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演奏技法
[中图分类号] J621.1"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111-04
一、作品简介
当代中国青年作曲家特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近年来,他们的作品在国内与国际比赛中屡获殊荣,在世界范围内频频上演、深受好评。他们的创作离不开对中国这一概念的思考,他们渴望以此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身份去立足于世界。他们的创作共性在于:以个人创作为纽带,用现代音乐的形式来表述、来接续中国传统音乐所独具的审美旨趣和文化意蕴。这一切也激发了演奏家的热情和想象力,深刻启发了演奏家如何对此类作品进行更准确的“二度创作”的思考与实践。
《凝望原野的片刻》创作于2021年,是一部获奖作品。当青年作曲家李肖昀静立于故乡丽江雪山下那一片无际原野之中时,扑面而来的巨大自然生命力令其获得了强烈的创作灵感。作品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代表了作曲家的五种不同的感知瞬间。在作品的前三部分,通过展现各种各样的现代长笛音响,试图描绘自然中的“空境”;而后两部分则采用单声线条化的、歌唱式的写作手法,以诠释人与自然如织线般交汇的形态,以及“空境”不空,意象、生机、审美无所不在的创作主题。这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二、结构划分
笔者以不同的速度标记将作品分为五个部分,每部分的速度分别为:第一部分: =63;第二部分: =42;第三部分: =72;第四部分: =110;第五部分: =70。这五个部分互相承接,分别呈现了作曲家五种不同的心理感知,笔者将根据每一部分的风格特点,冠以标题。
三、演奏中“意象空间”的构建
(一)“意象空间”概述
“意象空间”是言说心灵、表现心灵的审美空间,并非简单的三维立体空间,而是充满了情与意的语境空间。而属于自己的演奏“意象空间”是通过音符、力度和长笛现代演奏技法等创造的音乐,用音乐营造演奏家心中的所思所想,使听众与演奏家的情感融合。
“意象空间”可以分为“意”“象”“空间”三个部分。
首先,“意”就是人的情感,也就是演奏家的情感。正是演奏家的所思所想,决定了演奏家所表现出来的音响效果。“意象空间”从本质上来说是主体性的空间,是演奏家的“意”与“情”的有机彰显。“情”融合在“意”中,而“意”在彰显“情”,所以,先要了解作曲家在创作时的所思所想,在作曲家所描绘的蓝图中,再融合演奏家自己的情感,将这蓝图描绘、扩大,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演奏“意象空间”,这空间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风一花,则皆来自演奏家的“意”。
其次,“象”就是具体的实物,“象”更像是一种介质,一种媒介,它把演奏家的“意”与听众的思想连接到一起,使听众理解演奏家所表达的“意”,在作品中表现为“风”的意象、“原野”的意象、“鸟鸣”的意象,等等。
“意”与“象”相辅相成,有“意”无“象”,作曲家的所思所想以及想表达的情感,只是呈现在谱面上,无法与听众的思想达成链接;有“象”无“意”,虽然演奏家完成了谱面上的具体技法,但是没有融合作曲家想表达的情感,也没有加入自己的所思所想,即使与听众的思想达成了连接,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意”与“象”缺一不可,它们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意象”。
最后,“空间”就是放置这些“意象”的场地,它即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有限是指乐曲总有终止的时候;而无限则是演奏家在作曲家构建的世界中任意遨游,随心所欲。正如作曲家所说的:“这片原野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也可以是沟壑纵横的山与水;还可以是白雪皑皑的雪山脚下;也可以是春意盎然的林间小路。”①有了“意”与“象”才使得这“空间”生机勃勃。这“空间”就像是画纸;“意”便是画笔;“象”则是墨水;“意象”就是画中的山与水;“意象空间”就是这幅水墨画。
(二)“意象空间”的特点
“意象空间”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形态,是主体对艺术境界极致的追求,其中“虚”和“灵”是最典型的特征。[1]所谓“虚”,即“虚而万象入”[2],在本作品中情感的体现更注重在想象,“虚空”“虚无”。作为演奏家,我们在演奏时情感是充盈的,这时在本作品中,我们对艺术的塑造更加偏向对于“虚空”、“虚无”的体现。正如作曲家所说的:“仿佛一切都静止了,万物都停在了这片刻,有云,有风。原野上的万物有无姓名是无所谓的。从眼前一直蔓延到天边,模糊了间距,最后仅剩一抹灰。其间,有鲜活的吟唱,有腐朽的哀号,还有比远方更远的风。高亢与柔和,委婉与激昂,牵动着落日的余晖,绮叠萦散,飘零流转,将原野上的生命凝结在那片刻。”②在演奏中,“虚”对应着休止符号、停顿等。虚实相生,沉浸在“虚空”“虚无”的演奏中,对于休止的把控,也会更好地把演奏家的“情”和“意”展现出来。
而“灵”就是通过保有自身的灵性而展开活动。要演奏好本作品,我们首先要学会思考、学会想象,在内心中构建出一幅画面之后再进行演奏,这个过程,就是演奏家自身灵性的体现。正是因为保有自身的灵性,我们所演奏出来的作品才会具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才会更好地把自己想表达的情感链接到听众。在演奏中,“灵”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具体如长音的处理、强弱的对比、自由延长记号的处理等等。整个演奏过程也是意象创构的过程,“灵”的运用会使每位演奏家的呈现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四、作品中“意象空间”的形成
(一)“在原野上”
第一部分没有小节线,意在让演奏家的表演更加自由,更富有即兴性。这一部分大量使用了如自由延长音、滑奏、装饰倚音、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现代演奏技法。开头用三个连续跳进的倚音跳进到小字二组的E延长音上,以mp的力度渐强至f力度保持,并运用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即通过控制气息与强弱,在颤音的基础上加入节奏变化。然后力度回到pp力度,旋律音依然保持在小字二组的E音上。随后力度突然加强,用四个连续级进的倚音和三个跳进跨度巨大的倚音(共七个连续的倚音)只在小字二组的E音上短暂停留。这里呼应开头的三个倚音,塑造了本部分第一个风的意象。
紧接着,作曲家使用到了自由延长音记号与较长休止符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并在自由延长音记号下方标记了渐强至渐弱的力度标记,这是长笛作品中十分常见的演奏技巧,在现代派作品中,这样的力度对比会更加夸张,笔者在之前的章节中介绍了“意象空间”的特点,“虚”和“灵”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二个无边无垠的原野的意象。
滑奏与自由延长音记号相结合的使用,更加强化了风的意象。然后前倚音与自由延长音记号相结合的使用,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三个鸟鸣的意象。
连续四个向下跳进且跨度越来越大的倚音,最后停留在小字一组E延长音上,这样的叹息式的音响效果塑造了本部分的第四个一望无际的参天大树的意象。然后作曲家重复了开头,最后结束在小字二组E的延长音和花舌上。进一步增强风的意象。
至此,这部分的“意象空间”已经形成:在无边无垠的原野上,风呼啸而过,地上的小草随风摇曳,看似刮不完的风,也有片刻偷懒,四周异常安静,风又呼啸而过,这次在风中还夹杂着几声鸟鸣,随着鸟飞翔的方向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参天大树,但这大树也阻挡不住风的去路。
(二)“逃离原野”
在第二部分的开头,小字一组A音向下半音滑奏营造绝望叹息般的音响效果,紧接着跳进至小字一组C音并使用现代演奏技法中的气声加花舌在气息与舌头的控制下将音响效果保持在pp的力度上,然后在同一个音上使用现代演奏技法气啸音,如喷射般的音响效果,使力度从pp力度加强至f力度。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一个风的意象,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这里的风更加急促,更加让人难以捉摸。本部分开头的四个音是本部分的动机,笔者称之为风起意象动机,共出现了七次,每次出现时,均会稍有音高或节奏上的变化。
接下来,作曲家使用了气音制造出呼啸、急促的音响效果,通过调整风口与笛口的位置,加大风口与笛口的角度,使得气息更加贴近水平的方向吹出。在小字二组D音上再次使用到了气啸音,冲刺后回落。衔接到下行花舌音程进行,回到p力度,并在这一乐句的最后一个音上使用气声,通过调整口风的位置并打开,营造出风声呼啸的感觉。
接着作曲家重复了乐曲开头,强化风的意象,同样使用到滑奏、气声、气音、气啸音和花舌。紧接着使用到连续不规则跳进的六个气音(第六个气音带有倚音),再用三个实音(第二、三个实音之间使用滑奏)连接至连续不规则跳进的四个气音,最后停留在小字一组气声与花舌结合的C音上,这部分力度由f渐弱,在实音处渐弱至mf力度最后渐弱到p力度。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二个随风漫天飞舞的落叶的意象。
作曲家再次使用了风起意象动机发展旋律。紧接着使用到了六次上行音阶的音响效果,前两次使用风起意象动机连接上行音阶,第三次没有使用风起意象动机连接,第四次上行音阶缩短至四个音,第五次上行音阶缩短至三个音,第六次用长笛现代演奏技法气啸音代替了上行音阶,并回落至小字一组气声的C音上。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三个迷路人的意象。然后作曲家再次重复开头,再次强化风的意象,并在本部分的结尾处,再次使用了气音的上行音阶呼应前曲,最后停留在小字一组气声与自由延长记号的C音上。
至此,这部分的“意象空间”已经形成:风一次比一次急促,让树叶在空中翩翩起舞,而在原野上有一位孤独的人,他害怕这风,想要逃离这原野,但在这无边无垠的原野上,他迷失了方向,每次都回到了起点,他只得停留在原地,听着风从耳边呼啸而过,他不愿放弃,做出了最后一次尝试,可结果令他绝望,风依然在他耳边呼啸。
(三)“风起天地间”
第三部分使用到了大量的长笛现代演奏技法,如:花舌、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滑奏、指颤音、气声、气音、人声、泛音等。开头使用连续三次近乎相同的动机发展旋律,笔者称之为风呼啸意象动机,第一次,在小字一组C音上使用了花舌和气声的结合,在pp力度上营造风起的意象,随后使用泛音与花舌的结合,通过气息的控制、指法的变化和指颤音来体现风由远及近的运动。第二次,在风呼啸意象动机上,只在最后一个音上加了花舌,使得风起的呼啸感更加强烈,第三次,在风呼啸意象动机上多重复了一次泛音与花舌的结合,这次并没有结束在小字二组的D指颤音上,而是向上跳进至小字二组的F花舌音上,在使用滑奏回落至小字二组的E花舌音上。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一个风越来越急促的意象。
在此之后,作曲家继续发展风的意象,分别使用到花舌、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滑奏、指颤音。在这部分的第七小节,旋律在小字三组的D音上使用了短指颤音,并在滑奏的同时吹奏花舌,最后停留在小字三组的#C音上。
第八小节是第七小节的完全重复,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二个鸟鸣的意象,笔者称之为鸟鸣意象动机。然后作曲家使用到连续上行气音音阶结合鸟鸣意象动机,在本部分的第十小节,使用到了全曲唯一一次的人声,在吹奏小字一组的D音时保持嘴型,使用喉咙哼唱小字一组D音的音高。这一部分几乎使用到了本作品之前所有使用到的现代演奏技法,音符在实音、气音和泛音中来回交替,也在这里到达本作品的高潮。每次上行音阶进行到最高点时,都用下行音阶、滑奏和花舌的结合进行回落,这样处理意在为最后一次冲刺到最高音小字三组的泛音A做铺垫,最后停留在小字一组的E气声音上。这里塑造了本部分的第三个翩翩起舞的人的意象。
至此,这部分的“意象空间”已经形成:风起天地间,风越来越张狂,突然,耳边传来一声鸟鸣,放眼去寻,却不见鸟儿的踪影,就在这时,那鸟儿像故意勾引你一样,那熟悉的鸟鸣声再次从耳边传来,这次你发现了它,向它挥舞双臂,你呼喊,你舞蹈,在这孤独的原野上,这鸟儿似乎是唯一的朋友,它与你擦肩而过,它环绕在你身边,与你翩翩起舞,突然间你不想逃离这原野了。不知不觉中太阳落山了,风不知何时也停了。
(四)“自得其乐”
第四部分几乎没有使用到长笛现代演奏技法,只在结尾处使用了花舌和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来继续营造风的意象。演奏家在吹奏这部分时要区分前面使用大量长笛现代演奏技法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回归于传统长笛的演奏方法,需要保持音准与节奏,注意节拍和强弱力度的转换。这一部分的表达基于它的速度,作曲家只想通过音高和节奏来描绘音乐。不使用长笛现代演奏技法是为了避免音色音响的“同质化”。所以作曲家将一个不使用特殊技巧的快板部分安排在这里,主要目的是区分其他部分。在旋律的发展上,在每一次音响效果向上进行到高点时,都会对旋律做向下进行的音响效果上的处理,这样处理,是为了平衡旋律发展,又为了强化音乐形象,塑造了这部分第一个在原野上勇攀高峰人的意象。
在这部分唯一一次的自由延长记号处,到达本部分的高潮点。随后在连续两次上行旋律,并在小字二组的降B音上加入花舌,在结尾处的小字二组的F音上加入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这里塑造了这部分的第二个风再起的意象。
至此这部分的“意象空间”已经形成:太阳渐渐落下,天空中繁星点点,在这孤独的原野上,这是不曾见过的景色,你只想离它们近些,好好欣赏这番景色,就在不远处有一座高山,你来不及思考,一路勇攀高峰,但上山的路哪里是一帆风顺,这一路上曲折蜿蜒,走走停停,但你一直遥望着天上的繁星,在你的坚持下,终于登上山顶,天色微微亮起,风再次吹过你的脸颊,轻轻地,只是轻轻地。
(五)“天人合一”
第五部分的开头由小字一组的D音连续的跳进与级进,最后停留在小字二组的#G音,并使用到有着云南纳西族民歌风格元素的指颤音[3]。之后使用到了倚音与花舌的结合以及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与花舌的结合。这里塑造了两个意象,一个是指颤音和倚音构成的鸟鸣意象,一个是花舌和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构成的风意象。
在第三小节由小字一组的E音连续的跳进与级进,最后停留在小字三组的#G音,并再次使用拇指颤音,使之强化。这里是第一小节的变化重复。这一部分有许多的大跳进行和指颤音的使用,使用旋律化,线条织体的表达,整体上在使用倚音、指颤音、花舌和带节奏与力度变化的颤音之间相互转化结合。
演奏时要注意,在延长音与各种长笛现代演奏技法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注意气息和嘴形的控制,以保证演奏家有充足的气息去完成演奏。至此,这部分的“意象空间”已经形成:山谷间飞翔的小鸟,在风中翩翩起舞,山间的溪流也有鸟儿在玩乐嬉戏,你与他们为伴融合在这天地间,有的鸟儿俯冲之下,有的鸟儿迎风而上。充满自由的气息,漫步在林间小路,阳光穿过树叶散落在草地,有鸟鸣,有鲜花,完全沉浸在这原野上,在这原野上也不孤单,处处生机勃勃,你随着阳光慢慢前行,渐行渐远,最后只留下这天地间的原野,风呼啸而过,却不见我在哪里。
结" "语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与深度,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赞赏与认可。纵观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存在音乐审美上的差异,但几乎所有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思路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融合”二字,即形式与内容的融合,民族与世界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融合。
《凝望原野的片刻》是一部优秀的长笛独奏作品。通过探索和发掘各种各样的长笛现代演奏技法,设计和展现丰富多彩的长笛音色、音响,从而更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象空间”概念。这部作品也是笔者演奏的第一首中国现代长笛作品,它不仅吸引了笔者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关注,也启发了笔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传统艺术审美等观念和方法带入演奏之中,以实现更高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二度创作”。
参考文献:
[1] 初娇娇.论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的空间性特征[J].中国文学批评,2020(04):151-152.
[2] 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71.
[3] 郭雅.纳西族颤音现象的音乐文化研究[D].上海音乐学院,2021.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