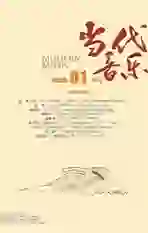格林卡歌剧《伊万·苏萨宁》民族性特征探究
2025-01-18张芯源翟庆玲
[摘 要]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1804—1857),被誉为“俄罗斯音乐之父”。他创作的歌剧《伊万·苏萨宁》是俄罗斯民族歌剧的开端,作品取材于俄罗斯民间故事,音乐中大量使用了民族音乐元素,该歌剧作品不仅体现了格林卡个人音乐创作风格,也对19世纪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格林卡歌剧中的民族性探究为研究对象,就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为基础,从作曲家的生平出发,阐述格林卡学习西欧作曲技法的历程,以及对俄罗斯民族乐派音乐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格林卡;《伊万·苏萨宁》;民族乐派;强力集团
[中图分类号] J652"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101-03
“某种以一定价值观念形成的审美产物吸收一种与自身相异的价值,通过相互撞击发出的光芒照亮自己;这种光芒就是一个新的审美价值,它使原来旧的价值物在价值对撞后所产生的新的关系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1]这种现象在音乐美学上称为音乐的异国主义,19世纪以后的欧洲音乐大规模地接受异国音乐,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原则运用于专业的音乐中。在这次音乐大潮中形成了一个派别——民族乐派,广义的“民族主义”是指,受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在艺术领域凸显出民族特征的艺术作品。在俄罗斯音乐艺术领域首先使用“民族主义”词汇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音乐训练的作曲家们,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融入了俄罗斯本土音乐素材,带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这一乐派在俄罗斯的出现可以准确地追溯到1836年,格林卡创作的一部“爱国英雄悲剧歌剧”[2]《伊万·苏萨宁》的首演,这部歌剧被作为“奇迹的开端”[3],由此建立了俄罗斯民族乐派。
一、格林卡的生平
(一)音乐学习经历
1.俄罗斯学习与创作阶段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出生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这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是格林卡音乐思想萌芽的地方。格林卡虽在音乐上起步较晚,但是其接受了非常全面而专业的音乐教育,掌握了扎实的传统音乐作曲技法,优渥的家庭条件使他从小就学习了钢琴和小提琴,在自家祖宅中排练与指挥农奴管弦乐队,进行古典音乐和俄罗斯民间音乐训练,自学了曲式和配器知识。
在圣彼得堡贵族学校学习期间,格林卡结识了十二月党人中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等其他领域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这段经历让格林卡萌生了对民族音乐的创作激情,朋友们对他的激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民族主义的道路上前行的决心。
2.西欧作曲技术的学习阶段
格林卡24岁时遇到了老师列奥波德·赞博尼——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歌剧团总监,在他的教导下,格林卡学习了意大利歌剧的传统形式,包括歌唱与对位法等,并参演了几十部罗西尼的歌剧。
1830年,格林卡为了学习更为系统和专业的西方作曲技法,去往西欧长期居留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浪漫主义作曲家,如:柏辽兹、多尼采蒂等,通过对他们作品的学习和模仿,逐渐掌握了意大利歌剧的音乐风格和技法。为了追求音乐的严谨的“头脑”之美,他奔赴德国柏林,在老师齐格弗里德·德恩的指导之下,学习了严谨的对位法与理想主义美学。“他不仅把我的知识,还连同把我对艺术的想法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格林卡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的老师德恩,可见在国外学习的经历让格林卡对往后的艺术创作有了更加夯实的基础和更为明确的目标。格林卡在30岁时回到了故土俄国,着手准备他的第一部具有俄罗斯音乐风格的歌剧《伊万·苏萨宁》。
(二)俄罗斯民族歌剧创作概况
最早的俄罗斯世俗音乐称为“坎特”,是演唱世俗歌词的合唱或是合唱协奏曲风格的歌曲,这种音乐体裁是最初级的试图将俄罗斯本土的民族音乐与西方风格的音乐相融合的尝试。在凯瑟琳二世统治时期,通过给予欧洲歌剧作曲家们高昂的酬劳吸引他们来到这片寒冷而遥远的帝国,为她创作优秀的歌剧作品。凯瑟琳二世的这一举措使俄罗斯音乐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喜歌剧和严肃的意大利歌剧开始在宫廷中上演;二是俄罗斯作曲家开始接受来自意大利作曲家的训练。这对俄罗斯的民族乐派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歌剧《伊万·苏萨宁》中民族性的体现
(一)民族性创作题材
留学归国后,格林卡宣布要创作民族歌剧时,得到了文学社的同僚们的支持,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提出了以“伊万·苏萨宁”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创造一个浪漫传奇的民族神话,希望格林卡将传奇与历史融为一体,将民族主义的基石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展现。由此,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歌剧就这样从英雄神话故事中缓缓展开了。
《伊万·苏萨宁》主要讲述了俄罗斯民族英雄伊万·苏萨宁的故事,他是居住在科斯特罗马城郊的多米尼诺村的农民,他所居住的村子是当时沙皇米哈伊尔母亲的领地,因此苏萨宁一家对沙皇十分忠心;此时波兰国王得知俄罗斯选出新沙皇的消息后十分恼怒,便派遣多支分队潜入科斯特罗马,企图在新沙皇上任前将其杀死。一支分队闯入多米尼诺村并胁迫苏萨宁做他们的向导,带领他们找到沙皇米哈伊尔,苏萨宁将计就计佯装自己受金钱诱惑带领波兰军队往森林的深处走去,同时派儿子去给沙皇报信,得知消息的沙皇顺利躲过了刺杀,而苏萨宁却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最终英勇就义。[4]
(二)俄罗斯民间音乐曲调与节奏运用
格林卡在民族歌剧创作之初,便意识到如何完美地将民族音乐素材融入他的歌剧音乐之中是该剧创作的关键所在,他摒弃了其他作曲家们将民族音乐置于一个装饰性的边缘位置,采用多种西欧音乐为主体的创作模式,迈出了俄罗斯民族歌剧格局创立的第一步。
以歌剧第一幕为例,苏萨宁在给女儿写的信里问道“你怎么能想到在这样的时候结婚?”[5]此处的旋律是格林卡听到一位马车夫哼唱的曲子,是格林卡在歌剧中运用的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民间音乐之一。再以歌剧第四幕为例,苏萨宁将敌人引领进了广袤无垠的大森林里,决定在这里埋葬自己和波兰士兵,此时波兰人也意识到他们被骗了,苏萨宁开始演唱宣叙调:“死亡到来,我不怕他,我的责任已经尽到,请埋葬我吧,大地啊!”这里引用了俄罗斯的民间歌曲,旋律来源于脍炙人口的俄罗斯民歌《顺流而下的伏尔加母亲河》,作曲家运用大三小三柱式和弦交替,以及庄严肃穆的旋律,极大地烘托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迸发,民歌的熟悉旋律也能更好地引起俄罗斯民众们情感的共鸣。
从调式应用角度来说,俄罗斯民歌十分善于运用小调以及大小调的交替变化,他们将小调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民歌也主要以自然大小调为主。格林卡善于发现和挖掘与俄罗斯本土音乐相似的旋律,并对其进行本土化的创作。在歌剧的第三幕的一个唱段《我悲伤啊,我痛苦》,整段旋律采用了俄罗斯传统的生活浪漫曲,该段旋律采用g小调,小调音乐忧郁悲伤的情绪展示了安东尼达内心的担忧不安,抒情而动人的曲调也展示了安东尼达悲伤欲绝的心境;在该乐曲的第二部分,格林卡采用了大小调交替的作曲技法,在流畅的广板中,乐曲由小调转至大调,转调技法的应用形象地刻画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也预示了民族意识在压迫中逐渐觉醒。
格林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歌剧中突出戏剧性的根本在于音乐风格对立,在歌剧中风格对立的方式能够有效表现出两国音乐风格的差异,从而凸显出俄罗斯民族音乐风格。在歌剧的第一幕,具有俄罗斯民族音乐特征的农民合唱和重唱成为该幕的核心;第二幕则穿插了明显的“波兰”舞蹈,随着节奏的不断加快,戏剧性也不断地加强;第三幕中,格林卡精心的管弦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气氛渲染的作用,营造出波兰人步步紧逼的紧迫感,他们抓住了苏萨宁,苏萨宁大声喊出“上帝,拯救沙皇!”时,俄罗斯的二拍子音乐与波兰的三拍子音乐短暂叠加,对比鲜明,冲突到达顶点。
在17—18世纪,俄罗斯“坎蒂”音乐风格蔚然成风,这是一种三声或四声部的音乐,是俄罗斯音乐中最早的西方化世俗题材,常被用于赞颂或者欢呼。合唱的表演方式使该题材更加宏大,更易于深化主题思想、表达情感。整部歌剧中无论何处,只要事关沙皇统治的神圣权利被提及时,合唱旋律的主题必将出现(下谱例为《伊万苏萨宁》结尾的“圣歌进行曲”1—4小节)。
合唱旋律的唱词大致意思为:
我们沙皇的家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地方,
被上帝坚定的力量包围!
其下是整个俄罗斯的力量,
在城墙上面,一身白衣,
那是有翼的天使们在守卫!
这段作品的主题动机在当时被称为“圣歌进行曲”,且在当时的俄罗斯被称为第二首国歌,可见其产生的影响之深远,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段极具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的标志性旋律动机,被格林卡应用于歌剧当中,成为写意沙皇权利的主导动机。
三、格林卡对俄罗斯民族主义音乐的影响
(一)对强力集团建立的影响
“强力集团”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乐派团体组织,其创建之初的核心创作观点便是以格林卡为旗帜,并秉持着延续格林卡音乐创作风格的理念,摆脱欧洲古典音乐风格的束缚,创作出属于俄罗斯风格的民族主义音乐。强力集团将俄罗斯的民间音乐作为创作的灵感源泉,将创作的根扎入俄罗斯传统音乐的沃土中,作品具有浓厚的俄罗斯乡土气息。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他们学习格林卡将民间音乐语言与音乐作品相融合;除此之外,他们还广泛借鉴其他民族的音乐元素,使作品充满了“异族情调”。
例如作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除了增加了俄罗斯民间歌曲中宽广的旋律特点,还加入了具有东方音乐色彩的曲调;在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套曲的《漫步》中,调式音阶以自然音阶为主,善于运用四度音程,节奏也十分不方整,这些都是典型的俄罗斯民间音乐特征;歌剧《鲍里斯格杜诺夫》使用了俄罗斯风格的管弦乐拉开乐曲的帷幕,大量使用民间音乐调式和和弦,唱腔上采用了俄罗斯民间的哭腔。由此可见,格林卡的音乐创作思想、作曲技法、风格特征对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形成,以及音乐家们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
(二)从柴可夫斯基到格拉祖诺夫
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第一批专业院校培养的音乐家,他毕业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器乐培养和音乐教育,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音乐体裁,由于学习了系统的西方作曲技术理论,所以他十分注意西欧作曲技法的运用,将专业的作曲技巧同俄罗斯民族音乐传统有机结合,创造出极具个性和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
他的一生创作了105部艺术歌曲,其中大部分歌词取材于俄罗斯当时著名的诗人,他用俄罗斯语作为歌词并不是因为他语言的局限性,而是因为他热衷于母语,且他认为歌词应服务于音乐。他的作品经常性地引用民间音乐,他采取的处理方式也融合了他的人生阅历和作曲经验,例如,《弦乐小夜曲》中的第四乐章,直接引用了俄罗斯民歌《在牧场上》和《在绿色苹果树下》,这两首歌曲取材于巴拉基列夫的民歌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极富俄罗斯气质,在创作时将特有的小调忧郁气质和旋律都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作品中。
格拉祖诺夫被称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最后一人,他完满继承了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传统。他在1879年遇到了他的老师巴拉基列夫,二人亦师亦友,他在巴拉基列夫那里继承了许多创作优点。在音乐创作中,格拉祖诺夫热衷于以俄罗斯民间的音乐素材作为基础发扬俄罗斯的音乐文化,强力集团对格拉祖诺夫的音乐创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时常看到鲍罗丁宏伟壮阔的史诗性音乐、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辉煌灿烂的配器手法和柴可夫斯基优美抒情的旋律特点,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们对格拉祖诺夫有着深远影响可见一斑。他是一位有头脑的作曲家,虽受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影响,但他没有变成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在俄罗斯民族乐派与西欧乐派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展开了广泛的联系,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下,他以更加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俄罗斯音乐的发展方向,并试图引进德奥传统的音乐教育体系实现俄罗斯与西欧音乐文化的融合。
结" "语
格林卡被誉为“俄罗斯民族音乐之父”,是19世纪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民族乐派音乐家,他以一部民族歌剧《伊万·苏萨宁》开启了俄罗斯民族乐派光辉灿烂的新篇章,同时打造出俄罗斯历史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歌剧。格林卡对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对西欧先进音乐技巧的掌握,是俄罗斯作曲家中史无前例的。他引导了俄罗斯诸多的音乐后继者,踏上了探索民族音乐的道路,格林卡之后的民族乐派作曲家长期致力于挖掘、整理俄罗斯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民间歌曲、舞曲并进行主题运用或改编,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应用和推广。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们延续了格林卡将俄罗斯文学诗歌与俄罗斯音乐相结合的方式,不仅促进了民族乐派的发展,还将俄罗斯音乐作为一种载体,推动了俄罗斯文学的普及与传播。
参考文献:
[1] 蒋一民.音乐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31.
[2] 理查德·塔鲁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第三卷[M].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187.
[3] 尼古拉·戈尔.彼得堡笔记第七卷[M].V.V.卡拉什编辑,1836:340.
[4] 朱璐.歌剧《伊万·苏萨宁》中的俄罗斯音乐元素研究[J].北方音乐,2015,35(18):44-45.
[5] 孙志福.歌剧《伊凡·苏萨宁》中男低音所饰人物形象分析[D].天津音乐学院,2013.
(责任编辑:庄" 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