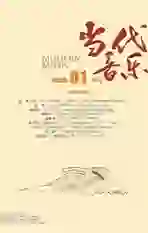国家在场视域下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
2025-01-18江雯吴艳
[摘 要] 自明清以来,徐州琴书以师徒传承为主、师生传承为辅的方式传承了两百多年。然而20世纪中国社会环境的变革,导致徐州琴书传承转变为以师生传承为主、师徒传承为辅的方式进行传承,并发展延续至今。从徐州琴书传承方式的变迁过程中,可以清晰地体察到“国家在场”的种种影响。本文试图运用“国家在场”这一研究方法,厘清徐州琴书传承方式的变迁过程,从而进一步探索其传承方式发生变迁的多重原因。
[关键词] 徐州琴书传承;国家在场;变迁
[中图分类号] J607"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083-05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导致与传统音乐相互依存的民间环境动荡不安。在原有生存秩序不断被干预的情况下,作为扎根于民间土壤的说唱艺术,徐州琴书随着时代的浪潮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着自身的存活形式。这里的存活形式是指徐州琴书为适应国家制度、民间环境、社会观念等因素寻求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多种形式,包括音乐、曲本、传承、场所等。传承作为徐州琴书的存活形式之一,从百年来以师徒传承为主的传承方式转变为近代以师生传承为主的传承方式。这样的转变自然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在现有徐州琴书传承方式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大多将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独立看待,鲜少关注其衍变过程。张振涛在《追寻唢呐——晋北鼓吹乐的平描与深描》一文中提及:“改朝换代,更旗易帜,另立门户,自然导致了民间社会艺术表现方式的相应调整,调整的具体步骤,则是观察民间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1]
其中提到的“调整的具体步骤”即变迁的过程,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仅关注变迁的前身和变迁后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对其变迁过程的忽略。本文意图厘清在国家在场的力量之下徐州琴书传承方式的变迁过程,而后进一步分析其传承方式发生变迁背后的原因。
一、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研究方法:国家在场
“国家在场”的概念源自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于1988年在《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一书中提出的“a state in society perspective”一词,即“社会中的国家”[2]。其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国家意识处于高位并凌驾一切的认知。后来该概念不仅成了社会学的核心热点话题,也被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
近年来,“国家在场”这一概念被作为研究方法或视角带入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领域,其首先被运用于仪式音乐的研究中。张振涛在《晋北采风二题——民间花会与国家在场》一文中采用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分析鼓吹乐在民间花会中组织形式、象征意义、行为性质等产生的变化,以揭示国家在场对鼓吹乐变迁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3]。张振涛在《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同样采用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晋北鼓乐乐队组成、乐班起落、音乐本体等多层面变化的剖析,阐述了晋北鼓乐在国家在场影响之下发生的变迁[4]。随后,“国家在场”被陆续运用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研究中。在民间音乐的研究中发现,音乐本体、活动、文化、乐班、传承等研究均对“国家在场”这一概念有所使用或涉猎,而在聚焦传承的国家在场相关研究中,主要关注民间音乐传承场所的变迁,暂时未对其传承方式变迁给予关注。
“国家在场”的概念界定虽从无定论,却在前人多个领域、多种层面的研究成果中逐渐明晰。“国家在场”即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括,其中包含两层动态的相互制衡、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是国家意识通过中央、省、市、县不同层级权力机关的政治与行政力量参与到民间社会、文化和艺术活动中,使后者被动地存在于国家意识中;二是民间社会、文化、艺术为体现其正当性冠以国家符号展开活动,前者主动地将国家意识融于自身之中。两层关系都导致了一种结果,即民间社会、文化、艺术活动中包含着国家意识。本文对“国家在场”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强调国家各级行政力量对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的影响,以及在传承关系下艺人、学生和社会观念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
二、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概念界定
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乍一看似乎区别不大,师指传道授业者,而徒和生都有向其学习的意味,所以二者使用时常常有混合交叉的情况。然而,这两种传承方式虽在字面上仅一字之差,但在深层含义上却相隔甚远。为防止二者含混不清,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
(一)师徒传承
“师徒”即师傅与徒弟的合称。《韩非子·诡使》中提到:“私学成群,谓之师徒”[5],意指违背君主教令而私自设学的各家学说中存在的传授关系,即为师徒。其阐明了师徒传承的内核,简单来说,就是师傅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以其个人意愿为主导,私自招收自己传授技艺的人选,二者之关系,称为师徒。在正式确立师徒关系前,一般会举行拜师仪式。师徒关系建立后徒弟跟随师傅生活,吃穿用度皆由师傅负责。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不拘于固定场所和时间,有时正式在家中教,有时兴头上来也会在演出前后教,甚至可以说师徒传承是浸润在生活中每时每刻的。其传授关系往往为一对一,传授方法为手口相传,重点聚焦于实践操作。在出师前,师傅要保证徒弟所学技艺足以独立谋生。如若不能,则不可出师。
(二)师生传承
“师生”即老师与学生的合称。近代以来,由于西式教育的引进、教育类机构的创办与班级授课制度的确立,老师与学生的称呼逐渐被广泛使用。师生传承往往存在于政府支持下的教育机构,由机构招聘老师和招收学生,老师在教室或其他固定场所以班级为单位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艺。师生关系无须通过举行仪式来确定,只要学生通过此类机构的招生标准,而后就会和机构的老师学习技艺。师生传承的传授关系一般为一对多,老师对学生的传授只存在于课堂之中,一下课,传授随即停止。其传授方法也受场所、学生人数和时间的制约,多为老师在课上讲授技艺知识,学生在课下自己练习。学生完成在机构学习的年限后,就代表着师生关系的结束。无论学生学习程度如何,老师对学生都没有继续教育的责任。
由此可见,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在依附关系、传授关系、传授时间、传授场所、传授方式及责任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徐州琴书国家级传承人魏云彩也曾在采访中说到:“教学生和收徒弟的概念不一样,我学生很多,可以说到处都是,但学成的很少,有的是一时的热爱,学一阵子就完了,我对他们也没有继续教育的义务。但徒弟就不一样了,徒弟是要我一辈子去教的,我要把我一生的所学都毫不保留地传给他们,一点一滴都不留。除此以外,我还要逼着他们在我的基础上创新,青出于蓝胜于蓝,冰出于水寒于水。[6]”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不同的传承人都多次强调徒弟与学生的差异。可见,徐州琴书的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泾渭分明,不可等量齐观。若忽略其差异、含混其概念,不仅对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过程难以做出清晰的梳理,也会导致传承方式变迁的原因及其对徐州琴书发展的影响被忽略不计。
三、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
从现存资料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之前,徐州琴书主要依靠师徒传承为主、师生传承为辅的方式进行传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由于国家力量之下的种种影响,其转变为以师生传承为主、师徒传承为辅的方式。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以师徒传承为主、师生传承为辅的传承方式
徐州琴书从明清时期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主要依靠师徒传承为主、师生传承为辅的方式得以流传。
1.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的师徒传承
自徐州琴书萌芽之际,师徒传承便伴随着其发展。笔者将徐州师徒传承分为家传与师传两种情况:一是家传,即师傅与徒弟属于同一家族,具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如师傅招收子女或子女的配偶作为弟子,除师徒关系外有着另一层亲属关系;二是师传,即师傅与徒弟不属于同一家族,无血缘或亲戚关系,多为弟子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师传弟子需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人介绍,并请担保人作保,托代笔师写下拜师帖,师傅同意后方才招收进门。
不管是家传弟子还是师传弟子,师徒关系完全确立还需举行一种仪式——拜师仪式。该仪式须在师傅同意收徒后,正式传授技艺之前举行。只有仪式圆满完成,才代表新徒弟正式成为师傅的弟子,成为该门派中的一员。徐州琴书这一行有一严格的行规,即无师门者不得演出。举行仪式相当于昭告天下,赋予徒弟在这行身份的正当性,给予徒弟可以演出的权利。徒弟的演出水平影响着师傅的名声,昭告天下的仪式让世人皆知其师傅为何人,所以师傅必须认真教学,让徒弟的演出得到观众的认可。仪式的举行,不仅代表着徒弟对师傅的尊重和顺从,让师傅多一重心安,同时也约束着师傅对徒弟的行为,让徒弟最终学有所成。
在拜师仪式后,师傅正式开始向徒弟传授技艺,学期一般为3—6年,具体时限视徒弟学习情况及其意愿而定,基本要等徒弟技艺成熟能够独立演出后,才允许出师。在拜师学艺期间,师傅要向徒弟传授演唱、演奏的技艺和主要的书目,徒弟需依规将演出的全部收入上交给师傅。出师一年后,徒弟不必上交演出收入,但在逢年过节之时需向师傅有所表示,礼品轻重均可。等到师傅年事已高无法演出谋生时,徒弟就有供养师傅之责。师傅百年之后,徒弟执子礼为其送葬。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家传弟子还是师传弟子,师徒关系之中都夹杂着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亲人之情。师傅看待徒弟就像是看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希望他能在这一行有所成就而倾囊传授,师傅好也让徒弟铭记于心,在其暮年之时尽心照料,师徒传承由此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的、良性的传承方式。
2.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师生传承
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开始于清末由政府支持下举办的育婴堂、清洁堂等慈善机构中,慈善机构将盲童根据其兴趣与天赋进行分班分组,聘请专业老师为他们集体教学丝弦(徐州琴书的旧称),形成了师生传承的关系。该类机构由于清政府的崩溃,于民国三年前后纷纷停办[7]。自此,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进入了空白时期。
1958年,徐州专区文化艺术学校曲艺班经徐州专区公署批准正式成立,标志着徐州琴书近代以来师生传承的继续。该曲艺班招收徐州琴书专业学员二十余人,学制三年,开设语文、政治、乐理、表演、形体、专业课等课程。聘请孙成才、朱邦侠为徐州琴书专业课老师[8]。孙成才、朱邦侠等人是当时徐州琴书界的泰斗级人物,专业程度自不必说。但由于二位大师文化程度有限,并没有形成教学大纲,主要以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一般情况下,女生学扬琴和打板,男生学坠胡,将器乐学会后再学唱。教学曲目以琴书小段为主,如《刘二姐算卦》《猪八戒拱地》等[9]。为了检验与加强教学效果,学校偶尔还会组织学生们到各地演出。从1958年徐州文化艺术学校的师生传承中可以看出,该阶段的徐州琴书师生传承略显青涩,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师徒传承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同时对徐州琴书学员进行了文化素质和声、台、行、表等舞台表演素质的教学。
虽然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徐州琴书的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都各有发展,但纵观徐州琴书的传承谱系,师徒传承自徐州琴书产生之际就一直稳定地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观师生传承,不仅比师徒传承出现晚,且其延续出现断层。总体来看,徐州琴书传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呈现出以师徒传承为主、师生传承为辅的传承样貌。就是在这样的传承方式之下,徐州琴书流传了两百多年之久,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门派。
(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以师生传承为主、师徒传承为辅的传承方式
好景不长,就在徐州琴书师徒、师生传承并行发展之际。1966年,徐州琴书传承戛然而止,依靠官方支持下的师生传承被快速叫停,民间的师徒传承也迫于压力随即停止,师生传承与师徒传承在此期间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十年浩劫后,徐州琴书传承逐渐转变为以师生传承为主、师徒传承为辅的方式。
1.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师徒传承
1976年,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曲艺传承环境逐渐宽松。然而,十年的停滞使得极度依赖民间环境自我发展的师徒传承遭受了严重的打压,艺人们迫于压力纷纷转行。而后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以及徐州琴书师生传承对师徒传承优秀资源的占有,使得徐州琴书民间传承市场渐渐缩水,师徒传承自此日趋衰弱。
2.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师生传承
与师徒传承相反的是,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由于官方的支持在各种徐州琴书班中迅速复苏。1977年5月,徐州市文工团(前身为徐州市曲艺团,于1970年并入徐州市歌舞团成曲艺队,艺人多称其为文工团)开设声乐、形体、乐理、专业课等课程,聘请孙成才、朱邦侠为琴书专业老师,招收琴书学员数名;1980年丰县曲艺队经县文化局批准,举办曲艺培训班招收琴书学员;1984年邳县曲艺研究小组于县文化馆举办徐州琴书培训班,聘请孙成才、朱邦侠为老师,培养了十三名青年琴书演员。
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历经百年的风雨和磨难,于21世纪初逐渐趋向成熟。2002年,徐州文化艺术学校招收琴书学员若干,学制为4年,开设文化课、基础课、专业课三大类课程。聘请魏云彩、蒋立侠、张巧玲等人为徐州琴书专业课老师。魏云彩制定了徐州琴书的教学大纲,并对徐州琴书的教学内容以半学期为单位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笔者将其规划列成表格如下(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2002年徐州文化艺术学校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相较于1958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有了详细的教学大纲,教学过程设计更加循序渐进;二是器乐与唱腔教学不再分开,而是齐头并进;三是在器乐教学方面进一步拓展教学其他的民族乐器,培养徐州琴书学员演奏其他乐器的能力;四是增设学生自主设计唱腔的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徐州琴书的曲本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五是课程目标从教会学员唱琴书小段曲目提升至中长篇曲目,增强琴书学生的专业能力。
此外,除专业课与文化课外增设了基础课程,主要包含台词、乐理、视唱练耳和声乐,为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专业课较以前也有了更加丰富的设置,不仅包含唱腔课、说表课、器乐课、音乐课、形体课、排练课这些必备课程,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专业水平,还设置了讲座课及专业实习。与此同时,文化课也增设了课程,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和历史,使用全日制高级中学统一教材,较好地兼顾到了徐州琴书学生的文化修养。此时的徐州琴书师生传承正式进入成熟阶段,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过程等方面都更加科学、细致和全面。
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与师徒传承在共同经历“文革”后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前者在国家的帮扶下快速回暖并迈入成熟阶段,后者依靠民间环境却有着无力回天之兆。至此,师生传承接替了延续百年的师徒传承在徐州琴书传承中占据主导地位,徐州琴书传承完成了由师徒传承为主转向师生传承为主的变迁过程。
四、国家在场下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原因探析
在国家影响之下导致的一系列变革使得徐州琴书的传承方式由师徒传承为主转向了师生传承为主。笔者将从国家、艺人、学生和社会四个方面切入,分析徐州琴书在国家在场影响之下传承方式发生变迁的原因。
(一)国家支持下的师生传承
1985年,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指出,“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化艺术生活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文化大普及,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必须大发展大跃进,必须全面规划,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各省、市、自治区都能建立起完整的艺术教育网。省、市、自治区和有条件的专区和县争取在三、五年内都能建立综合性或专科性的高等和中等文化艺术学校”[11]。徐州文化艺术学校和艺术团体中的曲艺班在全国艺术教育大跃进思潮和中央会议任务下达的官方干预下应运而生,如此一来,得以继续发展的师生传承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
特殊时期结束后,师生传承有着国家的支持而被优先延续下去,托举师生传承发展的各类徐州琴书班由文化部门统一招生,经过层层选拔,被挑选中的学生通常有着十分优秀的条件。学生有了,必然要聘请教授徐州琴书的专业老师,民间的知名艺人就成了不二人选。一些民间的知名艺人,如孙成才、朱邦侠、杨氏喜等人相继成为徐州琴书教学班的琴书专业老师。这些艺人拥有了文化部门统一招收的学生,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徐州琴书教学班的教学工作中,自然也就将自己收徒的事情搁置一边了。值得注意的是,知名艺人一般都是技艺精湛,在琴书界影响较大的人物,这样的艺人往往能吸引更多的徒弟慕名。然而,由于官方支持下的琴书教学班聘请这些知名艺人为老师,导致一些知名艺人停止收徒。依赖民间环境的师徒传承情况在十年停滞的冲击下,加之名师和优生缺失的多重影响下走向衰弱,而被打上官方印记的师生传承在各类徐州琴书班不断涌现中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试想一下,如果师生传承没有国家的支持,经历特殊时期之后的徐州琴书传承大概率是会回归到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师徒传承还是已经中断近五十年的师生传承?答案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国家支持下的师生传承才是导致徐州琴书传承方式变迁的根本原因。
(二)民间艺人对老师身份的认同
在笔者进行田野考察的过程中,有幸采访到孙成才、朱邦侠的家传弟子孙茂荣,传承人孙茂荣回忆父母在学校的执教经历时说道:“我爸爸妈妈在戏校(即徐州文化艺术学校)当老师的工资不够养活一家人,而赶集一天都比两人一个月拿的工资还多,所以想过回去赶集唱书,但挣扎再三还是在学校坚持下来了”①。从上述田野记录与现有资料中可以看出,尽管戏校微薄的工资使孙成才、朱邦侠夫妇入不敷出,养家糊口十分艰难,但夫妇俩仍然不愿辞去学校的工作,回去赶集唱书,而是不停地在各类琴书教学班中执教。不仅是孙成才、朱邦侠夫妇,大多数被聘请为徐州琴书专业老师的艺人也鲜少再去赶集摆摊唱书,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各类琴书教学班一直任教直至退休。
笔者认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艺人与学校的学生产生了师生之情,出于对学生负责、不愿耽误学生的态度,尽管艺人收入微薄,但仍坚守在徐州琴书的教学岗位上。其二是身份的转变。艺人们普遍觉得唱徐州琴书被人们看不起,而官方支持下徐州琴书教学机构的出现,赋予了艺人全新的身份——老师。艺人摇身一变,从被人看不起的、摆地摊的说唱艺人变成了受人尊重的、在课堂执教的老师,世人目光与工作场所的转变,使艺人感到备受尊重,加深了艺人对老师身份的认同。双重原因之下,进一步巩固了徐州琴书的师生传承。
(三)学生对“铁饭碗”的渴望
在20世纪,学生学习徐州琴书的主要目的是谋生,这些学生一旦考入官方支持下的琴书班,在毕业之后能够直接获得事业编制,成为国家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人事管理权限属于国家相关部门,工资、各项福利待遇等都有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相当于拥有了一个“铁饭碗”。无论是谁,在当时能够有个“铁饭碗”是极其不易的事情,“铁饭碗”就代表着生活的稳定和光鲜。这对自古以来需要跟随师傅到处摆摊、尝尽人间冷暖还不知能否得到观众喜爱的徐州琴书学徒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据1988年考入徐州文化艺术学校的传承人吴长青所说,学生想考入这些琴书班是很困难的,不仅选拔十分严格,报考人数也非常多,个位数的名额往往有几百名学生过来报考,竞争是异常激烈的①。窗明几净的教室和技艺精湛的名师,加上毕业之后就能够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使得大批的琴书学生对琴书班趋之若鹜。在“铁饭碗”的吸引下,琴书班学生络绎不绝,也使得师生传承在这种优质学生源源不断的输入中更加蒸蒸日上、繁荣兴旺。
(四)推崇师生传承观念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动荡结束,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师徒传承被人们看作旧社会的产物。因为学徒在出师前都不能获得演出的收入,而是全数上缴师傅。同时,师傅对徒弟的行为有着绝对的管束权和话语权。于是,师傅被描绘成万恶的“黄世仁”,徒弟则被比作可怜的“杨白劳”。这种社会观念悄无生气地浸润并摧毁着师徒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对师徒传承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此时,存在于官方琴书班中平等的师生传承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推崇。
时至今日,师生传承仍活跃在中小学、高中、各大院校以及社会团体中,培养着徐州琴书的高质量青年后备军,致力于将徐州琴书发扬光大。未来徐州琴书的传承依然任重道远,但道阻且长,行则将之。相信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以及徐州琴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努力下,徐州琴书终有一天会洗尽铅华,大放异彩!
结" "语
当我们面对一种已经发生变迁的事物时,有必要分清其变迁前与变迁后的情况分别是怎样的,厘清其是因为何种原因变迁,而后又是通过何种方式继续延续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清楚完整地洞察事物的变迁过程。
徐州琴书的传承方式在国家在场的影响下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师徒传承为主转为师生传承为主,发生变迁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国家强制力支持下的师生传承对原有师徒传承名师、优生等资源和市场的占有,也有民间艺人、琴书学生与社会观念对标记了“国家符号”的师生传承所带来的身份、待遇等方面的迎合。在两重原因相互作用与相互制衡的关系下,徐州琴书的传承方式历经磨难完成了它的变迁,然而需要进一步深思的是,徐州琴书传承方式的转变给徐州琴书的发展带来了何种影响,如今以师生传承为主的传承方式是否是徐州琴书传承的最优选择,师生传承可否从延续两百多年的师徒传承中取其精华完善自身发展,当下的徐州琴书传承如何适应时代发展推陈出新为徐州琴书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笔者后续将撰文对徐州琴书传承的一系列问题作进一步阐释。
参考文献:
[1] 张振涛.追寻唢呐——晋北鼓吹乐的平叙与深描[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03):97-104.
[2] 崔沁宇.“国家在场”视域下沭阳县淮海剧团历史发展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20.
[3] 张振涛.晋北采风二题——民间花会与国家在场[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01):101-105.
[4] 张振涛.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467.
[5]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448.
[6] https://news.cnr.cn/dj/20161228/t20161228_523406386.shtml.
[7] 魏云彩.徐州琴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360-361,376-380.
[8] 单兴强.徐州曲艺考[M].徐州:徐州市文化局,2006:261-262.
[9] 于雅琳.谈徐州琴书的师徒传承与师生传承[J].音乐时空,2015(21):13-15.
[10] 同[7].
[11] 佚名.到基层去办文化艺术学校: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办学方针和跃进计划[N],人民日报,1958-9-13.
(责任编辑:刘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