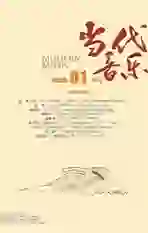音乐风格阐析的“新视野”
2025-01-18田际宁
[摘 要] 风格是音乐作品表现的方式、形式与样式,也可被视作作曲家一切特质的集中体现。因此,阐析音乐风格成为西方音乐研究的重要话题。而风格分析又触及技术理论、社会文化视野等多种因素。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奥多尔·阿多诺的社会学视野便为阐释音乐风格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种研究音乐的新方法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与艺术美学、作曲理论等各个领域知识的全面精通,也使得他在阐释音乐风格时运用大量社会学方法思考音乐现象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种关联不仅涉及音乐的社会功能与形成音乐风格的社会性成因,也涉及对音乐风格的国别性、阶级性等层面的关注。本文以阿多诺最负盛名的音乐文论《新音乐的哲学》为研究对象,夯实与梳理其中所运用的音乐社会学理论,以作者对音乐风格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具体案例作深入分析与二度阐发,谈及勋伯格的音乐大量涉及批判性特征,映照着二战时期特权阶级横行而催生出的人民的批判与反抗精神,斯特拉文斯基与社会潮流的调和导致了其音乐的退步等音乐现象。此外,笔者还试图将这种新视野引入当代音乐研究方法中,通过运用阿多诺文论中挖掘出的理论与方法,以更好地解读“风格”这一西方音乐的重要话题。
[关键词] 阿多诺;音乐风格;音乐社会学;《新音乐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 J605"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059-05
阐析音乐风格是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永恒话题。那么,什么是音乐风格?《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将其定义为:“一种表达方式……既可以表现音乐的普遍性,又可以表现音乐的特殊性。”[1]查尔斯·罗森在《古典风格》中认为:“一种风格可以被比喻性地描述为一种探索语言、凝练语言的方式……也正是这种凝练聚焦,使所谓的个人风格或艺术家的独特性成为可能……一个群体风格体现某种综合的程度……它将时代中相互冲突的力量调节为同一的和谐。”[2]如此便为我们揭示了一种观点,即音乐风格与时代要素之间有着某种紧密联系。
在这一视角下,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为笔者提供了启示。他在《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提出“音乐形式,甚至音乐反应的组成方式,都是社会形式的内化……音乐不仅是内心的自我塑造以及从迫切的社会需求中得到自我解放的形式,也同样是一个社会事实。甚至连音乐中从未被社会整合的部分,本质上也是社会的。”[3]这一观点无疑揭露了音乐形式与社会因素的联结,在其音乐社会学相关的论述中,我们也能发现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乃至国家民族与音乐的联系。
在对阿多诺相关著述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其不仅深耕于社会学理论,还将社会方法活用于解读音乐现象与音乐理念中。在他最负盛名的著作《新音乐的哲学》中,便涉及对大量重要作曲家、音乐文化工业的论述与批评,如他所说:“艺术作品……是被转化为现象的潜在的社会本质……艺术作品的形态仍是对客观的社会状况的客观回应”[4]。他因此通过广泛的社会学视角阐析了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品质,其中有对音乐生成与社会阶层及意识形态关联的论说,也有对这些音乐作品的社会意义乃至社会功能的剖析。
由此,笔者希望在本文中梳理并夯实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通过解读《新音乐的哲学》中的案例,抽离其中的方法范式,最终阐释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音乐研究中的价值。
一、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
洛秦认为,“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是一种批判意义的哲学思考……告知大众怎样从音乐的‘言谈举止’中分析社会现象”。这种说法显然准确而富有洞察力。我们可以在阿多诺的表述中找到类似的观点,“音乐社会学一定得建立在音乐形态与社会分析的断层和缝隙之中,研究其中发生的事情……音乐社会学是一种以艺术手段进行的社会批评”[5]。由此可见,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并非抽象的术语概念,而是在对音乐现象的分析过程中找寻音乐生成与社会背景的紧密联系。笔者在此将其理论中的重要部分凝练解读。
音乐是否具有社会功能?在阿多诺看来,音乐中切实带有一种“交流性”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来自音乐所带有的“第二语言性”,其表现在听众无需理解音乐作品,便可以通过特定的术语联系起音乐的形式与内容。这种交流性的语言使得音乐带有类似社会功能的作用,“它之所以如此轻易地、毫无抵抗地从艺术中浮现出来,是因为音乐艺术很晚才拥有自主自为”。[6]
这种自为性或者说“自然”与资产阶级社会由商品原则所导致的功能缺失相关。对商品交换的否定,更准确地说对“同一化”的否定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根基。《否定辩证法》中写道:“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共识,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7]。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纳入商品交换,用同一性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一切事物,可是这种平等下掩藏着分配不均。而这种商品原则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缺失,“现实的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从其本身原则中发展出来,而必须与前资本主义的、古老的原则合并才能发展。在一个彻底功能化的、完全受商品交换控制的社会里,功能缺失就变成了功能的第二性征。”[8]由此,社会功能的缺失使得音乐作为特殊的文化产物而获得了自为,因为由人创造的艺术本身便带有对社会语境的批判意味。
但这种自为也同样被资产阶级社会所利用,他们将音乐贬为无关紧要之物,又通过营销手段来推销这种没有实际功能的文化商品。在这种手段下,人们逐渐失去理解音乐内容的能力,对“充满美学语境寓意的音乐欣赏能力退化了”。这便照应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之一:“盲目且无条件地接收某一事物及其现状”。这种原则所对应的功用昭然若揭,“有效地防止人们对自身及社会的反思”[9]。音乐的这种社会功能也为人们提供了虚伪的满足,越是嘈杂的音乐越天然带有这种鼓舞作用,使得沉浸其中的人们感受到声音的力量,从而忘记生活中的失败。诸如此类,音乐的功能随着营销手段的改变而改变,最终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社会的整合,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中提供虚假的即时感。在这一方面,“社区音乐”与电影音乐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不带有自为的音乐内容,通过绵延不断的音响让听众忽略其感知存在,而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
另一方面,音乐依附功能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也带有社会必需的外貌,它“培养调教人的无意识,把无意识变为条件反射。”[10]在这种环境下,思想意识的形态逐渐减少,人们的批判意识被褫夺,只空余单调重复的现状与任意编造的谎言,进而将更加含糊的思想内容强加于音乐功能。
我们该如何抵抗音乐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消耗呢?阿多诺认为,只有反对“那些脱离音乐的或者散乱的关系模式”[11],支持一些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对世界与自身进行批判的人们才可以改变现状。在他看来,勋伯格的作品便是这样一种存在,这也是他在《新音乐的哲学》中将勋伯格的音乐视作进步的原因。
阿多诺认为,音乐所特有的社会功能及其附带的意识形态掩盖了潜藏其中的阶级存在。这是由于独裁者所营造的“愚弄民众”的语境造成的,也就是说现行音乐是虚假的社会思想意识的来源。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不难理解勋伯格的音乐为何激起如此大的争议,原因之一便是其作品不能为社会稳定服务,方才被独裁者贬为“腐败的音乐”。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音乐能反映社会整体的阶级关系,音乐风格所展现的社会立场并非音乐本质,而只是附带的一种现象。作曲家越能理解社会与个体的对抗关系,越能将音乐所象征的社会意义展现得更深,音乐作品陷入虚假的意识形态的风险便越小,便越能表达其客观意识的内容。
总而言之,“音乐只能以自己的结构再现社会的矛盾”,其越通过结构形式展现对社会的对抗,越能灵活利用音乐形式语言表现矛盾与对立,便越能以音乐载体表现社会灾难,从而以音乐特有的形式来呼吁人们改变现状。如他所说:“音乐不应该是一个无助而又惊恐的社会旁观者;如果存在于音乐内部的、作曲艺术中最核心部分的社会问题,能以音乐自身的材料,依照自身的形式规范得到表现的话”[12],音乐方能完成其真正的社会功能。
二、社会学视野阐释音乐风格实例分析
在构筑音乐社会学理论时,阿多诺便以截然不同的态度论述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风格。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他对这两位作曲家的分析则更加深入与全面,其中不仅涉及以社会学视野对音乐作品形态与风格的分析,还直接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如在《勋伯格与进步》的末尾,便表达了他对社会、阶级、音乐之间的看法——“音乐与阶级以及各种社会势力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抽离该书中在社会历史语境下论述音乐的案例,分析其中的音乐现象与社会学方法。
作为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的音乐应时代人文而生,也客观反映着社会与历史。在“孤独的辩证法”一节中,阿多诺便提出,“勋伯格由于无条件地执着于孤独性,他就触及到了孤独性的社会性特征”[13]。最为凸显这一特质的音乐作品是他的音乐剧《幸运之手》,其中不仅体现着对资本工业的批判,叙事结构也映照着工业社会与个体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部音乐剧中的批判显现在每个细节之中,如第三场的台词“那件事可以更简单地完成”便象征着对工业多余工序的批判。其中,对生产过程的虚假化也呈现出劳动个体与社会经济体制的矛盾关系。主人公用魔法刹那间将金块变成饰品,显然脱离了客观的劳动生产过程;旁观工人对此的轻蔑,也象征着资产阶级劳动个体与工业体制的割裂。笔者认为,其将工业生产过程视作魔法,也表现着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工业生产之间的隔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音乐不应去粉饰,而应该是真实的”[14]。《幸运之手》这部作品便显现出表现主义音乐的本质,源于假象,却客观反映着真实社会。
在纯音乐领域,勋伯格的音乐语汇仍体现着音乐的批判功能,以其最为著名的十二音技法为例,阿多诺认为。其“作为拥有控制权的高超技能,排除了任何他律性的东西”[15]。这便照应着上文“音乐的社会功能”中所谓的音乐自为即“自然”,这种特质使得音乐更具有社会批判功能。为此,勋伯格试图在音乐中掺入“实证主义”的因素,并思考如何让十二音技术建筑而成的音乐结构带有社会意义,即上文中所谓以自身结构再现社会矛盾。在其晚期作品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他通过对十二音技术一定程度的抵抗,从而使得艺术的主体部分回归,让技术能够“服务于存在它自己的内在本性之外的目的”[16],即带有社会批判功能。
然而,十二音技术的运用也使得声音本身受到侵害,主要体现在对不协和音的“解放”,曾被审慎使用的“小二度”被任意使用,使得不协和音貌似丧失了原有的历史意义。但阿多诺认为,“和弦中每一个声音都与和弦结构中的其他声音结合在一起,但在这一和弦结构内部每一个音又全都互相不同”[17],由此,和弦内部的矛盾结构让不协和音的历史意义再次显现出来——通过音响表现紧张、矛盾与痛苦,这种音乐意味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积淀”,最终成为既定的音乐素材,再次照应着阿多诺所谓以音乐结构再现社会矛盾、展现灾难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除了以上隐性展现社会矛盾的作品之外,勋伯格也曾直接将社会与政治问题涉入音乐,其作品《华沙幸存者》便真实地反映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也表达了明确的政治倾向。莱博维茨写道:勋伯格决定把当时历史上最恐怖的插曲放入音乐中,他的这种艺术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和历史的一种参与。正是勋伯格对社会的积极参与,使他的音乐品质与社会要素紧密联结,如莱博维茨对该作品的评价所说,“对社会现实及美学现实的整体介入使得这部作品成为当时最具独特重要地位的作品”[18],也是这种“对待现实的态度”使他成为了阿多诺笔下的“进步者”。
同对勋伯格的评价截然相反的是,阿多诺认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象征着一种倒退,不仅缺乏社会批判精神,其主导的“新古典主义”不能表现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自然现象。
为探讨其音乐的生成语境与形式风格,阿多诺首先剖析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精神内涵,认为他所针对的是“一切逃避社会控制的东西的印迹”[19]。为此,他在市民阶层中着手复旧的尝试,希望一切新音乐如他所希望听到的样子。这种复旧观念与其同时代的哲学理念有所关联,“放弃一切心理主义,还原为纯粹的假象,使事物像他自身存在那样”[20],这种理念开辟了“真实存在的”领域。若以社会学视野来观察,其反映的便是对现实社会与其意识形态的矛盾,即一切“事实”与其精神的矛盾。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斯特拉文斯基栖身于远古的野蛮风俗领域,去除音乐中一切文化要素,反叛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让远落后于时代的音乐盲目运行,其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一切音乐的社会功能不复存在,音乐的意义也变得盲目。
其音乐同样涉及社会现象,以《彼得鲁什卡》为例,其中便称赞了劳动分工这一现象——在勋伯格《幸运之手》中予以批判——他甚至试图将劳动分工发展至极端,以其形式摆脱其内在本质。他的和声飘忽不定,失去音乐的一切趋势,一切演员的狂热情绪,高超的技艺都在无意义的领域中重复,从而呈现出极致的本质与形式的分化。在结构上,这部作品由无数的片段组成,呈现出无序与对抗。从音乐表象中我们能触碰到其作品的特性,牺牲艺术的主体而只空余形式,从而使音乐失去一切意义。
在斯特拉文斯基另一部著名作品《春之祭》中,延伸了其一以贯之的反人道主义理念,诚如考克托所说:“我们应该想象,一个主要是由异性选出的少女的牺牲对于春天的复苏是必须的”[21]。这部音乐反映的“野蛮人”的时代,其也蕴含着作曲家对消除现存社会现象的渴望,彰显了“市民阶层的和谐也强大的假面具之后的真理的追求”[22],正如上文“音乐与社会阶层”中所说——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带有特殊的阶级特点,一切音乐表达都是站在其自身立场的抒发,带有鲜明的特权阶级特征。另一方面,音乐内容的复旧也势必造成作曲技法上的倒退,如勋伯格所指出的,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的节奏概念变得十分狭窄,“牺牲了节奏组织化的全部成果”[23],一成不变的节拍使得音乐失去表现力,由于缺乏连贯的节奏关系,音乐的内在结构也被破坏,使得音乐失去以形式结构表现社会内容的能力。
因此,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无疑与阿多诺所尊崇的启蒙精神——表现在处处都在支持对社会统治势力的反抗——相悖。他限制了音乐的自为与社会意义,并导致音乐技术的倒退,也正是由于其音乐的倒退倾向、与社会潮流相调和的倾向被阿多诺称作新音乐的“投降书”。
三、生成语境、价值阐发与当代延伸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阿多诺将其所构筑的音乐社会学理论与对音乐风格、音乐家的分析与批评相联通,从而能够对音乐进行细致入微、包罗万象的考察。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敏锐感知与积极思考,进而衍生出了一种社会批判思想。
这种观念的生成也离不开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精神。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创建理想社会要通过引起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关注来实现”,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就负有这种庄严的使命。因为在他们得自黑格尔的艺术观念中,艺术的内容乃是精神、理念和真理。在违背真理的社会里,真正的艺术必然具有社会批判的功能,“反抗的因素内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艺术“能唤起人们对于自由的回忆”。[24]正因如此,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时刻阐发新音乐中对异化社会的批判和抗议的因素。对他而言,作为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艺术必然具有社会批判功能。音乐的纯形式中包含历史、社会、精神等元素,因此对音乐的分析与批评也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
这种体察音乐的方式也与该书的创作时代相关,“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25]由此,阿多诺为何如此强调音乐的社会批判功能便不言而喻了。即使在他看来,音乐并非能直接深入社会深层,而只是“真正的海上传信的浮瓶”,这种特殊的文化产物也有其特殊的“启蒙”意义。
在这种语境下,他对“新音乐”寄予厚望,因为“纯粹的艺术作品必须遵循自己的法则,并彻底否定商品社会。”[26]“艺术若能一方面吸收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业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能遵从其自身的经验模式并且同时表现经验的危机,那便成了真正现代的艺术……现代艺术更有可能反对而非赞同其所在的时代精神。”[27]正是“新音乐”承载了阿多诺的“启蒙”精神与对社会建制的抵抗,才使得他扎根于社会学土壤考察这一特殊的音乐类型。
由此,我们可知,并非所有音乐都能用社会学视野考察,只有能够客观反映社会矛盾与社会要素紧密相连的作品,才能以这种方式分析。这让笔者不禁联想到于润洋首次提出的音乐学分析“如何以社会-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音乐”。姚亚平写道,“以开放的姿态,将音乐视作一种与人、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的精神文化现象,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分析和研究音乐”[28]。如此看来,音乐学分析显然与阿多诺以社会学视野阐释音乐有着异曲同工的意味,但并不相同——阿多诺的运用社会学分析音乐的方法更侧重于音乐作品再现社会矛盾,展现对社会的批判功能;而音乐学分析则是将作品置于社会历史等生成语境中全方位地考察。笔者认为,这种转变与社会时代相关,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们或许不再需要用音乐来批判社会了,但将音乐文本与社会文本建立联系的思维是切实必要的,只有在从音乐的分析中过渡到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将对艺术的理解与对历史时代的理解相结合,才能达到阐析音乐的新高度。
此外,这种社会学方法也许为我们理解一些当代作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29]。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优秀文艺作品都与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紧密相连。以董立强的作品《挽歌》为例,该作品便将“7.28”“5.12”“3.11”数组重大灾难时间点化作音级、音程等音高组织遍布于全曲之中。作曲家将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凝练至作品之中,便与阿多诺所描述的能够表现重大社会灾难的音乐功能相似。那么,针对诸如这类作品,我们不妨站在社会视野加以解读,思考音乐作品与时代人文的紧密联系,或许能产生“1+1gt;2”的效果。(本文系南京艺术学院首届“全国音乐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发言论文)
参考文献:
[1] 斯坦利·萨迪主编,约翰·泰瑞尔(JOHN TYRRELL)执行主编.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 第24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638.
[2] 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M].杨燕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1.
[3]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244.
[4]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7.
[5]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6.
[6]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44.
[7]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M].庞学铨总主编.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43.
[8]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45.
[9]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45-46.
[10]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59.
[11]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60.
[12] 西奥多·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谢钟浩,洛秦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79.
[13]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55.
[14]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71.
[15]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76.
[16]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79.
[17]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96.
[18] 勒内·莱博维茨.勋伯格画传[M].叶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9-141.
[19]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46.
[20]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49.
[21]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55.
[22]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56.
[23] 泰奥多尔·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M].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63.
[24] 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 文明批判[M].曹卫东编选.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13-214.
[25]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4.
[26]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42.
[27] 阿多诺.美学理论 修订译本[M].王柯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60-61.
[28] 姚亚平.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04):8.
[29]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8.
(责任编辑:庄" 唯)
猜你喜欢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