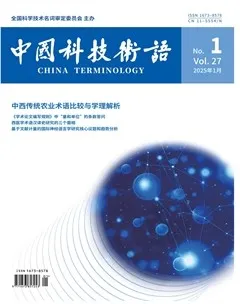中西传统农业术语比较与学理解析
2025-01-10张瑞娥陈德用
摘 要:文章旨在对中西传统农业术语进行比较和相关学理分析。采用描述和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术语观对中西传统农业术语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中西传统农业在农事活动和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客观共性,同时由于中西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中西传统农业术语之间有一定相似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文章从术语本体、概念释解、质性表征等维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原历史语境,对相关差异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性探讨,并总结其对当下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传统农业;中西农业;术语比较
中图分类号:H083;F313" DOI:10.12339/j.issn.1673-8578.2025.01.001
Contrastive and Interpretive Study on Terminologie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ZHANG Rui’e, CHEN Deyong
Abstract: Adopting descriptive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and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the paper aims to have a contrastive study and also a relevant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agricultural terminologies. Due to the objectiv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agriculture in term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as well as the exchange of agricultural cultur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re 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agricultural terminologies, but the differences are more significant. Based on comparing the two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erminological ontology,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qualitative representation, we resto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onduct an explanatory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relevant differences, and summarize their revelation for the present.
Keyword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agriculture; terminology contrast
收稿日期:2024-05-18" "修回日期:2024-07-0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近代中外农学术语互译与当下农业语言服务启示研究”(2022AH040229)
作者简介:张瑞娥(1972—),女,博士,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术语与语言服务、跨文化对比、翻译理论与实践。通信方式:ruiezhang@163.com。陈德用(1971—),男,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翻译理论与实践。通信方式:ahfycdy@163.com。
0 引言
传统农业前承原始农业、后启现代农业,其开始的标志是铁器农具的使用。在中国,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前221)开始,铁器农具就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民国(1912—1949)结束,2400多年的时间,都属于传统农业时期。在欧洲,铁制农具的使用更早。自公元前6—前5世纪,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欧就进入了传统农业阶段,一直到1900年,西方一直处在传统农业阶段。可见中西方传统农业无论是在时长还是时段上几乎都是重合的。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阶段,中西农业都产生了大量的农业术语。目前,学界对中西传统农业术语的研究主要涉及语言、文化和翻译交流等层面。首先是语言层面,这类研究关注传统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语言形式和语义等,较典型的有游修龄指出《说文解字》对“禾、黍、来、麦”等术语在语言形式和语义解释上的欠妥或失误之处[1]。李军论述了中国传统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语言形式和语义演变等[2]。在对传统农业术语承载的文化内涵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毕旭玲和汤猛认为二十四节气术语承载的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太阳历,将其与古埃及科普特历相比较[3];阎莉和戚晓明以二十四节气术语为例,探析农耕文化的特征[4]。此外,张竹云以生产组织形式、地租形态和所有制等方面的术语为例,比较了西欧庄园和汉代田庄之间的异同[5]。在对传统农业术语与翻译之间的关联研究方面,游修龄的成果较为典型,其认为“甘薯、玉米、花生、烟草”等外来术语不能按汉字的字面去理解,而应追溯其来源,否则会导致误解[6]。游修龄还从翻译的角度对引进外来作物产生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现象进行了探讨和分析[7]。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截至目前,对中西传统农业术语进行直接对比的研究较少。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对中西传统农业术语进行比较,挖掘两者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反观当下,总结相关启示具有积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引用的部分术语虽然来自于日本人译写的农书,但由于他们译写时参照的是西方农书,因此相关术语也视为西方农业术语。
1 中西传统农业术语本体比较
1.1 范围比较
由于农业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中西传统农业术语有不少共性,虽然产生的具体术语不同,但在类别和范畴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19世纪中期,中西农业都致力于土壤改良、农产品品种改良和引进等,因此,这一时期双方都产生了不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和畜产品品种等术语,这些品种有本土改良的,也有从别的地区和国家引进的,既有脱胎于原有术语的,也有通过翻译产生的全新术语。不仅是范畴和类别相似,有些术语甚至在内涵方面的相似度也非常大,例如1837—1873年间流行于英国的“高级农业”(high farming)这一术语与1866年开始在中国珠三角兴起的“桑基鱼塘”第二次高潮,所体现的都是有机整体农业观[8],都是将水陆动植物资源有机联合、综合利用从而获得高经济回报,类似于现在的“生态农业”。再比如19世纪的英国,将工厂榨油剩下的渣滓用作肥料,称作油饼(oil cake)[9],同时期的中国也有相似的“油饼”或“麻饼”。另外,在制度性术语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在耕作传统上,英国的轮作制(plot system)有“二圃制”和“三圃制”等术语,中国则有“间作”“轮作”“套作”等术语,虽然具体的做法有差异,但这些术语承载的都是充分利用耕地达到产出最大化的理念。
除了农业活动和发展阶段这类客观共性,中西传统农业术语相似性的发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交流。19世纪以前,英国使用的是被称作“阿得犁”的木犁,由于材质和结构的原因,这种木犁的使用范围有限,而且耕作质量较差。到17世纪,中国铁犁传到了荷兰,被称作“罗瑟兰犁”,这种铁犁由犁烨、犁壁、犁架组成,结构非常完备,以人力或畜力作为动力,可以用来碎土、翻土、开垄。由荷兰传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后,“罗瑟兰犁”几经改造,越来越适合西方的耕作条件。到了19世纪,经过J.艾伦·兰塞姆的改造,铁犁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被称作“兰塞姆金铁犁”,1830年之后,美国又有了“迪尔铜犁”[10]26。这些术语听起来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在设计理念和功能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如都是使用金属材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产出等。当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中西农业术语交融使用的情况。例如出版于1897年的《农学丛书》第一集第十册收录了萨端翻译的《畜疫治法》,其中一个药方中就出现了“春燕麦”“杜松子”“黄连米”“硫酸铁”“炭酸曹达”这些中西混融的术语,另一个药方中则有“机挪布”“黄连”“乾草”“硫磺铢”“糖蜜”“白兰地火酒”等[11]。
19世纪以后,中西农业术语在范围上更多体现出的是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差异愈发凸显,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有两个,一是西方传统农业术语迅速突破原有范围和框架,各种类别和范畴的术语层出不穷,远远超过了农作物品种、动物种类、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的范围,在农业气象学、土壤学、植物学、动物学、农业化学、农业管理、农业教育等不同领域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术语体系,而同时期中国传统农业术语突破较小。二是西方出现了更多的理论术语,且这些术语分属不同的范畴和层次,愈发细微具体。而中国传统农业新产生的理论术语较少,为数不多的理论术语往往都以“阴”“阳”“五行”和“气”这些词为核心,例如“阳气”“阴气”“土气”“干阴”“补阴”“扶阳”“祖气”“谷气”“岁气”等。
1.2 命名方式比较
在命名方式上,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例如西方以人名命名的农业术语明显多于中国。中国以人名作为农业术语多出现在北魏之前,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录了三种命名作物品种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以人姓字为名目”,也就是以品种选育者的姓名命名作物品种,例如《种谷第三》中所记录的诸如“李浴黄”“孙延黄”“阿居黄”“刘沙白”“刘猪赤”等都是粟品种术语。这种以人名作为术语的做法在北魏之后就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名命名的术语在增加,例如水稻中的“江西早”“抚州早”“苏州早”等[12]。
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西方农业术语中,以人名命名作物、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做法数量较多,持续时间较长,17世纪之后更有增加的趋势。上文提到的诸如“罗瑟兰犁”“兰塞姆金铁犁”“迪尔铜犁”就是以工具发明者或改良者的名字命名的。在生产方式上,杰斯罗·塔尔在总结自己耕作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马力中耕农法》(The Horsehoing Husbandry)一书,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作“塔尔农法”(Tull System Husbandry)[13]。随着农业发明的增多和科技的进步,以人名命名的术语数量迅速增加,例如在农业气象领域,“乔唐式日照计(Jordan Sunshine Recorder)”“康培司托克日照计(Campell Stokes Sunshine Recorder)”“福尔廷式晴雨表(Fortin Barometer)”就是以其发明者命名的。
在《齐民要术》中,记载有“观形立名”和“会义为称”两种中国传统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这两种方式依然还在发挥作用。前者是指按照农作物的形态特征例如作物的颜色、形状、茎秆的高矮、芒的有无、穗形大小等进行命名,例如按照水稻的颜色有“紫芒稻”“虎皮林”,按照黍的形状有“稻尾黍”,按照山芋的大小有“鸡子芋”等。“会义为称”是指根据农作物的成熟时间或者生长特性进行命名,例如对于水稻,将在蝉鸣时间成熟的叫作“蝉鸣稻”,将耐水耐涝的品种称作“水黑谷”;对于粟,将生长时间短、成熟早的叫作“百日粮”,将抗鸟雀的称作“雀懊黄”,将质量堪比稻米的称作“辱稻粮”[14]。这种术语的优势是较为直观而且通俗易懂,即便从来没有听说过诸如“六旬黄”“望暑归”“黄瓜釉”“鼠牙稻”这些术语的人,也可判断出它们的成熟时间、颜色和形状等。
1.3 范畴化程度比较
范畴化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范畴化的完备程度也反映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程度。18世纪之后,中西传统农业术语在范畴化程度方面的差异愈发显著。以肥料术语为例,1897年6月,由罗振玉主编的《农学报》刊发了王丰镐译写的《论粪田》一文,此文既写到了当时中国使用肥料的情况,又译介了同时期西方应用肥料的做法。从下面的这段话就能看出同时期的中西传统农业在肥料术语范畴化程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抵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15]
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中国人认识到许多废弃之物都可以用来作为肥料达到肥田的效果,按照经验,他们将这些废弃之物进行范畴化得到了关于肥料的术语,例如“人畜之矢”“草木之质”和“物之毛骨”等,这些术语较为概括笼统,纯粹凭借农业实践经验总结而得,从认识论角度看,这种直观的经验总结未深入到物质的构成与作用机理,看不到其中的化学元素构成,也就认识不到这些肥料产生效果的具体原理。
与同时期的中国肥料术语不同,19世纪末的西方农业在肥料方面已经上升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他们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进行农业试验(……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肥料进行了成分分析和原理总结,不仅明晰了不同肥料的成分(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还明确其发挥作用的过程,掌握了相关原理(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这种截然不同于单靠经验的路径,生成的是另一套肥料术语体系,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诸如“植物性肥料”“动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间接肥料”和“杂肥”等不同基本范畴层次的肥料类别术语,也可以看到诸如“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揩尼脱”“二磷养四”“硫氧三”和“钙轻四”等处于下位范畴的具体肥料术语,以及处于次下位范畴层次的诸如“氮”“磷”“钾”等肥料元素。在范畴层次上,19世纪末期的中国农业肥料术语只有三个层次,而西方则有四个层次,层次数量的差别反映出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别,以分析科学为基础的肥料认识必然比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认识更为深入。认识论是构建一门学科的根本,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有农无学”、农学学科难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在基础理论层面形成的肥料术语,西方在制肥、施肥等应用技术层面,也形成了诸如“酸化”“化合”“结晶”等技术术语。可以看出,同时期的西方农业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层面,基本形成了农业肥料学的框架和雏形。
18世纪以来,西方农业术语在范畴结构上更加具有层次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体现出西方农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分析性特点。在作物品种、种植和管理技术等方面,这些特征都非常显著。当然,此时期的中西方农业术语在范畴上也有相通的地方,例如在基本范畴层次,“人畜之矢”“草木之质”“物之毛骨”这些中国农业肥料术语分别对应或者部分对应西方的“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实际上,18世纪之后,中西方农业术语在范畴化方面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等层面,不仅生产资料类术语如此,涉及作物品种和农业技术类的术语也往往如此。
以蔷薇术语为例能够说明中西方作物品种术语范畴化程度的差异。在清代陈淏子的《花镜》中,蔷薇只有上位范畴和基本范畴两个层次,基本范畴类只有“家蔷薇”“野蔷薇”两个术语,在此之下就没有下位范畴层次的术语了。这种对蔷薇的范畴化到了19世纪末还在沿用。
野蔷薇,一名“雪客”。叶细而花小,其本多刺,蔓生篱落间。花有纯白、粉红二色,皆单掰,不甚可观,但最香甜,似玫瑰,多取蒸作露,采含蕊拌茶,亦佳。患疟者烹饮即愈。若花谢时,摘去其蒂,犹如凤仙花,开之无已。此种甚贱,编篱最宜[16]172。
然而,在19世纪末《农学丛书》第二集刊发的由林壬翻译的《蔷薇栽培法二卷·上》中,我们能够看到同时期西方农业术语的范畴化程度。此书中处于上位范畴的“蔷薇”在基本范畴层面包括“一季蔷薇”“二季蔷薇”和“四季蔷薇”等术语,其中“一季蔷薇”的下位范畴术语包括“园蔷薇”“苔蔷薇”“刺蔷薇”“斯咳矶蔷薇”和“蔓蔷薇”等,这五个术语之下还有次下位范畴,分别包括不同种类,例如蔓蔷薇的次下位范畴包括6类,每一类又分为具体的不同品种,包括“哑鲁洗蔷薇”“柏鲁绍鲁脱蔷薇”“常盘蔷薇”“杂性蔓蔷薇”“玛鲁几讣弱拉蔷薇”和“普锐累蔷薇”等26个不同蔷薇品种术语,“二季蔷薇”和“四季蔷薇”也是如此[17]。可见西方的蔷薇术语至少分布于四个范畴层次,甚至具备五个层次,体现出科学分析的特征。
涉及农业技术类的术语也是如此。例如在《知本提纲》中,杨屾对于树木裁剪之法的论述极为简单,其中能够算得上术语的只有“上忌树梢”和“下贯横木”[18],至于其他的具体方法则一概全无,与其说这两个是技术术语,不如说是裁剪原则。而在傅兰雅和徐华封合作翻译的《种植学二卷·上》中,西方的嫁接方法从基本范畴来讲,包括“靠接法”“枝接法”“株接法”和“芽接法”,其中“靠接法”的下位范畴术语包括“平常过接法”“弓形过贴法”,前者的次下位范畴术语又包括“平面过接法”“尖槽过接法”“英国过接法”,这就形成了四层范畴化结构,“枝接法”“株接法”和“芽接法”也是如此[19]。
2 中西传统农业术语的概念释解比较
在术语体系中,术语与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语境中术语和概念可以相互替代。概念解释术语,术语是概念的浓缩。因此,在语言形式上,术语简洁凝练,概念围绕术语进行阐释,而且会尽量使用术语中的语言成分。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农业术语的概念较为简单、模糊,西方概念则相对精确、详细。
诸般花木,若听其发干抽条,未免有碍生趣。宜修之修之,宜去之去之。庶得条达畅茂有致。凡树有沥水条,是枝向下垂者,当剪去之。有刺身条,是枝向里生者,当断去之。有骈枝条,两相交互者,当留一去一。有枯朽条,最能引蛀,当速去之。有冗杂条,最能碍花,当择细弱者去之。但不可用手折,手折恐一时不断,伤皮损干。粗则用锯,细则用剪;裁痕须向下,则雨水不能沁其心,木本无枯烂之病矣。至伐木之期,必须四月、七月,则无虫蠹之患,而木更坚韧耐用。若非时斫伐者,必须水沤一月,或火炽极乾,亦不生蠹。[16]66
以上是《花镜》中对花木修剪技术术语“整顿删科法”的概念解释,是针对所有花木的,“宜修之修之,宜去之去之”是对事物性质的模糊描述。这种凭借经验的做法只能是靠人的主观领悟,相关方法的操作说明也较为笼统、概括。从文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宜修”“宜去”枝条只包括“沥水条”“枯朽条”这样的残枝坏枝和“冗杂条”“骈枝条”这样的多余枝条,对于其他枝条的整删则没有提及,对于如何整删以及整删程度,也只能靠自己把握。无论是概念内涵还是外延,都是不确定的,其阐释空间很大,不具备确定性和精确性。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民国时期,《花镜》都是修剪花木的范本。
同样是针对修剪整枝,1899年刊发于《农学丛书》第三集由沈纮翻译的《果树栽培全书》体现出很大差异。该书在《第一编 总论》中专辟了第五章讲述果树的“剪定及整枝”,在此基础上展开下面四编,其中第二编是“仁果类”(包括梨、苹果、柑橘、枇杷、石榴、柿和榅桲七种果树),第三编是“核果类”(包括桃、樱桃、杏、李、巴旦杏、枣和梅七种),第四编是“浆果类”(包括葡萄、悬钩子和无花果三种),第五编是“壳果类”(包括栗、胡桃和榛三种),每种果树专辟一章论述,其体例基本相同,每一章都包括“剪定”一节,也就是针对20种具体果树分别给出了不同的修剪方法,每种果树包括数种修剪法。单是树型,梨和苹果就各有七种修剪方法,其中梨有“哥尔登佛的加尔生蒲尔整枝法”“披拉米特整枝法”“加尼特拉蒲尔整枝法”“爱文他依由整枝法”“夫由苏整枝法”“伯而美脱整枝法”和“架上整枝法”,苹果有“哥尔登佛的加尔生蒲尔整枝法”“披拉米特整枝法”“加尼特拉蒲尔整枝法”“爱文他依由整枝法”“法司整枝法”“伯而美脱哇利松他尔整枝法”和“哥尔登哇利松他尔整枝法”。不同的方法对应不同的术语,而且辅助图片,这些术语的概念解释非常详细,属于定量的精确分析,例如对于苹果的“披拉米特整枝法”,相关概念如下:
此法最为壮观,结果多,栽植距离先方六尺至九尺,经四年,树姿如七十图。此法在沃地当用接喳嗓砧之栽子,否则形不整。第一年如七十图,甲令生枝六本至八本。下枝距地一尺至一尺五寸,四方排枝,平线伸枝。第二年生乙枝,第三年生丙枝,第四年生丁枝。每年令顶端之一枝伸长。如此逐年按序整枝,至所需之高度而止。其旁枝则据剪定法剪定之。[20]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苹果树和梨树,前四种修剪术语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这四个术语的概念解释却因苹果树和梨树两种树种的不同而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爱文他依由整枝法,用于梨树修剪的概念是:
此法整枝梢如第四十九图,状若羽扇,故名鹅附状,又名孔雀尾状。先截干身令长一尺一二寸,从是生三主枝,下部二枝相近接,截短中心主枝,令生二枝,故有八主枝。一主枝又分二枝,故为十六枝,株间一丈二尺。[20]
而此法针对苹果修剪的概念则是:
干身高三寸至一尺,从是生三枝,行短剪定,整枝梢排列之位置为扇形,栽植距离一丈至有丈二尺。[20]
不仅修剪如此,由于采用了相同的体例,针对20种果树的每一章都囊括了相同的主题,例如风土、种类、繁殖、栽植、剪定、诱引、耕业、肥料、器械、除害和收实,这些相同的主题涵盖了相应术语,每个术语都有确定、翔实的概念,即使在同一主题之下的不同果树有相同的术语,其概念也是不同的。
可见,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术语的概念人文性较强,模糊语言使用较多,概念解释界限不明确,表现出万能的倾向,在语气和情态上较为主观,相关概念传达的多是笼统的具有经验性、整体性、意会性或模糊性的知识,需要凭借农业生产中的观察和体认才能达到对术语概念的认知。而西方的农业概念多为量化描述,使用科学概念和数学语言进行表述,在语气和情态上倾向于客观中立,其表达更具逻辑性和精确性,具有显著的数学化和实证化倾向。“概念的一般化,和社会的发展有关。”[21]“一般来说,生活中重要的东西,语言表达就缜密,概念的细致化也极为突出。‘语言分割’的详略与人们关注的程度紧密相连。”[22]随着时间的推进,西方农业愈发重视术语概念的缜密,体现出显著的科学化走向,反映出人们对于科学认知的重视。
3 中西传统农业术语的质性表征比较
3.1 经验与实验
中国传统农业术语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紧密关联的,传统农学以经验为基础,人们顺应有限的自然条件,以耕种为主,凭借经验,讲究精耕细作,在耕种的过程中以传统的阴阳五行、物候天象知识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和感悟,因此形成的农业术语具有浓厚的经验式和感悟式特征。例如评花馆主(本名“陈葆善”,1861—1916)在《月季花谱》中列出九个栽种术语:
月季花先止数种,未为世贵。考之花谱,种法未明,……余有月季之癖,栽种之法颇得其精用。将生平历试之法著之以供同好,列目为九,一曰浇灌,二曰培壅,三曰养胎,四曰修剪,五曰避寒,六曰扦插,七曰下子,八曰去虫,九曰品类。[23]
以上引文中,作者鉴于月季花“种法未名”,而自己又“有月季之癖,栽种之法颇得其精用”,因此列出了栽种月季的“九目”,作者将这九个术语称作是“生平历试之法”,很显然,这是作者栽种月季花的经验之识,对其进行总结的目的并非有园艺学的追求,只是将其“以供同好”而已[24]64。
17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18世纪,西方农业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重视个体分析和实验,在农事行为中,他们“讲学问历练等事,凡气是何物,水是何质,光有几色,土有几等,植物有几种,培植有几法,均须切实精究。故今日欧美诸国出产,比之前数十年收成加至若干倍。”[25]因此西方的农业术语体现出较强科学性,如出版于1897年的由山本正义翻译的《农学入门·卷三》第三章的主题为“论果树蕃殖”:
作物概据种子蕃殖,虽为通法,自种所生之果甚多,性质有异于母树者,或有生不良之果实。故欲蕃殖,多用接木法,又或用插木、压条、分根等法。……接木之法,接果树之梢或萌芽而接合于砧木。其法有居接掘接之别。居接者,于适宜之所植砧木及成长……掘接者,……。插木者,截树枝插之土中令生根,压条者,挠树枝压之土中……截根移植,以为苗木,其法曰根分法。[26]
上文先是将果树的繁殖方法分为“接木法”“插木法”“压条法”和“分根法”,在将这四种方法进行概念解释的基础上,又将其按照不同维度进行更为具体的分类并逐一解释,例如按照方式,将接木法分为“居接”和“掘接”,按照部位,分为“芽接”和“枝接”,其中“枝接”按照方式又分为“割接”“合接”“剥皮接”“唤接”。这些术语不仅分类细致深入,其概念解释也非常科学严谨,甚至对于每种方法的操作尺寸、位置都有非常具体的数字明示。例如“割接者,取砧木之大者或表皮厚者,于接穗之下部凡一寸五六分削之……”
3.2 静态与动态
在中国传统农业术语体系中,农作物、耕作和农具三类术语占有很大比例,整体表现为缺乏理论术语,而已有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呈现静态,演进更新较慢。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耕织结合”自然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是封闭的,涉及的生产因素较为稳定,传统农家往往“世代使用同一生产要素”,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农事方式和农事行为缺少变化,因此这些农业术语的数量和种类也较为稳定,整个术语系统较为封闭,缺少更新。早在秦汉至魏晋时期,在旱地耕作方面,中国就形成了以“耕-耙-耱-压-锄”为主要特征的技术体系,在水田耕作方面,则在唐宋时期就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技术体系,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旱地和水田耕作术语;到了明清,虽然耕作有了进一步的精细化,但是由于耕作体系几乎没有创新,因此也没有相应术语的更新。在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方面,明清时期几乎没有产生真正的新术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遇到了瓶颈[27]。唐宋时期,冶铁技术、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方面的重大发展为中国农业带来了全新术语。此后,中国一直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有的农具能够满足这样的经济模式,客观上没有产生改进和发明新式农具的需求,而这样的工具也只能支持此类经济模式的存在和运营,同时,这种经济模式只能容纳这样的农业工具,未形成发明动力,因此二者互为因果。另外,由于农民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经济上的贫困,使他们缺乏发明创造的动力,即便是有发明新式农具的意愿,也没有技术和经济支持——当时的农具大多是以畜力、人力、水力或风力为动力的铁木工具,要想发明新式农具,必须要以新的动力资源和材料为前提,而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并不能提供其他动力和材料,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而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农具是基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蒸汽和电力为动力、以合金钢为材料而更新发展起来的。如此导致中国的农业技术难有新的突破,农业工具也没有质的改进。例如清代的《授时通考》和《农具记》分别收录了192种和65种农具术语,其实这些术语全部来自元代的《王祯农书》(共收录了235种农具术语)[28],可见清代的农具术语几乎都是前代的重复。
与此相反,18世纪以来的西方农业术语则更新变化较快,单是19世纪50年代,通过改良或发明,英国就有一大批生产工具术语得到普及,如“除草机”“排水泵”“松土机”“播种机”“割捆机”“蒸汽拖拉机”“蒸气犁”“收割机”“扎束机”“便携式脱粒机”等。这一时期的农具制造和销售最能直观反映农业术语的多样性。据统计,1840年瑞胜农业工程公司(Ransomes)就制造出86种冠以不同术语的犁,甚至在伊普斯威奇地区有上百种。1853年,英国皇家农业协会展出了2000种冠以不同名称的农业生产工具[29]。在农业动力工具方面,除了18世纪发明并得到进一步改进的蒸汽机之外,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1876年)、“煤气内燃机”(1876年)、“交流发电机”(1878年)、“农用内燃发动机”(1892年)、“柴油机”(1897年)。有了这些动力工具,大量的先进农具就出现了,随之而来伴随大量的新式农具术语,如耕耘机类有“绳索牵引耕作机”(1832年)、“蒸汽钢缆牵引犁”(1854年)、“蒸汽轻型拖拉机”(1856年)、“跨行中耕机”(1856年)、“蒸汽拖拉机”(1858年)、“履带式拖拉机”(1859年);收割机和脱粒机类有“水车动力脱粒机”(1723年)、“圆盘式收割机”(1811年)、“牵引式收割机”(1820年)、“马拉收割机”(1831年)、“联合收割机”(1841年)、“玉米果穗收摘机”(1850年)和“轻便型脱粒机”(1850年)等,不一而足[28]。
不仅是生产工具术语,其他方面的术语也是如此,例如在牲畜品种方面,通过杂交改良,产生了一系列表示新品种牛、羊和马的术语,如“迪什利牛”“达拉姆牛”“纽莱斯特绵羊”“萨福克羊”和“夏尔马”等[10]27-28;在农药方面,有“波尔多液”(1882年)和“砷酸铅”(1892年);在肥料方面,则有“磷酸钾”(1842年)、“硫酸氨”(1842年)和“磷肥”(1878年)等[28]。
3.3 主观与客观
相较于西方农业术语,中国传统农业术语表现出主观感性,有些甚至具有显著的文学性特征。以清朝的月季术语和同时期的西方蔷薇术语进行对比:上文中提到的《月季花谱》是典型的月季专著,其最后一部分专门介绍月季品种,其中“上品”列了45种,包括“水月妆”“汉宫春晓”“汉口黄”“猩红海棠”“通草宝相”“南海天竹”“姣容三变”“雨过天青”“岳阳三醉”“珠盘诧彩”“飞燕新妆”“国色天香”“银红牡丹”“桃湖春晓”“西施醉舞”“朱衣一品”“小玉楼”“大富贵”“黑葵”“一捻红”“洞庭秋月”“杏花天”“紫骊珠”“映日荷”“宿雨含红”“丹桂飘香”“枫叶芦花”“欢合巫山”“绿珠春醉”“血芽黄”“金砂宝相”“醉青莲”“醉杨妃”“粉妆波斯”“银红卍字”“七宝冠”“佛骨回光”“冰轮”“秋水芙蓉”“豆绿芙蓉”“琪绿”“绿葵”“耧春”“朱衣象笏”“玉颜红汗”;“上品之尤贵者”10种,包括“蓝田碧玉”“金瓯泛绿”“朝霞散绮”“虢国淡妆”“赤龙含珠”“晓风残月”“淡抹鹅黄”“春水绿波”“六朝金粉”“玉液芙蓉”[16]。可以看出,从基本范畴开始,这些术语名称具有显著的主观色彩,下位范畴术语更是充满了文学想象和感性特征。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西方农业术语总体上较为客观,没有这么显著的文学性。例如上文中提到的《蔷薇栽培法二卷》,基本范畴层面的“一季蔷薇”“二季蔷薇”和“四季蔷薇”等术语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下位范畴术语也仅以其客观外形为依据进行命名,例如“园蔷薇”“苔蔷薇”“刺蔷薇”“斯咳矶蔷薇”和“蔓蔷薇”等。
4 原因解析
总结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以来西方农业术语较为完备、发达,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传统农业术语生成发展的滞后性愈发显著,其中的原因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点。
4.1 近现代科技知识发生路径
长期以来,中国重人文、轻科技,重体悟体认,生产技术多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产生的理论术语较少。而长时期内中国的农业是封闭的自给自足模式,由于缺乏外来知识的支撑和动力的推动,这种模式发展到高峰,反而形成了瓶颈停滞不前,在语言载体上就表现为农业术语更新迭代的乏力与停滞。
17世纪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与运用加快了西方农业的发展进程。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知识,其源头是西方产业革命的发展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创立,伴随这两大重要事件,产生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的理论学说和应用技术,其中最根本的理论学说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和李比希农的化学学说,这些学说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为西方传统农业的改进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农作物和畜牧品种选育提供了理论支撑,产业革命和实验科学的结合也改进了一系列的农业技术,为西方农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术语,反之,这些术语又体现出科技知识的发展走向[30]。
4.2 学科地位
在中国传统农业阶段,大多数从事农业的人不识字,而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层导致多数文人重文轻农,“以农为贱业”,他们不从事农业也不研究农业,亦即罗振玉所说的“农不通学,士不习农”,“明清两代农学家的人数(被认定为农学家的标准不是很严)共得72人,其中进士出身的仅14人,而明清进士总数高达51090人” [14]。如此悬殊的比例体现了梁启超所言的“学者不农”这一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农业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理论升华乏力,从而农学的发展层次难以提升,导致中国传统农业“有农无学”,即有农事无农学,而这种局面又反过来影响了农业发展,使中国长期以来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农业术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经验性和感悟性,没有基础理论支撑,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在术语种类上,以反映传统技术经验的术语居多,体现出浓厚的重实用、轻理论的特点。
与此相反,17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有农有学”,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终生从事农业劳动或推动农业改进,如英国的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 1674—1740),他受过法学高等教育,曾出任过律师,担任过国家公职,但他终生务农,致力于农耕方法的改进并加以推广,同时期的阿瑟·杨(Arthur Young, 1741—1820)博学多才,一生也以推动农业改革为志向,这在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法国,魁奈的重农主义甚至发展演变为重农学派,由于知识结构和传统性情的差异,西方农业在处理与自然条件的关系上体现出更多的能动性和征服性行为,不仅在国家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研究农业,重视农业理论,因此,他们的农业术语不仅是技术性和理论性术语并重,且其技术性术语背后也往往有理论支撑,这就使西方农业在理论方面发展较快,农业的地位也得到提升。17世纪之后,西方科学理论和技术一直处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他们的农业术语体系也呈现出很强的开放性特征,术语的变化较快。
4.3 主体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绝大多数不识字,亦即所谓的“农者不学”,农民依靠世代相传的经验从事农业活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民国。而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农民的文盲率逐渐下降,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农民的文盲率下降到了2/3,18世纪中叶降到1/3;1880年,法国农民的文盲率是1/3;到1900年,英、法两国总人口的文盲率还不到5%,而此时期中国农民大部分仍是文盲[30]。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在农业术语生成与传播结果方面的巨大差异。
18世纪以来,西欧出现了各种农民社团,这些社团给农民提供了交流生产技术的机会。社团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向农民传播新的农业科技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这些社团,在官方的组织下,西欧出现的专门农业推广组织与机构在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推动农业改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定时期内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形成了农业推广的良好传统。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传统愈发完善,在不少国家,农业推广人员和机构都按照农场规模进行配备,形成了农业术语生成与传播的良好循环,而同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这种社团和机构[30]。
在主体层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进行农业研究的机构较多。这些机构采用试验的方式研究农业原理和技术。自其19世纪中叶出现到1900年半个世纪的时间,这类专门研究机构达到500多个,其中最有名的是成立于1843年的英国洛桑试验站。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农业的发展,也为西方农业体系贡献了大量专业、系统的术语。
4.4 传播媒介
西方农业术语较为完备和发达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17世纪以来发达的传播媒介。印刷术传到西欧后,印刷本逐渐淘汰刻本。多数西欧国家都有本民族的农业书籍,伴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和印刷成本的降低,17、18世纪农业出版物数量持续增加,尤其是农业期刊增加迅速。这些期刊主题多样,篇幅短小,发行灵活,传播速度快,与农业书籍形成互补。农业期刊的出版与发行在19世纪已相当成熟,到19世纪末已有相当数量的西欧农民定期阅读不同期刊中的涉农文章,可以说,西欧农民已经形成了一种边学习农业知识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传统[30]。这对于农业术语的产生、传播和演进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5 结语
17世纪之前,中国传统农业术语与同期的西方农业术语相比,更为精细、系统,不仅种类多、数量大,且许多术语承载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但是17世纪之后,西方农业术语逐渐凸显出优势。对这两种术语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挖掘背后的原因,对于新时代新背景下的农业语言服务、农业生产以及农学学科发展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当下,宏观层面我们需构建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生发与演进路径,为农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保证,中观层面需要强化农学的学科地位,而在微观层面,我们必须提高和保证从业者、研究者的素养。而在外围,则需要传播媒介等方面的保障,从而为农业术语的产生和演进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游修龄.《说文解字》“禾、黍、来、麦”部的农业剖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57-63.
[2] 李军. 试述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特点[J]. 中国科技术语, 2012,14(4): 44-48.
[3] 毕旭玲,汤猛. 重估中国二十四节气在人类历法体系中的地位[J]. 中原文化研究,2023(1):96-103.
[4] 阎莉, 戚晓明. 农耕习俗的时令性探析[J]. 农业考古,2024(1):190-196.
[5] 张竹云. 汉代田庄与西欧庄园比较研究[J]. 史学集刊,2002(2):29-34.
[6] 游修龄. 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及外来词[J]. 中国农史,1992(4):11-14.
[7] 游修龄. 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J]. 古今农业,2011(3):46-50.
[8] MINGAY G E, Holderness B A, Turner M.Land, Labour and Agriculture: 1700—1920 [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1991:149.
[9] OVERTAN M.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3.
[10] 张梦醒. 论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的繁荣[D]. 南京:南京大学,2014.
[11] 夫敦. 畜疫治法[A]//罗振玉. 农学丛书(第一集第十四册). 萨端,译. 上海:江南总农会石印本,1897.
[12] 贾思勰.齐民要术今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 董恺忱. 论十八世纪中期中英农法演化成就与变革趋势[J]. 古今农业,2007(3):1-21.
[14] 游修龄. 我国农作物品种命名的历史发展[J]. 中国农业科学,1983(3):32-36.
[15] 王丰镐,译写. 论粪田[J]. 农学报,1897(4): 4-5.
[16] 陈淏子. 花镜[M]. 伊钦恒,校注. 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17] 安井真八郎. 蔷薇栽培法(二卷)[A]//罗振玉. 农学丛书(第二集第二十四册).林壬, 译. 上海:江南总农会石印本,1898.
[18] 杨屾. 知本提纲[A]//王毓瑚. 秦晋农言. 北京:中华书局,1957:71.
[19] 傅兰雅,徐华封,译写. 种植学(二卷):上[A]//罗振玉. 农学丛书(第一集第九四册). 上海:江南总农会石印本,1897.
[20] 福羽逸人. 果树栽培全书(三卷)[A]//罗振玉. 农学丛书(第三集第三十五册). 沈纮,译. 上海:江南总农会石印本,1899.
[21] 王力. 汉语词汇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13.
[22] 李军.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12:18.
[23] 评花馆主. 月季花谱[J]. 农学报,1899(78):1.
[24] 刘小燕.《农学报》与其西方农学传播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1.
[25] 李尹蒂.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农学的兴起[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4-140.
[26] 稻垣乙丙. 农学入门(三卷):卷三[A]//罗振玉. 农学丛书(第一集第二册). 山本正义,译. 上海:江南总农会石印本,1897.
[27] 李根蟠. 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比较[J]. 河北学刊,2003(2):155-162.
[28] 闵宗殿. 试论清代的农业成就[J]. 古今农业,2002(1):17-24.
[29] MINGAY G E. Land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50—1980[M]. London: Longman, 1994: 195.
[30] 张家炎. 传统农业的转化西欧经历与中国发展[J]. 农业考古,1998(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