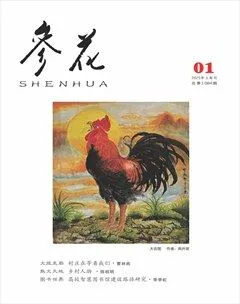川味相投
2025-01-01杨盛龙
与人交谈时,我的蹩脚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别人问:你是四川人吧?我说:我是湘西人,老家与老四川交界,湖南有四分之三的人说四川话。
又遇到类似提问,我再解释:我们县说四川话,惯用西南巴蜀思维,爱吃川菜。
当年首次离开湘西上北京,在火车上,我以一句四川话体系的湘西话说了什么,别人没听懂。从此以后,我将乡音埋在心底,用带着浓重家乡味的普通话交流。
初到北方,举目无亲,除夕夜我孤独地听了一晚上密集的爆竹声。几天后到首都体育馆看演出,中场休息时听到近旁有人说四川话,我感到好亲切。
到二龙路蔬菜商店买菜,我对营业员说:“买一蔸白菜。”一位中年顾客听出我的口音,说:“呵呵,一蔸,你是四川人吧?”我说,我是湘西人,湘西、湘北、湘南等地区的人都说四川话,只有湘中一小块地方的人说湘方言。好不容易找到同道,我很激动地想同他说几句,他却离去了。
和朋友在一个景点拍照,有游客听出我们的口音,用家乡话说:给我也逮一张嘛。“逮”这词是我们家乡几个县的人爱用的,许多词语比如吃饭、砍柴、读书、做作业、打扑克等,其中的动词都说“逮”。遇到真正的乡亲啦,我一阵感动。
听到一折四川话讲天气预报的段子,时不时模拟播出:下面播送天气预报,今儿夜嘎到明儿早上都是黑夜,明儿早上到明儿夜嘎都是白天,晴间多云,大部分地方阴天,有时可能有雨,小雨转中雨或者大雨,下好大算好大,下好久算好久,下得了就下,下不了算逑。
特别是最后一个字音,带波浪音,上扬,拐几道弯,很生动。
四川话属汉语西南官话,广泛使用于西南、中南地区,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之一,语言体系比较完整。当年在师范性质的大学读中文系,我因为在商店里将鞋子说成“xiezi”而受到了说“haizi”的同学的嘲笑。我的家乡直到近两年才在学校逐渐推广普通话,除了机关单位少部分人以外,我们的社交用语仍然是家乡话。
在我们家乡,以前出远门的人一般是为了打工。打工人来自四面八方,说普通话便于交流。家乡人讨厌那些本来方言说得溜,回到家乡却硬憋着说普通话的人。我们家这边有一个从外面回来的打工人,戴着一块跟老板借的手表。他操着普通话,似乎本来的家乡话也不会说了,还给我们正音:你们说“gaihuan”(解放),我们说“jiehuan”;你们说“gaicao”(改造),我们说“jiecao”。会普通话的人都晓得,他的普通话只是将家乡话变了音调,除了“解”其他的字音都不对。
北京是首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不能你说南腔我操北调,说普通话便于交流。例外的是,北京周边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人操家乡话与人交流,自认为他们那的方言跟普通话差不多,其实差得很远,不好懂。听不懂?你慢慢理解吧。操四川话的人到了北京,只能憋普通话。操四川话的人私下里说几句四川话,说“安逸”“巴适得很”,感到亲切。
在北京生活,我先后有过几个说四川话的朋友,平时说带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遇到说四川话的朋友,就说几句川味话语,开心得很。比如:麻起了(完成了),啷个搞的嘛(这是怎么回事),满咚咚的(很满),拦中半腰(中间,半路),等等。
我们经常互相说哪里人更爱吃辣椒。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重庆人往火锅里放佐料,如同铲煤烧锅炉般用铲子添加辣椒粉。贵州人坐席,面前的火锅里红油翻滚,每人面前还摆着一碗辣椒粉蘸水。讲四川话的朋友问:听说你们湖南以辣椒哄小孩?我说:我家小弟弟两岁时饭碗里米饭拌辣椒拌红了,担心他伤胃,限制他吃辣,将他碗里的辣椒拿走,他大哭;将拿走的辣椒归还给他,他破涕为笑。讲四川话的朋友还问:听说你们那里煎鸡蛋也放辣椒?我说:你放点辣椒吃试试。
我和在北京交的操四川话的朋友一起吃饭,互相都喜欢川渝口味,带麻辣味的,喜欢那几个老四川风味饭馆,炒菜麻辣,浓香四溢,不约而同地往饭馆那个方向走。那时候的物价啊,四角五分钱就点一个回锅肉,三角五分钱就买一份夫妻肺片。那川菜,放进花椒粒,浇上辣椒油,色泽美观,肉嫩味鲜,麻辣浓香,非常适口,想起就满口生津。重庆火锅热辣辣的,香喷喷的,大夏天摇着扇子吃,吃得满头大汗,通体清爽。
我同那位从小生活在长江边的四川朋友出行,总是走平路,走得远了,似觉得老走平路腿脚连同身子不爽,还是上上下下走舒坦。没想到的是,我说到南长河乘坐游船去吧,朋友说,那也叫河啊?那也叫游船?
北方的人工湖虽然不如长江的水势和气氛,野泳还是很有情趣的。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已经游了很久,太阳下山了,气温低了。我们中的一个征求意见似的说,上岸吧。另一个软绵绵地柔声说,不嘛,还要游……
一起逛公园,花前月下,林深不知所往,印证着相对论,忘路之远近,忘了公园关门时间,夜深了,只有翻越围墙出来,大度的男士先出来,女士从围墙上跳下,男士满怀接纳,乘势拥抱,放开还是不放开?
在西藏工作生活的四川人很多。西藏与四川相邻,四川话成了跨省(区)的“通用粮票”。西藏各大小城镇川味饭馆密集,四川人吃着川菜,说四川话,不用说普通话。其他省的人在西藏说普通话。我的家乡话说出来太土太重,又因为我是从北京到西藏的,只能说带土味的普通话。
在拉萨,由于海拔高、气压低、沸点低,只有鸡蛋能用一般的锅煮熟,煮米饭煮面条都得用高压锅。在机关大院吃了一小段日子中灶,做饭菜的师傅是四川人,炒菜都是川味的,多数人喜欢吃,其中一个来自江苏的干部怕麻辣,吃菜时说太麻太辣,说是舌头嘴唇都麻木了,从菜里挑出花椒粒放桌上,将“一个”说成“吖个”,他吃饭怕麻辣,见到带红色的菜比如西红柿、苋菜都不吃。
后来一段时间我在大灶食堂就餐,吃米饭吃馒头总觉得有点夹生,还是自己做饭菜合口味,便和一位操四川话的朋友合伙做饭菜。他曾在朋友开的川菜饭馆待过,当过见习厨师,厨艺颇高,瞧不起我的炒菜水平,我就只有打下手,择菜洗菜什么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拉萨,大家的工资都不高。机关大院各家都在房前盖一间小玻璃房用以种菜。号称“日光城”的拉萨阳光好,温室的蔬菜长得青葱可爱。有朋友不时送给我们一点自种的蔬菜。人们说,有钱人吃菜,缺钱人吃鱼。我们经常买鱼,还有就是每次出差必从成都带一些猪肉和蔬菜,自己炒菜,鱼香肉丝,豆瓣红烧鱼,吃得香。朋友炒菜放油多,总是爱用泡生姜、泡海椒、泡蒜头等佐料,味道好极了。
吃惯了朋友做的川菜,再吃其他风味的菜,似乎都不够味了。
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还是一口充满四川味的普通话,吃饭还是喜欢麻辣味川菜,每见到川菜馆眼睛就放光。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在一个二十多层楼的楼顶餐厅用餐,吃川菜,望满天星空,看京城夜景,叙友谊,谈旧情。那边,莫不是双肩岭,一削溜光,天堑秀景。远处,似杜峦坪,沃野一片,坦坦荡荡。左面的两座西式建筑圆顶高耸,相对而出,险峻无限。中间的长河湾,流水弯弯,波光闪闪,湿地公园水草丰茂,假山奇石,岸柳残月,曲径通幽,暗黑至极。边看景边享受舌尖上的佳肴美味,葡萄美酒轻轻碰杯,再碰杯,不觉夜已深,食客已经很稀少了。两人乘电梯下楼,到十九层,电梯停下,电梯门开,楼道忽明忽暗,那人站在电梯门外说:“满满的太挤了,再等下一趟吧。”只有我俩啊。电梯门关上,继续下行。耸了耸肩膀,缩了缩身子,好像真的很拥挤似的……
每在街上走,遇到人,人家听我口音,就说我是四川人。我向别人自我介绍说是湘西人,不会说湘方言,喜欢湘菜的程度远不如川菜。我这人从小过惯了苦日子,读到初二失学后过了几年“瓜菜代”岁月,我家经常挖蕨打葛,老是吃洋芋、红苕,时常将萝卜剁成颗粒和大米煮烂啪饭。吃遍南北方各种菜系,什么口味的菜都喜欢,什么东西都能吃,要是叫我从多种口味中选,还是喜欢吃川菜。交朋友喜欢交爱吃川菜的朋友,吃饭去川菜馆,喜欢麻辣,与川味相投。
(责任编辑" 肖亮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