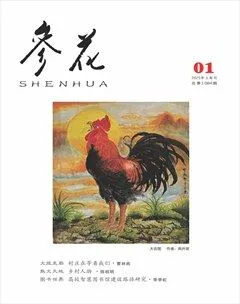《搜神记》中“预兆梦”的意蕴探究
2025-01-01王嘉宁刘利凤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孕育了志怪小说这一独特的小说体裁,玄释道之风盛行的社会状况促使志怪小说走向属于它的历史舞台,《搜神记》便是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文学明珠。《搜神记》系东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干宝所著,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为写作目的,是记载神怪志异之事的笔记体志怪小说,其内容可谓兼容并包。《搜神记》内容蕴含着浓厚的虚幻色彩,但因其记载之事多源于《左传》《史记》等正史,亦含有一定程度的史学色彩。这种既虚幻又真实的写作手法赋予《搜神记》独特的历史地位,甚至作为“搜神体”被后世研究。现今主要研究的《搜神记》是由明人胡应麟搜集整理而成,经过范宁、李建国等前辈学者的多方考证,汪绍楹加以校注的20卷本。本文将以此书为底本进行研究,通过对《搜神记》中“预兆梦”故事的分门别类,感受故事中的“真幻”“因果”“逍遥”之美及时人对人性美的追求,以干宝《搜神记》“预兆梦”故事为主线,探究“预兆梦”故事所含有的深刻意蕴。
二、《搜神记》中“预兆梦”的类型
《搜神记》中有关梦事的故事约为43个,其中与“预兆梦”相关的约为31个。按照类型进行分类,31个“预兆梦”故事可分为占梦、姻缘梦、因果梦三个类型。(1)占梦。《搜神记》中的占梦故事大致可分为某人梦见某具有特殊含义的事物,经过解读是预示着某种命运的故事,以及某人在特殊的时间做某梦是某种命运的预兆。前一类故事代表如《孙坚夫人》《禾三穗》等;后一类故事则以《新井》《孔子梦》等为主。(2)姻缘梦。《搜神记》中有关姻缘梦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某男梦神女主动与其相配结为夫妻;其二为某人于某地因戏言将自己或某女婚配于鬼神及产生的后果。前者以《弦超附知琼》为代表,后者则以《张璞》《蒋山祠(三)》为代表。(3)因果梦。《搜神记》中因果梦的故事可以根据产生因果的主体分为两类。首先是以人为主体,如《三王墓》;其次是以动物为主体,或为报恩,或为报仇,如《华亭大蛇》《董昭之》。此三类“预兆梦”故事可以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审美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显现,贾建秋的著作中提出,这一时期的审美思想糅合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审美观和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审美观;包容了人类初级的愉悦性的审美感受和高级社会形态下具有鉴戒、伦理意义的审美感受;交织着玄、释、道的审美趣味。因此,结合该时期显现的美学思想来分析《搜神记》中的“预兆梦”故事,更有利于对其意蕴的探究。
三、“真幻”“因果”美学的显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不同于先秦两汉庄重严肃的审美氛围,而更为崇尚简朴自然之美,因而赋予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更自然多元的美学表现。
占梦是三类预兆梦故事中蕴含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类故事,其中包含的美学思想可以从“真幻”美学角度进行探究。从表面上看,《搜神记》中占梦故事体现了儒学的世俗化需要,这类占梦多为统治阶级服务,无论是孙坚夫人梦日月入怀,还是蔡茂梦殿梁上三穗禾,都是为“贵人”身世或职位升迁等提供某种来自神的启示,以抬高其身份或为某种现象增加合理性,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是受儒家“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体现了某种世俗化需要。但跳出这种世俗化需要,分析其故事内非世俗化的宗教因素,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真幻”之美,体现在文学文本之中,我们可以从占梦故事中出现的日、月、三穗禾等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意象出发进行探究。各类宗教和哲学思想都离不开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讨论,道教的“有”“无”,西方柏拉图的“理式”都是对世界本体的代指,体现在佛教思想之中,便是“真幻”中的真。在《搜神记》占梦故事中,对“真幻”的呈现可以解释为这些神秘的意象是“真”的化身,而化身所出现的地点为梦境,是虚幻无形的,真实有形的美好事物却又出现在虚妄无形之处,则为佛家之“幻”。这种“真”和“幻”互相交织的矛盾复杂,让占梦故事拥有了神秘又富有张力的美感。
《搜神记》中的几则因果梦故事,顾名思义受“因果轮回”思想的影响,在此观念中,人的命运受因果的影响,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可以说是一种教人向善的传统伦理教化思想。在《搜神记》因果梦故事中,楚王杀干将是因,因干将儿子赤比而死是果;陈甲和董昭之对大蛇和蚂蚁的一杀一救是因,结局的一死一活是果。干宝受因果观的影响,在故事中设置了这样的因果线,故事的发展也完全按照这条线来进行。同时,主人公获得善果和恶报的方式充满着神秘色彩,无论是主人公预知命运的方式还是获取报应的形式,都充满着奇幻神秘之美,且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赋予故事理想浪漫主义之美。
四、超脱俗世的道家“逍遥”之美
《搜神记》中姻缘梦故事既涉及姻缘问题,便不可避免地与世俗社会相联系,但干宝所创造的姻缘梦故事之中却存在着一种超脱俗世的“逍遥”之美。这种“逍遥”的审美意识来自道家美学代表庄子,是一种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庄子提出,“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列子御风而行”,也还是 “有所待者”,而真正的 “逍遥游”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是无所“待”的。这是一种至乐至美的审美愉悦,是超脱功利和世俗的。《搜神记》所记载的故事《弦超附知琼》中,弦超梦天上的玉女成公知琼与之相配结为夫妻,梦醒后果有神女降临。神女与弦超有着这样一段对白:“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可得远味,异膳,增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神女婚配食异膳、用素常,不生子、不妒忌、不碍世俗婚姻,这种姻缘婚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现实的,在二人夫妻八年、弦超婚配之后仍与之往来,直到弦超泄露秘密,神女不得不与其分开,但五年后二人又结为夫妻。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反现实反世俗的,神女的行为不受世俗牵绊,完全出自本心,是合乎“道”的。故事中的神女不在乎功名利禄、世俗名分,行为举止完全出自本心,且神女不受外物之累,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这些都来自“道”,神女因得“道”而从心,因得“道”而逍遥。道家的“逍遥”之美同时亦来源于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即顺应规律,不强加要求。《弦超附知琼》中的神女知琼顺应天命嫁给弦超,亦因秘密的泄露与其分离,后又于机缘巧合同弦超重逢,她的种种行为皆是顺应自然而行,保持着一种自然淡泊的超脱态度,没有过度的情感表达和世俗牵绊,即使相聚多年,神女依旧坚持原则选择离去,即使相离多年,仍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重聚,这种突破了时间和身份限制的无谓态度,反映着道家对生命生活的豁达观,是超脱俗世的道家“逍遥”之美的个性体现。
五、对人性美的追求
魏晋南北朝所尊崇的人性之美,是不脱离道德伦理,符合社会伦理规则,合乎儒释道三家伦理美学,同时亦在传统伦理规则中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的品性。《搜神记》“预兆梦”故事中多肯定真善美,否定假恶丑,表现对孝敬、慈悲、善良等品行的赞赏,对凶恶、傲慢、不公等品行的批判。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在干宝《搜神记》的创作中,给予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肯定或否定。《董昭之》中董昭之救蚁,蚁王梦中出现报恩让董昭之因善行获得好的结果;《华亭大蛇》中陈甲射杀大蛇触犯了杀生之罪,是违反人性的恶行,后来其因梦中大蛇报复而死。故事中出现的妖怪形象赋予了故事神秘色彩,但其报恩或报仇的行为则充满人性化色彩。两则故事均实现了善得好报、恶得恶报的结果,亦是借文学作品对社会进行道德教化,即人性美就会获得好报,人性恶则会受到惩罚,实现“以神道设教”的目的。
《搜神记》中《三王墓》《栾书冢》《华亭大蛇》《董昭之》四个故事除了对善行的肯定和对恶行的批判,亦有一个共同因素。《三王墓》讲述的是干将和莫邪之子赤比向楚王复仇的故事,故事主线是对王的复仇;《栾书冢》讲述的是汉朝广川王掘栾书的墓,伤墓中白狐左足,白狐出现在王的梦中以伤王左足的方式报复他;《华亭大蛇》中陈甲无故射杀大蛇,招致大蛇报复;《董昭之》救蚁王,但船上同行的人反对救这种蜇人的毒虫。这四个故事的主线虽然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但其中仍有并不符合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因素存在,这就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中存在着伦理教化及自我人格之间的冲突,封建伦理教化的规则并不完全符合人性,甚至部分是反人性的。赤比杀王并不符合传统伦理思想但符合人性,而王死是符合恶有恶报的传统伦理思想的,其他三个故事皆是如此。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所真正追求的人性美是不脱离传统伦理教化的约束,不脱离社会制定的规则,同时又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坚持人性自由的独特品性。
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宗教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渗透,使魏晋南北朝的审美意识将真善美囊括在内。“预兆梦”故事中主人公的善行受到鼓励和赞赏,恶行则受到唾弃和惩罚,借助梦这一载体实现则是借助鬼神来增加威慑力,在当时科学意识还未发展的古代,无疑是极具影响力的。对人性之美的赞赏,对真实、善良品行的鼓励,不但能在社会层面实现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同时亦有对在传统伦理教化中仍保持自我人格意识的品性的肯定,此类都清晰地代表着魏晋南北朝民众对真、善和人性美追求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
六、结语
梦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中国古代极重要的文化主题,对政治领域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左传》中就有大量与梦相关的故事。《汉书·艺文志》所记:“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可见周朝存在占梦官这一职务。在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派创立者弗洛伊德极重视对人类梦境的解析,他认为梦境是人类内心潜意识欲望的反映。他于1900年创作发表的《梦的释义》充分阐释了他对人类梦境的解读和观点。战乱频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独特的文化环境,干宝《搜神记》一书便创作于这种社会环境之中,成就了该书独特的审美意识。梦因其内容的多样被分为许多类型,但就其影响和价值而言,“预兆梦”这一类型在进行梦的研究过程中是难以忽视的。同时,探究“预兆梦”故事意蕴亦推动我们对《搜神记》文本的进一步认识。对干宝《搜神记》中“预兆梦”故事意蕴的研究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内涵难以用一篇文章进行概括。中国古语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西方弗洛伊德将梦总结为潜意识的运作。“预兆梦”故事中梦中所出现的特殊意象和情节皆是现实生活在梦境的迷幻化反应。《搜神记》给读者创造了一个魔幻又现实的文学环境,干宝借“幻梦”喻“真世”,借“虚事”表“真理”,一切看起来光怪陆离的虚幻故事,却又与现实紧密结合,正是干宝的高明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社会氛围和该时期显现的众多美学思想也赋予《搜神记》更丰富的审美价值,阅读其文本亦是后来人对当时美学思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的学习,影响着后来人的文学创作。干宝《搜神记》的“预兆梦”故事,为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同类小说发展提供了前鉴,并启发了后世唐传奇等小说类型的创作发展。
参考文献:
[1][东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傅正谷.中国梦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J].文物,2006
(06):61-71.
[5]贾剑秋.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审美思想[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1):47-51.
[6]潘显一.“虚静” “逍遥” “玄德”:道教美学情趣论[J].社会科学研究,1997(03):96-101.
(作者简介:王嘉宁,女,硕士研究生在读,长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文艺学;刘利凤,女,硕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