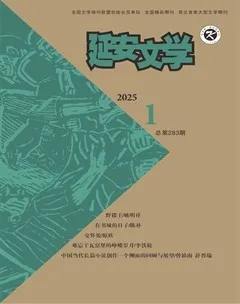茶马古道
2025-01-01马海
马海,回族,云南华坪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当代》《四川文学》《诗潮》《北方文学》等。出版散文集《味蕾上的云南》等。
马帮,云南高原上的岁月之舟,在上世纪末的最后一个黄昏,摇着响铃渐行渐远。这似乎已是无法违背的历史选择。但它伴随无数边地人的先祖走过千年驿道,在年轮上敲打出的辉煌,哪能轻易从当代人的意识里被冲刷掉?从解放初享誉全国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到本世纪初屡获大奖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从存入一代人记忆的小说《神秘的马帮》,到体现大香格里拉热的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神奇的马帮所拥有的看点,及其感染后人的探险精神,竟是一直未曾在人们心灵的驿道上冷却。
云南马帮,最艰险卓绝最具代表的,是滇藏贸易古道——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茶马古道,是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与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的一条神秘古道,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动人心魄的道路。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穿行。滇、川、藏三地许多人的祖先,在这条路上赶着马帮,驮着茶叶和各种山货,来往于西藏和云南之间,书写了一部繁荣经济的史诗,一部民族团结的史诗,一部奋斗不屈的史诗,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史诗。今天,探险活动与户外旅行已成为世界新潮流,不少人都把目光投向这块叫做“神川”的神秘地带。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自西向东并列成“川”字,浩浩荡荡奔流南下,进入滇西北高原的大峡谷中。这里海拔多在三千米以上,有的高山海拔甚至超过五千米,山尖积雪,牦牛望月,峡谷浪吼,天悬一线,是世界最壮观的大峡谷之一。一边是悬崖峭壁直插云天,一边则刀劈斧砍般濒临深谷大江,藤萝或羊肠般的驿道穿绕其间,人或动物稍有不慎就跌下深谷大江,连尸首都捞不回来,在这样的地方运输往来,船只、牛、大象、毛驴都无法派上用场。勤劳智慧的滇西先民,培育出了能在九曲十八拐的山道上作长途跋涉的“云南马”,以及更具耐劳能力的新品种——骡子。一代代高原汉子,赶着骡马组成的商帮驮队往返于滇藏,穿行于莽莽大山,涉过浩浩江流,走过茫茫雪域,惊天地、泣鬼神的茶马古道文化被写进了岁月的苍茫。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主要产自滇西或滇西北。大理白族的马帮称“喜洲帮”,因赶马人以喜洲为主;鹤庆白族、汉族组成的叫“鹤庆帮”;腾冲汉人组成的称“腾冲帮”;丽江纳西族组成的称“丽江帮”;中甸、德钦藏族组成的称“古宗帮”;巍山、宾川回族人组成的“回回帮”等等。这些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各族马帮,共同绘制了茶马古道的繁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滇越铁路和滇缅古道被封锁截断时,从滇西至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旗号为“木家帮”“罗家帮”的即为此列。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为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据民俗学家估计,到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号有1500多家,每年来往于云南、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约有30000匹之多!
与民国时期那些地方军阀、地主武装、土匪团伙、江湖帮派等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否则,马帮就无法在那动荡不安硝烟弥漫的时代生存发展。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步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头骡奔,二骡跟,尾骡稳”,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驮子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来了。头骡的威风,二骡的霸气,尾骡的老到,整个马帮气势逼人,一路浩浩荡荡,马嘶人吼,马蹄踢踢踏踏,敲出火花,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头。马帮的行走,带来了驿道沿途马栈业的兴盛。一般驿道沿途的集镇或山野都有大小不等的马店,为马帮商队提供休整歇宿的方便。马帮露宿,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野外露宿,一是不易防范土匪和野兽,没有安全感;二是生活不便,天寒地冻,休息不好,影响行程;三是不便与商户交接生意;四是夜晚娱乐内容少,生活枯燥。山垭野村开设的马店,一般较简陋,可为马匹遮风挡雨提供夜料,为赶马人提供火塘、稻草铺等。在丽江通往四川的要道上,一个叫养马丫的荒村马店里,就题写着随马帮而行的文人写的一首诗:
依山刳木取泉遥,分得银河落九霄。
淅沥声惊客梦醒,恍疑檐外雨潇潇。
诗里的况味,大致可以感受到那时那地的孤旅愁绪,冷风吹进马店,夜马嚼食草料,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寂寥长夜,唯有围坐火塘边,对点旱烟,把酒话旧事,打发荒村夜色,不时还会担心狼群或土匪的袭击,于是瞌睡来临也不时惊醒。而集镇上的马店宽大气派,一家马店可同时容纳几支马帮;要道上的集镇甚至开设好多家马店,几十支马帮投宿在一个集镇上,其热闹场面超出想象。这种时候,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马帮可能会产生投合之意而结为兄弟帮,大碗喝酒,大声对歌,赛唱赶马调子,马店的院子里篝火冲天,马嘶人欢。特别是善歌的白族、纳西族、普米族或藏族马帮凑在一起,其赶马调子就十分精彩。白族马锅头的调子豁达爽朗:
草绿坝宽好放马,妹子心宽带得人。
哪里有草就牧马,哪点有情去哪边。
纳西族赶马调子纯真乐观:
马帮插红旗,红旗小妹插。
小妹装饰马,阿哥捆驮子。
想歇没有水,想歇没有柴,
只有烧马粪,只有喝雪花。
当然,茶马古道的辉煌时期正值乱世,驿道石板上的一个个马蹄窝里,装着的可能是雨水、汗水、月光、阳光,也可能是泪水、血水、刀光、火光。土司、土匪、帮派、流官、散兵游勇、军阀鱼龙混杂,杀人越货、抢夺财物的事经常发生。叼着烟斗、背着水烟筒的赶马汉子,不但一路上要善于察言观色,还要有勇有谋,自保平安。马店里的风流艳遇,可能会得到爱情,也可能是一个陷阱而掉脑袋。山道上遇匪,可能因自身人缘广、来头大而化险为夷;也可能枪杆子不认人而遭遇到杀人夜、放火天,弄得人死货丢马帮散!茶马古道上的雪灾、泥石流、暴雨、山洪、狼群、虎豹、匪患、险山恶水……一系列难以计数的威胁,使茶马古道的旅途充满冒险和奇幻色彩。“苦闷的灵魂,寂寞的旅途,赶马人一根长鞭驱赶孤魂。风霜雨露落满披毡,上驮,赶马,火焰催白天色,篝火的灰烬,化尽一夜风险。”短短的诗句,无疑是一幅活生生的《茶马古道夜宿图》。正因为茶马古道马帮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识的,其冒险精神才会在今天闪耀光芒。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为了生存,为了贸易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生命代价去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搭进几代人,仍然一无所有。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运行的茶马古道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被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对要生存、要发展的马帮来说,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茶马古道上马帮的探险精神是遗留至今最大的一笔财富。
马帮的利益跟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在一起。马帮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就势必倚国重民,这就造就了马帮的爱国精神。民国年间,西南有不少马帮一直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与外国商人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时候,常常因为自己国家民族的羸弱,而在生意上吃很大的亏。从国内来说,如果政府腐败,贪官横行,政局不稳,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马帮的生意和生存。因而,马帮们常常体现出一种向心力,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昌盛,具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许多赶马人就积极投鞭从军,成为保家卫国的极好战士,因为他们平时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和纪律,而且人人会打枪战斗,又熟悉地形道路。当时他们就唱出了这样的赶马调:“马铃儿响叮当,马锅头气昂昂。今年生意没啥子做,背起枪来打国仗。”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辛勤奔波于茶马古道上,为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运输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仍有许多昔日流落在外的赶马人回到祖国报效尽力也是明证。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息叛乱的岁月里,他们也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尽了不可或缺之力。
今天我们回望茶马古道的历史时,目光应落在它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取向上:茶马古道的马帮绽放的是高原民族祖祖辈辈奋斗不息的精神,壮大了不断自强不断探索的人类力量。因为如此,茶马古道驮出的辉煌,才不会从我们心灵的长河消逝!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