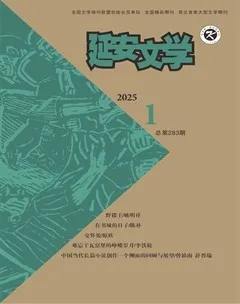讲述鲜为人知的延安故事
2025-01-01胡松涛黄蕙心
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群生命浪漫的党员,一片飘荡着战火和人间烟火的土地……《延安典故》是一部书写延安时代的散文随笔集,挖掘大量鲜为人知的典故,通过密集而富有意味的细节,展示了一代革命者马上打天下的壮观场景,书写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塑造文化江山的绚丽景象。
黄蕙心(《延安典故》责任编辑):胡老师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您的《延安典故》出版后,读者反映是一部既具历史深度又具文学魅力的作品。我们知道,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毛泽东讲哲学、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您用随笔、散文的形式书写了那个大时代的这些大事件,内容生动,文字活泼,全无阅读其他类似读物时的枯燥感。我和读者都想知道,您是如何用文学的形式创意表现延安时代的?
胡松涛(《延安典故》作者):文学创作都有其主题性,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延安典故》以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为题材,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是基于我对延安时代的神往和理解。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黄金时期。遥想1935年至1947年间,共产党人在偏僻贫脊的中国西北,住窑洞,吃小米,艰苦奋斗,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全中国的梦想而流血牺牲。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又多次到历史的发生地学习和采访。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牵动着我,探索以文学的方式,以今天的目光,聚焦延安时代,讲述延安时代的故事。延安是汪洋大海,我取其一瓢。《延安典故》书写延安故事,勘探“今天”的来路,是对弘扬延安精神的文学响应,是在文化意义上书写延安精神。可以说,创作《延安典故》,始于好奇,探得珠玉。
黄:读《延安典故》,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延安人”,看到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也看到了他们的苦恼、矛盾以及冲突。比如说,一位红军干部与一位女知识分子结了婚,两人在延河边散步,正赶上十五月圆,女人感到无穷情趣,指着月亮高兴地说:“这月亮多美呀!”男人说:“月亮就是月亮,像一块大烧饼挂在天上,有什么美不美?”再比如,许多革命者刚住进简陋粗糙、低暗阴冷的窑洞时,难免会“吐槽”,发出一些牢骚和埋怨。而到最后,他们是扎下根来,团结群众,接连地气,对待窑洞的感情、立场也随之改变了。感觉这些东西真实而有趣。
胡:写这样一组涉及重大题材的非虚构的作品,首先要有真实的史识,真实是第一位的;但同时它又得是文艺的,不能是说教的或是授课的。这本书是以文学形式对延安故事的重写和再现,需要突破文学对政治伦理的概念化书写、依附性书写,写出文学的、个性的、独特的东西。人物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写作中,要从团体“我们”中写出个性“我”,既要写出人物的精神世界,也要写出他的日常生活——吃饭、穿衣、洗澡、恋爱等,写出内心矛盾乃至革命人之间的矛盾,写出多样性与复杂性。不人为拔高,不刻意煽情。对一些“敏感”的故事也不遮蔽,不回避。书中写到一些同志在“整风”运动中被毛泽东批评后的苦恼;“七大”中没有当选中央委员的苦恼,还有“洋包子”与“土包子”工作生活恋爱中的苦恼,等等。这样写,作者会有一些压力。但是不这样写,就写不出历史的真实,也写不出革命者的真实面目。实践证明,那些革命内部的矛盾以及革命者内心的冲突,都是非常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在文章中形成大的张力。这样写,更容易走进那一代人的心灵,写出一代革命者的初心,写出“延安人”的精神世界,写出那种永恒不易的东西。这不仅无损于革命者的形象,反而使革命者的面孔更清晣更亲切了。在写作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自己正走进他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且被他们照亮。
黄:重回现场,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像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感觉这种题材非常不好驾驭,写出来也不一定好读。我读《中共七大历史现场》等,感到非常好读,有进入现场的感觉。
胡:如何书写大时代、大事件?党史是一种写法,教科书是一种写法,文件也是一种写法。《延安典故》采用文学的写法,立足现场去写,这是继承革命文艺的好传统。在延安时代,文艺家就是以文艺的形式表现延安、宣传革命的,像歌曲《延安颂》、歌舞剧《白毛女》、钢琴曲《黄河大合唱》、小说《白洋淀》等,都是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我在创作《延安典故》这组系列文章时,尽量让世界依其原样而自在重现。回到现场,回到历史语境,就是回到事件的本来面目,回到那个元气满满的地方,仿佛老子说的“复归于婴儿”。延安是个大现场。《延安典故》聚焦或截取一个个具体的现场,展示革命者的精神风貌。《中共七大历史现场》是其一,这篇文章在《美文》杂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两个整版,被许多报刊转载。许多朋友喜欢这篇文章,说有身临历史现场的体验。《延河:流水十四章》以延河为现场,写革命者“临清流处”的事迹。现场就在那里,许多时候我们把它忽视了、忘却了,关注的是现场之外的东西。我的写作是复归于现场,让现场“说话”,因为现场给人的感觉要比非现场强烈多了。人物、故事、话语只有放进具体的现场才能显示其意义。这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在返回现场,让人物、故事在现场重现,让精神和心灵在那个现场空间中展现。再比如《延安桃园记》,这个桃园不像七大礼堂那样还在,桃园已经不在了,我对这片桃园进行“重建”,构建了革命延安的“桃花源”。《延安窑洞是如何打成的?》更是直接把人带入打窑洞的现场。现场,不仅是纪实的场,也是展现精神的一个场,充满生命张力的场。现场不仅是纯然外在的时空,更是人的心灵所构造的世界。回归现场,恢复历史的鲜活,将80多年前故事发生地的场景拉到我们面前,揉进当下的理解。用今天的目光对所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描绘,使得亘古的永恒在自在的鲜活中呈现,将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
黄:在《哲学的窑洞,哲学的延安》中,您将毛泽东哲学的一个个问题放置于窑洞、延河等具体场景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抟虚为实”的写法,使得人生哲理随处可见,自然之趣映现其间,把“枯燥”的哲学和谈哲学的人都写活了。您是如何考虑的?
胡:这是一个“如何写”的问题。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可不可以虚构现场?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叙事方便虚构了一些现场,打破“非虚构”和“虚构”的壁垒,司马迁老先生肯定尝到了虚拟的甜头,所以你看《史记》中的许多篇章(比如《项羽本纪》)写得眉飞色舞。《五灯会元》说:世尊在灵山拈花示众,一言不发,众弟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惟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这个故事,见宋朝普济的《五灯会元》卷一。这个故事之所以讲得好,是虚构了一个现场。所有佛经中都没有这个记载。尽管是虚构的,也不影响它在禅门中的无上位置,并且它比许多经典都流传得久远。中国的禅宗特别善于通过造境来传达哲理。创作《延安典故》时,我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演绎、还原、想象、重建现场。毛泽东一辈子研究和谈论哲学,如何把他的哲学观点生动地表现出来?哲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个“枯燥”的话题,如何把它形象生动地讲述出来?抟虚为实,蹈光蹑影,有了这篇《哲学的窑洞,哲学的延安》。这篇长文,以尊重史实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建立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使内容与形式达到一种平衡,以方便表现哲学内涵。在这里,窑洞、延河等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或者说不再是一个物理事实,而是一个心灵真实,一个哲学生命体验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仿佛自然天授的空间里,哲人沉思,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讲述自己的哲学,展现哲人的精神风采,呈现出丰盈的审美性。毛泽东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篇文章的这种写法,不知道算不算一种试验。我感觉,这样写,有写作的激情,也能增加阅读的热情。
黄:《延安典故》一书中,写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写一些理论问题,您将大历史与小细节巧妙地融合起来,即使是那些不那么好处理的理论问题,因为有故事,有情节,读起来也很有趣味。这本书中,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延安故事,写了一些值得反复看的故事。您是如何挖掘故事,捕捉细节的?
胡:故事,是承载历史事件最有力量的载体。延安时代有许多好故事,故事中有许多好细节,可惜在许多反映延安的图书中看不到,大量的是概念,是观点,当然这也需要。一些“党八股”叙事者“舍事而言理”,把一些好故事好细节“过滤”掉了。没有故事,没有细节,文章容易走向空心化和肤浅化,变成空洞无物的说辞。进入历史要通过故事与细节,这是能够让我们走进历史真实的唯一途径。在写作《延安典故》中,我下了一些功夫去搜集挖掘故事和细节。一个是到现场采访,我在陕西行走多年,在革命圣地的现场搜集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当然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写作准备阶段,我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延安的回忆录,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寻找故事。有时翻一本书没有找到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细节,痛苦得不行。我心想,一定不能让读者读我的书时,遇见这种痛苦。这本书中,我努力加强文本的故事性,用故事支援宏大叙事。像《马,毛泽东打天下的马》用传统笔记的形式写马在革命中的传奇,“堆积”几十则“马的故事”。总之,这本书写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好玩的细节。
黄:皎然在《诗式》中说:“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延安典故》中,巧妙地融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诸多经典语录,文采斐然,有许多好句子,让人爱不释手。
胡:谢谢您的鼓励。汉语具有天然的诗性。延安葱郁美丽,革命者在延安如朝阳初启,灵光绰绰。他们的精神就像玫瑰的芳香从革命事业中散发,他们在创造闪闪发光的功业的同时,创造了许多充满诗意的句子,彰显出革命的智慧。这部书所表现的内容,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原生的影响力。作者的文学创作不应该仅仅依赖题材客观上自带的光环,还必须摇动一支笔,以作者的风格为故事增光添彩。我读一本书,喜欢书中的好句子。作为一本写青春延安之书,我希望从中受到延安精神滋养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好句子的享受和提升,希望《延安典故》中的句子比“作者”高明。
黄:您通过《延安典故》一书,巧妙地将延安的历史与文学融为一体,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宏大又细腻的时代画卷。您的新作《遵义三日》也即将出版,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非常期待您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历史与文学交织的佳作。
胡: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延安时代。改天换地的遵义会议是创建革命圣地延安的序曲,辉煌的延安时代是遵义会议带来的壮丽华章。《延安典故》选取了延安时代的典型场景进行书写,以十几篇随笔和散文的形式来呈现革命者的精神风范。《遵义三日》则集中书写了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那场为期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可以说生死攸关,惊心动魄。因为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起死回生,毛泽东从生命的至暗时刻开始走向辉煌。《遵义三日》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生死关头的传奇,一个反败为胜的奇迹,一个否极泰来的命运神话。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