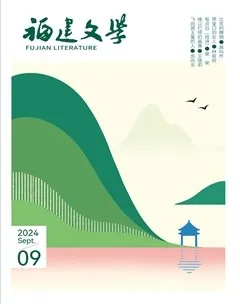风云起东关
2024-12-31张威
1
邵武民谚曰:“十万旱天雷,风云起东关。”正如马星辉长篇纪实文学《东关尘》中所言:“邵武东关是一个传奇的地方,它是一个繁华之地、包容之地、善恶之地、传奇之地。时尚落后与富足贫穷并存,真善美与假恶丑同行。各种势力在此龙争虎斗、刀光剑影,岁月带不走发生过的故事。”
《东关尘》由31章34个短篇故事构成,各篇文字写俗世奇人故事,其作品风格取话本文学之旨趣,并接近于古典传奇之色彩。书中所讲之事之人,以邵武东关市井生活为背景,多居民国至“文革”期间,其素材收集于长期流传于邵武东关的民间传说,人物之奇特,闻所未闻,故事之精妙,亦令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每个人的命运里总会有一根无形的绳索,串联着岁月的每一刻。跟大多数小说一样,《东关尘》拥有一个诞生故事的背景。书中描述民国时期的邵武东关,是一个富庶的地方,作为紧靠富屯溪的水陆码头和交通枢纽,这里的居民鱼龙混杂,性格迥异,行业繁多。因身处乱世之中和动荡时期,便出现了许多奇人,他们依靠着高超的手艺自立谋生。他们有的思维灵活、伶牙俐齿,有的敦实憨厚、一身本领,有的投机取巧、自讨苦吃,有的机智过人、能化险为夷。诸如“东关四杰”里的名医何逸夫、甘草爷欧阳云峰、水鬼敖东拉、鱼鹰王宋大龙,还有豆腐王、朱半仙、橹子裁缝等角色,既混迹于上层阶级,也流转在市井民间。虽然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故事,但实际上他们又是一个整体,任何人都是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因其间蕴含着的“俗世精神”,所以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谈到此书的创作动机时,马星辉说:“我曾经在东关工作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里,‘东关’这两个字很平凡,但在我的眼中它是钢铁、是传统、是男子汉。但它又有点缠绵,有点无奈。它没有姹紫嫣红,只有五味杂陈中的那么一点酸,一点甜,一点苦,一点辣,一点咸。所以我想记录下发生在东关的这些布满了灰尘的岁月与往事,在记下东关英雄人物的同时,亦要记录下东关平凡群体中的你、我、他。”因此,在长时间对人物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他用生动的笔法赋予东关人物不同的性格与风采,也写出了邵武的民风民俗、地域人情乃至人间烟火。有些字句以邵武方言连缀,既突出体现了当时邵武东关的社会风貌与历史背景,也让读者能够从书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浓的经典邵武味。这让我想起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个描述:“劈开宇宙,向自己的体内跳去。所以作家既要能写纵横捭阖,还要能写日常生活,既有大胸怀和大视角,也要有写高度生活化的日常细节的写作能力。”
每一个当下,都是由过去无数个当下而来,又引出未来无数个当下,没有纯粹而决绝的某一个当下时刻。每个人所有的观望,都是在审视自己。就如《东关尘》里的每一个用词、意象、念头,涌现在马星辉心中的,是历史烟云里的一次次徘徊、思索、吟哦,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也是马星辉借东关这一方土地,更好地看这个世界,看风云人物,映照出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
2
在福建文学界,马星辉是一位有作为的通俗小说家和散文家。作为一名高产作家,马星辉对通俗小说的钟爱在于他对历史文化有着执着的情怀和独到的理解。尤其对于通俗文学作品,他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逻辑和阐释方式。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余岱宗评价他的历史小说特色时说:“马星辉在于将个体传奇的神奇力量发挥到一个极高的程度。”(《形象特色、叙事结构与文化价值——评〈天道·张三丰传奇〉》)他创作的每一部通俗文学作品,都有他独特的心得和写作范式。我们可在他历年创作的作品中得以管窥,如早期的《小城人物》《小城故事》《古道随笔》等;尤其是他的系列通俗小说,如《李纲传奇》《张三丰传奇》《星溪风云》《天道》等,也包括这部《东关尘》,其“对话、场景、悬念,一应俱全,一丝不苟地塑造人物,推进故事,一个个人物被演绎出来,鲜活无比”。
在邵武城市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码头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码头脾气是邵武人性格的骨架,是邵武人“炽烈爽利、逞强好胜、充溢活力的地域性格”的基因。于是,马星辉从“一件件遗落”的“细节”入手,记录下这座城市最富魅力的文化个性,这也是时代更替过程中,渐渐逝去的独特而鲜明的“城市个性”。他将这一生存法则称为“硬碰硬”。比如“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由此,造就了“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这些“活神仙”成为《东关尘》里的重要角色,也成为马星辉诠释这座城市“炽烈爽利、逞强好胜、充溢活力的地域性格”的“标本”。比如,传奇人物敖冬拉是“东关四杰”之一,由于他有一身不同寻常的水上硬功夫,在水下可以屏住呼吸潜水三分钟,而在深水中双脚踩水,上半身可以跃出水面达到肚脐眼的部位,如此高的技艺,让包括鱼鹰队队长宋大龙的所有人都甘拜下风,所以东关人将他称之为“水神”。这是一种江湖原生性的,未经过过多修饰的一种自然表露。还有橹子:“橹子近30岁,独身,他是一个拐子,小儿麻痹症坏了他一条右腿,细得像根麻秆。走起路来总是左手搭在左大腿上先迈出一步,紧接着上身向前一扑,腰一弯,屁股一撅,半拖着右腿从外向里画了个大弧圈,连串起来就像大猩猩的动作。”这些生动而细致的描写,停留在我们的阅读记忆里,让人读后不能忘怀。
《东关尘》的语言运用很是用心。首先是运用了大量的邵武民间方言。诸如“漆里骨黑”“天公(早晨)”“马娘”等,就连用在旁白的介绍时,也会冷不丁给你来一句“最好听是火烧竹,最好吃是蒜炒肉,最好玩是肚对肚”“颈子再长,也高不过脑壳”“把头给你做菜墩”“人怕没理,狗怕夹尾”“女怕口漏缝,男怕耳煽风”等,其东关独特的生活气息在语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你酸什么醋?好像很有文化一样,真是洋油箱(卖弄)得很。”“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长短。”“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这些富有邵武方言味儿的浓厚语言和诙谐的味道,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其次是谐音的化用,妙趣横生。诸如:“城边巷开瓷器的迟花花的姓与卖的货都与‘慈’字谐音,便理所当然地称自己是‘瓷喜太后’;城门口补车轮胎的刘二麻子,叫自己的店为‘拿破轮修理店’;在兴化巷口卖糖果的唐九丘,把店名叫作‘糖太宗京果园’;中山路613号开布庄的吕小波是子承父业的年轻老板,人长得英气,当仁不让地叫自己为‘吕布’;那精瘦干巴、卖碗糕的高老五,有鼻子有眼地说自己是‘汉糕祖’投胎……”阅读《东关尘》,那些具有邵武民间方言特质的语言,既生动又简练,勾勒出旧时期邵武东关市井街巷里的奇人奇事,也赋予了小说的灵动性和代入感,让我们在反复阅读后,仍觉得意犹未尽,欲罢不能。
3
读《东关尘》了解东关的历史,倾听城市深处的生活,会让我们的内心丰盈。现在,每每我经过东关,走在它身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从回望故园到融入城市的深情歌者,星罗棋布的东关小巷前后左右,照应有加,无论是屋舍、水井还是基石、石板都藏满了玄机。在光线衬托下的一个转身或一个回眸,常常会让人跌入某段遥远的记忆,你也可以读取出东关人蛰居在巷子里谋求安身立命的符号与密码。站在桥面上,看匆匆忙忙的人流,他们忙着去上班上学、忙着去买菜做饭……这俗世生活里展开了人间烟火,展开了这座城市生动的表情,又似乎滚滚东关尘,就在这古桥上,随富屯溪水荡漾、远去……
我想,在最熟悉的地方,寻找到最美的风景,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正如马星辉在后记里说:“历史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更因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