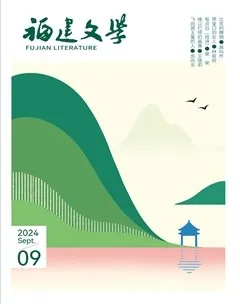修桥记
2024-12-31萧令安
1.我在福州修大桥
下岗后,我在广东待了两年,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悻悻而归。在家又闷了半年多。过了春节,看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我家马路对面的火车站,我正为去哪里打工发愁,恰巧老家一帮人去福州修大桥,有个同族兄弟来我家歇脚,我临时起意,跟他们一起来到了福州乌龙江大桥工地。到了地头一看,这桥只剩下几十米就快要合龙了,最多只有半年多的工期。看这境况,半年后又要四处流浪了。
民工住的工棚建在一处凹地,地面没有硬化,潮湿蒸沤。二层竹编大通铺,挤着二十来个民工。各种气味从地下、床底、铺盖、人体散发出来,熏得人无法呼吸。老乡们照顾我,把我的床位安排在上层的窗边。说是窗,就是把石棉瓦墙捅破个洞,铁丝绑块木板,用竹棍支住。不过空气的确好了很多。
好像上辈子做过桥工一样,从来没有进过大桥工地的我,对大桥各种施工工艺有一种隔世的熟悉感,很快就成了一名熟练的大桥民工了。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那时的老板把民工带到工地,交到各个工班,由职工带着干活,职工对民工很友善,宽松的管理也纵容了部分人的懒散。
一天下午3点多,我们工班在桥上预应力张拉,一个民工油子摊手摊脚,头枕在氧气瓶上,口沫横飞地吹牛。班长说,还有一索,拉完走人。年轻的班长平常太好说话,那几个好像没听见一样。我想早点下班上街买收音机,睡前听听音乐,接着班长话道,兄弟们,过来干活呀,早干早了。
吹牛的民工瞪了我一眼说,关你什么事。
我说,干完下班,早点回去吹不好吗?几个民工起身过来。
那人骂道,有本事你一个人干呀。他吐出横叼的烟,爬起来指着我骂起来。
我脑子一热,操起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绞线,朝他抡去。正在工地巡视的值班经理冲过来,一把将我们拉开,狠狠将我批评一通。下班后,那位姓丁的经理叫我去他宿舍,我以为他还要批评我,他却叫他妻子炒两个菜,请我喝酒。大公司领导主动请民工去家里喝酒,真不多见。
20世纪90年代,是福州市城市建设的蓬勃期。这年6月,乌龙江大桥尚未完工,青洲大桥又开工建设。丁经理调去青洲大桥主管2号墩施工,把我带了过去。2号墩承台吊箱围堰有两个篮球场大,号称亚洲第一。聘请境外监理公司,不光工地管理非常先进,民工生活条件也大幅提高。每个民工发两套工作服换洗,进出工地统一着装,还住进了装有空调的活动板房。2号墩是青洲大桥的主墩,1000多平方米的施工平台建在离岸1公里左右的水上,我们乘轮渡上下班。百多号施工人员,十几台新型钻机日夜开工,一到晚上,施工平台灯火辉煌,照在闽江之上,站在岸边看去,宛如一座水上城堡。
班长马师傅是一位部级劳模,不善言辞,上班就自顾自不停地干活,身体里像有使不完的力气。那段时间里,我跟马师傅学到了许多工作技能,对桥梁施工有了新的理解。每天上班前,马师傅都要把每根装吊的卡环和钢丝绳检查一遍,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提醒我们不能穿滑底鞋上工地,高空作业须系好安全带,一步一挂。下班了,当我们涌向第一班交通船,他还要在工地再收检一遍,乘最后一班船返回。那年中秋夜,久晴乍冷,我们加班到晚上10点多上岸,只见马师傅刚从河南老家来探亲的妻子和女儿,站在码头边昏黄的灯光下,不停地搓着双臂等候。
项目部不远处有家日杂烟酒店。门口大榕树摆了个茶台。老板是位退休船长,我对茶道仅有的知识,便是在那里了解的。离小街稍远还有一个村庄集市,有位草医罗婆婆,带一个徒弟。罗婆婆说话风趣,是个女版的“老顽童”,工友们感冒了爱去她那喝一碗凉茶,跟罗婆婆说笑,其实是去看她漂亮的女弟子。罗婆婆自称会看相,她说我鼻梁上的痣是“狠”痣,性子急躁,好胜斗勇。说得我大为叹服,鼻梁因此留下了一点凹痕。后来见几个电影明星鼻梁上也有与我相同的痣,生动且帅气,深感自己的痣点掉可惜了。
经过7个多月风雨无阻、紧张忙碌的施工,我们赶在春节前几天,把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超大承台的整体沉箱式围堰安全顺利地安装成功了。下一道工序要将围堰底部与钻孔桩之间的缝隙堵住,抽干水后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本来由专业潜水工下水堵漏,不知什么原因潜水工没有到位,丁经理叫我动员一批工友下水。腊月二十几了,年关节气,福州天气虽然不是很冷,但闽江的潮水依然刺骨。平台上布置了一个热源温室,准备了白酒姜汤、毛巾和大衣,做好了充分的保障,我带着20多个工友,利用三天平潮的当口,用快干水泥沙袋堵好了围堰。当我最后一个从水里出来,丁经理给我裹上一件大衣,满怀真诚地说,有你这样的民工,我到哪里,一定要带去哪里。
堵漏完成后,我们一行人高兴地出去吃饭庆祝,来到罗星街一家餐馆。由于经费有限,我进门便跟老板说好按200元一桌安排。点的菜上完后,服务员还不停地送菜过来。大家尽情地吃着喝着,我却暗暗叫苦。又怕扫了大家兴致,忐忑地吃完这顿饭,硬着头皮去前台结账,老板笑着对我说,今天他们新店开张,我们是店里头一批客人,又是青洲大桥的建设者,大过年在工地赶工,不能回家团聚,这顿饭算作他的心意。我记得那天有一道红烧小章鱼,特别好吃。之后数年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饭局,只要菜单有小章鱼,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点来,却怎么也吃不出那次的味道来了。
一天工余,我坐公交车去市区,手里拿着一张福州市旅游图在看,邻座一对情侣主动跟我攀谈。男的姓林,穿着西装系领带,阳光精干。他的女友圆脸短发,明眸皓齿。听说我要去三坊七巷,就说他们正好住在南后街。下车后,两人不容推辞,请我吃了我平生第一次麦当劳。那几年我四处碰壁,进过鞋厂,做过清洁工,在建筑工地扛过水泥,睡过桥洞,饥饱无常,失意怨叹。与人接触怀着深深的戒备之心,买一包毛巾也要再三问清楚价格,怕一不小心着了别人套路。而一次寻常的偶遇让我收获到了真情,打开了心扉。
青洲大桥2号墩承台浇筑完成后不久,丁经理调往广西桂林解放桥工地,又把我带了过去。离开福州时,我心里涌出深深的不舍。未到福州前,我如暗夜野行,步步荆棘。离开福州时,我的天空已是阳光明媚,充满了勃勃生机。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时间停下来,认真打量福州这块福地。
2.漓江之上有座桥
1999年12月30日,我从福州马尾青洲大桥工地撤出来,回家休息了快一个月,接到电话通知,到桂林参加解放桥重建。我召集了二十几个工友,乘大巴转火车奔赴桂林。
虽然武昌是始发站,一半人还是没有座位。一个有经验的工友说,火车每节车厢虽然两头都有门,但一般只开一头。他带着我们迅速抢占了另一头车门通道,垫了报纸,铺开被褥,坐的坐,睡的睡,几人还甩开了扑克。到了解放桥项目部,已经是31日下午3点左右,接待的项目部领导见我们一脸疲惫,问过后知道我们没有吃午饭,就说这个点食堂没饭吃,出门右拐100米有家米粉店。他叫我带兄弟们先垫垫,强调说:“桂林米粉很有名的。”我们不光没吃午饭,大部分人嫌火车上的盒饭贵,早餐也没吃。我们找到那家米粉店,几个慢悠悠吃米粉的游客,见一帮民工把小店挤得满满的,急忙扒几口,把整个米粉店让给了我们。只见老板娘把雪白的米粉用滤勺放到沸水里烫开,倒进碗里,浇一勺卤水,上面盖几片卤牛肉、几根牛肚丝,几颗花生拍成粉末,再加上几粒黄豆,上面撒上葱花,五色齐备,赏心悦目,香气扑面而来。那是我第一次到桂林,第一次吃桂林米粉。
项目部紧贴靖江王城墙根。出门左顾,跨过滨江路,就是传说中的漓江了。
老解放桥是1937年建的中山大桥,那时没有钻孔桩,承台用木桩围堰,三合砼掺熟糯米夯筑而成,比混凝土还有韧劲,二尺见围的木桩拔出来根根如新。这里是桂林历代的官道,唐时就在此用结船的方式搭了一座永济浮桥。徐霞客游记有“浮桥贯江而渡”。
新桥址上游搭了一座人行便桥,不远处是伏波山。下游约2公里是象鼻山。桥东几百米是七星岩,桥西的独秀峰耸立在王城中央。解放桥便是漓江两岸山水之中的一道彩虹。
第二天是元旦,项目部没有安排我们上班。早上一起来,工友们直扑桂林的各处景点,虽然没买门票,不进景区,但桂林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大公园,走在桂树成林、花香弥漫的漓江岸边,也是一种享受。
我们的工作是在水上打钢桩,用桁架拼装水上施工平台。桁架是苏式军工梁,十几种序号的万能杆件,长短轻重不一,最重的1号杆件长4米,重75公斤,要两个民工从料场抬到拼装现场。桁架四边的外框杆件加上接头和夹板,有四五层,几乎每个连接点的螺丝孔都会错位,不能直接穿螺丝,要先打入与螺丝孔等大的冲钉,使杆件的孔位收拢对齐。拼支架虽然简单,但每一个步骤都是力气活,没有哪个工友没磕伤碰伤的。
漓江河床底部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几乎每根桩底都会碰到石头,电锤一启动,钢桩就滑到一边去了,不能保证桩位的准确性和垂直度。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施工船上沿着桩位插下竹篙,身上绑着绳索,带着撬棍,顺着竹篙爬到水底把石头撬开。一次撬不动,上来换口气再下去,一个人完成不了,换一个人再来。初春节气,下水的工友冻得浑身发抖、嘴唇乌黑,上来喝几口三花酒,蹦跳几下,又生龙活虎了。
施工平台完成后,接着在上面装一部大型龙门吊。要将几十吨重的桁架横梁,用导链葫芦一点一点拉到20米高的立柱顶上。十几个工友站在横梁上,听信号员统一号令,一齐拉动导链葫芦,随横梁同步上升。眼见不到一米就到达安装位置,横梁上的工友们各就各位,手持扳手大锤、冲钉螺丝,准备连接。就在这时,一台导链葫芦打滑,横梁一端失去平衡,一角急速下坠,倾斜了下来,导致另外三台导链也不同程度地打滑。工友们趴下来紧紧抱住横梁,有个工友没有稳住,从上层桁架空隙处掉在两层钢梁中间,挂在安全带上,像秤砣一样摆来摆去。另一端的四台导链葫芦虽然没有打滑,但也承受着大梁失衡增加的负荷,发出恐怖的咔嚓声响。整个横梁随时有下坠、扭曲,或因链条断裂而倾覆的危险。操作导链的小董在链条下滑的间歇,一手死死抓着起重链条,一手迅速把导轮链条在起重链条上缠了两三道,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控制住了起重链条下滑的趋势。趁这个当口,我们迅速用钢索锁住横梁,更换导链葫芦。一场特大事故就这样消弭于萌芽之中。
春节一过,工地全面展开,民工越来越多。项目部为了便于管理,在已有三家成建制的民工队外,把零散的民工组成了第四支民工队——湖北民工队,交给我负责。我挑选一批在福州修过大桥,熟谙水性,有丰富的水上作业经验的民工,配合两个主墩施工。工地的起重浮吊和一条机驳船,也由我们使用管理。下岗船长小卫成了这条船的船长。
进场之初,正是枯水季节,为了快速启动,工地在河滩上筑了一条施工便道,把漓江拦腰截住,重叠埋了三层泄水管道。开春之后,桃花汛至,江水漫灌,施工便道成了一道水坝。7月间,夏汛如期而至。随着水位不断上升,水坝上下游落差越来越大。东边河沟处水急尤甚。我们在长江边长大,长江水面宽阔,洪水滔滔而来,顺流而东。不看水边的标尺,不知道一天涨了几分几寸。而漓江两岸奇峰秀岭连绵不绝,江如玉带,美则美矣,此时却有不畅之弊。上游山区一下大雨,山洪倾覆而下,流急而泄缓,肉眼可见洪水一寸一寸往上弥漫,才真正体会到“汹涌”二字的含义。明代刘诚有诗云:
雷声起枕上,雨势欲拔屋。
蛟龙一夜争,暴涨弥平陆。
这天夜里,诗中的情景再现了。吃过晚饭,休息了几天的工友们精力旺盛,打牌的打牌,吹牛的吹牛,还有两伙人吆五喝六在喝酒。10点左右,喝酒的舌头开始短了一截,几个手气不好的工友叫着再打两圈扳本。大家正在吵闹,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工棚顶的石棉瓦被一阵旋风“咔嚓”几声掀开了两块,大雨从棚顶倒水一样浇了进来,几个睡着的工友哦嗬一声从床上蹦了起来。我带几个工友在棚顶上折腾了个把小时才修好。换好衣服正准备睡觉,一个值班的工友神色慌张闯进来大叫:“浮吊,浮吊。”我抄了雨衣到江边一看,才过了半天,洪水已暴涨了一米有余,昨天停泊浮吊的东岸,已成急流之所。水坝成了一道弓背,一米多高的水头直击下游的浮吊。浮吊原用四根钢缆拴住,前方两根主缆,侧方两根艄缆,泊在岸边。风助水势,水助风威,昔日温情脉脉的漓江,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头凶狠的猛兽。在洪峰的冲击下,浮吊不时抛到急流中,前后蹬扯,上下颠簸,甩到岸边与岸岩碰撞后,又推回到了水头。四根钢缆不能同时受力,发出阵阵紧绷的弦啸。情况不妙,我马上叫醒小卫,带人发动机驳船,加足马力向浮吊冲去。
以此时的水流和风速,机驳船自身航行尚能勉强,无法驾驭体量大于本身的浮吊,只能先去浮吊下游勉强顶住,以减缓洪峰对浮吊的冲击力。我带着十来个工友,在西岸仓库领了一根百多米粗钢丝绳,葫芦串一样一人一节,从人行便桥小跑过江,穿过已经上水的东江老街,很快把钢丝绳拖到靠近浮吊的岸边,一头在岸上锚固,一头抛绳引索,把钢丝绳拉到浮吊上来。准备把这根钢丝绳对折成两根缆绳,利用浮吊冲击后惯性回弹的时机,收缩钢缆,再用绞盘把浮吊绞到岸边加固。钢缆刚拖上浮吊还没系好,浮吊左侧的一根艄缆在一次猛烈的蹬扯中发出骇人的声音,发生了小股断裂,在第二次蹬扯时突然从中间绷断。钢缆像两根钢鞭,一半弹回岸上,一半打到浮吊上来,浮吊上的工友惊慌失措,有人喊道:“快上船,浮吊快冲跑了。”几个人慌张地跳上了机驳船。
漓江水势从伏波山折转向东,被訾洲滩头阻住水势,在九娘庙处转而西南,水阵直指象鼻山码头。几十条游轮停泊在码头上,樯桅毗接,黑压压一大片。如果这只浮吊脱缰,随洪峰而下,就是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在游轮中爆开,然后随着撞散的游轮一路下行,所到之处,后果不堪设想。情况万分危急,我冲到机驳船上,对他们大叫:“我们都是大江大河里闯过来的人,哪年没见过大水……”喊了几句后,我戛然而止。其实我心里一点底气也没有,若是再断一根缆索,最后两根也将无法受力,肯定会递次而断,谁也无法回天。理性地选择,应该保证工友们安全,马上上船离开。我们默不作声,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剩下的三根缆索,等着浪头的再次击来。小董手持太平斧,站在机驳船与浮吊的缆桩处,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立刻砍断机驳船和浮吊连接的缆绳。小易和小华几个紧紧抓着船舷的扶栏,弓步作势,默默地做着进退两手准备,只等这阵浪头一过,如果再断一根缆绳,就退回船上,断缆离开。轰的一声,一个巨浪正中击来,浮吊往下一沉,船头没入水里,刚才还在岸上喊着加油、小心、注意安全的人,这时全都屏住了呼吸。我耳里已没有了风雨雷声,只有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跳动,越跳越响,越跳越高,仿佛随时要冲出喉咙。
两根主缆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紧绷着发出阵阵的弦啸。洪水和浮吊像两头势均力敌、斗红了眼的水牛,一秒、二秒、三秒……时间静止了五六秒钟,水牛一个松懈,浮吊船头轰的一声从水里昂起了头。船长小卫在驾驶台看得真切,一声长鸣,把马力拉大到极限,排气管轰地冒出一股黑烟。不由分说,工友们半秒没有犹豫,快速跳上了浮吊。四人加固粗缆,其他几人分别把缆桩上两根主缆的缆结松开,放长缆绳,使之与加固的粗缆等长,达到同时受力的状态。工友们配合默契,动作飞快地完成了一轮操作,退到浮吊中间各自扶好,稳住身形,等着下一波浪头的冲击。轰的一声,随着一阵紧绷的弦响,提前受力的一根小钢缆应声而断,浮吊一侧失控,急速向江心飞去。岸上水上一齐惊呼,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如果换上的粗钢缆承受不了这一波的冲击,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将付之流水,不光是那些游轮,就连桂林地标象征的象鼻子恐怕也会殃及。工友们这时即使逃到机驳船上,也来不及与浮吊解绑了。大家双手死死抓住栏杆,停住呼吸,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根粗缆上……电光石火的一瞬,那根钢缆从水底跳出水面,向上抛出一个弧线,又是一声巨响,粗缆像一根皮筋,好像拉细了一圈。就在这时,另一根放长的钢缆受力了。巨大的冲击力把浮吊缆桩拉斜,又是一声巨响,焊接缆桩的浮吊箱体钢板被拉得突起了一大片,浮吊去势不减,继续向江心甩去。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内侧系在岸上的艄缆也是一声闷响,把水泥铸的一米多高的三角岸锚拖出两米开外,被另两块岸锚卡住,甩向江心的浮吊止住了去势。这头斗红了眼、套上了龙头也不肯下场的水牛,坚持了十几秒钟,终于不情愿地被拽了回来,摆进了缓水区。船长再次鸣笛加速,我们像八尊静止的机器人突然被人同时按下了开关,分别冲向歪斜的缆桩前,以最快的速度收紧松弛的缆绳,把浮吊控制在缓水区内。这样不断地几次收紧,浮吊终于被我们重新锚住了。大家这才把心落回腹腔,吁出一口长气。相视环顾,工友们不知不觉中早都扯掉了救生衣和雨衣,还有两人赤着上身。雨水冲刷着身上冷热交替的汗水,江风袭来,格外地爽朗。
山里的洪水来得急,去得也快。过了两天,水位回落,我们冲洗干净施工平台上的污泥杂物,恢复了施工。站在漓江中间,看着阳光下两岸的桂林。前面伏波山,孤峰立岸;右边七星岩,别有洞天;左岸王城之内,一山独秀;下游的象鼻山,那只石象浑然不知它那只豪饮的鼻子,前几天差点就被撞没了。再看这云山雾罩、烟雨迷离的漓江,缓缓流过眼前,多了几分亲切的气息。我盘算,哪天桥建好了,一定要把漓江从头到尾走一遍。
一年后,没等解放桥通车,我又随丁总奔赴新的工地,贵港、柳州、南宁,然后又回到柳州、桂林。广西成了我走不出的第二故乡。
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过去住的工棚那片区域,建起了一座与江南三大名楼齐名的逍遥楼,靖江王城正阳门前,恢复了明清古街东西巷。前不久,我又去了一次桂林,从訾洲公园步行,经七星岩门前,慢慢走过华灯闪烁的解放桥,来逍遥楼下,到东西巷里,吃了二两桂林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