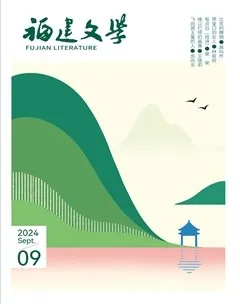风车
2024-12-31孙贵书
那天,经过一片洋葱田,看到路两边的灌溉渠边,各放有一根黑色管道,几个人在忙碌着。正在我疑惑之时,承包这片洋葱田的农场主走了过来。他说,这一片洋葱田准备使用滴灌系统。滴灌是现代化农业的体现,可以根据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需水量自动调整,时间可以精确到秒,数量可以精确到滴,节水、节电,优化改善土壤结构。原来现代化的灌溉技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智能化水平,小时候追逐风车、追逐抽水机等汲水工具的场景,一一浮现在眼前。
1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乡,条条清波荡漾的河流,把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农田分隔成各种图形,河边上一台台随风而转的风车,构成了农村中最美的景色。这景色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总认为这是农村最美的风景。
比风车早的是水车,完全靠人力驱动。汲水量大的水车,得要四个人一起踏。踩水车的人或手扶或趴在一根齐胸高的木杠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用双脚交替踩踏板。踏板俗称木榔头,设计成榔头状,自然是为了方便踩踏。踏水车的时候都是边踏边打号子,让人看起来劲头很足欢快得很,好像踏水车是很快乐的事。那时候有这样的说法,“喝酒最痛苦,踏车最快活。”因为喝酒的人每喝一口酒眉头都得皱一下,而踏水车的人没有一个不高声唱起来的。其实,踏水车的人齐声高歌是在打拍子,打拍子是为了保持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一旦有人走神,稍不注意,跟不上节奏,木榔头就会打脚。轻则淤青肿痛好几天,重者会骨折。反应快的立马抓住面前的横杠身子往上一蹿,像个不会玩单杠的人把自己挂在单杠上一样,两只脚尽力往上提,怪异得很,大家都会笑他“吊田鸡”。农村孩子都有体验,抓起青蛙的两只前腿拎起来,两只后腿会努力往上,狼狈且怪异。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事。一个年轻的姑娘,一次在踩水车时,不知怎的没跟上趟,一下子“吊田鸡”了,裤腿扯在了木榔头上,只听得“嘶”的一声,外裤和内裤一起被扯了下来,春光乍泄,羞得姑娘提起裤子狂奔回家,不吃不喝躺了三天才起床,很久都不愿意出门。更不幸的是,姑娘的对象听说了这件事,立马悔了亲事。姑娘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在一天夜里用一根绳子自尽了。
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其实踏水车可比这三样苦多了。因为农时不等人,庄稼不能缺水,而水车的提水效率又很低,尤其在插秧时节,踏水车得白天黑夜连轴转,歇人不歇车,直到水量够了为止。而农忙时除了要踏水车还有其他活要干,一旦遇到干旱天气,踏水车的人会累趴下,甚至是留下病根。
2
许是受了风力的启发,有人对水车进行改造,借助风力来驱动水车,于是就有了风车。风车比水车先进多了,完全解放了人力。当年做木匠的父亲,是制作和维修风车的能手,凭这手艺在四里八乡很受尊重。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在家加工风车的零部件。长长的、正方形、一头大一头小的叫拨,相当于现在齿轮的轮齿;薄薄的、长方形、中间有个长方形小洞的叫柫板,是引水用的;还有“乌端子”“槽齿”“水轴”等几十样零件,一个个精美得很,看得我眼花缭乱。父亲边制作边娓娓道来,我看得兴致勃勃听得津津有味,心里想,长大了我也学做风车,那多有成就感呀。后来,铁制风车走进了水乡农村,那时候我们的工业极不发达,某些构件来自国外,于是人们就把这家伙叫作洋车。洋车黑色锃亮,苗条轻盈,比起木制的风车,不但结构简单、提水效率高,还很少出故障,很受农民的欢迎。失落的只有父亲,因为他的手艺无用武之地了。而年幼的我,刚刚激发起来的理想就这么轻易地被击碎。当然,童年理想的破灭只在一瞬间,在乡下孩子的眼里,风车就是一个个大玩具,有得玩就是王道。
一次,我们几个差不多同龄的孩子,聚集到了“洋车垛子”上。不用汲水的风车,像一个熟睡中的孩子,静静地安卧在小河旁。一路打闹而来的我们,惊醒了沉睡中的风车。调皮的二甩子一到风车前,就卸掉篷布的风叶,“咳”的一声,用手带动了风叶,风车慢悠悠地开始转动,跟在后边的鼻涕虎又加了一把劲,带动另一片风叶。你来我往,风车旋转的惯性上来了,越转越快。“哈哈!水马上要上来啦!”大家一起欢呼起来。突然,传来“哎呀,没得命哪哇”的惨叫,大家回头一看,小平右手的食指不知怎么卡进了正在转动着的齿轮里,鲜血直流。同伴们吓得不知所措,二甩子带头向不远处狂奔,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正在劳动的家长们。小平的父亲“麻小伙,麻小伙”地叫骂着,背上小平就往大队赤脚医生那里跑。结果,小平右手食指的第一节关节永远没有了。长大后,小平很想和两个哥哥一样去当兵,可是失去的右手食指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当兵梦。
小平失去了手指头,没有当成兵,已经够惨了。比这更惨的,有人玩风车竟然摔断了腿。邻村一个八九岁的小孩,人称“戴大胆”,长得精瘦精瘦,一贯天不怕地不怕。一次,几个伙伴一起去玩风车,他灵活地爬上已经扯上篷布的风车,一只手抱着风叶杆,一只手抓着绳子。慢慢地,起风了,微风扯开篷布,风车慢悠悠地转了起来。他高兴地唱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歌曲。渐渐地,风越来越大,风车的转速加快,耳边只听“呼呼”的风声。“戴大胆”此时也感觉到了害怕,呼喊着:“救我!快救我!”可是同伙都是和他差不多大的小孩,他们怎么懂得去控制已正常运转的风车呢。呼救无果,“戴大胆”眼睛一闭,愣是从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摔断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
3
再好再灵活的风车,都是借助风力的驱动,它才能运转自如。在酷暑难耐只闻知了高叫不见树枝动摇半分的天气,风车纯属聋子的耳朵——摆设。风车是“固定资产”,总是趴在那里不动弹,一旦在哪里“安家落户”,之后就很难再挪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灌溉好了,其他地块就是旱得裂了口子也只能爱莫能助,干瞪眼。
“黄秧落地,老少低头”,刚刚栽在田里的秧苗,可经不住缺水和太阳的炙烤,广大农民做梦都想,如果有一种风车可以在没有风的天气也能汲水灌溉,那该多好呀。如果有能“四处游走”、听人使唤的风车就更好了,哪里的田缺水,风车就移动到哪里。终于,抽水机走进了水乡农村,圆了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也让我们这些童稚未脱的农村孩子多了一个“冒险”场所。
我们当时称抽水机为打水机。打水机船一般用2.5吨到3吨的水泥船做主体,水泵安装在船尾的夹舱里,中舱里固定着柴油机,为水泵提供动力。柴油机离水泵两三米的距离,一根宽宽的皮带把两者连接起来。需要灌溉了,把机船撑到灌溉渠的机口处,发动柴油机,河水就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汩汩地涌进灌溉渠里,流往田间地头。
特别喜爱玩水的我们,每当看到有人撑着船尾竖立着抽水机管的打水机船时,就知道又要给稻田打水了。光着屁股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打水机口,争先恐后地帮机工把抽水机管搁在机口上。带好船桩,机工就用摇把启动柴油机。随着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我们先把耳朵贴在抽水管上,听着水泵叶轮搅动河水的“嗡嗡”声;接着又转脸从抽水管口往里看,翻腾着的河水像粥锅里煮开的米汤一样,泛着水泡向上奔来;就在河水即将要到机口的时候,我们双手抓着水管的法兰盘,试图用肚皮去堵出水管口。伴随着“哗啦哗啦”的响声,翻滚着的水流从管口喷涌而出。光着屁股的我们欢叫着,或在水里嬉闹,或迈动着小腿,沿着灌溉渠两边的堤岸,追逐着奔涌向前的河水。
一个夏天的下午,光着上身穿着裤头的我和雨哥哥,盯上了生产队的打水机船。负责打水的包师傅,将柴油机发动后,就扛上铁锹,沿着灌溉渠,去开挖通向各个田垄的放水口。我和雨哥哥瞅准机会,像猴子一样爬上机船。看着从机器肚子里流出来的热水,看着“笃笃,笃笃”不停地喷出蓝烟的消声器,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将水浇在快速转动着的皮带上,那水花飘起来,哈哈……我拿起挂在舱板上的一只小水勺,从河里舀起一勺水,朝“咔嗒,咔嗒”转动着的皮带泼去。就在水泼到皮带上的一瞬间,转动着的皮带脱离了皮带轮,翻滚着掉了下来。突然失去负载的柴油机成了脱缰的野马,转速飙升,滚滚浓烟从消声器里喷出来,“突突突”的声音大得怕人。我吓得赶紧扔掉水勺,逃到机舱的前面,雨哥哥慌乱地躲到了机舱的后侧。听到异常响声的包师傅,飞快地跑进机舱,采取措施控制住了“飞车”的柴油机。雨哥哥的肚子上溅满了从机器里喷出来的润滑油,像个大癞蛤蟆,躲在机舱前面的我吓得哭出声来。
事后,大人们都为我俩庆幸,幸亏包师傅处置及时,脱缰的柴油机未能继续疯狂。否则飞转的曲轴会捣坏机身,飞出的碎片一旦砸到我们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柴油机“飞车惊魂”事件,使得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去亲近机器了。退伍回乡后,有了自己的承包田,分到远离村庄一公里外的田垄,几户人家筹资共同置办了柴油机、水泵,我才不得不与柴油机接触。每次打水,光用那几斤重的摇把启动机器就得费好大的劲,一次不成功再来一次,每一次都令瘦弱的我膀子酸痛。有时候,就是费上九牛二虎之力精疲力竭,它也是“呆若木鸡”,不得不去请精通机械的老师傅来“会诊”。
4
那时候,经常听到用机器的人闹出的一些笑话:有启动机器时被摇把打掉门牙的,有因为没能及时加机油,烧坏了机器轴瓦的,有田里急着要上水,大力士累趴下了,机器就是启动不了的……特别是抗洪排涝的关键时刻,面对那不买账、不架势的机器,更是让分管排涝的领导急得团团转。
1991年夏,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涝,水乡兴化成了一片汪洋。“天大地大,抗洪最大”,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紧急动员劳力封堵好各个联圩的口子后,乡里紧急调拨各村的抽水机,统一集中到各个圩口,不分昼夜地向外河排水。负责大农业的孙书记理所当然成为排涝抢险第一负责人。他和水利站站长一起站在紧贴水面飞速向前的快艇上,对每一处坝头、闸站进行巡视。所到之处轰隆声震耳欲聋,沿岸一排排长长的抽水机管,争先恐后地往外河喷涌着水柱,蔚为壮观。
当快艇开到西大圩透界河的口子时,孙书记远远望见有一台抽水机的机管不冒水。“怎么回事,那台机器为什么不排水?”还未等快艇停靠稳,孙书记就一步跨上了联圩,到了那台机器前。“孙书记,油泵坏了,马上就好!”几个正在忙着维修柴油机的机工说道。
“笃笃笃!”沉默了不久的柴油机响了起来,可是水管刚刚出水,又停了下来。几个机工拆开一看,刚换上的油泵又坏了。连续换了三只,都是刚出水机器就熄火。这时,一个在扬州农机局接受过培训的老机工正巧从联圩上经过,他一眼便看出了柴油机的毛病所在:“换个油泵总成试试。”听到指令的几个机工,又是一阵忙碌。看着终于正常出水的抽水机,孙书记一巴掌结实地印在一个个子矮矮的30多岁的男子后脑勺上:“饭桶!做了十几年机工了,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干什么吃的?!”这个笑话一直是这个机工的心病,几十年后的今天,谁提起这事他都会给谁脸色。
5
随着农村电气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条条供电线路延伸到了田间地头。“这下好了,我们能用电动机打水啦!”广大农民欢呼雀跃。闸刀一推,电动机轻盈地“嗡”一声,奔涌的河水就哗啦啦地被抽了上来。
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从中央到地方,保证水稻旱涝保收的“硬着子”陆续出台。供电企业闻风而动,查勘、预算、备料、放样、立杆、架线,一根根电杆在卷扬机的欢叫声中稳稳当当地立在了预定位置,一路向前,直扑建在河边的电灌站、排涝站。傍河而建、灰墙红瓦的站房成了水乡田野里的又一独特风景。
骄阳似火,晴空万里,邻村200多亩的家庭农场,碧绿的秧田已经返青,长势趋旺。管水的老邹走在田间3米多宽的硬质化水泥路上,时时俯下身子查看秧田里的肥水情况。“要打水了。”老邹自语着走到位于农场中间靠近河边的电灌站前,掏出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电灌站的门,按下按钮,电机“嗡”的一声,墙上伸出的出水管顷刻间冲出一柱水流,旋转着的水流奔腾着流往四通八达的硬质水渠。老邹从塘角拿出一根前端带钩的钢筋,沿着水渠,将插在各个田垄进水口的闸板一一拎起,水渠里的水争先恐后地流进秧田,急急地环抱住健壮嫩绿的秧苗。一个下午的工夫,老邹就完成了200多亩秧田的上水任务。关掉电机,放好闸板,回到家,不一会儿便悠闲地坐在桌前喝起了老酒。
老婆看他像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喝酒,嚷嚷开了:“早点吃点饭去看水呀,哪有闲情喝酒?”
“水已经打好啦!你以为我还要像以前那样开夜工呀?!”
“这么快就打好水啦?哈哈,我以为你还要去开夜工呢!”
“放到从前,十几台抽水机一起抽水都达不到这样的水流量,我现在可以以一当十呢。”老邹扬扬得意,“吱”的一声又干了一杯。
6
进入21世纪初的又一次洪水,让处于“锅底洼”的水乡人民痛下决心:“大灾后反思,反思后大干。”从这一年开始,水乡兴化通过灾后重建,疏浚河道、加修圩堤、新建圩口闸与排涝站,多个项目扎实推进,稳妥实施,全面提升排涝能力。
“行得春风,必有夏雨。”在春天不住刮风的时候,有经验的老人就会说,看来今年又要发大水了。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夏季,一贯脾气平和的老天爷,突然发怒,大雨没日没夜地往下倒。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和监测着河水动向的水务部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判断极有可能出现稍逊于1991年的洪水,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放闸板,关闭闸门,所有联圩口全部闭合后,做惯了“闲老倌”的排涝站,即刻发挥出它的威力。
请求供电所合上高压熔丝后,400KVA的变压器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站房内的配电柜上指示灯闪烁,表示电压、线路状态正常。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有关领导的指令。
“开机!”电话里传来党委、政府的命令,在现场负责排涝工作的副镇长让人启动按钮,一字排开卧在地上的三台“巨无霸”电动机,依次旋转起来,发出一种轻盈的低鸣。瞬时,三个并排的出水管,奔涌出滔滔水流,如万马奔腾,似狂飙怒涌。
仅半天的时间,还在为河坎上的黄豆浸在水里焦虑的农民们,发现黄豆已慢慢探出了娇嫩的头。围观的群众看着滚滚涌入外河的河水,发出由衷的感叹:“这下好了,再大的洪水也不用我们操心啦!”
7
科技的发展速度,快到令我们有时不能适应,直呼自己“老土”。腰包已经鼓起来的“蟹老板”,现在用电动机打水,“懒”得连按钮都不用碰,在手机上点一点,电动机就能听从指令,或启动或停止,有的干脆根据蟹塘里的溶氧高低,设置成自动开启或关闭电动机与增氧机,再也不用为溶氧的高低操心。而我看到的滴灌系统更是令人稀奇赞叹。
人有时候矛盾到连自己都不能理解,比如我吧,明明知道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尤其是提水灌溉技术的更新迭代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效益,却偏偏留恋过去,尤其留恋童年记忆中河边那一座座随风转动的风车,固执地认为那是农村里最美的风景。
但我知道,那样的风景离我太遥远了,遥远到只能埋藏在自己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