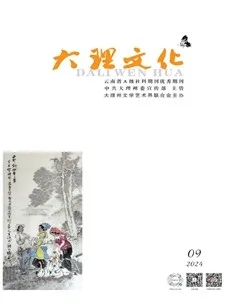风土记
2024-12-31梁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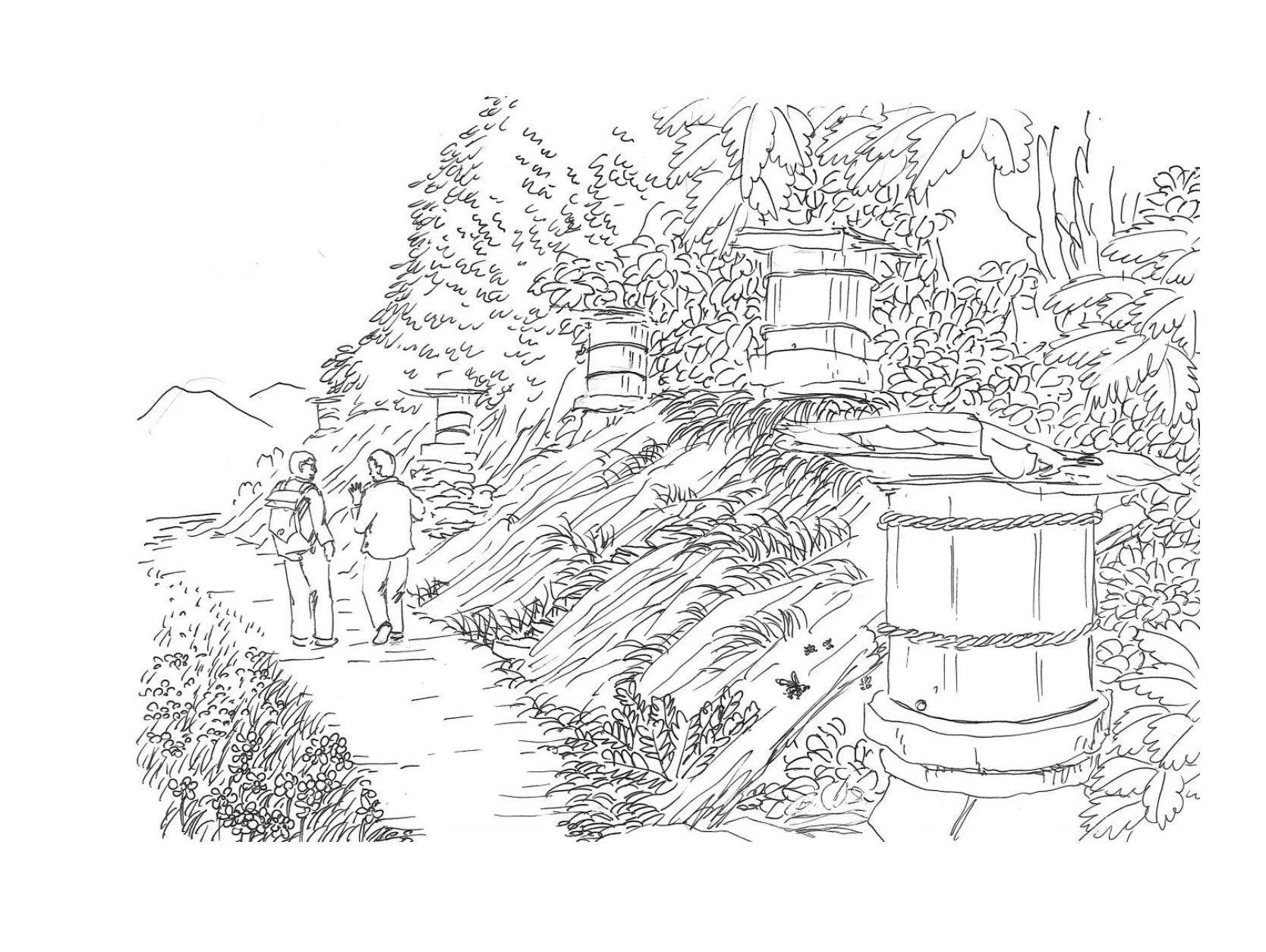
药" 草
那是盛夏的一个傍晚,我和小伙伴罗子在村头的晃桥河里游泳,他的父亲在饮牛,母亲在洗衣物。我忽然听到从河对岸传来“咚咚”声,上岸一看,叶老草医向我们走过来,一手捧着一个碗大的小鼓,一手拿着一截充当鼓槌的鸡腿骨。老人胡子花白,像电影里的红军那样打着绑腿穿着草鞋。罗子的父亲陈海林赶紧迎上去,将吸得正欢的水烟筒递给老人,罗子母亲张秀丽也停下手中的活计跟他打招呼。老人一边将水烟筒吸得咕噜咕噜响,一边像孩子看到陌生人一样仔细地端详着罗子父母的脸。他忽然问海林:“你是不是经常头痛?”海林忙不迭点头。老人随手一指一丛鱼腥草说:“连根带叶掐一把来!”罗子手快,转眼就把鱼腥草捧到老草医手里。
老人把烟筒往身边的大青树粗壮的躯干一靠,从他肩挂的那个看不出颜色的布袋里掏出一个大木碗,用马蹄般的乌黑的大手几下就把鱼腥草揉搓成泥,到河里舀了点水进去端过来,又从布袋里摸索出一张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的草纸,点燃放进碗里,顿时,奇香扑鼻,他要海林面向他手端的碗,并吩咐:“用鼻子使力吸。”海林照办了。老人嘴里念念有声,五六分钟后,海林满头大汗,哇地吐出一口黑血。老草医用手示意我们看吐出的黑血:天哪,里面竟然蠕动着四五条大大小小的蚂蟥。这时,他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一低头,从鼻孔里先后爬出了两条小蚂蟥。
我和罗子站在一旁目瞪口呆,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罗子的父母先后跪倒在老人脚跟前以示敬谢,我们才听到水声、风声和鸟声。而我看到,叶老草医嘴角溢出的笑容,流露出一种浓浓的成就感、获得感。
后来我长大了,再没有看到游走在村村寨寨击鼓行医的叶老草医的身影,但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还能记起:“识得半边莲,可以伴蛇眠。”“半边莲”的花朵像莲花,却只有半边,另一半像被人给生生剪掉了,它在田埂、河边随处可见,老人这样说,足见其艺高胆大。
在春夏,无论是在平坝还是山野,是草木生长最旺盛的时季。如果用一名称职的草医的眼光打量,遍地都是药草或者说都是宝贝:沿着地面爬行的酸浆草、黄花草、铁线草,长身秀挺的白花草、锁眼草,到处草木芬芳、花事不断:马鞭稍草、白花草、三棱子草、狗尾巴草、苦蒿、去炎多棵、癞蛤蟆棵、苦马菜、老母猪棵、羊咩咩树、金银花、打碗碗花,七颜八色,大的比海碗还大,小的如扣如米……它们或朴实无华,或妖娆多姿,或一枝独秀,或众草成片,散发着属于自己的甜的香的辣的苦的腥的臭的膻的麻的气息,让我想起它们与众生安康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不禁对这些花花草草充满深深的敬惜和感恩。
有一年,我到一个山区乡采访,工作完成时间尚早,就跟一个姓毕的草医去采药。在翻山越岭的路上,他指着形形色色的草木如数家珍:金薄荷,全草人药,能解毒消肿、活血散瘀,主治风湿性关节炎、菌痢;大藤铃儿草,全株入药,止痛、降压、止血,用于治疗各种疼痛、咳嗽、高血压、血崩、内伤出血、跌打损伤;猫胡子花:全株药用,用于下气、咽喉疼痛、扁桃体炎、牙痛,煎水洗痔,外敷治风湿痹痛、痈疖疮毒、毒蛇咬伤、跌打损伤;地米花,全草或种子用于高血压、痢疾、小儿乳积、崩漏、止血、清热明目、消积,根烧灰治红白痢。路经一个三七种植基地,他告诉我这叫“万草坡”,以前,在这方圆十里的地方,他就能够找全治疗百病的药草。眼下,这片呈扇形的坡地均被黑色的遮阳网所覆盖,只能从“万草坡”这一名字,猜想出早年花木深沉、百草摇曳、药香弥漫的场景。我看到他动手采药时,有着蜜蜂采蜜一样的专注。
在群山深处的石则坡村,一天黄昏,我跟着一众村人,到了离村子三公里外的地方。在众人的望眼中,乱云飞渡,林涛如海,天地浩茫。老毕摩攀爬上村头最高的山峰,那峭拔的山峰顶着最后一抹夕照,平常是云朵和风雨的练兵场,也是老鹰起飞的跑道。山风正烈,77岁的人,竟然还有猿猴一样的身手,但他站在上边时,身子小成一点鸟影,夜色像他身披的蓑衣,已经浓得化不开。有人告诉我,老毕摩不仅仅会做法事,还是一位本领高强的草医。每过十年,他才上这座山峰采一次药草。这时夜雾升腾,我相信我听到天神叹息的声音。我站在山脚下,站在村里的男男女女中间,站在飞舞的蠓虫之间,仰望山峰上那团比一朵油菜花大不了多少的火。和众人一样,我手中端着满满一大碗酒,心中满满地怀着大山一样深沉的虔诚。
我到红河岸边的木多村采风,正赶上一家人办丧事大宴宾朋,青青的松毛上摆满了菜肴。我到人情挂账处交了100元,舒坦地坐在青松毛上。人们谈笑风生,坐在我对面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汉子却一直不说话,只顾低头吃喝。有人介绍,他叫李雷,读过很多书,是一位有名的草医,还是一位养蜂能手,有一肚子的故事,我便端了酒走上前坐在他身边。两碗酒下去,我们便很快熟络了。李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黑么村的老人石光,靠养羊,家底一年年厚实起来,于是经常扔下羊群,骑摩托到县城的超市购物、吃香喝辣,但好景不长,一天生病到医院一检查,竟是绝症。老石到处求医无效,最后找到木多村,李雷告诉他:羊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老石连连点头。羊吃的苦蒿、麻叶、酸果、甘草等,他生吞活吃,羊喜爱去粪坑边啃硝,他也照样跟着啃。这样“草食”半年,人们从他身边走过,再也闻不到一丝“人气”,闻到的是扑鼻的腥臊。但奇迹发生了,快20年过去,老石一直还活着。
说起自己的老本行养蜂,李雷双眼闪光,说话时八字胡一飞一飞的,他用吟诵诗歌一样的腔调告诉我:哀牢山比天大,但十坡八洼的花草,足够我养5桶蜂了。每桶蜂只有一个蜂王。你不要多操心,蜜蜂都是自己把自己养大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开,蜜蜂的一生一世,就像好花开不长;花开花落过一年,蜜蜂就活过三代五代了。人么,是活得长些,但活不过一棵树,他自己养的都是平常蜂,采的都是土生土长的百花,不值一提,而村头祭师养的蜂就神奇了,据说能采霜花、雪花、浪花,甚至火花。这样的蜂酿的蜜,祭师“神药两解”,不仅包治百病,还能让人消融爱恨情仇。他结婚那年,他阿爸送他5桶蜂,现在还这么多。蜂蜜,一年割一回两回,卖3桶蜂的蜜贴补家用和打酒,另外两桶蜂的蜜呢,一桶呢,会被老熊偷吃,老熊吃苦竹更贪蜂蜜,最后一桶呢,留着自己吃,蜂蜡呢,卖给山外人拿去寺庙供奉给佛,用蜂蜡做成的烛,能燃起世界上最甜最香的火……
在李雷的故事里,万物有灵,万物都有着人的灵魂。听着他的讲述,我的眼前一片清明,心海上宛若有一种暗香在澎湃,口腔里似含着一团蜜。
在药草中沉浸久了,不断听闻有关药草的传奇,萦绕在心,让我久久不能释怀。30岁以前,我一直在泥水里劳作,有意无意地嗅遍了各种花草的气味:白花草散溢的是嫩黄瓜气,酸浆草的气息有一股淡淡的酒香,而狗牙花是奶水的味道,马鞭梢有着男人的汗味,如果不小心坐在去炎多棵旁,它会用公羊的腥骚味逼你走开,至于鱼腥草的气味,就更不用说了,我想,当初简直是有人手里拿着一条鱼为它命名的,要多贴切就有多贴切。俗名是事物的乳名与小名,它既体现了花草自身的原始形象或某种特性,又流露出一种民众对故土万物的亲昵之意与随意的心理。身处其间,我默想着荷尔德林的《归乡——致亲人》的几句诗:“一切都似曾相识,甚至擦肩而过的问候,也充满情谊,每一张笑靥都充满亲缘。”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也在寻找一种药草,一种能为我平庸的书写注入夺目神采的药草?
舍多祭师
这些年,我把太多的大好岁月用在路上。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远离城市的乡野,那些地气旺盛、温暖、光亮、芬芳的村落,我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是红河哈尼梯田这样的山水间。
云生水起。在那里,祖坟依偎着村庄。站在自家屋檐下,红河哈尼人可以看到这里的一切生命,以及他们最终的归宿。他们与这方山水之间恒定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微妙的天然联系。在这里,我仿佛听到百年前一位农民向费孝通先生发出的感慨:“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看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
数年前,有媒体记者在采访了红河梯田后写道:那连绵起伏的山岗,站着坐着都是一个模样;改变它容颜的力量,只有季节的雪雨风霜。在很多大山里,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四个维度同构的文化景观,既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典范。外界的冲击越来越大,大山的子民仍年复一年因循节令:他们农历二月撒秧、三月底栽秧、九月收割、十月铲埂草……他们也固执地将粪草堆放在沟渠旁,任流水将天然肥料带入梯田。
早春的一天,我走进以前去过多次的哀牢山深处的一个村子——舍多。昔日热闹的村落连晚上也是空荡荡的。一问,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山打工去了,只留下年老的男女在耕种梯田。
我在一位年老的祭师家留宿。我遇到了我一生中第一个这样的夜晚。夕阳西下,到了古书中写到的夜未央,房前屋后桃红如火,杏花如雪,我被一个白发齐胸的老者迎进家。数杯烈酒后,老人亮出身份,说他是舍多村唯一的祭师,祖传多少代记不清了,识文断字,还教过几年书。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哀牢山,不会超过一百人。”
夜静到能听到彼此的心跳,老人坐不住了,他在火塘里点燃火把,带我巡视村庄。抬头满天星斗,低头一地水银,火光下闭门歇户。我们回屋接着喝酒。孤独如酒意,越来越浓。老人长叹一声,随后像是在自言自语:“大年一过,春天一来,他们都出去打工了。梯田之上,山和水都在,神灵和白鹇鸟也还在头顶,可有手有脚的人都出山去了,连二月初二祭龙都没有多少人了。熟路渐成陌路。真想时时把自己灌醉;祭龙的日子,只能找出村出纳员留下的户口本,依照上面的姓名扎一些草人,用桃木剑和咒语指挥他们,在月光下跳舞……”老人说着找出他的法具——一把锄把长的木剑,他说这是用有百年树龄的桃树削成的。他含了一口酒,喷洒在木剑上,说:“将就着给你表演一下吧。”他又从屋子一角抱出几个有模有样的草人,草人都没有穿衣裳,但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性别:男人一律长手长脚,生硬如铁,女人一律丰乳大臀,温软如水,像见到他们的真身一样,我似闻到浓浓的泥腥味、汗味、酒味、奶水味。在他手中,桃木剑持重如国之重器,在虚空中舞动,像是一种隐性的书写,他吐出的一段内容,如泣如诉短语长歌,如滔滔的天问——据说都是礼赞和祈祷山水神灵护佑苍生的语言。
草人们舞之蹈之,忘乎所以,朦胧中,有一个男人来夺我的酒碗,有一个女人把她的长发打在我脸上,我跟着他们跳将起来。不知不觉间,第一缕晨光入室,火塘渐暗,似乎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祭师突然停下,时间定格。祭师淡然地表达着:他们会回来的,回家来耕种自己的梯田,回家来成亲,盖大房子或过年,对了,还有送葬,而有的就是几根枯骨,或一件两件饰物还乡,也会像雨水终将回到泥土。毕竟,梯田才是自己的大地,梯田之上,才有自己的天空。祭师说完这句话,捧着酒碗一言不发。
第二天,天刚亮,我向他辞别,他目送我走上露水打湿的田埂。惠风和畅,粉黛黄绿,看到梯田顶上丛林中那些干干净净的鸟儿,我仿佛从梦境中走出,回到花与鸟禽的人间……
“由于水稻生产效益较低,人们转种经济作物和经济林,如甘蔗、茶叶、神明果、草果、印楝、膏桐、芭蕉芋、橡胶、棕榈等,减少了水梯田,蚕食了生态林。梯田种植辛劳还低酬,哈尼年轻一代拒绝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加入各地农民的外出打工大军。如今45岁以下的人很少肯种田了,哈尼梯田日渐乏人耕种,水浸苗长延续1200多年从未断绝的生产线有终止的危险,这也是当下各地古代梯田共同遇到的严重问题。”著名作家廖奔先生曾到过红河哈尼梯田采风,他在《梯田中国》一文中这样描述。
有时,我们会发现,“人,诗意地安居”这句话,与其说出自一位伟大的诗人、艰涩的哲人,不如说出自一位逆来顺受的人。
钟" 声
在滇南晃桥河沿岸方圆几十里的村落,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都用钟声来向社员们发布出工、收工和开会的号令,在树枝上挂一块锈迹斑斑的犁铧,要不就是挂一个拖拉机的破齿轮当钟敲,用钟声指挥、调度着社员。晃桥河两岸村子稠密,村与村之间最近的只隔着几垄田块或是一溜草堆要不就是麦垛,炊烟、饭菜香和鸡鸣狗吠声交织重合。大多数村子开工、收工的钟声总在前后10分钟开始和结束,这些形状、质地不同的破铜烂铁发出的声音,没有人会听混。钟声有的尖锐火爆,像泼妇在骂街;有的高亢深长,像一头养足精气的骡子对天嘶鸣;有的深沉持重,像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在说话;而有的急促紧迫,像喊人去救火,有的拖泥带水,像一个人在泡透的池塘里移动步子。好像只有一个村坚持吹铁皮哨子发号。这个村虽离我们村不远,那哨声却飘忽、松散,还不如我们脚边草丛里的蟋蟀“唧唧唧唧”的叫声明晰。
十村八寨的钟声响起时,整个晃桥河谷就像在微微晃荡,人们都像被装进一个大鼓里。不用说,村村寨寨的钟都是队长敲响的。我们村也敲钟,钟是一个拖拉机的破齿轮,它发出的声音清亮明快,像磨了一夜的刀子,再疲累的人一听到,就像被浑身一激,会猛地打起精神。这盘破齿轮用牛筋系着,挂在离牛滚塘几十米外的一棵大青树上一根大人手臂粗的枝条上。有一回,我看到一只肥大的耗子在打那条比拇指还粗的牛筋的主意,但它尖利的牙齿一扎进去,就像咬到一块炭火一样赶紧跳开。后来我才听说,当初揉搓牛筋时,村里曾向外村一个老草医要了一包叫“鬼见怕”的草药来处理过,据说,别说耗子,就连猫,吃下“鬼见怕”,也会要它的小命。
听村里的老人说,他们还是孩子时,这棵树就有现在这样大了,它有牛腰一样粗,它的枝枝叶叶投下的阴影,能严严实实地盖住一个篮球场。人们得退到远离河边的田地里,把头仰得和肩一样平才能看到它的尖梢。我到十几里外的龙潭坡上放马,不经意地俯视了我们小村一眼,发现这棵大青树像一杆绿色的大旗,高高地飘在蜂巢似的房舍前。望久了,感到我们小村在跟随着它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我赶紧闭上眼睛。
日子一天天在钟声中走远又走近。让人惊奇的是,栖息在这棵近30米高的大青树上的数十只鸟雀,当晨钟敲响时,也一起叽叽喳喳地欢叫起来,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队长在说什么。用村里最有文化的张会计的话说,住在这棵树上的鸟雀,很懂得自律,从不会像住在别的树上的同类一样,把粪拉在人的头上身上。后来我观察到根本不是这回事,是这棵树的枝叶太过繁茂,把鸟雀拉下的粪给截住了。每天黄昏,晚钟响起,这些长翅膀的生灵们会从田野三五成群,紧随人的身影飞回村,栖息在树上。
我们这些孩子,只要没有天大的事,每个月的初一,都会不约而同爬上树,看何有顺、张红花夫妇的两口棺材,被四个男人抬着,行走在村里房舍之间的宽街窄巷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不羡慕何有顺、张红花夫妇,20岁结婚,30岁不满,生育6个孩子,清一色的男孩子,一个个虎头虎脑,一个个聪明伶俐。也许是年轻时透支了身体气力,反正到了60岁,何有顺、张红花老两口便体弱气衰,好在6个儿子都已经成人。树大分枝,人大分家,村上逐年划批地基,弟兄6人的家安在村里各处。老两口先是跟老六吃住在一起,由另外5兄弟均匀付他家一些钱粮,但老六夫妻为人吝啬,老两口吃穿如叫花子。5个哥哥一商量,决定轮流供养,每月去一家,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周而复始。在老六家时,老两口早就对其将兄弟们一起出资为他们打制的一大一小两口棺材,用去装粮食或其他杂物而心怀不满,等到轮到去老五家吃住时,就请人将两口棺材连着铺盖碗筷一起送去。村人都行注目礼。老五夫妻心肠好,却家贫如洗,连张床都没有给老人睡的,老两口只好把被褥放进棺材,将就着睡。到老三家时,老两口已经不习惯在床上睡了,三儿子家只好请人来将他们的棺材弄回家。再以后,老两口到哪个儿子家,就请人把棺材抬到那家。几年下来,村人见怪不怪,见到何家搬动棺材也视而不见。只有一个云游到此的疯汉,据说这人当年写诗走火入魔精神失常,他指着棺材大叫:“终要埋在土里的家,不该在天空下露面,不能啊不能。”没有人理他。疯汉又继续大叫:“每个人的命,都是一场大雪,最好多想着躲开阳光。”还是没人理他。他再喊:“光天化日下的棺材,以后埋藏了,坟头无法长出野草。”这回,他被何家老三踢跑了。
一次,乡计生办一位工作人员到村里检查工作,见到此等情形,目瞪口呆,随后用随身带的相机拍了又拍,几天后,老队长到大队部开会,大队支书披头盖脑丢给他一份省报,村长看到,何家抬棺材的场面占了报纸巴掌大一片。图片的标题是:多生儿子未必是福,老两口棺材随身流动。老队长为计生工作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捅娄子影响村子名声而恼火。几天后,县民政局又有人找上村长家门,要老队长动员何家把棺材处理了,县上对县城附近的村寨废止土葬、推行火葬的政策就要出台。每个月光天化日之下,何家老两口的棺材在村里走动一次的仪式就此告终,只有村人知道,棺材还在被来回搬运,趁着夜色。
后来,我们的村土地承包到户,就不用敲钟派活儿了。村里要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或是收提留款,催交公粮,村里有人家要办红白喜事请帮忙的人等,村长就打开刚接通的电喇叭。刚开始那些天,没有钟声的村子,日子无头无尾,村人变得六神无主,很多大人都睡到太阳照屁股才起床。我们这些孩子,以前每天黎明,几乎都跟着大人起床上学,没有钟声,经常迟到。村子尽管鸡鸣狗吠声似乎比以前变大了,但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似的。
这年仲夏,我的好伙伴宝贵的哥哥从部队回村探亲。宝贵的哥哥当兵不久,就寄来两枚红五星,宝贵一枚,我一枚。宝贵的哥哥已经当了6年兵,多次被评为标兵,听人说有提干的希望。回来的当天晚上,亲朋好友都聚在他家喝酒,我也厚着脸皮到他家蹭饭。人们猜拳行令间,忽然,他竖起耳朵:“你们听,这么晚了,还敲钟。难道村里要开会?几年不听,这钟声怪好听的。”喧闹的屋子里一下死静下来,大人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竖起耳朵。
有人对宝贵的哥哥说:“老队长去年死了,村里早就不兴敲钟了。”灯光下,宝贵的哥哥张大嘴巴。
到底是当兵的人,宝贵的哥哥放下手中的酒碗,拍了拍耳朵:“估计是我幻听。”说完哈哈大笑,但没有人跟着他笑。
事实上,不光宝贵的哥哥,村里用上电喇叭很长一段时日,仍有人不时会听到钟声,有时是在清晨,有时是在黄昏,总之是在往常敲钟的时刻。我也曾不由自主地在各个时段侧耳倾听,但往往除了风吹草动声、流水哗哗声和鸟雀发出的不同啼鸣,什么也没听到。
这晚宝贵的哥哥竟又听到了,我吓了一跳。
我向宝贵使了个眼色,我们踏着一地如水的月光来到晃桥河边的“敲钟树”旁,这里空无一人,在深重的树影下,那盘悬挂着的破齿轮,只能模糊看到一个圆圈,河风吹来,许多树都在摇晃,它却一动不动。在夜里,晃桥河除了没有阳光,其他什么光都有,星光、月光,萤火虫的光,癞蛤蟆皮上的绿光,一种村里人谁也叫不出名字的怪鸟眼中的青光,还有地平线上的地光,它呈蛋黄色,一亮一条线,十几公里长,每十几秒亮一次;而下过雨,天又骤晴的夜里,不远处,武姓人家那一堆一堆被风雨削平的老坟地,就会有磷火闪跳,(村人叫它“鬼火”),流星也常见,拖着长长的尾巴落在离人或远或近的田里,每次三颗五颗,大多是单数,时有猫头鹰用爪子紧攥着吱吱惨叫的耗子从低空飞过,晃桥河两岸的杂木树间,蝙蝠像黑色的雪片在纷飞,翅膀扇起的气流,有着弓的颤响,无法听清它的频率……这些都是我们眼里寻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悻悻而回。
牛头记
谷子在田里被晒干晾透,被赤膊露臂的男人,担到村中心的大晒场上,码成三层楼高的谷垛,这时,村里拉开了播种冬小麦的序幕。播种,是农民最苦累的时候,尤其耕牛更是主力,春种后养起的壮膘,会在耕风耘雨中化为血汗,洒在四蹄下的泥水中,等播种完最后一块田地,牛看上去就像小了一号似的,让人心疼。有一年,就在秋播的头一天,村里的老牧人郭老三把村里的牯牛放丢了一头。老郭是称职的饲养员,也是讲故事的好手,什么《三国》《西游》《聊斋》,张口就来,晚上村里的饲养场,孩子们都在他身边,一边为他拌糠、剁草,一边听他讲故事。大队派民兵连长召集了各村七八十个民兵,把老郭平常放牧的龙潭坡山和晃桥河两岸十里大大小小的村寨拉网式地搜寻了个遍,无果,武队长严令老郭:“给你一个星期去找牛,牛在你在,牛不在你不在!”
后来,他给村人讲了他找牛的经过,我们听了,就像就跟在他身后,和他一起去找牛。
牛丢了以后,老郭脸上着急,可心里一点也不慌,在他的意识里,牛还活在人世间,它又不是一只蚂蚁,说不在就不在了。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把家里仅有的10元钱揣了,像走亲似的,体体面面地出门找牛。10元钱的用场他想好了,牛肯定被一户好心肠的人家收留了并精心喂养,找到后他有义务赔偿人家的工时草料费。
鬼使神差,3天里,老郭穿着崭新解放牌鞋子的脚竟然将他带到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的热闹小镇,这里早已听不到晃桥河的水声。小镇一角,肉汤飘来迷魂般的香气。3天来水米未进的老郭却一点也不感到饿,他的心里整整装着一头牛。直到坐在一家苍蝇狂舞的牛肉铺里,忽然感到心空了。那一刻他决意:切半公斤牛肉,打半公斤酒。吃完,他就往村子的方向走,跳晃桥河。自己浪里白条的水性在河里不好死,他早已想出了法子,在河边割几根手指粗的青藤,把一块石头绑在身上,打十几个死结,找个河潭跳下去,一了百了,一锤定音。主意打定,他放开肚皮,胡吃海喝,与其他食客谈笑风生。酒干肉净后,他内急去后院解决,惨淡的马灯灯光映照下,他看到了他的牛,从一面墙壁伸出它的头角。醉眼迷蒙,他不放心,伸出手去摸,果然,牛还在,只剩下了一个头,挂在了墙壁上。他的酒意一下烟消云散,客气地让店主结账,走人。
那年月的派出所破案具有惊人的效率。顺藤摸瓜找到嫌疑人,三拳两脚,贼人招供,从重从快,获刑4年,外加扒掉贼人家3间房子,将大小梁柱拆下赔偿给我们村。听人说,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牛头就挂在大队老书记身后的土墙壁上,牛头上,两只角粗壮对称,黑得发亮,但由于当初处理不当,双眼紧闭。七老八十的大队书记坐在那里办公,一天上级领导来检查,看不惯老书记这种做派,老书记讪讪地解释说自己挂牛头,是激励自己一辈子像老牛一样勤勉。领导笑了,说,哪有闭着眼还能勤勉的领导。领导一走,老书记就唤人叫老郭把牛头扛回去。牛头被老郭放在晃桥河里泡了两天,用柴火烧黄,下锅用猛火煮了一天,竟剥下一脸盆皮肉。老郭全家大小无不欢天喜地。村长和村里的其他头面人物也分享了这顿牛头大餐。第二天一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我的同班同学,老郭的小女儿小杏,还不时用她红润的舌头,舔舐她的那双小手,令人羡慕不已。
记得一天晚上我们用铡刀帮他铡草,他给我们出了一个谜语:“中间有条缝,夜夜有人弄,一个喊腰酸,一个叫腿痛。”孩子们都猜不出,恰巧玩伴小春的妈秋兰来叫儿子回家,小春便说了谜语,要他妈猜。想不到,平时见人就笑的秋兰,一张又白又圆的脸,一下拉长了变红了,望着老郭轻轻啐了一口,说“老不正经。”老郭一下恼了:“秋兰你想到哪里去了。”他一指铡刀,我恍然大悟,心里却在疑惑:秋兰怎么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人家。
土地承包到户后,村民割下稻子在田里晒干,把掼盆抬到田地脱粒后,将星散在田里的草把一层层呈圆形地堆在田一角,一个个草垛便如一朵朵金花开放,在这时节已显枯索的大地上,直到来年秧苗把水田染绿。老郭为节省土地,砍来树枝架在田头两米宽的水沟上,码起了一个大大的草垛。仲冬才舍得去取草。人们取草时总是挖一个口,从里一个个拖出草把,这时的草总会散发一股浓浓的酒香。很快,老郭家的草垛中间,被搂出一个大大的洞。有一天下雨,六七个大男人都挤进去避雨。这天,老郭又去取草。他一走进草垛时,一股冲天的腥气扑鼻而来,使他忍不住大呕。
突然,整个草垛动荡开来,他连忙往外撤。他刚冲出草垛,只见一条大腿一样粗的大蛇把头伸出草垛。他吓得魂飞魄散,回家后还一身是汗。次日一早,村里的男女老少人人手持锄头、木棒,跟在老郭身后。到了田里,老郭小心翼翼地走近草垛,掏出火柴,把草垛引燃了。在熊熊的大火中,只见一条三四米长的大蛇扭曲着身子一头从草垛奔出,头颅竟然有脸盆大,它用两只鸡蛋大的眼睛草草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跃下水沟,摇头摆尾地快速游向晃桥河。人们反应过来,大呼小叫着跟上去,看到落在河两岸树上的鸟惊叫着冲天飞起,可人们到了河边,那蛇早就不见了。河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如平常那样带劲地流着。老郭长叹了口气,悻悻地说,这条蛇他在童年时就见过了,那时它只有镰把粗。以后他可不想再见到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