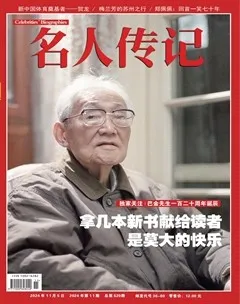晚年巴金的清醒之痛
2024-12-31周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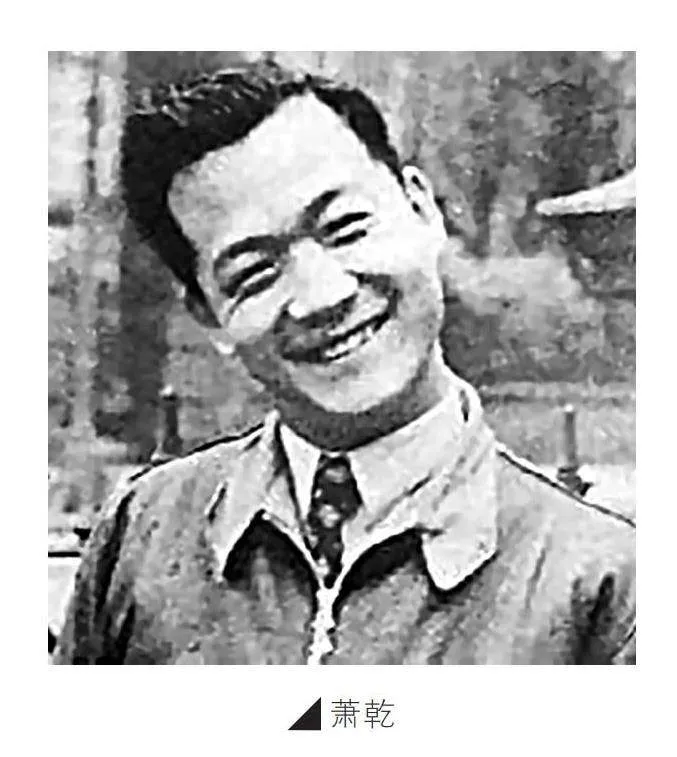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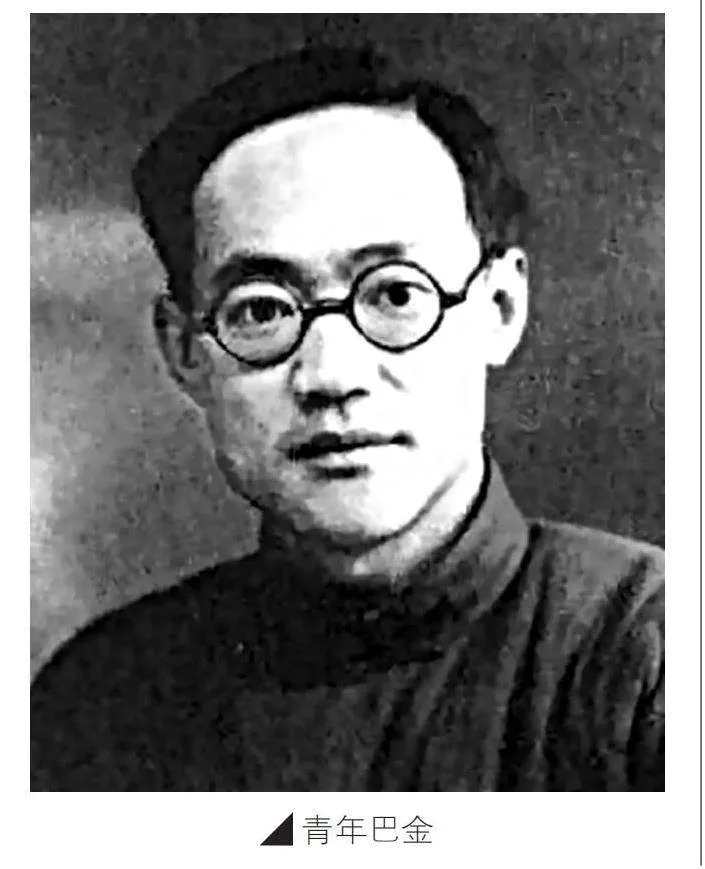
躺在病床上还是挂在墙上,巴金会选择哪一种?
早在1999年,巴金术后“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与医院的病床相伴了六年许。在一次抢救后,巴金对侄女李舒说,自己想要“安乐死”。但术后的巴金也会说,“我是为大家而活的”。
2005年4月,巴金肺部经常感染;到了10月份,消化道开始出血,肾功能减退,小便明显减少,同时血压开始下降。据院方说,医院竭力抢救,最多时一天输血三百毫升,同时二十四小时做血透。
巴金1999年开始长期住院。2005年11月25日,是巴金一百零一岁生日,医院原以为他能像之前一样再次渡劫。“他活得太苦了,长时间都在弥留状态,气管切开,吃东西是从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的,话也不能说了,但思维还正常。”在做气管切割手术前,巴金要和“大姐”冰心通一次电话,最终未果。
“去世对巴金来说或许是种解脱。”这是很多人心照不宣的心理活动。因为住院后期的巴金,朋友们早已凋零,即便健在也无法、也不便来探视。刚住院时,巴金还能认出人,能睁开眼睛点点头,后来身体愈加虚弱,为预防交叉感染,人们就不便再来了。
长寿的他几乎被世俗社会遗忘,文学圈之外的人或许会感叹:“巴老还活着?!”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消息瞬间传开,公众的记忆被激活,短暂的高潮之后,巴金的离场,让一个时代的记忆最终走向遗忘。
只是“青春期的产物,并非成熟的好作品”,巴金好友李健吾的这句话可以用来评论“泛五四一代”大部分作家的作品。1935年11月3日,李健吾批评巴金的作品:“革命和恋爱的可笑言论,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 巴金则回敬李健吾没有看懂《爱情的三部曲》。李健吾再次反驳作家不能强迫批评家改变自己的批评观。二人的论争据说持续了大半年。论争之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集《咀华集》《咀华二集》。
1936年,“说真话”的鲁迅去世。抬棺者中,有三十二岁的巴金。然而,在巴金跨越世纪的漫长人生里,鲜见衣钵的传承者,在其逝去的数十年间更是未见传人。
2024年是巴金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在喜欢作品和喜欢“说真话”之间,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显然更喜欢真实的巴金。
一直在矛盾和痛苦中写作
1927年1月25日,一个来自四川成都的年轻人踏上了驶往法国马赛的邮船。这个叫李芾甘的青年,此时还没有成为巴金。他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满怀理想,在更早前说,“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为什么去法国?
巴金回忆说:“当时还年轻,主要是想去学法文,多读点书,把思想搞清楚一点。法国当时思想界很活跃,是很多外国知识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向往的地方。另外,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不高,经济上还负担得起。”
李芾甘始为巴金,是两年后的1929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刊》上,笔名“巴金”。《灭亡》发表后,巴金以写作为终身职业,巴金尊叶圣陶为“一生的责任编辑”。1957年9月27日,巴金在致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拆解了笔名:“1928年8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同样是1928年,同样在巴黎,巴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巴金在回复家乡小学生的信中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
有人问巴金:“写作才能从哪里来的?”
巴金说:“我并没有才能,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他们(评论家)写得认真,读了不少书,思考了不少问题。有些我写作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我是中国人,读了大量的外国书,又在中国生活,我写的又是中国社会,单靠外国人的影响是不行的。自然,我和‘五四’一些作家一样,思想和写作受到外国影响比较大。”
有人问巴金:“为什么要写小说?”
巴金说:“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去抒发我的感情。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就不苦闷了,也就不矛盾了,这样的话,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可能去参加革命了。”
有人问巴金:“为何说自己一直在矛盾和痛苦中写作,想搁笔又不能?”
巴金答:“我写文章也是有矛盾的,有时也很痛苦,过去批判我没有在小说里为读者指出一条道路。其实我自己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没有办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我在解放后的大批判面前投降过。所以,现在我走成这个样子,并不是我的本意。……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真话和空话困扰着巴金。这不难理解,真话说得太晚,其实还是空话。
巴金对自己写过的一些文章有着复杂的情感:“过去有些东西是别人拉稿写的,现在也有拉稿的。要尽量避免。替别人完成任务,要你写什么稿子你就写什么稿子,是浪费时间。”
有人问巴金在“文革”中接受翻译家汝龙和戏剧家李健吾赠款的事。
巴金回答说:“有这回事。哪一年记不清了。好好想想就能想起。第一次是汝龙赠我的,是托李健吾的女儿带钱来的;第二次是李健吾赠我的,也是他女儿带来的。‘文革’时,我的存款被冻结了,每月生活费很少,还有人生病。我一直是靠友情生活的。”
“有人生病”,指的是妻子萧珊。后来,萧珊去世,有人去看望巴金,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痛苦地背但丁的《神曲》。
从1978年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随想录》收录了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
没有人否认,《随想录》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巴金说:“我写第一本和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巴金讲真话,卢梭是其第一个老师,但他受鲁迅的影响时间最长:
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
1986年,巴金在文章中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
“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晚年的巴金想建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了1993年巴金写给江泽民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上面有江泽民的亲笔批示。巴金在信中写道:“最近我收到现代文学馆来信,对文学馆目前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感到很不安……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又老又病,写字困难,请原谅。一切拜托,敬候批复。”
不久,新馆奠基,巴金已卧病医院,他写了一封信:“我因病不能远行,但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新馆。”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巴金的老朋友们又聚集在了一起。这不禁让人想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总编辑巴金身边聚集了一个庞大的文学圈,出版的作品有《故事新编》《骆驼祥子》《雷雨》《日出》等二百二十六部;会聚的作家有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艾芜、郑振铎、穆旦、何其芳、唐弢、黄裳、柯灵、张天翼、王统照、胡风、吴组缃、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冯至等八十六位。
其中,巴金挖掘了《雷雨》,是曹禺的文学引路人。曹禺后来回忆说:“我怀念北平的三道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了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这件事我说了多少遍,然而我说不完,还要说。因为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
虽为伯乐,但巴金认为曹禺比自己更有才华。巴金在致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巴金多次说:“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八十多岁的时候,朋友们每来拜访探视,总看到他独自坐在客厅角落的书橱旁。
“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这是冰心对巴金的评价,“他的可佩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
黄裳记忆里的1949年前的巴金“很少参加闲谈,他总是一个人在楼上工作。到了吃饭或来了客人时才叫他下来……(他)披着一件夹大衣,手里拿着一本小书,踏着有韵律的步子从楼上慢慢踱下来,从他那浮着微笑的面颜,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从阅读中获得的愉乐……巴金在我们身边,可是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像一群孩子那样围着他喧闹,当他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时,他才是活泼的、生动的。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里出版的新书”。
萧乾夫人文洁若说:“萧乾老说他是朋友堆里滚大的,可是最好的朋友是巴金,巴金是他的挚友、益友和畏友。”在文洁若看来,巴金在《随想录》中写了自己的忏悔。萧乾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于否定自己”,是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
“我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1985年,四川作家协会请求恢复巴金故居。巴金不同意:“不要重建我的故居,我的一切都不值得纪念,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如果一定要有个地方,让大家在我去世后来看我,那么就立个牌子,写上‘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就行了,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1986年10月,巴金连续写三封信致李致(巴金侄子),再次“申明”他的意见:“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不要用我的名字”,这是巴金时常说的话。
巴金生前不主张出版日记,他说:“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虽然巴金写过《回忆我的哥哥李尧林》,并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但巴金不希望别人代写传记。巴金认为写传记,最重要的是了解传主的生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时代最重要,背景、环境最重要。我不想别人替我写传记。我写过去,也需要好些时间来思索,来回忆,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
巴金说:“过去写传记最困难是材料。我为啥要提出建立文学馆呢?就是为了保存材料。成立文学馆还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成为研究中心。我的意思,先应该是资料中心,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提供资料,主要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服务,还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服务,为很多人服务。研究中心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后发展当然可以办。写传记有了资料也就方便一些。本人谈的只能参考,特别是家属,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大符合事实,家属提供的情况好话说得太多。最困难的是时代怎样创造这个人,能把时代写出来。这个时代出现这个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巴金说,编印《巴金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说,第四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五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分很大。他说:“《爱情的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当别人对“废品论”提出异议时,巴金说:“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巴金是清醒的。他一定怀念年轻时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的作品开风气之先。李健吾曾说: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
金庸在小学六年级时成为《家》的读者。他曾回忆,“我最初读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正在浙江海宁家中,坐在沙发中享受读书之乐。哥哥见到我正看《家》,说道:‘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我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哥哥那时已在读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意见很有权威,我就信了他的。”但当时年少的金庸最爱读武侠小说,并且也避免不了在阅读时引入自己的观点,所以对《家》这一类小说,仍觉读来不够过瘾。直到后来自己也写小说,他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在金庸看来,巴金、鲁迅和沈从文三位先生是他“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鲁郭茅巴老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六位经典作家。其中,鲁迅去世最早,老舍、郭沫若、茅盾、曹禺分别于1966年、1978年、1981年、1996年去世。唯有巴金活到了千禧年。但巴金并不认为这是件幸事——“人老了”,“书也老了”。晚年的巴金,痛苦地清醒着:
30年代、40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