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人家,山上学术
2024-12-22王建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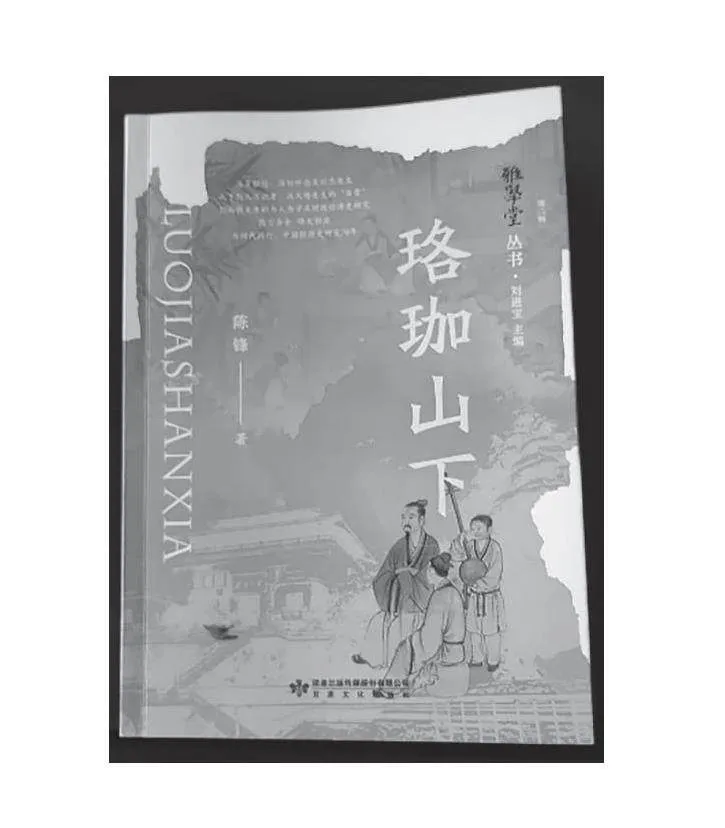
我和《珞珈山下》这本书的作者陈锋,相识于1980年左右。那时我们都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他早我半年是七七级,我是七八级。他侧重于中国史,我侧重于世界史,原本不会有往来,但我们却彼此熟悉。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作为学生,都喜欢写作,且在那一代学生当中写作成果较为突出,也算是惺惺相惜之故。后来我们走了不同的路子,他留校做教师、做学问,我则毕业分配到出版部门工作。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但我们都毕生钟情于学术。对于这本书,我先在朋友圈里见到。他发消息说有这样一本书要出版,我点评道:“山下人家,山上学术。”这既是戏言,也是对他学术之路的一个评价。我用来做了这篇书评的标题。
这本书是一本随笔杂谈集,有三个部分:回忆与访谈、序言与评论、演讲与杂说。作为同辈来读这本书,我或许有与他学生辈不同的感受。
我在读这本书时,感觉最亲切的是第一部分“回忆与访谈”。
这一部分虽只有5篇文章,其实是这本书的重点,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对武汉大学的几位名师彭雨新、吴剑杰、冯天瑜的忆念;二是陈锋本人对从学生到教授经历的回顾,所写差不多都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那些事。这三位老师我都很熟悉,或多或少打过交道。尽管如此,我还是从陈锋的有关叙写中,知道了许多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加深了对这几位先生的了解。比如彭雨新教授,作为陈锋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曾给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写过一首诗,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最后一句是“风雨鸡鸣共读书”。陈锋的书里写到,彭先生为整理李剑农先生遗著所做的一切,令人感佩,体现了老辈学人的风范与情怀。赵德馨先生称赞吴剑杰教授,是在世学者中研究张之洞的第一人。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冯天瑜先生最后在病床上校对文稿,或为他人审阅文稿,体现出一位学者为学术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治学精神。梅贻琦说,“大学乃是有大师之谓也”。我相信每所大学都有这样杰出的学者,他们是教书育人的时代楷模。作者在书里还有两篇文章,回顾了他的学术成长经历。一篇回忆在读生涯,那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改革开放之门初开,十年积压的人才涌入大学,学习的热情是后来的学生难以比拟的。几十年一晃而过,那一代学生成为退休或将要退休之人,有的或因有特殊的学术地位而延聘。陈锋在那一代人里,是从学生成长为大学教授的一个典型。这种经历对于欲走学术之路的莘莘学子来说,是有启迪意义的。还有一篇文章回顾了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深入探究盐税、军费开支以及官员俸禄的经历,并总结了自己对于清代财政史研究领域的见解。文章中,老一辈学者的悉心指导与作者个人不懈的努力,都历历在目,令人记忆深刻。陈锋通过他的笔触,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人事变迁与风貌特征,以及那个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远影响,都生动地呈现在纸上。这是他自己的学记,也是一代人抹不去的学术记忆。
第二部分主要是序跋书评,共计13篇。为人作序,是一位学者在治学上取得一定成绩后免不了的事情。陈锋是治清史,尤其是清代财政史的专家。清人关于序跋的见解亦很丰富。文学家汪廷珍说“生平不轻为人序文”。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校证》出版时也说:“夫书既成,而平生不喜为人作序,故亦不求序于人。”顾炎武则有一句:“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受清人严谨学风的影响,陈锋为人作序比较谨慎,不跨界作序,所作序都在他的治学范围内。从该书所收10余篇序文来看,专业性很强,也不做过分之语,言说尽可能把握其书特点。如给《彭雨新文集》所写的序,总结了彭先生研究的几个特点:对经典作家的论述灵活运用,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进一步分析;注意历史的回溯和宏观归结;善于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概括与分析,对一些多面向的问题进行辩证论述;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善于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解释。这算是吃透了彭先生学术的知人之论。再比如,对于任放所著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归纳其特点是:对明清市镇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评述;对资料的爬梳下了很大功夫;对明清市镇所依托的人文地理环境进行了探讨;对市镇的归纳与分析有独到之处。要准确归纳出这些特点,是需要学识和功夫的。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意思是,写序要有合适的人,要在某一行有专业特长。陈锋就适合写这一类序文。
最后一部分共计9篇文章,从篇名即可看出是一组入世文章,《中国传统社会的税收、财政与国计民生》《清官·庸官·干吏》《第一好官》之类,体现了他做学问之外的社会关切与兴趣爱好。他的社会关切还包括世风与养生,都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了新思考。他的兴趣爱好是收藏,砚台收藏是他收藏的大宗,曾在香港举办过陈锋收藏砚台展。书中的《历史上的“四大名砚”考辨》一篇,把收藏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对历史上所谓的“四大名砚”之说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否定观点,认为并不存在“四大名砚”的说法。那么“四大名砚”之说从何而来呢?书中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将这个问题留作他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些社会关切与兴趣爱好,给治史者以启发:一位学者不能只闭门治学,应该有广泛的学养。
陈锋的学术研究范围是很有意义的。古人云:“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新唐书·杨炎传》)陈锋的这本书,既是他治财政税赋史的学谱,更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在学术论文之外的学术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