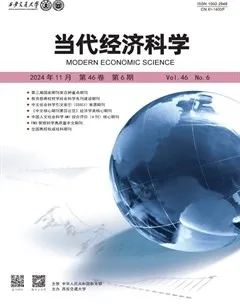中国经济“三重压力”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货币协同
2024-12-11杨脉刘定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对于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加强政策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拟合了2019年第四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消费与劳动供给数据的演变路径,模拟了“三重压力”的经济环境,进而定量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社会福利效果,探讨财政货币协同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面对“三重压力”,政府增加民生支出能产生显著的消费乘数,切实增进社会福利;第二,相对于税收融资的货币主导型政策组合,债务和通货膨胀融资的财政主导型政策组合能够提升公共投资的稳增长效果;第三,相对于货币主导型政策组合,减税降费会持续放大财政主导型政策组合下的财政政策效果,并且改善财政政策空间。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可暂时转向财政主导型来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改善应对“三重压力”的能力;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应平衡好生产性和民生性支出,在发展中稳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关键词:中国经济“三重压力”;财政政策效能;政策协同;财政乘数;社会福利效应;民生支出;公共投资;减税降费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4(06)001217
一、问题提出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不仅是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形势的重要论断,还凸显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2020—2022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实际消费均显著偏离其线性增长趋势,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多次跌破荣枯线,共同凸显需求端的收缩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在短时间内大幅攀升,以及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的骤降,均反映了供给冲击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此外,就业、收入等不同口径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全面下行,折射出市场主体的预期发生普遍弱化。这些指标变化既是“三重压力”的现实表征,又凸显了有效应对“三重压力”的紧迫性。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低于潜在水平,那么短期经济运行压力就可能逐渐演变为中长期经济发展难题。长期低增长态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比如创新发展可能因缺乏动力而受阻,绿色转型可能失去活力,协调发展难以实现,开放发展可能陷入停滞,共享发展可能退化为低水平再分配。长期低增长还可能积累风险并最终导致风险爆发,威胁经济金融安全。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使财政收支压力高企,导致积极财政政策空间日益收缩,财政可持续性减弱[12]。一方面,“六稳”“六保”等系列措施扩大了财政支出。2020年,为了突出民生兜底,财政部将教育、医疗以及社保就业等方面的支出从8万亿元增至8.8万亿元,同时通过发行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途,为地方“六稳”“六保”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缩减了财政收入。2020年全国新增的减税降费规模达到实际GDP的2.47%,间接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增至实际GDP的6.19%,这两个数字均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为应对财政收支紧平衡和经济下行挑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强政策协同是必要选择。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2024年11月第46卷第6期杨脉,刘定中国经济“三重压力”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货币协同因此,如何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和加强财政货币协调配合,有效应对“三重压力”,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和理论问题。对此,学术界争论较为热烈。刘尚希等[3]提出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必要资金,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Galí[4]认为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来看,在经济疲软、低通胀甚至通缩时期有限度地进行一些货币融资或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行的。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何增平等[5]将之总结如下:一是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会有损中央银行独立性,并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二是财政部门的扩张倾向会导致这种协调方式难以退出,从而破坏财政纪律;三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四是中国现阶段仍有足够的政策执行空间。这些争论表明,有必要在“三重压力”环境下定量探讨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以及不同政策组合方式的影响。然而,国内涉及积极财政政策或货币财政政策协同的研究并没有聚焦“三重压力”现实背景。
理论上讲,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具有不同的协调搭配方式。根据Leeper[6]的界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分别划分为积极型和被动型政策取向。当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作出强有力反应时,它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AM),着力稳定价格水平;反之,它就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M)。换言之,AM遵从泰勒原则,而PM违背泰勒原则。类似地,当财政政策对政府债务作出强有力反应时,它就是被动型财政政策(PF),着重稳定政府债务;反之,它就是积极型财政政策(AF)。换言之,李嘉图等价在PF下成立,而在AF下不成立。根据以上划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搭配可以分为四种组合:AM/PF、PM/AF、PM/PF和AM/AF。其中,AM/PF与传统货币数量论具有相似的内涵,因此也被称为货币主导型政策组合;PM/AF则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一致,一定程度上允许财政赤字货币化,因此它也被称为财政主导型政策组合[78]。这四种政策组合对经济均衡有着不同的含义:在AM/PF和PM/AF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在PM/PF下,DSGE模型存在多重均衡,即均衡不确定性;AM/AF则意味着DSGE模型不存在任何稳定的均衡。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中识别和估计了不同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并且探讨其宏观经济效应。比如,有研究指出中国货币财政政策组合符合PM/AF[910];也有学者指出PM/AF下的财政扩张能更有效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1112]。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聚焦中国“三重压力”经济环境,探讨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且比较不同政策组合的作用。具体而言,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种财政政策工具的NKDSGE模型,然后通过拟合2019年第四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实际GDP、实际消费以及劳动供给数据的演变路径,识别出结构性经济冲击,进而模拟“三重压力”的经济环境,最后定量测算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探讨不同财政货币组合的影响。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归纳为三点。首先,率先对“三重压力”经济环境进行理论建模。“三重压力”是中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困难,不只是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还是中长期都需要加以应对的挑战。但是,已有文献基本上停留在定性讨论。相比之下,本文利用理论模型和结构性冲击来表征“三重压力”,并研究相应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其次,探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方式对“三重压力”环境下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既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融资方式的作用,又为非常时期中国是否需要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提供了理论见解。最后,多维度评价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度量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时,本文不仅计算了常用的财政乘数,还测算了社会福利增益指标,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提供了多维度的考察视角。
二、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够表征“三重压力”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NKDSGE模型。该模型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主要部门,区分了政府消费、转移支付、民生支出和公共投资支出等四种财政支出类型,其中,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费互补,公共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企业生产函数。另外,模型纳入了偏好冲击、劳动供给冲击和技术冲击,以表征“三重压力”;考虑了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等税收工具,以全面探讨积极财政政策。
(一)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由大量无限期生存的家庭组成,其总量被标准化为单位1。代表性家庭由编号j表示,j∈0,1,通过选择消费Ct(j)、劳动时间Ntj、债券Bt(j)和资本Kt(j)来实现终身效用的现值最大化,其目标函数形式如下:
maxCt(j),Nt(j),Kt(j),Bt(j)E0∑∞t=0βttC1-σtj/1-σ-χNηtN1+φtj/1+φ(1)
家庭面临如下预算约束:
Ct(j)+It(j)+Bt(j)≤wt(j)Nt(j)+rkt(j)Kt-1(j)+rt-1Bt-1(j)-Tt(j)+TRt(j)+Ψt(j)2
Kt(j)=1-δKKt-1(j)+It(j)3
其中,Et、β、t和ηt分别表示预期算子、主观贴现率、偏好冲击和劳动供给冲击;C~t是家庭总消费,它由私人消费Ct和政府民生支出CGt通过常替代弹性(CES)函数复合得到:C~t=ξC(v-1)/vt+1-ξCGt(v-1)/vv/(v-1);ξ度量了私人消费和政府民生支出之间的替代弹性;v表示居民消费的权重;σ和φ分别为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和劳动工资弹性的倒数;χN衡量了劳动供给在效用函数中的相对权重;rt和πt分别为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且名义利率满足it=rtEtπt+1;Tt(j)=τctCt(j)+τwtwt(j)Nt(j)+τktrkt(j)Kt-1(j)是家庭缴纳的税收额,τct、τwt和τkt分别为消费税税率、劳动所得税税率以及资本所得税税率,wt和rkt分别为市场工资水平和资本回报率;TRt(j)是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Ψt(j)是家庭部门凭借对中间产品厂商的所有权而获得的利润,δK表示物质资本Kt(j)的折旧率。
给定工资水平,代表性家庭向劳动力打包者提供差异化的劳动Nt(j)。劳动力打包者通过技术Nt=
∫10Nθw/(θw-1)t(j)dj(θw-1)/θw将这些劳动力加总为无差异劳动,其中θw表示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总工资和每种劳动力的工资之间的加总关系为wt=∫10w1-θwt(j)dj1/(1-θw),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得到劳动力打包者对差异化劳动力的需求为Ntj=Ntwt/wt(j)θw。
(二)最终产品厂商
最终产品厂商购买中间产品Yt(k),并将中间产品生产成为最终产品Yt。生产技术为CES复合形式:Yt=∫10Ytkθ/(θ-1)dk(θ-1)/θ,其中θ表示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最终产品厂商的名义利润为Πt=PtYt-Pt(k)Yt(k)。完全竞争假设下,求解得到最终产品价格为Pt=∫10Ptk1-θdk1/(1-θ),最终产品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为Ytk=Ptk/Pt-θYt。
(三)中间产品厂商
垄断竞争市场中存在测度为1的中间产品厂商,用k表示。中间产品厂商利用公共资本KGt、租用私人资本Ktk并购买劳动力Ntk进行生产。生产函数服从CobbDouglas形式,为Ytk=At·Kαt-1kN1-αtk,其中α∈0,1衡量了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At=AtKGt-1αG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包含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At和公共资本存量的滞后项KGt-1。KGt的累积方程为KGt=1-δGKGt-1+IGt,其中δG和αG分别为公共资本的折旧率和产出弹性。中间产品厂商的成本最小化问题为:
minKt(k),Nt(k)wtNtk+rktKt-1k4
s.t.AtKαt-1kN1-αtk≥Ytk5
对此求解得到中间品厂商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分别为wt=1-αmctYtk/Ntk和rkt=αmct·Ytk/Kt-1k,其中mct=rkt/ααwt/1-α1-αA-1t为生产的边际成本。采用Calvo[13]提出的价格粘性设定,假设在每期存在ρ比例的中间产品厂商按照上期的价格进行定价,剩余1-ρ比例能通过利润最大化来进行定价,其中0<ρ<1。中间产品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Pt(k)∑∞s=0βρst+sλt+s/tλtPt+sk/Pt+sYt+sk-wt+sNt+sk+rkt+sKt+s-1k6
s.t.Ytk=Ptk/Pt-θYt7
其中,λt是拉格朗日乘子λt=C-σtCt/Ct1/v/1+τct,同时也表示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求解上述问题得到中间产品价格,整理和换算得到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
lnπt=βEtlnπt+1+(1-ρ)(1-βρ)mc︿t/ρ8
其中,mc︿t=lnmct/mc表示生产的边际成本相对于稳态发生变化的百分比,通货膨胀率πt满足πt=Pt/Pt-1。
(四)政府部门
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总和Tt以及发行债券的所得收入Bt,财政支出包含民生支出CGt、公共投资支出IGt、政府消费PGt和转移支付TRt,以及上期国债的本金和利息。综上,政府的预算平衡方程为:
Bt+Tt=Gt+rt-1Bt-19
其中,Gt=CGt+IGt+PGt+TRt表示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定义cGt=CGt/Yt、iGt=IGt/Yt、pGt=PGt/Yt、trt=TRt/Yt分别表示政府民生支出、公共投资、政府消费、转移支付相对于实际GDP的比值,这些比值的变化反映了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变动。同时定义gt=Gt/Yt、bt=Bt/Yt和τt=Tt/Yt分别为财政支出产出比、政府债务产出比和税收产出比,式(9)可改写为比例形式:
bt+τt=gt+rt-1bt-1Yt-1/Yt10
参考已有文献的通常做法[10,14],假定财政支出规则均服从AR(1)过程:
cGt=ρgcG+1-ρgcGt-1+εCGt11
iGt=ρgiG+1-ρgiGt-1+εIGt12
pGt=ρgpG+1-ρgpGt-1+εPGt13
trt=ρgtr+1-ρgtrt-1+εtrt14
其中,ρg表示财政支出的自相关系数,体现了政策平滑或连续性;εCGt、εIGt、εPGt和εtrt分别为相应的政策冲击。张龙等[15]发现1996—2020年的中国资本所得税对财政赤字规模存在正反馈作用,故本文设定τct、τwt和τkt的税率规则分别为:
τct=ρcτc+1-ρcτct-1+εct15
τwt=ρwτw+1-ρwτwt-1+εwt16
τkt=ρkτk+1-ρkτkt-1+1-ρkφτbbt-1-b+εkt17
其中,ρc、ρw和ρk表示τct、τwt和τkt的自相关系数,体现了政策平滑动机或连续性;φτb表示τkt关于政府债务产出比的反应系数;εct、εwt和εkt是扰动项,分别对应政策冲击。
考虑到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以价格型为主,本文将利率政策设定为标准的泰勒规则形式:
i︿t=ρii︿t-1+(1-ρi)(φiππ︿t+φiyY︿t)18
其中,ρi表示名义利率的自相关系数,体现了利率变动的平滑动机或政策连续性;φiπ和φiy分别为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响应强度。
利用政府预算平衡方程、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以及费雪方程式,政府债务产出比可表达为如下的自回归形式:
b︿t=β-1-1-ρkφτbb︿t-1税收调整+β-11-ρiφiππ︿t-1-π︿t融资成本-β-1ΔYt产出增长+Ξt19
式(19)表明,债务产出比的变化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第一,政府税收调整和债务融资成本变动;第二,产出增长;第三,其他因素ΞtΞt=b-1gg︿t+β-1[ρii︿t-2+(1-ρi)φiyY︿t-1]-b-1τcC/Y(τ︿ct+C︿t-Y︿t)+b-1[α(1-ρk)τkτ︿kt-1+(1-α)τwτ︿wt]-b-1[(1-α)·τw+ατk]mc︿t。。其中,第一方面因素的作用渠道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直接相关。如果φiπ>1-ρi-1,即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足够大,这会推高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和融资成本;此时,稳定政府债务要求财政部门调整税率,即φτb>β-1-1/1-ρk,因此财政货币组合服从AM/PF。如果φτb<β-1-1/1-ρk,即财政政策不对政府债务作出强有力反应;为了确保债务稳定和均衡唯一性,中央银行需要实施低利率政策,通过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和利用通货膨胀来稀释政府债务负担,相应地,φiπ<1-ρi-1,因此财政货币组合服从PM/AF。
(五)结构性冲击与“三重压力”表征
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和相关文献的建模方式,本文利用结构性冲击组合来表征“三重压力”情景。首先,采用偏好冲击捕捉“三重压力”中的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1617]。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和经济增长下滑超预期等负面因素,私人部门信心和经济增长预期走弱,导致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和企业降低投资,使得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不足,经济出现负向产出缺口;同时,负向产出缺口、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相互强化,会导致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18]。其次,利用外生的劳动供给减少来刻画供给冲击,体现生产成本增加。劳动、投资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拐点相继出现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多点散发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相叠加,共同推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压缩了企业经营空间[1920]。最后,在当前“三期叠加”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技术进步仍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21],并且西方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遏制和打压已经呈现长期化趋势,因此技术冲击也是“三重压力”环境需要考虑的元素郭克莎.化解三重压力,稳中求进实现高质量发展[EB/OL].[20220412].https://news.gmw.cn/202204/12/content_35651523.htm。。
综上,本文利用偏好冲击t、劳动供给冲击ηt和技术冲击At的共同作用来表征和刻画“三重压力”。参考FariaeCastro[1617]的做法,假设这些结构性外生冲击均服从AR(1)过程:
︿t=ρ︿t-1+εt20
η︿t=ρηη︿t-1+εηt21
A︿t=ρAA︿t-1+εAt22
其中,ρ、ρη和ρA是自相关系数,εt、εηt和εAt分别为各自的新息或扰动项。
(六)一般均衡和市场出清
给定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不同形式的外生经济冲击,家庭最大化效用,企业最大化利润。竞争均衡满足家庭和企业决策的一阶条件、政府预算约束、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规则和以下的市场出清条件:
∫10Ktjdj=∫10Ktkdk23
∫10Nt(j)=∫10Ntkdk24
∫10Btjdj=Bt25
Yt=∫10Ctjdj+∫10Itjdj+CGt+IGt+PGt26
式(23)~(26)依次表示物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国债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从而使经济实现了一般均衡。
三、参数校准
首先,对于一些常见的结构性参数,本文尽量与主流文献的校准值保持一致。这些参数包括β,σ,α,φ,ξ,v,θw,δk,αG,δG,ρ,θ。与卞志村等[22]的研究相同,令家庭主观贴现率β的季度值等于099,以此对应2002—2020年中国国债的一年期利率2.55%。参考李力等[14]的研究,将家庭的消费风险厌恶系数σ和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α分别校准为2.0和0.5。将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φ校准为4,这和王文甫等[23]的研究相同。对于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权重系数ξ以及私人消费和民生支出的替代弹性v,本文参考李戎等[24]的研究,将其分别确定为0.80和0.25。根据李戎等[25]的研究,将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θw校准为10,这对应了约11%的工资加成率。将私人资本的季度折旧率δk设定为0.025,对应年化的资本折旧率为0.100,这和卞志村等[22,26]文献的做法相同。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αG在文献中的取值通常在0.1~0.3之间,本文参考王文甫等[23]的做法,令该参数等于0.1。借鉴郭长林[26]的研究,将公共资本存量的折旧率δG设为0.092。根据卞志村等[22]的研究,将Calvo规则下每期无法自由定价的中间产品厂商比例ρ校准为0.75,即中间品厂商平均每四个季度调整一次价格。借鉴Liu等[10]的做法,令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θ等于11,这对应了中间品10%的价格加成率。
其次,对于一些结构性参数和变量稳态值,本文根据相关文献的取值以及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矩条件来进行校准。中国实际GDP和实际消费在2019年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大致保持了线性的增长趋势,因此本文将2019年第四季度的变量间关系作为参数的匹配标准。具体地,实际消费和政府公共投资占实际GDP的比例分别为C/Y=38.65%和IG/Y=3.29%。按照李戎等[24]的界定,将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的支出总额视为政府民生支出,然后利用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的数据计算得到CG/Y=8.19%,扣除这部分支出后,得到PG/Y=7.81%。根据以上条件,得到私人投资占实际GDP的比例为I/Y=42.05%。这些取值均位于大多文献校准的区间之内,基本符合近年来的中国经济特征。参考严玉华等[27]的方法,假定劳动力平均每年的劳动时间约为2304小时,扣除平均每天8小时的睡眠时间后得到16小时的可利用时间,那么平均劳动时间占总时间的比值为N=2304/(365×16)=0.3945。根据这些条件可得到劳动负效用参数χN为4.19,该取值位于广泛校准的1~10之间。参考卞志村等[22]的研究,本文将τc、τw和τk分别设为0.125、0070以及0.220。通过这些取值可以反推出模型稳态满足T/Y=26.78%、TR/Y=7.31%以及B/Y=1703%,与现实经济数据和现有文献的对应取值进行对比,这些匹配结果也是合理的。
最后,对于表征外生冲击的自回归系数以及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本文通过借鉴最近文献的估计值加以校准。表征“三重压力”外生冲击的自相关系数包括ρ、ρη和ρA。对于跨期的偏好冲击,本文借鉴王立勇等[28]的研究,将其自相关系数ρ校准为0.9;参考彭俞超等[29]的研究,将劳动供给冲击的自相关系数ρη设定为0.588;对于技术冲击的自相关系数ρA,本文借鉴高然等[21]的研究将其赋值0.7945。政策规则相关参数有{ρg,ρc,ρw,ρk,ρi,ρiy,φiπ,φτb}。根据李力等[14]的研究,将政府支出的自相关系数ρg设为0.84;为着重考察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进行反应的单一目标,本文将名义利率的自相关系数ρi和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ρiy均设定为0。参考张龙等[15]的研究,将税率的自相关系数ρc、ρw和ρk分别设定为0.279、0.225和0.253。根据前文对财政货币组合体制的定义,φiπ和φτb需要满足AM/PF和PM/AF的相应取值范围。本文参考彭俞超等[2930]的估计结果,分别设定φAM/PFiπ=1.510和φPM/AFiπ=0.896;同时根据Bhattarai等[11,15]的研究,分别设定φAM/PFτb=0.2092和φPM/AFτb=0。
四、数值模拟与传导机制分析
为了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在“三重压力”下的作用,全面考察财政政策实施空间的变化,本文将数值模拟实验依次划分为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匹配实际GDP、实际消费以及劳动供给的演变路径识别出模型背后的结构性冲击,并将这种模拟出的“三重压力”环境视作基准情形进行对比;其次,在“三重压力”环境下分别模拟增加民生支出和增加公共投资的经济效果;最后,在“三重压力”环境下模拟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的经济效果,然后进一步模拟政府同时减税和增支的影响。
(一)“三重压力”的理论表征及其经济影响
模拟经济事件和构建结构性冲击的技巧主要包括完美预期求解和条件预测方法。和完美预期求解相比,条件预测方法不仅能快速识别出经济中的外生冲击组合,其经济行为人的非完美预期假设还更加符合现实行为规则。给定实际产出、实际消费和劳动时间的演变路径,本部分运用条件预测方法估计出“三重压力”冲击组合的时间序列。具体而言,首先通过BlanchardKahn的矩阵分解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然后转换得到简约的一阶状态空间形式:
yt=Tyt-1+Rεt27
其中,yt是由模型中的前定变量和非前定变量堆叠而成的列向量,εt=εAt,εt,εηt′是表征“三重压力”的外生冲击组合,T和R分别表示yt-1和εt的参数矩阵。将yt划分为可控的部分和不可控的部分,其中模型匹配变量Yt,Ct,Nt′是可控的部分。通过对式(27)进行代数求解,可以得到εt的具体取值。
图1中的结构性冲击变化表明中国经济持续受制于“三重压力”,这和决策层的判断相一致。在2020年第一季度(Q120)至2022年第四季度(Q422)期间,εt、εηt和εAt呈现出剧烈波动的态势,其取值显著不为0,并且在2020年第一季度最为明显。在AM/PF下,三者偏离稳态的比值分别为-38.60%、59.45%以及-663%,分别反映出家庭消费意愿减弱或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劳动供给成本上升以及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在PM/AF下,这三项外生冲击的取值分别为-37.64%、60.43%和-6.63%,可见结构性冲击的取值在不同财政货币组合下非常接近,其冲击方向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后,虽然结构性冲击水平有所弱化,但εt和εAt仍然大多处在负值区间、εηt仍然大多处在正值区间。此外,εt、εηt和εAt组合能够精准匹配实际产出、实际消费和劳动供给的演变轨迹,佐证了这些冲击组合解释“三重压力”的有效性。
根据政府预算方程式(10),如果“三重压力”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就需要通过上调税率或者提高债务产出比来维持财政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一方面,如果债务产出比不变,那么政府将上调税率,但这在客观上将与减税降费的现实目标相悖;另一方面,如果税率保持恒定,那么提高债务产出比就会涉及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2]。这两方面构成了“财政不可能三角”,即政府无法同时维持财政支出、降低税负和控制债务。从一般均衡视角来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存在额外的情况:对于第一种情形,债务发行所产生的铸币税效应能够部分地稀释偿债压力,从而降低税率上调的程度;对于第二种情形,如果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能够扩大消费或提高要素报酬,那么税收增加就能够减轻政府债务压力,从而改善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财政政策实施的具体影响无疑是复杂的,至于何种力量更为突出,则需要通过定量的分析方法来对财政政策实施空间进行梳理。本文模拟了相关变量的演变路径,来观察财政实施空间的动态变化。图2的结果显示,在“三重压力”下维持各项政府支出的力度不变,消费和要素回报率下降所产生的税收缺口加剧了政府债务压力,此时“财政不可能三角”成立。
图1表征“三重压力”的外生冲击组合注:实际产出、实际消费和劳动时间的经济数据通过如下步骤转换得到:第一,剔除实际GDP和实际消费数据在2017—2019年的线性趋势,然后通过线性趋势和实际数据的比例关系,将2020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的实际GDP和实际消费水平化;第二,将产出、消费和劳动时间的模型稳态值与水平化的经济数据进行匹配和换算。
图2“三重压力”的宏观经济影响两种财政货币组合对于税率和名义利率的调控存在差异,其中AM/PF下的资本所得税税率和债务产出比上升,并且均高于PM/AF。根据式(19)对于债务产出比受影响因素的分类,由于产出路径是给定的,那么可以通过税收调整和债务融资成本变动来考察债务产出比的变化。在AM/PF下,要素价格下降缩减了税收收入,同时通过降低价格水平提升了债务实际值。对于这种情况,中央银行下调名义利率以图缓释债务实际值上升的压力。在标准的税收规则设定下,资本所得税税率根据债务产出比的滞后项作出响应,但由于资本所得税税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响应程度不充分,政府不得不依赖更多的债务融资。债务产出比提升到0.19以上,并且要素回报率的降低导致税收产出比出现了较大缺口。在2020年第一季度之后,资本所得税税率随着债务产出比增加而持续上升,从而加深了AM/PF对应的内在形成机制。与之相反,PM/AF在国债增发的同时允许通货膨胀适度上升,使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变化发生背离。增发的国债通过铸币税效应进行部分融资,使债务产出比实现了相对较低的增长,因此这实质上也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种实现形式。由于财政部门此时无需调整资本所得税税率,要素回报率的下降幅度得以减轻,因此税收产出比的变化路径将位于AM/PF的路径之上。这些结果表明,PM/AF在“三重压力”下能够提供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实施空间。
(二)“三重压力”下财政支出扩张的效果
实现经济快速恢复和缓解财政实施空间,往往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实施。作为一种政策选择,积极财政政策既包含政府支出在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上的“双管齐下”,也包含精准有力的减税降费措施。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同时“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稳住经济基本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Chen等[31]的研究,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从8.19%增至8.70%,公共投资占GDP的比值从上个季度的3.29%增至570%。本文据此分别假设εCGt=0.50和εIGt=2.41,即cGt和iGt分别增加0.50和2.41个百分点来进行相应的数值模拟。增加民生支出时的宏观经济效应如图3所示,其中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相关变量在PM/AF和AM/PF下相对于“三重压力”的增长率本文未讨论经济主体对财政货币组合的预期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原因如下:第一,2019年第四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期间,财政货币组合发生突然转变的可能性较小;第二,现有研究对中国财政货币组合的估计结果并不统一,并且一些文献更倾向于PM/AF,降低了讨论这种预期的必要性;第三,该预期所需的MSDSGE模型具有随机性质,这与本文的确定性模拟方法难以结合,即使实现,其成本也将远超收益。。
图3“三重压力”下政府增加民生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从图3可见,增加民生支出的经济刺激效果取决于财政部门的融资取向以及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具体立场,其中PM/AF下的产出和劳动时间实现了比AM/PF更大的增长。在AM/PF下,即货币政策积极稳定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积极稳定政府债务,增发国债会提高未来的资本所得税税率,推高家庭部门要求的资本回报率,挤出私人投资。对于规模收益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投资需求下降会降低均衡工资水平。在2020年第一季度,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费所形成的需求增长仅使产出相对于“三重压力”增长了0.01%;伴随着民生支出冲击的淡出和企业要素需求的减弱,产出增长率很快转为负值,亦即产出水平低于“三重压力”的对应值。与之相对的是,PM/AF下的政府通过向家庭发行国债来为民生支出融资,同时中央银行选择容忍通货膨胀的上升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税率不会上升,这就使得家庭部门的预期财富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0.18%,表明扩大的总需求通过价格效应传导至企业,进而提高了产出、劳动、实际工资水平和资本回报率等变量。相对于“三重压力”,PM/AF政策组合下的产出增加了0.08%,显著高于AM/PF下的0.01%。一般认为增加政府的消费支出往往会通过利率效应挤出消费,因此政府支出的民生保障功能对于挤入消费至关重要。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比,民生支出冲击通过提高家庭的边际消费效用来刺激消费。尽管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在不同财政货币组合下发生分化,但民生支出冲击仍能透过不同的组合来刺激消费。此外,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产出增长在不同组合下的差异还引发了财政实施空间的不同演变。对于AM/PF,税收产出比在2020年第一季度增长了0.55%,并且随着产出增长率转为负值,其上升势头较为持续。税收产出比并没有缓解政府债务压力,这使债务产出比增长1.84%。而对于PM/AF,国债增发产生的铸币税效应引起了持续的要素回报率提升和经济增长,这进而为改善财政政策实施空间创造了条件。虽然PM/AF下的实际利率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政府偿债负担,但更高的产出增长率(0.08%)能够降低债务产出比的增长率(1.36%)。消费和要素回报率的增加非但没有加重经济个体的税费负担,反而减轻了财政支出的债务融资压力。
图4刻画了增加公共投资时的宏观经济效应,从中可见公共投资的生产性特征提高了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进而扩大了企业要素需求。在PM/AF下,公共投资冲击在供需两端的同步扩张使产出增长了0.44%,远高于AM/PF。根据菲利普斯曲线,考虑到企业边际生产成本和公共资本负相关,加大公共投资就会抑制价格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增发国债所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就会弱化。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不仅仅取决于上述传导机制。在PM/AF下,公共投资冲击所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仍将成立。中间产品企业将从价格上升和成本降低之间获取更大收益,通过生产和分配渠道扩大供需两端。总之,AM/PF下的产出增长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冲击本身,而PM/AF能够通过价格水平变动形成自发的生产扩大化。
图4“三重压力”下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增加民生支出下的情况相似,增加公共投资时,PM/AF下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财政政策实施空间仍然优于AM/PF。第一,在定量的公共投资冲击下,税收产出比在PM/AF下的增幅更大,从而能够更好地缓解债务融资压力。第二,相比于AM/PF,虽然在PM/AF下的实际利率上升会提高政府偿债成本,但更高的产出增长降低了债务产出比。
(三)“三重压力”下减税和增支的综合效果
财政收支同步扩张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扩大赤字,这对财政政策实施空间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更大挑战。2020年,中国延续了减税和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其中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项社会保险等相关费用的减免达到1.54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5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jd/xwfbh/lxxwfbh/202101/t20210128_408638.html。。鉴于本文中的劳动所得税已经包含社保缴费,故将社保费用减免作为减税降费的一个量化指标,换算为劳动所得税税率从7.00%降至3.98%来进行数值模拟。
图5的结果显示,政府通过PM/AF下调劳动所得税税率来提升劳动供给和投资,使产出相对于“三重压力”增长了0.50%。增发国债所触发的通货膨胀进一步通过价格渠道提高了企业收益,这与前面分析一致。虽然劳动所得税税率与国债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通过PM/AF形成了一种更为高效的协作机制。与之相对的是,AM/PF下的产出相对于“三重压力”仅增长了0.25%,原因在于国债融资的通货膨胀效应在AM/PF下会被中央银行的稳通货膨胀目标所抵消,提高资本所得税税率所产生的李嘉图等价效应使减税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执行。最终,企业投资未能得到足够的激励,减税的积极影响也会弱化。图5“三重压力”下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的宏观经济效应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减税的宏观经济效应,接下来同时模拟减税降费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效果。利用政策冲击满足εCGt=0.50、εIGt=2.41和εwt=-0.02进行模拟可得到图6的结果。本文同时还模拟εCGt=0.50和εIGt=2.41时的宏观经济效果,并使用虚线和实线来分别表示AM/PF和PM/AF。
图6的模拟结果表明,同步的增支和减税政策能够进一步促进产出增长,并且这一效果在PM/AF下更为持续。这一现象的核心理论机制在于由减税引发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转嫁到国债融资之上,使PM/AF的通货膨胀效应仍然成立。和前述分析相同,PM/AF下的要素价格上涨同时意味着税收增加和政府偿债能力增强,税收产出比的增长率从3.35%降至-1.10%,这远高于AM/PF下的-5.24%,同时债务产出比的增长率从10.30%增至16.13%。而在AM/PF下,由于财政支出需要通过税率进行融资,这将不可避免地和减税降费的政策目标相悖。如图6所示:一方面,尽管2020年第一季度的劳动所得税税率降低,但资本所得税税率将呈现出更加显著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债务产出比从增长14.30%提升至22.01%,也明显高于PM/AF的对应值。
图6“三重压力”下减税和增支对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五、“三重压力”下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评估
本部分通过计算“三重压力”下的财政支出乘数和福利增益指标,更清晰地概括财政政策效能,并为财政工具以及财政货币组合的选取提供更为精准和全面的依据。
(一)财政支出乘数
财政支出乘数是政府增加1单位支出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评估财政政策效能的关键指标。比如,1单位财政支出带来的产出增加量,就是财政支出的产出乘数。本文在模拟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和比较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支出乘数,重点关注产出、消费、投资以及劳动时间乘数,采用定基方法,以2020年第一季度作为基准期,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计算三年内的现值财政支出乘数:
MXG,t=∑th=0βhXFh-XTPh/∑th=0βhGFh-GTPh28
其中,GTPh和XTPh分别为财政支出和目标变量在“三重压力”下的取值,GFh和XFh分别为财政支出工具和目标变量在“三重压力”期间的取值。分子部分表示财政支出增量在“三重压力”期间的累计贴现值,分母部分表示目标变量的增量在“三重压力”期间的累计贴现值。
为了对民生支出和公共投资的政策效果加以横向比较,图7描绘了不同变量的财政支出乘数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图7“三重压力”下的财政支出乘数图7更加直观地表明,增加民生支出偏向于恢复消费,而增加公共投资侧重于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增加民生支出使消费的即期乘数达到2.29,并且这一数值几乎不随财政货币组合体制而发生转移。这表明政府每增加1单位的民生支出,将带来2.29个单位的消费增长。并且在民生支出冲击淡出之后,三年期的消费乘数仍保持在2以上。此外,产出乘数和劳动时间的即期乘数相对较低,而且投资的即期乘数降为负值,这主要是因为民生支出通过跨期替代路径挤出了私人投资。由于公共投资的生产性,增加公共投资产生了更大的产出和劳动时间乘数。值得注意的是,在PM/AF下,私人投资的乘数从基期的-0.87增至三年期的0.69,这一转变表明公共投资冲击从“挤出”投资逐渐转变为“挤入”投资,进而产生显著的经济提振效果。
积极财政政策在PM/AF下的乘数效应相对于AM/PF更为显著。增加民生支出时,除了消费乘数基本不变以外,PM/AF下的各项乘数均高于AM/PF,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扩大。增加公共投资时,PM/AF下三年期的产出乘数达到了2.57,高于AM/PF下的1.90,也就是说在PM/AF下增加1单位的公共投资能带来2.57个单位的产出增长。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民生支出和公共投资各司其职,在缓解“三重压力”方面展示出一定的互补关系,共同实现稳消费、促增长和稳预期的目标。
(二)社会福利效应
借鉴Bhattarai等[11]的思路来度量积极财政政策在“三重压力”下的福利效应,考虑如下等式成立:
∑th=0βhUCh,CGh,Nh=∑th=0βhU1+ceTPC,CG,N29
其中,式(29)左侧表示家庭部门效用在给定时期内的贴现之和,Ch、CGh和Nh是内生变量,而等式右侧C、CG和N表示固定的稳态水平。ceTP是家庭部门为了规避“三重压力”而必须放弃的消费量相对于稳态消费的百分比。这一指标通常被称作“福利增益”[11],它将福利测度集中于家庭实际获得的消费之上,从而能更直观地反映出家庭福利的变动。
从表1的结果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的“三重压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福利损失:为了规避“三重压力”,家庭愿意将消费水平降至稳态消费的90.92%。由于消费和劳动时间的演变路径是通过现实数据匹配得到,因此福利增益在两种财政货币组合下是等价的。在AM/PF下,增加民生支出的福利效应等价于居民消费相对于稳态降低了7.27%,而这一数值在PM/AF下为719%。相对于“三重压力”的基准情形,福利增益分别提升了19.93%和20.81%。同理,增加公共投资的福利效应等价于居民消费相对于稳态降低了7.54%和7.00%,并且相对于基准情形分别提升了16.96%和2291%。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时,福利增益分别提升至-9.02%和-8.68%,相对于“三重压力”分别提高了0.66%和4.41%。表1“三重压力”下积极财政政策的福利增益结果%反事实情景ceTPAM/PFPM/AF“三重压力”-9.08-9.08“三重压力”+cGt从8.19%增至8.70%-7.27-7.19“三重压力”+iGt从3.29%增至5.70%-7.54-7.00“三重压力”+τwt从7.00%降至3.98%-9.02-8.68此外,本文还通过计算福利增益在每期的增量,考察社会福利在积极财政政策下变化的绝对大小和持续性。这一增量从2020年第四季度到2022年第四季度的变动情况如图8所示。结果表明:第一,民生支出进入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使得这种民生兜底政策直接提升了社会福利,这种提升作用同时也依赖民生支出冲击的持续性;第二,增加公共投资和削减劳动所得税时,福利增益在PM/AF下的增量均明显大于AM/PF下的对应值,且更为持续;第三,综合来看,减税+增支在PM/AF下的福利改进效果优于AM/PF,其中增加民生支出发挥了主要作用。
图8“三重压力”下积极财政政策的福利增益变化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中国近年来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这对于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实现精准的宏观调控以及加强政策协同提出了迫切要求。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既未能考虑“三重压力”的理论模型构建,也没有充分重视政策协同的作用,因此无法为中国在“三重压力”期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尤其难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提供定量的理论见解。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NKDSGE模型,模拟“三重压力”的经济环境,定量分析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乘数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并且刻画财政货币组合体制在应对“三重压力”挑战中的作用。
研究主要得出三点结论。首先,政府增加民生支出不仅能促进居民消费,还能化解“三重压力”带来的福利损失。这是因为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能够提高居民消费及效用水平,在经济下行期间发挥关键的民生兜底功能。其次,在“三重压力”期间选取适当的财政货币组合,对于强化政府公共投资的稳增长效果发挥着关键作用。在PM/AF下,增加公共投资能产生更大的产出乘数和更持续的社会福利效应,其主要机制在于为财政支出扩张进行的债务融资能够产生适度的通货膨胀。利率政策在这种组合下选择容忍通货膨胀,不仅有助于改善企业盈利能力还能避免通货紧缩陷阱,从而增强公共投资在供需两端的双重刺激作用。最后,政府在PM/AF下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征劳动所得税不仅能促进经济复苏,还能通过扩大税收收入来降低债务压力,有效突破AM/PF下的李嘉图等价约束,从而显示出更强的政策协同效应。基于上述三点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财政资金投向民生保障领域的比重,应对消费需求减弱挑战。扩大消费是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近年来,中国消费增速减缓,消费预期较弱,扩大消费已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点。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本文结论不仅支持这一点,还认为应通过民生支出和私人消费的互补性,发挥国债的民生性功能和民生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加大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民生兜底工作,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而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确保民生福祉的广泛覆盖和可持续。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下沉力度,从而使财政释放出的流动性能有效分配到私人部门。
第二,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通过发挥国债的生产性功能,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在“三重压力”下,政府需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作用,通过公共投资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互补性来提升公共投资对于企业生产的溢出效应,发挥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撬动作用,进而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然而,如果货币政策恪守泰勒原则,那么“三重压力”将穿透这种政策反馈机制,不利于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相对于AM/PF,PM/AF下的公共投资冲击在应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时无疑更具应用前景。一方面,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协调能够更有效地化解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即使公共投资政策淡出以后,PM/AF产生更高的价格水平也能扩大投资需求,内源地扩大企业生产。
第三,在非常时期,货币融资或者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可用的非常之策。当政府面临同时维持财政支出、降低税负和控制债务的“不可能三角”,PM/AF框架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恢复经济增速和扩大税收两方面的作用,从而为缓解政府债务压力提供更多的正面反馈。如果减税降费势在必行,那么PM/AF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能突破李嘉图等价的约束,成为走出“不可能三角”的可行途径。虽然本文并未针对货币供应进行理论建模,但通过向家庭部门发行国债来资助财政扩张,能够加强财政资金的流通和使用,从而实现与货币扩张类似的效果。据此,本文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尚无须逾越禁止中央银行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这一传统边界。政策制定者应聚焦如何准确识别出“三重压力”下的核心症结所在,并据此制定高效的财政货币协调方案,使财政货币的有效协同成为中国经济的内生特点。
参考文献:
[1]李永友,杨春飞.中国财政抉择弹性空间估计[J].经济研究,2023(5):2340.
[2]吕冰洋,曾傅雯,涂海洋,等.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分析:研究框架与综合判断[J].管理世界,2024(1):120.
[3]刘尚希,盛松成,伍戈,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讨论[J].国际经济评论,2020(4):927.
[4]GALIJ.Theeffectsofamoneyfinancedfiscalstimulus[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20,115:119.
[5]何增平,贾根良.财政赤字货币化:对现代货币理论误读的概念[J].学习与探索,2022(4):101110.
[6]LEEPEREM.Equilibriaunder“active”and“passive”monetaryandfiscalpolicies[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1,27(1):129147.
[7]WOODFORDM.Priceleveldeterminacywithoutcontrolofamonetaryaggregate[J].CarnegieRochesterConferenceSeriesonPublicPolicy,1995,43:146.
[8]LEEPEREM,LEITHC.Understandinginflationasajointmonetaryfiscalphenomenon[M]//Handbookofmacro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Press,2016:23052415.
[9]杨源源,于津平,尹雷.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式选择[J].财贸经济,2019(1):2035.
[10]LIUD,SUNW,CHANGL.MonetaryfiscalpolicyregimeandmacroeconomicdynamicsinChina[J].EconomicModelling,2021,95:121135.
[11]BHATTARAIS,LEEJW,YANGC.Redistributionandthemonetaryfiscalpolicymix[J].QuantitativeEconomics,2023,14(3):817853.
[12]BIANCHIF,FACCINIR,MELOSIL.Afiscaltheoryofpersistentinflation[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23,138(4):21272179.
[13]CALVOGA.Staggeredpricesinautilitymaximizingframework[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3,12(3):383398.
[14]李力,温来成,唐遥,等.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J].经济研究,2020(11):3649.
[15]张龙,王姝,周佰成,等.财政规则、政策取向识别及动态反馈机制研究[J].经济学(季刊),2023(2):676694.
[16]FARIAECASTROM.Fiscalpolicyduringapandemic[J].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21,125:104088.
[17]HINTERLANGN,MOYENS,ROHEO,etal.GaugingtheeffectsoftheGermanCovid19fiscalstimuluspackage[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23,154:104407.
[18]刘汉,王李俊,刘金全.三重压力下经济下行的识别与溯源[J].经济科学,2023(6):527.
[19]蔡昉,张丹丹,刘雅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J].经济研究,2021(2):421.
[20]陈彦斌,刘哲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应对“三重压力”[J].财经问题研究,2022(3):39.
[21]高然,祝梓翔,陈忱.地方债与中国经济波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2(6):83100.
[22]卞志村,赵亮,丁慧.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J].经济研究,2019(9):5672.
[23]王文甫,王召卿,郭柃沂.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失衡[J].经济研究,2020(5):4965.
[24]李戎,田晓晖.财政支出类型、结构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J].中国工业经济,2021(2):4260.
[25]李戎,刘力菲.制度优势、货币政策协调与财政拉动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1(10):2038.
[26]郭长林.财政政策扩张、异质性企业与中国城镇就业[J].经济研究,2018(5):88102.
[27]严玉华,王燕武.中国财政扩张的消费倾斜效应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6(1):4049.
[28]王立勇,纪尧.财政政策波动性与财政规则:基于开放条件DSGE模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9(6):121135.
[29]彭俞超,鄢莉莉,方意.保经济增长下限与非线性财政政策:基于偶然约束模型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20(1):309328.
[30]张成思,刘瑶琚,王芳.国债流动性效应与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机制[J].管理世界,2023(5):925.
[31]CHENK,HIGGINSP,ZHAT.ConstructingquarterlyChinesetimeseriesusableformacroeconomicanalysis[J].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2024,143:103052.
[本刊相关文献链接]
[1]徐宁,丁一兵.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J].当代经济科学,2024(5):112.
[2]甘林针,钟钰.财政分权、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与粮食生产[J].当代经济科学,2024(4):112123.
[3]车树林,石奇.“双碳”目标下的金融摩擦与宏观审慎政策效应[J].当代经济科学,2023(6):1428.
[4]马海涛,秦士坤.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J].当代经济科学,2023(6):4457.
[5]刘灵辉,张迎新,傅鑫艺.从分权看发展:“省直管县”改革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23(2):5872.
[6]唐晓华,李静雯.经济增长目标、策略性财政政策与产业协同集聚[J].当代经济科学,2023(2):7387.
[7]庞伟,岳树民,孙玉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回弹效应”:机制与检验[J].当代经济科学,2023(2):4457.
[8]徐宝亮,李康,邓宏图.财政分权度与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政府与市场边界迁移的理论与经验解释[J].当代经济科学,2022(6):8496.
[9]任曙明,李莲青,卢佳蔓,等.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2(5):1427.
[10]尹雷,吴静,丁烨.开放经济条件下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的货币政策外溢效应与调控[J].当代经济科学,2022(1):112.
[11]吴立元,刘研召,赵扶扬,等.PPI与CPI背离、金融摩擦异质性与货币政策选择[J].当代经济科学,2021(3):115.
[12]唐晓华,景文治.多级政府框架下信号激励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19(6):1324.
[13]刘希章,李富有,邢治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与产业升级效应:基于结构主义增长理论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17(1):2129.
编辑:张静,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