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形赋义与为义塑形:非现实“再VP”的两种构式化路径
2024-12-08王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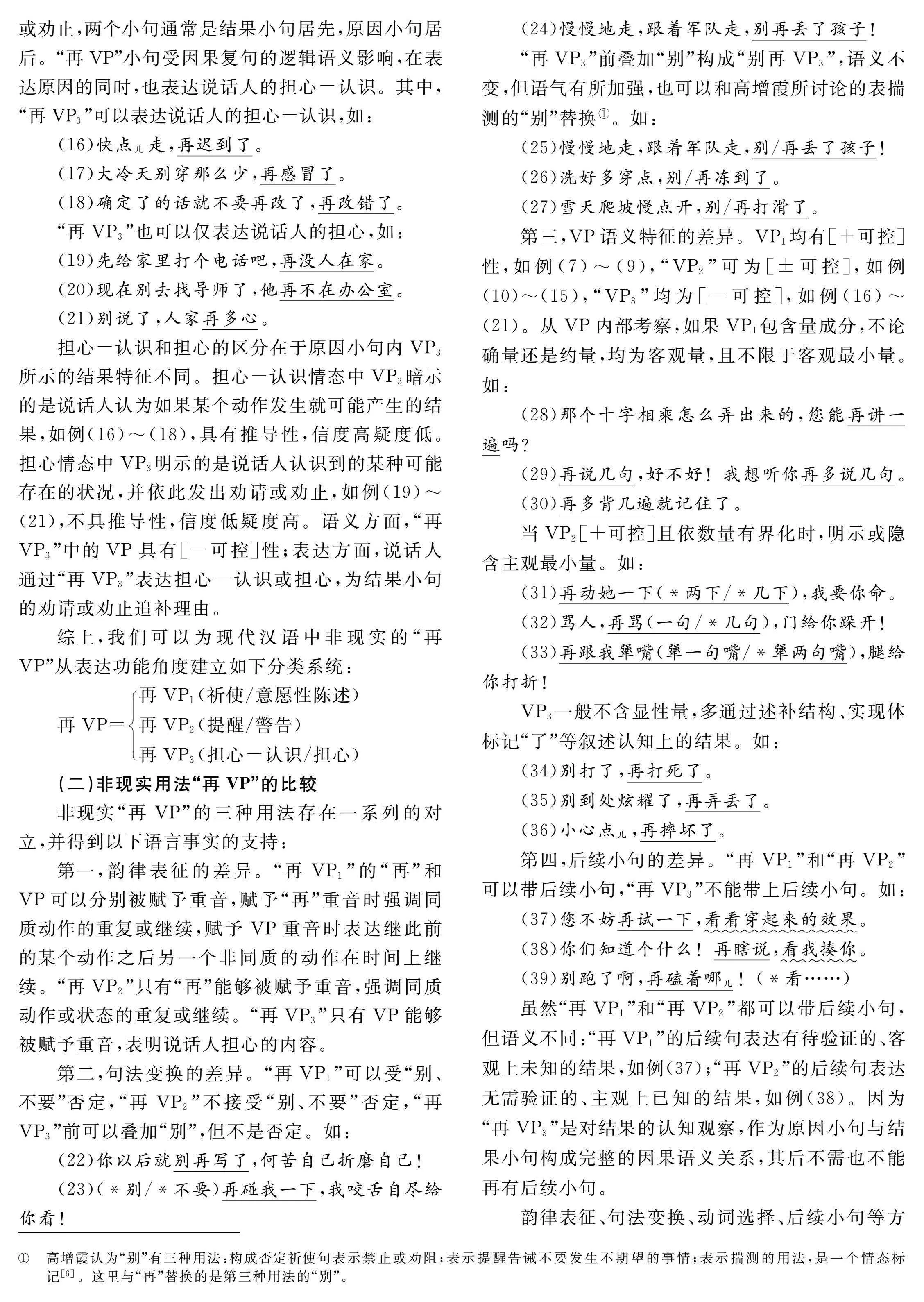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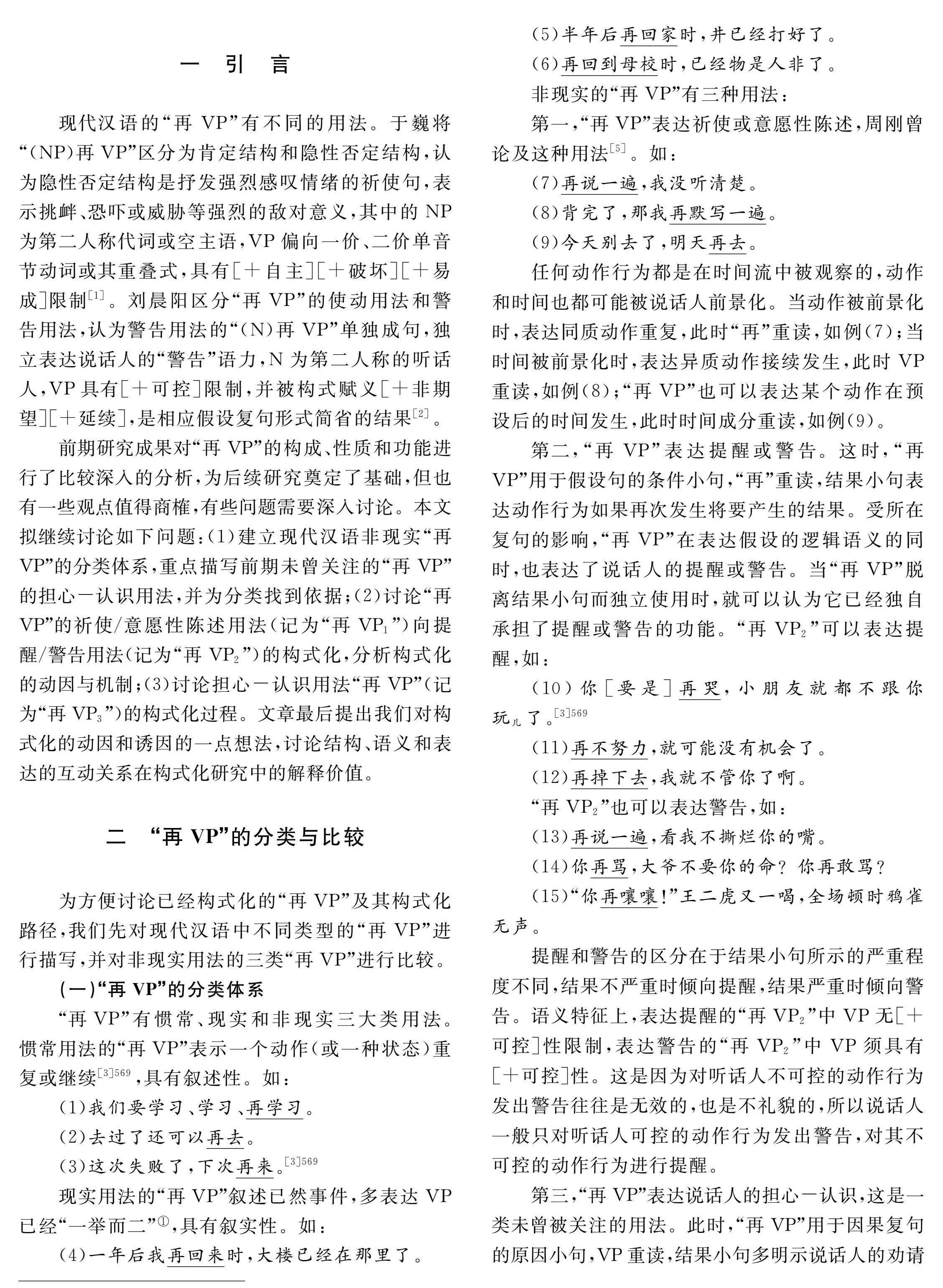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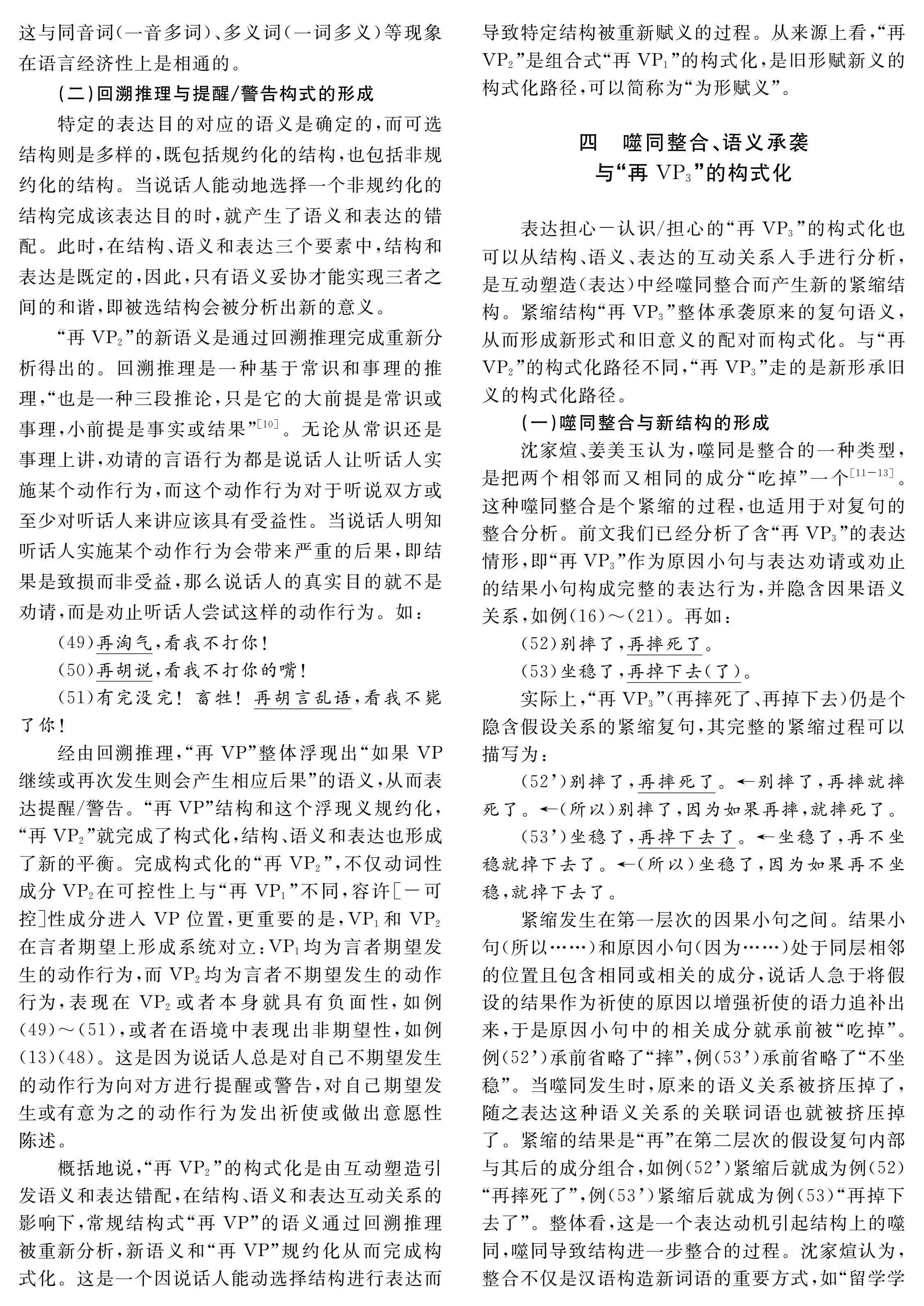
[摘 要] 通过结构、语义和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发现,非现实“再VP”有祈使/意愿性陈述“再VP1”、提醒/警告“再VP2”、担心-认识/担心“再VP3”三种用法。“再VP2”由互动塑造引发语义和表达错配,经回溯推理重新赋义,新语义和“再VP”规约化而完成构式化,这是构式化的为形赋义路径。“再VP3”由互动塑造引发噬同整合并产生新结构,新结构承袭复句语义而构式化,这是构式化的为义塑形路径。结构、语义和表达之间不仅具有平行关系,更重要的是还有互动关系。从结构、语义和表达的互动视角出发,可以对构式化和语法化做出合理的解释,可以将语法化的动因和诱因联系起来,值得深入讨论。
[关键词] 为形赋义;为义塑形;再VP;构式化
[中图分类号] H146;H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4)06-0096-07
Creating Meaning for Form and Creating Form for Meaning:
Two Constructive Paths of Non-Real “zai(再)VP”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n the Structure, Semantics
and Expression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WANG Shik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Through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structure, semantics, and expres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non-real “zai(再)VP” has three usages: imperative/willingness statement “zai(再)VP1” ,reminder/warning “zai(再)VP2”,and worry-recognition/worry “zai(再)VP3”.“zai(再)VP2” is shaped by interaction, leading to semantic and expression mismatches, which are redefined through retrospective reasoning; the new semantics and “zai(再)VP” become conventionalized,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process. It is the path of creating meaning for form in constructionalization. “zai(再)VP3” is shaped by intera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integration of similar structures and generates syntactic innovation; the new structure absorbs the semantics of complex sentences and undergoes constructionalization. It is the path of creating form for meaning in constructionalization. There is not only a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semantics and express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re is also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From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semantics and expression, we can mak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an link the motivation and inducement of grammaticaliz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n in-depth discussion.
Key words: creating meaning for form;creating form for meaning;zai(再)VP; constructionalization
一 引 言
现代汉语的“再VP”有不同的用法。于巍将“(NP)再VP”区分为肯定结构和隐性否定结构,认为隐性否定结构是抒发强烈感叹情绪的祈使句,表示挑衅、恐吓或威胁等强烈的敌对意义,其中的NP为第二人称代词或空主语,VP偏向一价、二价单音节动词或其重叠式,具有[+自主][+破坏][+易成]限制[1]。刘晨阳区分“再VP”的使动用法和警告用法,认为警告用法的“(N)再VP”单独成句,独立表达说话人的“警告”语力,N为第二人称的听话人,VP具有[+可控]限制,并被构式赋义[+非期望][+延续],是相应假设复句形式简省的结果[2]。
前期研究成果对“再VP”的构成、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有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本文拟继续讨论如下问题:(1)建立现代汉语非现实“再VP”的分类体系,重点描写前期未曾关注的“再VP”的担心-认识用法,并为分类找到依据;(2)讨论“再VP”的祈使/意愿性陈述用法(记为“再VP1”)向提醒/警告用法(记为“再VP2”)的构式化,分析构式化的动因与机制;(3)讨论担心-认识用法“再VP”(记为“再VP3”)的构式化过程。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对构式化的动因和诱因的一点想法,讨论结构、语义和表达的互动关系在构式化研究中的解释价值。
二 “再VP”的分类与比较
为方便讨论已经构式化的“再VP”及其构式化路径,我们先对现代汉语中不同类型的“再VP”进行描写,并对非现实用法的三类“再VP”进行比较。
(一)“再VP”的分类体系
“再VP”有惯常、现实和非现实三大类用法。惯常用法的“再VP”表示一个动作(或一种状态)重复或继续[3]569,具有叙述性。如:
(1)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2)去过了还可以再去。
(3)这次失败了,下次再来。[3]569
现实用法的“再VP”叙述已然事件,多表达VP已经“一举而二”
《说文解字》释“再”为“一举而二也”,任学良解作“同样的举动而重复之”,认为“再”有“重(重复)”之义[4]。,具有叙实性。如:
(4)一年后我再回来时,大楼已经在那里了。
(5)半年后再回家时,井已经打好了。
(6)再回到母校时,已经物是人非了。
非现实的“再VP”有三种用法:
第一,“再VP”表达祈使或意愿性陈述,周刚曾论及这种用法[5]。如:
(7)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8)背完了,那我再默写一遍。
(9)今天别去了,明天再去。
任何动作行为都是在时间流中被观察的,动作和时间也都可能被说话人前景化。当动作被前景化时,表达同质动作重复,此时“再”重读,如例(7);当时间被前景化时,表达异质动作接续发生,此时VP重读,如例(8);“再VP”也可以表达某个动作在预设后的时间发生,此时时间成分重读,如例(9)。
第二,“再VP”表达提醒或警告。这时,“再VP”用于假设句的条件小句,“再”重读,结果小句表达动作行为如果再次发生将要产生的结果。受所在复句的影响,“再VP”在表达假设的逻辑语义的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的提醒或警告。当“再VP”脱离结果小句而独立使用时,就可以认为它已经独自承担了提醒或警告的功能。“再VP2”可以表达提醒,如:
(10)你[要是]再哭,小朋友就都不跟你玩儿了。[3]569
(11)再不努力,就可能没有机会了。
(12)再掉下去,我就不管你了啊。
“再VP2”也可以表达警告,如:
(13)再说一遍,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14)你再骂,大爷不要你的命?你再敢骂?
(15)“你再嚷嚷!”王二虎又一喝,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提醒和警告的区分在于结果小句所示的严重程度不同,结果不严重时倾向提醒,结果严重时倾向警告。语义特征上,表达提醒的“再VP2”中VP无[+可控]性限制,表达警告的“再VP2”中VP须具有[+可控]性。这是因为对听话人不可控的动作行为发出警告往往是无效的,也是不礼貌的,所以说话人一般只对听话人可控的动作行为发出警告,对其不可控的动作行为进行提醒。
第三,“再VP”表达说话人的担心-认识,这是一类未曾被关注的用法。此时,“再VP”用于因果复句的原因小句,VP重读,结果小句多明示说话人的劝请或劝止,两个小句通常是结果小句居先,原因小句居后。“再VP”小句受因果复句的逻辑语义影响,在表达原因的同时,也表达说话人的担心-认识。其中,“再VP3”可以表达说话人的担心-认识,如:
(16)快点儿走,再迟到了。
(17)大冷天别穿那么少,再感冒了。
(18)确定了的话就不要再改了,再改错了。
“再VP3”也可以仅表达说话人的担心,如:
(19)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再没人在家。
(20)现在别去找导师了,他再不在办公室。
(21)别说了,人家再多心。
担心-认识和担心的区分在于原因小句内VP3所示的结果特征不同。担心-认识情态中VP3暗示的是说话人认为如果某个动作发生就可能产生的结果,如例(16)~(18),具有推导性,信度高疑度低。担心情态中VP3明示的是说话人认识到的某种可能存在的状况,并依此发出劝请或劝止,如例(19)~(21),不具推导性,信度低疑度高。语义方面,“再VP3”中的VP具有[-可控]性;表达方面,说话人通过“再VP3”表达担心-认识或担心,为结果小句的劝请或劝止追补理由。
综上,我们可以为现代汉语中非现实的“再VP”从表达功能角度建立如下分类系统:
再VP=再VP1(祈使/意愿性陈述)
再VP2(提醒/警告)
再VP3(担心-认识/担心)
(二)非现实用法“再VP”的比较
非现实“再VP”的三种用法存在一系列的对立,并得到以下语言事实的支持:
第一,韵律表征的差异。“再VP1”的“再”和VP可以分别被赋予重音,赋予“再”重音时强调同质动作的重复或继续,赋予VP重音时表达继此前的某个动作之后另一个非同质的动作在时间上继续。“再VP2”只有“再”能够被赋予重音,强调同质动作或状态的重复或继续。“再VP3”只有VP能够被赋予重音,表明说话人担心的内容。
第二,句法变换的差异。“再VP1”可以受“别、不要”否定,“再VP2”不接受“别、不要”否定,“再VP3”前可以叠加“别”,但不是否定。如:
(22)你以后就别再写了,何苦自己折磨自己!
(23)(*别/*不要)再碰我一下,我咬舌自尽给你看!
(24)慢慢地走,跟着军队走,别再丢了孩子!
“再VP3”前叠加“别”构成“别再VP3”,语义不变,但语气有所加强,也可以和高增霞所讨论的表揣测的“别”替换高增霞认为“别”有三种用法:构成否定祈使句表示禁止或劝阻;表示提醒告诫不要发生不期望的事
情;表示揣测的用法,是一个情态标记[6]。这里与“再”替换的是第三种用法的“别”。。如:
(25)慢慢地走,跟着军队走,别/再丢了孩子!
(26)洗好多穿点,别/再冻到了。
(27)雪天爬坡慢点开,别/再打滑了。
第三,VP语义特征的差异。VP1均有[+可控]性,如例(7)~(9),“VP2”可为[±可控],如例(10)~(15),“VP3”均为[-可控],如例(16)~(21)。从VP内部考察,如果VP1包含量成分,不论确量还是约量,均为客观量,且不限于客观最小量。如:
(28)那个十字相乘怎么弄出来的,您能再讲一遍吗?
(29)再说几句,好不好!我想听你再多说几句。
(30)再多背几遍就记住了。
当VP2[+可控]且依数量有界化时,明示或隐含主观最小量。如:
(31)再动她一下(*两下/*几下),我要你命。
(32)骂人,再骂(一句/*几句),门给你跺开!
(33)再跟我犟嘴(犟一句嘴/*犟两句嘴),腿给你打折!
VP3一般不含显性量,多通过述补结构、实现体标记“了”等叙述认知上的结果。如:
(34)别打了,再打死了。
(35)别到处炫耀了,再弄丢了。
(36)小心点儿,再摔坏了。
第四,后续小句的差异。“再VP1”和“再VP2”可以带后续小句,“再VP3”不能带上后续小句。如:
(37)您不妨再试一下,看看穿起来的效果。
(38)你们知道个什么!再瞎说,看我揍你。
(39)别跑了啊,再磕着哪儿!(*看……)
虽然“再VP1”和“再VP2”都可以带后续小句,但语义不同:“再VP1”的后续句表达有待验证的、客观上未知的结果,如例(37);“再VP2”的后续句表达无需验证的、主观上已知的结果,如例(38)。因为“再VP3”是对结果的认知观察,作为原因小句与结果小句构成完整的因果语义关系,其后不需也不能再有后续小句。
韵律表征、句法变换、动词选择、后续小句等方面的差异反映的是语义、表达和认知的不同。语义表达方面,“再VP1”表达的祈使/意愿性陈述可由“重复或继续”义的“再”和VP加合得出,组合特征明显。“再VP2”中的“再”虽仍为“重复或继续”义,但整个结构表达的提醒/警告已经不能由要素组合推导而出,组构性降低。“再VP3”表达的担心-认识或担心也不能从“再”和“VP”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推导得出,组构性降低。从三域角度观察,“再VP1”和“再VP2”属于言域,分别发出劝请和劝止的指令,再“VP3”属于知域,反映说话人的认知推理或推测。
三 互动塑造、回溯推理
与“再VP2”的构式化
刘晨阳认为,表达警告的“再VP”构式是相应假设复句形式简省的结果,得益于语用频率、认知思维、伴随形式的共同推动[2]。这种解释不无道理。我们认为:表达提醒/警告的“再VP2”的构式化可以从结构、语义、表达的互动关系入手进行分析,是互动塑造中说话人的结构选择引发语义和表达错配,经回溯推理语义被重新分析进而构式化,走的是旧形式赋新义的构式化路径。
(一)互动塑造与语义和表达的错配
朱德熙强调:进行语法研究,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结构平面研究句子里各部分之间形式上的关系。语义平面研究这些部分意义上的联系。表达平面研究同一种语义关系的各种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区别。这三个平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7]37此前的研究更加关注三个平面之间的区别,本文更重视其间的联系,尤其是不同平面之间的互动关系。
互动交际中,说话人永远都是带着既定的交际目的(表达)去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结构)以表达出服务该交际目的的意义(语义)。实现相同的表达目的,说话人既可以选择与表达目的相契合的规约化的表达形式,也可以能动地选择非规约化的表达形式。前者是一种常规的情形,后者则是一种超常规的情形。就“再VP”而论,“再VP1”是表达祈使/意愿性陈述的常规结构。祈使/意愿性陈述均蕴含尝试,而“一个完整的尝试事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动作行为的尝试,二是对尝试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的观察”[8],因此,表达祈使/意愿性陈述的“再VP2”后经常带上验证小句,表示有待验证的结果,具有[+有待验证]的特点。如:
(40)今天回家再试试,看能不能有松软的效果。
(41)再等会,看他们打电话不?
(42)再梳理一下,看看什么地方漏掉了。
此时,“重复或继续VP”的语义与说话人祈使/意愿性陈述的表达目的是和谐的,“再VP”是常规的结构式。互动交际中,当说话人能动地使用“再VP”进行创新表达,如:
(43)你们知道个什么!再瞎说,看我揍你。
(44)你再给我装!我把你这输液管子拔了你信不信?赶紧说!
(45)再让小毓哭,看我不剁了你!
这时,验证小句表达的是言者认定的、实施VP将产生的后果,具有[-有待验证]特征。从验证小句与“再VP”小句的假设关系可以推知,说话人使用“再VP”的表达目的并非祈使或意愿性陈述,而是提醒或警告,隐含劝止。这样就形成了表达上的“劝止”与常规结构式“再VP”规约化“劝请”义之间的矛盾,语义和表达形成错配。
那么,说话人何以选用表达劝请的形式去实现劝止的表达目的?一方面,“再VP2”和“再VP1”在结构和语义上密切关联,对比如下:
(46)再说一遍。(再VP1/2)
(47)再说一遍嘛!你再说一遍。(再VP1)
(48)再说一遍?敢再说生老头的气,我就敢扇你!(再VP2)
从表达角度看,例(46)既可以表达祈使或意愿性陈述,也可以表达提醒或警告。例(47)只能表达祈使,是常规用法,例(48)只能表达警告,是超常规的变异用法。但是,从构成要素角度看,“再VP2”的“再”仍表示“重复或继续”,整体结构表面上与表达劝请的“再VP1”也一致。此外,不论“劝请”还是“劝止”,都是通过“劝”来达到特定交际目的,二者在“劝”的角度上仍是相同的。此外,这种表达法符合语言经济原则,便于解决形式有限与意义无限之间的矛盾。“一种语言的句型再丰富,跟人类所要表达的客观事物和主观思想感情相比总是有限的,为了利用有限的句型表达无限丰富的语义要求,就需要突破常规句式规范的束缚。”[9]让一个结构承担不同的语义或表达功能,这恰好是汉语中常见的现象。这与同音词(一音多词)、多义词(一词多义)等现象在语言经济性上是相通的。
(二)回溯推理与提醒/警告构式的形成
特定的表达目的对应的语义是确定的,而可选结构则是多样的,既包括规约化的结构,也包括非规约化的结构。当说话人能动地选择一个非规约化的结构完成该表达目的时,就产生了语义和表达的错配。此时,在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要素中,结构和表达是既定的,因此,只有语义妥协才能实现三者之间的和谐,即被选结构会被分析出新的意义。
“再VP2”的新语义是通过回溯推理完成重新分析得出的。回溯推理是一种基于常识和事理的推理,“也是一种三段推论,只是它的大前提是常识或事理,小前提是事实或结果”[10]。无论从常识还是事理上讲,劝请的言语行为都是说话人让听话人实施某个动作行为,而这个动作行为对于听说双方或至少对听话人来讲应该具有受益性。当说话人明知听话人实施某个动作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结果是致损而非受益,那么说话人的真实目的就不是劝请,而是劝止听话人尝试这样的动作行为。如:
(49)再淘气,看我不打你!
(50)再胡说,看我不打你的嘴!
(51)有完没完!畜牲!再胡言乱语,看我不毙了你!
经由回溯推理,“再VP”整体浮现出“如果VP继续或再次发生则会产生相应后果”的语义,从而表达提醒/警告。“再VP”结构和这个浮现义规约化,“再VP2”就完成了构式化,结构、语义和表达也形成了新的平衡。完成构式化的“再VP2”,不仅动词性成分VP2在可控性上与“再VP1”不同,容许[-可控]性成分进入VP位置,更重要的是,VP1和VP2在言者期望上形成系统对立:VP1均为言者期望发生的动作行为,而VP2均为言者不期望发生的动作行为,表现在VP2或者本身就具有负面性,如例(49)~(51),或者在语境中表现出非期望性,如例(13)(48)。这是因为说话人总是对自己不期望发生的动作行为向对方进行提醒或警告,对自己期望发生或有意为之的动作行为发出祈使或做出意愿性陈述。
概括地说,“再VP2”的构式化是由互动塑造引发语义和表达错配,在结构、语义和表达互动关系的影响下,常规结构式“再VP”的语义通过回溯推理被重新分析,新语义和“再VP”规约化从而完成构式化。这是一个因说话人能动选择结构进行表达而导致特定结构被重新赋义的过程。从来源上看,“再VP2”是组合式“再VP1”的构式化,是旧形赋新义的构式化路径,可以简称为“为形赋义”。
四 噬同整合、语义承袭
与“再VP3”的构式化
表达担心-认识/担心的“再VP3”的构式化也可以从结构、语义、表达的互动关系入手进行分析,是互动塑造(表达)中经噬同整合而产生新的紧缩结构。紧缩结构“再VP3”整体承袭原来的复句语义,从而形成新形式和旧意义的配对而构式化。与“再VP2”的构式化路径不同,“再VP3”走的是新形承旧义的构式化路径。
(一)噬同整合与新结构的形成
沈家煊、姜美玉认为,噬同是整合的一种类型,是把两个相邻而又相同的成分“吃掉”一个[11-13]。这种噬同整合是个紧缩的过程,也适用于对复句的整合分析。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含“再VP3”的表达情形,即“再VP3”作为原因小句与表达劝请或劝止的结果小句构成完整的表达行为,并隐含因果语义关系,如例(16)~(21)。再如:
(52)别摔了,再摔死了。
(53)坐稳了,再掉下去(了)。
实际上,“再VP3”(再摔死了、再掉下去)仍是个隐含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其完整的紧缩过程可以描写为:
(52’)别摔了,再摔死了。←别摔了,再摔就摔死了。←(所以)别摔了,因为如果再摔,就摔死了。
(53’)坐稳了,再掉下去了。←坐稳了,再不坐稳就掉下去了。←(所以)坐稳了,因为如果再不坐稳,就掉下去了。
紧缩发生在第一层次的因果小句之间。结果小句(所以……)和原因小句(因为……)处于同层相邻的位置且包含相同或相关的成分,说话人急于将假设的结果作为祈使的原因以增强祈使的语力追补出来,于是原因小句中的相关成分就承前被“吃掉”。例(52’)承前省略了“摔”,例(53’)承前省略了“不坐稳”。当噬同发生时,原来的语义关系被挤压掉了,随之表达这种语义关系的关联词语也就被挤压掉了。紧缩的结果是“再”在第二层次的假设复句内部与其后的成分组合,如例(52’)紧缩后就成为例(52)“再摔死了”,例(53’)紧缩后就成为例(53)“再掉下去了”。整体看,这是一个表达动机引起结构上的噬同,噬同导致结构进一步整合的过程。沈家煊认为,整合不仅是汉语构造新词语的重要方式,如“留学学生→留学生”,也是汉语构造新句子的重要方式,如“他买了一条鱼重三斤”[11-12]。就本文所讨论的噬同整合而言,经噬同、紧缩而整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结构“再VP3”。这为“再VP3”的构式化准备了结构条件,即“形式-意义”配对中的形式条件。
(二)语义承袭与“再VP3”的构式化
仅仅一个新的结构“再VP3”尚不能说明其已经构式化,只有“再VP3”和一个特定意义结合,且结构的意义不能从组合成分推导而出,才能说明其已经构式化。
首先,语义承袭与“再VP3”赋义。噬同、紧缩只是发生在结构上而不是发生在语义上,即噬同只是吃掉了复句中的相同或相关成分,紧缩只是紧掉了关联词语,语义并不发生变化。噬同整合的结果是原来由假设复句表达的语义最终由紧缩后的“再VP3”承担。这样,“再VP3”由于承袭了复句语义,就已经构造了一个新的形式和特定意义的结合体。
其次,义类变异与非推导性。紧缩前的“再”仍旧表达“一举而二”,如例(52’)中的“再摔”是指动作“摔”重复或继续,例(53’)“再不坐稳”是指动作“不坐稳”继续。我们发现,表示“一举而二”的“再”与VP3是不具备组合条件的。因为在“再VP”的常规结构式中,不论其表达现实、惯常还是祈使/意愿性陈述或提醒/警告,VP都具有[-结果]义类特征,表现在其不能带上体标记“了1”。如:
(1’)*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了1。
(6’)*再回到母校了1时,已经物是人非了。
(7’)*再说一遍了1,我没听清楚。
(11’)*再不努力了1,就可能没有机会了。
而噬同整合造成的“再VP3”中的VP均具有[+结果]义类特征,表现在:第一,表示动作行为的VP后都可以带上体标记“了1”,如例(16)(17)(18)中的“迟到了”“感冒了”“改错了”;第二,VP也常用述结式,如例(33)(34)(35)中的“打死”“弄丢”“摔坏”;第三,当VP为非动作行为动词时,都表示一种具有结果特征的状态,如例(19)(20)(21)中的“没人在家”“不在办公室”“多心”;第四,VP保持着噬同前的义类特征。噬同前VP在结果小句出现,表示说话人假设的认知结果,具有认知心理现实性。这种认知心理现实性与[+结果]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从组合角度看“再VP3”是无法推导出担心或担心-认识义的。
概括地说,“再VP3”的构式化是由互动塑造引发噬同整合并产生新结构,新结构承袭复句语义,形成新形式和旧意义的配对而构式化。这是一个因说话人能动创新结构进行表达而导致新形承旧义的构式化路径,可以简称为“为义塑形”。
五 结论和余论
(一)结论
非现实的“再VP”有祈使/意愿性陈述、提醒/警告、担心-认识/担心三种用法,并在韵律表征、句法变换、动词选择、后续小句等方面表现出对立。表达提醒/警告的“再VP2”的构式化是由互动塑造引发语义和表达错配,经回溯推理“再VP”被重新赋义,新语义和“再VP”规约化进而完成构式化。这是一个因说话人能动选择结构进行表达而导致特定结构在语境中被重新赋义,是旧形式赋新义的“为形赋义”构式化路径。表达担心-认识/担心的“再VP3”的构式化由互动塑造引发噬同整合并产生新结构,新结构承袭噬同前的复句语义,形成新形式和旧意义的配对而构式化。这是一个因说话人能动创新结构进行表达而导致新形式承担原紧缩复句的语义,是新形式承袭旧语义的“为义塑形”构式化路径。
(二)余论
1.动因、诱因与构式化
江蓝生曾系统区分语法化的动因和诱因。“动因”往往着眼于人而不是着眼于语言结构本身,着眼于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通常涉及语用推理和认知心理,如估推(或回溯推理)、转喻和隐喻。“诱因”往往是就语言结构本身来说的,侧重于“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强调诱因不仅包括语义和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必要条件,更主要指向语法化的充分条件,即引发语法化的深层次的结构和语义上的条件。[9]概括地说,语法化的动因是表达驱动,诱因是结构和语义互动。
彭睿等人的研究界定了“构式”与“构式化”两个概念,归纳了图示性、能产性、组合性等构式化的基本特征,区分词汇构式化和语法构式化两种不同的构式化类型,提出“构式化语境”的概念以及基于使用的构式演化模式[14-19]。关于构式化的动因,刘大为等人认为,修辞、重新分析、语用推理、句法语境是构式化或构式变化的重要动因[20-23]。我们认为,如果将构式化严格限定在新的形式-意义配对的形成上,使用的、修辞的才是构式化的动因,可以概括为表达的动因,而重新分析、语用推理等是构式化的机制,构式化语境(句法环境)是构式化的条件,均不是动因。进而言之,表达不仅是构式化的动因,还是要素语法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动因和诱因被联系起来。以“再VP3”的构式化为例。因说话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假设小句和结果小句经过噬同整合而形成了新结构“再VP3”,新结构承袭复句语义而发生构式化。显然,说话人的主观能动性,即表达是引发构式化的原因,而重新分析是“再VP3”得以被看作构式的机制,句法环境是其得以如此进行重新分析的条件。“再VP3”构式化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常规结构式的义类变异,即常规结构式“再VP”中的VP均不具有[+结果]特征,而VP3均具有[+结果]特征,这成为“再”语法化的诱因,“再”也就被重新分析为情态副词。
关于构式化的路径,刘大为认为:“一方面语言不可能为修辞动因的实现准备单独的结构形式,一方面人们也更习惯于以已有的认知图式、交互模式为基础去接受新的认知经验及交互方式,所以修辞动因都是在已有构式上得以实现的。”[20]这已经隐含了构式化的一种路径,即为形赋义的构式化路径。我们认为,理论上,构式化的可能路径有三条:为旧形式赋予新的语义(为形赋义)、让新形式承袭原来的语义(为义塑形)和新形式新意义配对。刘大为所论的情形以及本文分析的“再VP2”的构式化是为形赋义的路径,“再VP3”的构式化是为义塑形的路径。彭睿等人讨论的情形属于新形式新意义配对的路径[14-18]。这些问题都还值得结合汉语实际继续深入讨论,以丰富构式化理论。
2.结构、语义和表达研究对构式化的解释价值
结构、语义和表达,句法、语义和语用,语表、语里和语值是我国三个平面的不同表述,虽然有小异,更根本的是大同。李思旭总结:20世纪80年代南北语言学界几乎同时提出了“三个平面”的思想,三个平面的思想立刻为汉语语言学界所接受,对推进汉语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24]。朱德熙一方面强调进行语法研究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另一方面也重视三个平面的联系和区别[7]37。储泽祥认为语法研究离不开比较,强调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从“表”“里”“值”三个角度看,比较语表,要联系语里、语值,比较语里或语值,也要联系另外两个方面[25]。马庆株主张从结构、语义和表达三方面研究汉语的组合和聚合,强调语义对语法有决定作用,表达对结构和语义具有解释作用[26]。袁毓林认为:“不仅应该分清语法的三个不同的平面,而且应该观察这三个不同的平面之间的互动关系。”[27]这无疑都指向一个问题:既要重视三个平面的平行关系及其在描写上的价值,更要重视三个平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在解释上的价值。彭睿认为构式化理论目前已经建构起了一个基本框架,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拓[14]。我们认为,构式化的动因和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这或许可以从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平面的视角切入进行尝试,三个平面不仅可以充分描写语言现象,也可以对语言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本文以非现实“再VP”的构式化进行了尝试,表明从结构、语义和表达的角度对构式化问题做出解释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至于提炼出更具有普适性和概括性的规律,还需要基于大量汉语事实,进行深入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于巍.“(NP)(T)再VP”结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2] 刘晨阳.警告义“再VP”构式探析[J].语言科学,2016(4):412-421.
[3]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任学良.“去”、“再”的词义史[J].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66-71.
[5] 周刚.说“再”[J].汉语学习,1994(3):28-32.
[6] 高增霞.汉语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别”的语法化[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1):97-102+112.
[7] 朱德熙.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 汤敬安,石毓智.现代汉语的尝试构式[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3):21-30.
[9] 江蓝生.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J].中国语文,2016(5):515-525.
[10]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4):243-251+321.
[11]沈家煊.口误类例[J].中国语文,1992(4):306-316.
[12]沈家煊.“糅合”和“截搭”[J].世界汉语教学,2006(4):5-12+146.
[13]姜美玉.汉语口误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14]彭睿.语法化·历时构式语法·构式化——IYOyhKNnO/hML/IA4Z72zA==历时形态句法理论方法的演进[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2):14-29.
[15]文旭,杨旭.构式化: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路径[J].现代外语,2016(6):731-741+872.
[16]龙国富,陈光.试论构式化的概念及其理论发展[J].外语研究,2018(2):6-10.
[17]杨旭,刘瑾.构式化的核心思想及其对构式习得的启示[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4):26-31.
[18]杨旭.构式化思想的演进及相关问题探讨[J].外国语文,2019(1):16-21.
[19]杨旭,王悦.基于使用的构式化:诠释与瞻望[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3(5):42-50+145-146.
[20]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J].当代修辞学,2010(3):7-17.
[21]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下)[J].当代修辞学,2010(4):14-23.
[22]陈满华,张庆彬.情态动词“至于”及其构式化路径[J].学术交流,2014(12):155-162+2.
[23]闫亚平.“一+量+形”的构式化及其修辞动因[J].当代修辞学,2015(2):47-55.
[24]李思旭.从语言类型学看三个平面互动研究[J].汉语学习,2014(2):20-31.
[25]储泽祥.语法比较中的“表-里-值”三个角度[J].汉语学习,1997(3):8-11.
[26]马庆株.结构、语义、表达研究琐议——从相对义、绝对义谈起[J].中国语文,1998(3):173-180.
[27]袁毓林.走向多层面互动的汉语研究[J].语言科学,2003(6):5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