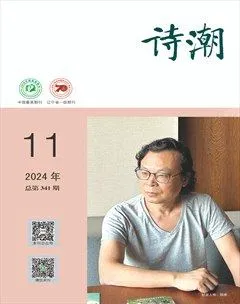蒋立波诗歌代表作品选
2024-12-06蒋立波
南山雨中作
无法再细的声音,温柔地洗着我的肋骨,
春天里,我来不及打开的诗篇。
雨中的树木显得多么不真实,
就像那些轻易得到的幸福,
承受过阳光的叶子,却挽留不住一滴最小的水珠。
破碎的事物,在雨声中悄然抱在一起。
我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支竹箫,
存放在母亲的木箱里,保持着长久的沉默,
任雨水撬开我厚厚的嘴唇。
(我听到一个披蓑衣的聋子在说:我听到了岩石中的流水。)
雨滴弹奏着春天的亡灵。
一滴雨,弹奏着所有的雨滴。
我看到母亲的白发,在一把檀木梳子的细齿间绿了。
南山已经更远。渐渐散开的大雾里,
一滴鸟声是否就是整座空山?
1990.02.23
重新命名
一年不来的人工湖看上去没多大变化
蝉鸣疑似使用多年的旧乐器
几支钓竿以45度角斜插向湖心
一棵朴树的树皮上,去年看到过的
“张小梅我爱你”这几个字还在
那用来刻写的锋利的刀片或许早就丢了
表白却已经长大了一岁,特别是那个
由于树身的扩张而被拉扁的“爱”字
已经变得像一个体态臃肿的孕妇
而在“我”和“你”之间,总是横亘着一个
新的人称,但不是“他”,不是具体的
名字与性别,而只是一片被推远的湖水
新的命名总是以看不见的方式发生
如同湖底苦闷的淤泥,用新的藕孔换气
2020.08.30
2020.09.13
公园即景(二)
蜻蜓低飞,双翅挑起一担滂沱乌云。
最大的绝望是金钱松下的绝望,
因为头顶并无钱币落下,脚下的人造草皮绿得
依旧不够诚实,而松鼠心不在焉的问候训练有素。
蝉鸣刚与社论的嗓门打成平手,
但跟骂街的蝗虫相比,仍然稍逊一筹。
人工湖的涟漪一圈一圈,似乎有一个中心
把我不断推远,成为远景、郊区、界桩,景深
等待冲洗
圆周率的小数点后面不断涌来的茫然。
成群结队的螺蛳像是一场没有口号的游行,
来不及吐尽满肚子淤泥,就已来到饕餮者的嘴边。
不管风朝哪个方向吹,荷叶上的水珠
依然稳稳地坐在那里,任凭池杉在倒影里
细数针叶,获得一种自我的对焦。
木质长椅仍然是空的,鱼在缺氧中浮出水面,
争相啄食一张边缘翻卷的肺叶。
2019.08.18
访罗隐故里①
回家,再离家,这是第几次?
当你挥手作别,光屁股的男孩儿刚好
一个猛子扎进村口的溪水里。
一只鹅,带领一群鸭子,游进唐诗下游。
葛溪与湘溪,两条小溪在这里交汇,
像江南司空见惯的约会被我们无意中目睹。
跟随一头水牛,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老家,
但已经没有牧童,用一支友善的短笛为我们指路。
只有两只忠诚的石虎还在给你守门。
而我们竟然胆敢靠近,仿佛一个时代的愚蠢,
已经受到宽恕,仿佛熏陶过你命运的风俗,
还在为我们升起祝福的炊烟。
你的名声早已超越这方圆五十里乡村。
你用语言的尺度丈量过的世界却依然找不到边界,
仿佛只有你亲手栽种的那两棵桂花树才有资格
散发芬芳,给奇数的灵魂带来偶数的礼物。
贤哲,乞丐,还是圣徒?
在庙宇倒塌的年代这些又关你鸟事。
桂花凋零之后,你恶作剧般的嘲弄已无人继承,
为了发明闪电,你首先发明了一种方言。
注:①据罗隐后人、乡邦文史研究者罗益平先生考证,富阳新登双江村为晚唐诗人罗隐故里。
2009.07.04
论灰烬作为唯一的礼物
(游岳麓山,赠长沙王砚、刘洵)
假道一种幻觉,我轻易地跨越了山脊
仿佛一滴松脂一瞬间治愈了
风景的痼疾。修辞的松针
在天空的蔚蓝里接受云朵的招安
只有死者跟死者的交谈,超越了时间的
碑石,并且一再获得山风的宽恕
一条蜥蜴从墓碑下爬出
像过时的闪电,照亮橘子内部的主义
一册苔藓覆盖的语录里,小径转弯
戴礼帽的“纯洁性”已恭候多时
那一刻,我差点叫出它的
名叫“正当性”的孪生兄弟
从来没有哪一座山,有如此多的墓冢
我像是在幽灵的队列里穿行,仿佛
志士仁人已习惯于被打扰,铁锈味的鸟鸣
仍在固执地为鬼魂代笔。唯一
被免予拆迁的是饥饿的地狱
它只能由定律、罪和黑暗的心喂养
灰烬懂得沉默,尚未完工的锁链
只为革命而定制。飞蛾槭扮演的刺客
在一种虚无的语法里,继续为那场
失败的行刺辩护。而找不到的
寺庙深处逸出的木鱼
一声声,超度鹤眼里溺死的塔影
2014.04.03
词源学
三口井竟然还在,一口正方形,两口三角形,
我最初所接受的几何学:从这里出发,我和世界
构成了无数个直角、锐角、钝角。而如今
面对被遗弃的荒凉,所有的公式都已宣告失效。
中年的杜甫?我不可能想象他的形象,或许只有
他内心蔓延的荒草能够替我丈量遗址的面积。
吹过我耳廓的秋风,一定也计算过他两鬓的白发,
那浸入草木的霜,遍地的瓦砾上,中年的积雪。
故乡是最大的虚妄,因为叫得出我乳名的人
都已经不在,我想拥抱的仇人也已在泥土深处
长眠。他们不可能再醒来,沉重的墓石背后,
缄默的嘴唇不会有任何一个词需要向我吐露。
但当我站在八十岁的阿叔和阿婶中间跟他们合影,
我几乎听到了头顶三只竹篮里储藏的土豆种子
那幼芽拱动的声音,我甚至想象他们拄着的拐杖
也在抽出嫩枝。这么多年我远走他乡,而我不可能
背走这三口井。记忆总是热衷于不断修改自己,
只有三口井忠实于自己的位置,它们分别被用于
饮用、洗菜、洗衣,很多年里都相安无事。
井水不犯井水,蛇和井绳彼此仿写来自命运的
紧张与敌意。乌鸦和喜鹊,在同一根树枝上
发表相反的意见。仿佛母亲的水桶还在依次碰响
井沿,蛙鸣,青苔,姓氏,晃动的冰块与星辰。
我已经习惯不断地删除,习惯与世界的平行关系,
但我保留了凛冽与暗涌的天性,一个隐秘的
锐角,或者说我与我之间固执的对质和争吵。
泉孔在看不见的地方教育着我,如同旧雪
在“记忆的阴面”①冰镇我的童年,一种不被讲授的
词源学,需要从枯枝那里借到一根仁慈的教鞭。
注:①“记忆的阴面”借用自耿占春。
2019.12.05
晨读阿莱士·施蒂格①
一本诗集的封面上,一只蝴蝶飞临。
敛翅的瞬间让一场风暴安静下来,
那些大大小小的圆像无数餐盘在我眼前旋转。
在无数个偶然中,它被一个必然选中。
在无数的睡眠中,它只被一个梦所虚构。
纤细的足像是试探:这是中欧的一个微型机场吗?
仿佛引擎还在轰鸣,诗学里的地缘政治微微震动。
优雅的姿态接近于一次完美迫降,
“从伤口另一端”,新建的跑道指向你的缺席。
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它们总是那么迅捷
找到清晨的光线如寻求词语的庇护。
意义保持了必要的沉默,以便事物开口说话。
翅翼如书本合拢,你被关在里面等待庄子的解救。
作为你从未谋面的陌生读者,
我的舌尖被回形针别进一条向内弯曲的道路。
藤条桌面上,光在玻璃内部“经受无尽的变幻和
滤析”。
蝴蝶携带的风暴让地图的页边翻卷,
而遥不可及的原文躲在背后,发出善意的嘲讽。
注:①阿莱士·施蒂格,斯洛文尼亚诗人,著有诗集《从伤口另一端》。
2019.08.15
死亡教育
我从小接受过死亡的教育,不知几岁起
灶台边安放了一口松木打制的棺材
一墙之隔,每次到灶头端菜,我都是胆战心惊
但在父母眼里,它似乎仅仅是诸多器具中
普通的一种,甚至像谷柜那样,常常被用于
存放稻谷,麦子,玉米。后来才慢慢知道
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曾有过另一个妻子
她生病死了,我的母亲才来到这个家
我当然从未见过这个不幸的女人,她也不是
我的妈妈,但父亲经常带着我和姐姐
去看望她的双亲,我一直叫他们外公外婆
我一直记得,那个外婆给我煎出的
酥脆金黄的带鱼,尽管我被允许每餐
只吃一块,这仅仅我一个人可以享有的特权
而这副棺材,就是父亲为那个外公准备的
许多年里,母亲伏在灶台上煮菜,一尾鲫鱼
在油锅里噼啪作响,而隔着一堵土墙
一口漆黑的棺材,那么安静,更安静的
是棺材里的粮食,就像死亡,用安静的声音
教育着我。许多年以后,我会想起那个
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我甚至觉得
是她生下了我:通过她的死亡——
这漫长的产道,我冒着危险来到这个世界
2021.02.18
欢潭拾遗
难以想象,这用铁锤砸开的七角形水潭
何以给偶然路过的士兵带来一场狂欢
同样难以想象,数百年后这重构的历史镜面
何以从一种对镜的诗学取回我们真实的脸
章回体的绣像小说,曾绘制我的童年
那众多惊艳的脸谱,并以狂热鼓点赎回
高悬的明月和首级,八千里路,那么多尘土
尘土深处的功名,如今都被传说收缴
诗人灯灯的一副耳机,被潭水收缴,仿佛
这过于清澈的水面,尚有暗流需测听
尚有金戈铁马需回放,尚有国家的河山
与地图,需要在身体上刺青,一种被征用的
修辞,如关闭的兵器博物馆,只在门口
陈列出一半兵器,说岳全传里那些英雄的名字
我都忘了,像卷曲、生锈的利刃,执迷于
方志的某个破绽,或一座倾覆的宫殿
游客中心里折纸飞机的顽童,活脱脱像是
我少年时迷恋的小岳云,只是他的手上已没有
两柄八棱梅花锤,那被收缴的文学形象
(莫非铸一块生死免战牌,还缺几斤废铜烂铁?)
烈日下枯焦的荷叶如一颗激烈的心
至今忧愤于恶的凯旋,淤泥糊成的金身
2022.08.26
在洞头不妨暂时放弃洞见
(回赠臧棣)
在洞头,不妨暂时放弃洞见而只保持
一种凝视,以捕获那些“没有被发现”
或者“已经遗忘”的事物,比如渔网的网眼里
滴下的一颗水珠,大海咸涩的眼泪
总结着世界的悲苦,就像那些被回收的
废水和废话,需要重新得到稀释
而当你走上这绝壁,或者说当你成为
自己的绝境,成为需要与之搏斗的对象
成为那惊叹本身,此时不妨放弃全屏模式
而只取半屏①,如同借一双鱼的眼睛眺望
一片消失的风景:一个厌食症患者
无法吞咽的部分,对话框里迅捷撤回的浪
不妨躲进鱼腹,与塑料、金属
和断桨为伍,在惊涛骇浪中穿过缠绕的水草
像一个卡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约拿
我相信海也在凝视我们,用一双鱼的眼睛
它以浩瀚的悲观,治愈我们渺小的悲伤
它弓起的脊背,替我们卸下背负的重物
注:①半屏山,位于浙江温州洞头。
2023.09.03
钉痕学
“你是怎样把每一个钉子都钉歪的?”①
对此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是一幅沉默的肖像
他躲在墙角的阴影里自己欣赏自己
因生平不详,他可以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
钉子不总是垂直于墙壁,很多时候
钉子钉住的是壁虎的一条尾巴,尽管壁虎
早就不知所终,只留下他在那里
面壁思过,这高明的逃遁术,不同于
蝴蝶的还魂,也有别于甲虫的变形
歪打正着乃是唯一的秘诀。而钉一幅画
和钉一个人,往往被我们混为一谈
人身上流出的血最终凝冻为冷硬的颜料
刽子手不会把钉子钉歪,他总是可以
把每一枚钉子准确地钉入一个人的
手掌和脚跟,像钉一件稀世珍品
没有人知道那钉痕,至今尚未在我们身上
获得愈合,如同无人知晓,每个人都是
一枚钉子,被一寸一寸钉入那无罪的身体
当你把一幅画挂上美术馆的墙壁
每一枚钉子,都带着各自的锋利和无辜
注:①引号内文字来自画家胡梦梦。
2023.04.02
阴影答疑
在医院大楼阴影里,努力辨认几种植物
柳树,云杉,玉兰,茶花,金钱松
我发照片请教朋友们,曲曲说
左边那棵应该是无患子,别名肥皂树
这就像一个诗人,也可能有一个俗气的名字
更多的是枯草,在时间中隐姓埋名
年迈的太阳,在冬日午后移动得如此迅捷
我们不得不跟随着一次次挪移
以追逐最后一块阳光,我能感觉到
它金黄的爪子踩过我头顶时那一瞬间
锐利地抓取,这里的植物也在过冬
区别在于,喂养它们的不是阳光和雨水
而是细菌和暗疾,逃逸的毒株
这里的鸟鸣与别处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每一个音节,都用消毒水擦洗过
这里说出的爱,像体检报告单上的医学用词
总是在不确定中保持某种迟疑和谨慎
2023.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