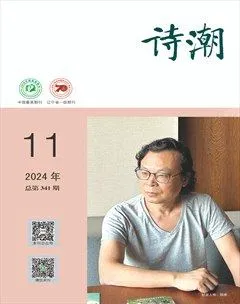对镜的诗学或“自我的辨认”
2024-12-06纳兰
最近,有机会集中精力、细致阅读蒋立波的诗,十分荣幸,获益良深。蒋立波诗的风格之陌异性在于偏离歧义丛生的航道,用语言的尺度丈量世界,在持续的写作如净化自身的过程中,“吐尽满肚子淤泥”(《公园即景(二)》)。整体而言,蒋立波在思与诗之间往返,将思纯化为诗,在诗与现实之间呼吸,将现实吐纳为诗;在诗与历史、记忆之间绵延,将历史和记忆呈现为诗;在诗与诗学之间挪移,以诗学素养来滋养诗,而这诗学是广义诗学或普遍诗学,一切理论都是经过自身经验的咀嚼之后所软化的感性诗学,更重要的是在诗与内心之间的那“一条向内弯曲的道路”(《晨读阿莱士·施蒂格》),将内心之烛火映照现实。他深谙隐喻之道以及隐喻中所暗含的真理和美。读他的诗,是“一颗发烫的星体渴望用一只木勺畅饮”(《七夕指南》),既有“发烫的星体”的热烈,又有“木勺畅饮”的快感。
或许,切入蒋立波的诗歌世界有无数扇“窄门”,我却选择从对镜的诗学与重获自身这个细小的角度,侧身而入。他曾写道,“何以从一种对镜的诗学取回我们真实的脸”(《欢潭拾遗》),“在一种反义中重获自己”(《皱缩的石榴》)。我所萃取的这两首诗中的句子,就是我这篇评论题目和角度的由来。作者在《欢潭拾遗》中,并未对“对镜的诗学”有过多的延伸与阐释,只是发出一个“何以……”的疑问,但并不妨碍“对镜的诗学”这一概念的有效性与广延性。这个所对之“镜”,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还是人(身体)之镜、语言之镜、世界之镜、社会(历史)之镜、诗学(理论)之镜。串联起主体和语言、身体和世界之“镜”等这一切的是蒋立波手中的那一枚轻巧的“修辞的松针”(《论灰烬作为唯一的礼物》)。即主体面对主体或他者,主体面对语言,主体面对社会历史世界,主体面对诗学(理论)所取回的“真实的脸”,对镜不再只是一种行为或姿势,而是一种诗学姿势。就在所对如此之“镜”时,我们将逐渐地重获一种自身或法身。
世界之“镜”
在世界之中,在山河的天眼里,诗人是“一枚因神秘的牵引而激动的浮标”(《零度以下写作》)。“隔着坚硬的冰块,鲤鱼们接见我/像接见一名用冰镐凿开词语的囚犯/它们长久地悬停在那里,像是在垂钓/那从钓钩里逃脱过无数次的我”,在与世界之镜的对峙中,我像是“一名用冰镐凿开词语的囚犯”。在“一块厚厚的镜片”的隔断中,“鲤鱼”与“我”完成了各自的自我辨识。
如果世界本身是一面镜子,则世间之万事万物均是这面镜子一个小小的碎片,我看世界如世界看我,青山看我亦如是。诗人发现,人间事与万物之间有着巨大的相似性,诗人说“一场婚礼和一场丧事,就像同一根枝条上/喜鹊和乌鸦相安无事”(《去高新区的路上》),照世界之“镜”,惊觉“来自命运的紧张与敌意”,如同诗人精确地表达“蛇和井绳彼此仿写来自命运的/紧张与敌意。”(《词源学》)诗人还发现了在相似性的背后潜藏着差异性,差异性不仅在于“乌鸦和喜鹊,在同一根树枝上/发表相反的意见”,还在于它们可以在一种反义中重获自己;不但是喜鹊是乌鸦的反义,乌鸦也是自身的反义,在这样的认知实践中,更加接近真理和意义。他在《重新命名》中说,“而在‘我’和‘你’之间,总是横亘着一个/新的人称,但不是‘他’,不是具体的/名字与性别,而只是一片被推远的湖水”。或许这就是诗人“对镜”之时的诗思,对照世界之镜,总能产生一种重新命名的冲动,这种“重新命名”不意味着发现了新的事物,而是“湖底苦闷的淤泥”“用新的藕孔换气”;不似自身位置发生了改变,而是打量、审视和所呼吸到的世界的改变,是一次呼吸练习。
在《欢潭拾遗》的结尾,有“烈日下枯焦的荷叶如一颗激烈的心/至今忧愤于恶的凯旋,淤泥糊成的金身”这样醍醐灌顶的诗句,这更像是面对世界之镜时的具体处境与结果。“枯焦的荷叶”是表象之我,“一颗激烈的心”才是本真性的自我,而“淤泥糊成的金身”更具有“无我相、人相和众生相”的无分别之识见。
对镜的诗学不是静态的和平面化的所见,而是动态的“苦雨”敲打芭蕉;不仅在于传达所见,更重要的是能够传达不可见;不仅是外观,还要有内视之眼,看见“柚子内部,聚拢的甜”(《己亥年正月十二,与唐晋郁葱庆根炜津诸友雨中同访郁达夫故居》),和“疯狂的石榴,如一个微型宇宙”(《皱缩的石榴》)。对镜的诗学不仅仅是在镜中重塑自身,这种重塑是“从一截木头里削出一柄宝剑”,还潜藏着“为试图隐身的作者完成一次测温”(《旧天堂书店的猫》)。
身体之镜
它是通过身体呈现在世界中,通过世界呈现在身体中的,它是肉身,也是语言。
——梅洛·庞蒂
依然是身体、世界和语言,它们的交织构成了混杂的经验文本,“习惯与世界的平行关系,/但我保留了凛冽与暗涌的天性,一个隐秘的/锐角,或者说我与我之间固执的对质和争吵。”(《词源学》)不论是世界之镜还是语言之镜,都更好地照亮了美好的存在。依然是“所见”,无论是站在世界之镜前的我观,还是我作为一面身体之镜的物观或“物哀”,这最终的“所见”,乃思想的结晶,盐一般的结晶。
在《从一截木头里削出一柄宝剑》之诗中,不再是身体之镜对万物的映照与打量了,而是“原来笨拙的身体中,也可以暗藏锋芒和利刃”,就像“它在一棵树里沉睡”,“心怀利刃”的心剑与“一棵树里沉睡”的木剑,在这里具有了相似性。诗人直抒胸臆地说“我急于寻找这个世界的漏洞,执着于/在自己身上创造一个陌生的对立面”,这个“陌生的对立面”或“异己”,就是木头里沉睡的宝剑,它挥舞着砍向了自身,完整自我的修正。诗之结尾,“持续到了今天,只不过我舞动的不再是剑/而仅仅是一根枯枝,甚至是衰老本身”,“枯枝”在变化的认知里,是“一根仁慈的教鞭”(《词源学》)。从剑到枯枝,非事物本身发生了变化,实则是心境之变,非剑是剑,非法是法,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随时间而来的诗之晚期风格。
蒋立波的《钉痕学》,也是一首独特而繁复之诗。“‘你是怎样把每一个钉子都钉歪的?’/对此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是一幅沉默的肖像”,我更愿意把这样具体的细节,理解为诗之钉子对读者的影响或作用,钉歪了,说明语言之钉的错置与虚掷。“很多时候/钉子钉住的是壁虎的一条尾巴”,说明诗只作用于身体的局部,而非整体。身体之镜在这里变成了身体之钉,“每个人都是/一枚钉子,被一寸一寸钉入那无罪的身体”,身体之钉,带着罪性的“身体之钉”,与无罪的圣体和神圣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质,而非质变。“当你把一幅画挂上美术馆的墙壁/每一枚钉子,都带着各自的锋利和无辜”,可能蒋立波的诗与我对他诗的评论,也正是一种“把一幅画挂上美术馆的墙壁”的展览过程,我的每一句评论的话语,也是我的锋利和无辜。《钉痕学》充分说明这是一首语言、身体和世界交织的诗歌文本。
语言之镜
诗人在洞头时的洞见,则是“大海咸涩的眼泪/总结着世界的悲苦,就像那些被回收的/废水和废话,需要重新得到稀释”(《在洞头不妨暂时放弃洞见》),这也潜藏着一种诗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净化废水如净化废话和被污染的语言。在他这里,语言的镜像是自身的呈现,是心灵的显影。借助语言之镜,诗人蒋立波达成了与世界的和解,与自身的和解。
语言乃密道,是“走到我的反面”的密道。是“到一个更大的矛盾里去辨认被遮蔽的自我”的独辟蹊径,是“到反义词里去辨析本义”的词源学里的往返。在词与人、语言与肉身的相似性的隐喻中,抵达反面的我,本真性的、异质性的自我。在语言这面镜子面前,无用的词与无用之我同义,“一种自我的急救”才是语言之妙用。“不迷惑提交它的迷惑给证据”才是语言之妙悟。“笔尖走动,直到第一个字,跳出字面意思”,就像我跳出了我,在对镜的诗学中完成自我重塑。蒋立波的《写在心电图报告单背面的诗》,更像是心电图的线性之图到语言的镜像呈现之间的转换。
语言之镜,需靠对语言的信赖与爱,来实现身体和世界的镜像化。蒋立波的《晚期风格》是一首以诗论诗的“元诗”。晚期风格,类似于遗嘱式的写作,是蒋立波所言的“烂熟的柿子砰然坠地的声音”和对“未走的那条路”的开辟和探寻,希望我对蒋立波诗歌的读札,能有“同秋风吹凉的枝头理解累累果实的厌倦”的浅薄的理解。读到蒋立波的《顶针》一诗,若有所悟,顶针既是缝纫用具,也是一种修辞手法,作为缝纫用具,它的功能是“逼迫着针尖去穿透坚硬之物”。我想到,评论文章也是一种“顶针”的功能,诗歌评论也是一种力量,它逼迫着针尖一样的诗去穿透心灵,让你痛感或快感。我想说的是,蒋立波的诗是有针尖一样的刺痛和缝合疗愈作用的。而他的“顶针”之修辞,不是用上句的结尾作为下句的开头,而是一首诗和另一首诗之间有顶针的修辞作用,更多的诗的集合之力,来唤醒你的感觉。
或许蒋立波所追求的晚期风格,是一种未完成的对镜的诗学的完成。
无论是他的诗集《听力测试》,还是《呼吸练习》,都是在一切迷雾与索引里,“一遍遍擦洗听觉里张开的伤口”(《灯塔博物馆》)。之后,对一切可以疗愈的声音的倾听与回应,都是观察者的技术与修辞的记录,都是感受性主体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对这个现实世界深深地介入和隐微地表达。这种“听力测试”不单单是针对自身,也是指向了更广阔的众生,因为行道是从闻道始。声音,意味着是一种洗礼“温柔地洗着我的肋骨”(《南山雨中作》),意味着一种对破碎事物的修复性拯救,“破碎的事物,在雨声中悄然抱在一起”。能否通过一次次的听力测试的标准在于“我听到一个披蓑衣的聋子在说:我听到了岩石中的流水”。往大和纵深里说,声音是蒋立波在1990年那时起,就建构的声音的诗学,声音里有可以看、听和触摸的“道”与肉身,因为他看见了“一滴鸟声就是整座空山”和听到了“岩石中的流水”。
诗,依然是一种古老的告诫:“舌尖的奖赏,甜,而危险”(《野生莓果学》)。但“无疑,这对镜的诗学仍是我们的功课”(《知音学》),这功课既是蒋立波持续在做的语言的灵修,也是评论家需要做的功课,对镜的诗学让我们可以在诗中认出自己,也可以在一切诗学中辨认出自己。就像蒋立波所说,以便在汉语的凛冽里,认出另一个自己,重述或重塑另一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