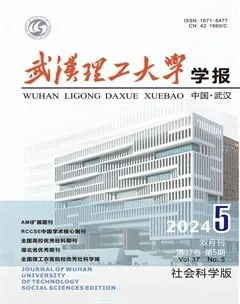从“重气”到“尚韵”: 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变迁理路探究
2024-12-06曹贵
摘 要: 考察从东晋顾恺之始至清末民初康有为、陈师曾和徐悲鸿等众多有识之士论画的1500多年绘画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文人画的美学品格经历了一个由“重气”到“尚韵”的变迁理路。而在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发生转折的关键点上,顾恺之、谢赫、张彦远、荆浩、郭若虚、苏轼、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等书画家,担负起了历史给予他们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尤其是明末画家董其昌,他对“董、巨逸轨”的中国文人画图式语言赞叹至极,并对中国文人画的“尚韵”理论作了全面、深刻且系统的总结。因此,从某种层面而言,中国文人画“尚韵”的理论主张始于苏轼,成于董其昌,的确是有道理的。
关键词: 文人画; 美学品格; 重气; 尚韵
中图分类号: J-22; J2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4.05.002
收稿日期:2024-04-08
作者简介:曹 贵(1984-),男,湖北宜都人,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史论、艺术美学和文化遗产学等研究。
一、 “传神”论:“气韵”说的先导
众所周知,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解放和大发展时期,那么,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大兴隆和大繁盛时期。单就艺术和美学言之,魏晋南北朝堪称艺术和美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可谓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陆机的《文赋》、顾恺之的《论画》和《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正是在这些重要论文和论著中,我们发现许多在中国艺术史和美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范畴在此时应运萌生。其中有的是从先秦的哲学范畴转化而来,如“气”、“神”、“妙”和“意象”等,有的则是在概括此时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美学范畴,如“风骨”、“隐秀”、“神思”等。此外,这些论文论著中提出了一些著名的美学命题,如“得意忘象”、“声无哀乐”、“传神写照”、“澄怀味象”和“气韵生动”等[1]183,所有这些范畴和命题,不仅在当时颇有影响,而且对后世亦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上面这些美学命题中,其中“传神写照”就是由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提出的一个有关中国绘画的重要命题。《世说新语·巧艺》第十三则《顾长康画人》这样记载: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2]
顾恺之的这句话,无论在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还是在艺术美学上,都是极有影响力的。恰是在顾氏的答语中,“传神”论的思想横空问世。但是,结合顾氏的上下文,他认为的“传神”主要在于眼睛,而不在于“四体妍蚩”。换言之,即此时的人物画创作要想传神,不应着眼于人物的整个自然形体,而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某个关键部位——如眼睛,面颊(案:“尝图裴楷象,颊上夹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晋书·顾恺之传》)。
那么,顾恺之理解的“传神写照”和同时代稍晚一些的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学者们较为感兴趣的话题。刘纲纪指出:“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这一著名的说法,谢赫所说的‘气韵生动’与它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但两者又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传神写照’和‘气韵生动’都要求表现人物的内在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顾恺之所说的‘传神’的‘神’是和玄学以及佛学所说的‘神明’联系在一起的,它强调精神超越于尘世和形体的内在的永恒性、绝对性。所以顾恺之认为‘传神’的关键在于眼睛的刻画,而不是外部的形体动作的描写,忘‘形’而得‘神’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谢赫所说的‘气韵生动’则不然。作为一个‘宫体’画家,谢赫虽然一点也不忽视‘神’的表现,但更为强调对形体动作、姿态的生动描写。”[3]叶朗指出:“过去对‘气韵生动’的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把‘气韵’等同于‘传神’,认为‘气韵’就是‘神韵’,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人内在的精神面貌、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等等。如元代杨维桢说:‘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他把‘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语。近现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杨维桢的这种解释符合‘六法’的本义。其实不然。……‘气韵生动’和‘传神’当然是有联系的……但是‘气韵生动’和‘传神’终究是两个命题而不是一个命题。‘韵’的涵义大致和‘传神写照’相当,‘气’的涵义却超出了‘传神写照’。”[1]222钟跃英指出:“……无论在汉代传神思想中,还是顾恺之的论述上,对人物传神尚着重在人的眼睛上,即三国魏初刘劭所说的‘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十分强调通过对眼睛的描绘来解释人的精神,正所谓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概念,则体现出对人物传神含义的进一步扩大,它不仅仅局限于通过眼睛来传达人物的神情,而且包含了一个人形体姿貌所显现出整体的状态,将传神的着眼点扩展到人体的各个方面。”[4]35笔者赞同上述三位学者的看法,并曾撰文指出,谢赫的“气韵”论是受到了顾恺之“传神”论的影响的。“气韵”不等于“传神”,“气韵”本身就具有“动”的势能,相比之下,“气韵”比“传神”更具有“动”的态势,包孕性更大。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人物画占据画坛主导地位的时期,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论为即将呼之欲出的谢赫的“气韵生动”说之诞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 谢赫“气韵”说的深刻内涵
“气韵生动”的美学命题,最早是由生活在南朝齐梁之际的绘画理论家兼画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提出的。诚然,“气韵生动”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美学和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气韵生动”作为绘画“六法”之首法,是谢赫“六法”品鉴思想的核心尺度(或准绳)。毫不夸张地说,“气韵生动”在中国绘画史和美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无怪乎有学者明确强调,“不把握‘气韵生动’,就不可能把握中国古典美学体系。”[1]213笔者亦认为,若不弄清谢赫《古画品录》语境下的“气韵生动”,便根本无法知晓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的变迁理路。换言之,中国文人画的美学品格就是从“气韵生动”正式开始的。下面,为了阐明“气韵”说,笔者拟从对“气”、“韵”之考证、谢赫“六法”之“气韵”意蕴和“气韵”与“生动”的关系三个方面加以剖析①。
(一) “气”、“韵”之考证
“气韵”一词,作为我国绘画艺术和美学上的重要范畴,它是由“气”和“韵”两个概念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背景下随着时间的发展自然组合而成的。大致说来,“气”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云气”、“声气”至哲学上宇宙万物生机论的“气”(即元气、元一之气)再到审美上艺术形象的生机之“气”的演化过程;而“韵”的概念由声韵、音韵之本义,经历了一个由人伦鉴识到文艺品鉴的发展过程。“气”和“韵”两概念,从其本义来看,都经历了一个从品人到品物(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谢赫之前以及到其同时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关于“气”的论述不计其数、举不胜举。此处,笔者就“气”之本义(形而下物质之气)、元气(形而上精神之气)、人伦鉴识之“气”和文艺品鉴之“气”的相关论述,兹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槫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十章》)
(2)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3)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庄子·齐物论》)
(案:(1)至(3)条,笔者参阅的《老子》《孟子》《庄子》诸书均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老子、孟子和庄子所言之气均为形而下的可感知的物质之气,可作“声气”、“云气”、“气息”解。)
(4)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者,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极、太一也”[5](《周易正义》)
(5)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老子·第四十二章》)
(6)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漏漏,故曰太始。太始生虚阔,虚阔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7](《淮南子·天文训》)
(案:(4)至(6)条,“气”均为形而上之“元气”解。)
(7)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8](《史记·李将军列传》)
(8) “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9](《后汉书·蔡邕传》)
(9)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0](曹丕《典论·论文》)
(案:自曹丕首次在文学创作中提出“气”的观念后,以“气”来谈论艺术风格的做法便逐渐在文学艺术中推广开来。)
(10)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秉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行。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11](刘邵《人物志·九征》)
(11) “《小烈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12](顾恺之《论画》)
(12) “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足散人怀。’”[13]318(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13)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王右军,……’”[13]376(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
(案:自刘邵之《人物志》问世以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实乃人伦鉴识之大成;魏晋以后,人伦品评和文艺鉴赏是同时进行的,既有品人,也有品物,谁先谁后之分并不明显。)
(14)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臣谓钟繇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14](袁昂《古今书评》)
(15) “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15](刘勰《文心雕龙·檄移》)
(案:(7)至(15)条,除(10)条“元一”作元气解外,其它各条中人伦鉴识之“气”可作气质解,文艺品鉴之“气”可作作品之风貌解。)
笔者上述就谢赫之前和同时代的有关“气”的代表性言说作了简略的列举。“韵”的出现,据韩刚在其著作《谢赫“六法”义证》中考证,应“多在汉末三国”。在没有其它证据能证明更早的前提下,笔者赞同韩刚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与“气”的历史和地位相比,“韵”的历史要短得多;另一方面,“韵”虽然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如“气”,但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凸现,成为了一个甚为流行的词语,以至于有“汉人尚气,晋人尚韵”的说法(此言主要是针对书法)。“韵”之本义,当作“声韵”、“音韵”和“韵律”等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音部》云:“韵,和也。从音,员声。”[16]东汉蔡邕《琴赋》中言:“繁弦既抑,雅韵乃扬。”[17]曹植《白鹤赋》中言:“聆雅琴之清韵,记六翮之末流。”[18]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亦言:“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19]这些诗文中提到的“韵”皆当“韵”之本义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晋陶潜的诗《归园田居》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20]其中“适俗韵”之“韵”应作“天性、自然”解。在高谈玄理、崇尚老庄的六朝时代,“韵”除了本义之用法外,也有相当多的论述是针对人伦鉴识和文艺品鉴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可谓是南朝刘宋时期品人之集大成著作。如“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13]539“襄阳罗友有大韵。”[13]555“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13]340除刘氏著作以外,此期前后的其它书中也可找到大量有关“韵”的言论。笔者在此亦作一些简要的列举。
(1) “嘲弄嗤妍,凌尚侮慢者,谓之肖豁远韵。”(葛洪《抱朴子·汉过》)
(2) “风韵秀彻。”(《晋书·桓石秀传》)
(3) “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晋书·庾恺传》)
(4) “乐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晋书·郄鉴传》)
(5) “会无玄韵淡泊。”(《晋书·曹眦传》)
(6) “风韵清爽。”(《南史·柳琰传》)
(7) “风韵清疏。”(《南史·孔珪传》)
(8) “祥少好文学,情韵疏刚。”(《南史·刘祥传》)
(9) “自然有雅韵。”(《宋书·谢方明传》)
(10) “彦伦辞辩,苦节清韵。”②(《齐书·周颙传赞》)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谢赫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气”“韵”两概念中,“气”更多的是用在审美范畴的意义上,具体到人伦鉴识上,“气”常作人的气质解,在文艺品评中,“气”常当作品之面貌或者气调(即或豪放,或婉约)解,而“韵”在其本义(音韵、声韵等)、品评人之风韵和风度以及品鉴作品风格之韵三方面意涵在同时期都有大量的使用。
(二) 谢赫“六法”之“气韵”意蕴
我们从上述对“气”和“韵”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在谢赫《画品》成书之前“气”、“韵”绝大多数都是分开使用的,有学者指出,“画之‘气韵’一词,是谢赫最早陈述出来的”[21]93。至于二者合为一词“气韵”连用是很少见的③。笔者认为,此梳理虽显繁琐,但对考证“六法”语境下的“气韵”是完全不可或缺的,谢赫的《画品》不可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而凭空自创。考之谢赫《画品》原文,谢赫合用“气韵”仅一处,即开篇小序中“气韵,生动是也”,单用“气”六处,单用“韵”四处,兹摘录如下。
用“气”六处为:
(1) “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第一品三 卫协)
(2) “风范气候,极妙参神。”(第一品四 张墨、荀勖)
(3) “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第二品一 顾骏之)
(4) “虽气力不足而精彩有余。”(第三品四 夏瞻)
(5) “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第五品二 晋明帝)
(6) “非不精谨,乏于生气。”(第六品二 丁光)
用“韵”四处为:
(1) “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第二品一 顾骏之)
(2) “体韵遒举,风彩飘然。”(第二品二 陆绥)
(3) “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第三品三 毛惠远)
(4) “情韵连绵,风趣巧拔。”④(第三品五 戴逵)
经详察文本,符合谢赫“气韵”标准的唯有陆探微一人而已。谢赫评价陆探微言:“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22]17所以,仅有陆探微一人达到了谢赫心中理想的极妙至美的“气韵”境界。
那么,“气韵”到底应作何解释呢?参阅近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述,对我们理解“气韵”大有帮助。如徐复观言:“谢赫的所谓气,已如前述,实指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阳刚之美。而所谓韵,则实指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阴柔之美。……气韵系代表绘画中之两种极致之美的形相。”[23]107阮璞言:“‘气韵’一词,本来指人的气质、风韵等而言。……‘气韵’二字是拟人化文艺评论所惯用的名词,是指存在于绘画作品之上的,由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一种气质、风韵。”[24]32-33张锡坤言:“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25]陈传席言:“简单地说,‘六法’中的‘气韵’指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人的形体中流露出的一种风度仪姿,能表现出人的情调、个性、尊卑以及气质中美好的但不可具体指陈的一种感受。”[21]102……所以,若非要给谢赫之“气韵”下个定义的话,笔者以为,其一,“气韵”应是就整个画面而言的,不是就画家本人,也不单是就画中某个局部而说,它是画面整体呈现出来的风貌、印象或状态;其二,若要用词语来形容此画面的话,它应是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生生不息、浑然天成的状态,它本身就具有“动”的秉性、势能,如用图像来说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气韵”的画面想象为一幅太极图。
我们知道,要创作这样的画面效果实属不易,要不然,也不会只有陆探微一人达到谢赫之标准。诚如谢赫所言,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如陆公那样“穷理尽性,事绝言5930191573298e358b6b82542a7dc8a26c1da56fd15648202ede43d6f5273cd8象。”对于达不到六法兼善的画家如何判定其品第高低?谢赫只好退而求其次,有的画家以“气”胜,如曹不兴之“风骨”⑤,卫协之“壮气”,张墨和荀勖之“风范气候”,晋明帝之“神气”。这些“气”大致可理解为一种豪迈、阳刚之气。有的画家则以“韵”见长,如顾骏之的“神韵气力”,陆绥的“体韵遒举”,毛惠远的“力遒韵雅”,戴逵的“情韵连绵”等,这类“韵”一般具有一种细腻、阴柔的内涵。但是,通观六品位置,第一品五人,除陆探微是谢赫心中完美的人选外,其他四人都是以“气”胜,无一人是以“韵”擅而被判为第一品的。就此论之,在“气”、“韵”不能兼善如陆公那样,谢赫本人是重“气”胜于重“韵”的。
(三) “气韵”与“生动”的关系
笔者上文对谢赫所言之“气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气韵”主要是画面整体上呈现出的一种虚实相生、浑然天成的风貌和状态。那么,“生动”又当作何解呢?一些现当代学者同样对“生动”不乏精辟之论,如钱钟书、张安治、阮璞、叶朗、陈传席、韩刚,等。
此处,笔者先借用阮璞的一段言论来解释:“关于‘气韵生动’的‘生动’二字,前面我已经指出过,‘生动’合上下二字为一词,是动宾结构,正如与之作对的‘用笔’合上下二字为一词,也是动宾结构一样。……‘生动’的‘生’字在这里是动词;‘动’字在这里则作名词用,其涵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惯说的动势、运动感之类,……可以看成是谢赫‘生动’一词的直接来源的,就是那个断言‘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的刘宋时的王微在《叙画》一文中所揭示出来的一条关于绘画造型性的重要法则:‘横变纵化,故动生焉’。很清楚,‘生动’二字就是‘故动生焉’的‘动生’的倒装用法。‘横变纵化,故动生焉’这八个字的意思是讲,在绘画上所有造型性因素,特别是构图、线、形、体、面等等,由于它们在整个画面上的巧妙运用,造成纵横交织,富于变化的效果,于是一种动势、运动感、形式感以及动静矛盾统一的节奏感,就会从画面上产生出来。”[24]33-34暂不论阮璞探究谢赫“生动”一词的直接来源是否准确,笔者是同意他的看法的——“生动”就是画面生出的一种动感、动势。至于生出的效果优劣,则是由前面“气韵”二字来决定的。但是,韩刚在《谢赫“六法”义证》中说:“综上述言之,作为动宾词组的‘生动’意当为:由于外在事、物的牵引或感动,心中生起摇荡不安的情绪。简言之即是‘心生之动’、‘生出情感’或‘生情’等。……如此,‘生动’之意蕴当是:心‘生’之‘动’,或情、意、欲等。相对于绘画来说,即是画家心中生出画意(想画的冲动或欲望)。心中有了画意之后,由于其不可抑制,才会迫不及待地要发之于外。自然而然的,才会涉及到‘六法’的后面‘五法’,即‘用笔’……”[26]这里,除对“生动”作动宾词组的看法外,笔者不太同意韩刚对“生动”的持论。确实,我们在品画、赏画中,至美妙极的具有“气韵”的画作会让观者心动、生情,即韩刚所言之“心生之动”,但这只是观赏者内心活动的一个环节,心动之后,观者的注意力又会重新回到让观者心动的画面上来。换言之,“生动”确实是画面生出的一种动感、动势,但经历了观者“心生之动”的中间环节,落脚点终归是回到了画面,也许这种由画作→内心→画作不止经历了一次循环,很可能是很多次。简言之,韩刚对“生动”的解读仅是停留在心生之动的环节上,而笔者之对“生动”的理解最后是停留在画面上的。这颇似六祖慧能之“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27]到底是画面生“动”在先,还是观者内心生“动”在先?说二者谁在先都在理,但笔者强调的是,观者内心生“动”当是画面具有“动”的秉性、潜质(即画面整体之“气韵”)所决定的。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谢赫所言之“气韵生动”,即指虚实相生、浑然天成的画面(亦即“事绝言象”之画面)本身具备“动”的潜质后而生发出的动势、动感。那么,作为谢赫“六法”之第一法的“气韵生动是也”,“气韵”是对“生动”之要求,画面是否呈现出虚实相生、生生不息、浑然天成之风貌,这将直接关系画面生出动感之效果。
三、 “气韵”说在谢赫之后时代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中的演变理路
如前所述,谢赫依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情景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气韵生动”概念。无疑,“气韵生动”本是就魏晋南北朝时代绘画中的人物画而言的,但是自唐代以后,相对于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也逐渐兴起,并且逐渐成为画坛三大科的主导,因此,“气韵生动”这一绘画艺术审美高标也随之扩展到山水画和花鸟画。那么,始自于谢赫时代之后的唐代,“气韵”说在中国文人画中呈现出了何种变迁脉络呢?为了帮助理解,笔者此处特引徐复观的一段颇具启发性的话以开启本部分的梳理和探讨。
谢赫所提出的“气韵生动”,……气是骨气,主要是形成阳刚之美;韵是风韵,主要是形成阴柔之美。在以人物画为主的时代,用笔系主要形成作品之骨,而傅彩则主要形成作品的韵。及气韵的观念转用到山水画时,则笔形成作品之骨,墨形成作品之韵。气韵相待而成,所以两者不能完全分离;但因作者及对象的特性不同,而有时不能不有所偏胜。此在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已可看出这种情形。山水画居于主要地位后,荆浩“合二子之长”,是笔墨相融,气韵并具。此后北宋画家,都是顺着此一方向发展。董源、巨然,因系写江南冲融蕴藉的山水,所以笔墨特显得柔和;但依然是笔墨兼具,以追求气韵的均衡,则与其他画家并无二致。不过在事实上,有一部分作品,是墨重于笔的。二米父子,则偏于墨的方面,化笔为墨,只能tnnID2G7v/D8utu3bmIqLA==以烟云见韵,这是偏于阴柔之美。李、刘、马、夏,则偏于笔的一方面,用墨如用笔,只能从山、木、石上见骨,由骨中见韵,这是偏于阳刚之美。元代赵孟頫出,恢复了人与自然的均衡,笔与墨的均衡,气与韵的均衡,而下开黄、吴、王、倪……所以在董其昌们所提的南北宗中,实际应可分为三大系,一为追求笔墨气韵均衡的一系,亦即“明”“暗”均衡的一系;一为偏于用墨,偏于取韵的一系,亦即偏于“暗”的一系;一为偏于用笔,偏于炼骨的一系,亦即偏于“明”的一系。董其昌实际所提倡的乃是偏于用墨取韵尚暗的一系;而为了撑持门面,将追求均衡的一系,勉强安放于偏于用墨取韵尚暗的一系中;实则除了对偏于用墨尚暗的一系以外,概斥为“纵横习气”,这在画史上为不实,在画论上为不平,实一无足取的。[23]280-281
以上,徐氏为我们粗线条地绘制了一幅自谢赫时代至董其昌时代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的发展路线图。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提纲挈领、脉络清晰,颇有道理。下面,笔者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张彦远、荆浩、郭若虚、苏轼、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等几位在文人画史理论或实践上的标杆人物展开考察和分析。
(一) 张彦远:“气韵”说的伟大继承者和开拓者
唐代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经过前期太宗“贞观之治”、武后和玄宗等朝的大力改革,无论文治还是武功,唐王朝均呈现出生机勃勃、自信大气的帝国风范。国家的安定、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富庶,无疑会对唐朝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此时期,审美风尚的演变,艺术经验的丰富和新材料的出现,还有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因素,促成了唐代画人和理论家对绘画艺术观念的崭新认识,尤其对“气韵生动”的涵义也发生了与魏晋南北朝创立之初时迥然不同的理解。在谢赫那里,“气韵”说还主要停留在画面虚实相生、浑然天成的效果意义上,而到了唐代中后期张彦远这里,“气韵”说的内涵已开始向着画家本人的主观精神层面拓展,具体言之,即“气韵”问题由谢赫时代单纯的绘画效果,变成画家主观精神(即张氏之“意气”)与笔墨表现两方面问题(到了北宋郭若虚时代,郭氏更是提出了“气韵非师”说,即论述到作画者自身的文化素养问题)。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张氏不仅有继承传统的历史贡献,而且亦有着开拓创新的价值担当。这主要体现在张氏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和“工画者多善书”这两个绘画命题的提出。
前一个命题“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见诸“开元中,将军裴旻善舞剑,道玄观旻舞剑,见出没神怪,既毕,挥毫益进。时又有公孙大娘亦善舞剑器,张旭见之,因为草书。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并非懦夫所能作也。”[22]177显然,张氏此处列举了书法、舞剑以及绘画三种艺术样式在传达中艺术家本人借助外因以雄强之气进行创作所形成的艺术效果。这种“雄强之气”,也就是画家作画之前的主观精神。张氏认识到,在进入到书画艺术传达时,张旭和吴道子笔墨技艺表现所达到的高超境界即“在于他们都是从观赏舞剑器时,其内在精神被那风驰电掣、神出鬼没、流电激空的挥舞中激发出一股勃勃生机,其内在生命的张力强烈地向外突溢,从而产生出不可遏制的表现欲望。”[4]79后来,苏轼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言道:“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28]4这实则生动地描绘了吴道子作画过程当中的高超技艺和磅礴气势。
后一个命题“工画者多善书”则见诸“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彦远试论之曰: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22]105-106张氏此处所言的“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可与谢赫“但取精灵,遗其骨法”[22]18结合起来加以理解,而“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则与谢赫“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22]18说法几乎相一致。从上述文字,我们完全可以见出:张氏认为的无论是“形似”,还是“骨气”,都有赖于画家的主观认识。只有将所描绘对象了然于胸中,从主观上加以明确,才能最终通过有生气的笔墨传达出既有“形似”又兼“骨气”的对象。有学者明确指出,“气韵生动”在张彦远这里“已不仅仅指所描绘对象的精神而言,它更为主要的是转向画家自身精神,由这种精神支配,贯注于用笔表现所体现出的生气活泼的画面效果。”[4]74此番言论,笔者认为是较为符合张氏原义的。
此外,张氏对“气韵”说在赋予新意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诚然,“气韵生动”的概念产生于人物画占主导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到了时代审美风尚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唐代,若还是把“气韵生动”的审美品格或批评标准限定在人物画科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然而张氏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言道:“至于台阁树石车舆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22]106此处的“台阁树石”,大致就是后起的山水画所关注的对象。在张氏眼中,由于自然山水没有生动的样态可比拟,所以便没有气韵可追求,仅仅注意位置构思和阴阳向背关系就可以了。显然,这一认识是较为片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人物画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22]3在画科中占首位;而自五代始,山水画则成为“画家十三科之首也”[22]196。这时对绘画理论有杰出贡献的大画家荆浩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给予“气韵”以新的解读和认识。
(二) 荆浩:“气韵”说从人物画拓展到山水、花鸟画的奠基人
荆浩,唐末五代初人,因天下大乱,隐居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以儒学为业,博通经史,能诗善文,而且还热衷于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荆浩是北方山水画风的拓荒者,同时他也是将山水画推向中国绘画艺术首位的关键人物。关于荆浩对“气韵”说所做出的贡献,徐复观曾言:“唐人几乎没有把气韵,尤其是韵,用到山水画上去的。将气韵的观念应用到以山水为主的作品上,到目前为止,我只能确切指出最早的是荆浩的《笔法记》。”[23]109因此,从徐氏的这句评价中,我们足以感知荆浩对发展和推介“气韵”说的重大贡献。《笔法记》在赓续唐代各家对“气韵”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把“气韵”解释为笔墨表现的效果,尤其是著作中提出的山水画“六要”说(即气、韵、思、景、笔、墨),无疑在相当程度上主宰了后世千余年山水画理论变迁的路向。
通览《笔法记》全篇,它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笔法的探讨来考察、分析和研究如何用笔使墨,以实现圆融的气韵效果。在此著中,荆浩借助和一位老者的谈话论道:
叟曰:子知笔法乎?曰:叟,仪形野人也,岂知笔法耶?叟曰:子岂知我所怀邪?闻而惭。叟曰:少年好学,终可成也。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29]3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荆氏强调的作画要领就在于“图真”二字。陈传席指出,“图真”论是《笔法记》的中心之论,是继顾恺之、宗炳、王微的“传神”论以及谢赫的“气韵”论之后进一步更深切的说法[21]230。所以,“图真”的本质就是“传神”,就是得“气韵”,而“不可执华为实”,“实”就是物之神、物之气、物之韵,亦即是“真”。那么,要达到“图真”,具体如何操作呢?荆氏明言要晓“六要”。有人说“六要”是对谢赫“六法”的分解,其实,笔者认为它是时代赋予中国文人画(主要是山水画)的新内涵,它既是作画方法,同时也是品画理论。
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29]4
这里,“气”和“韵”的意义和谢赫提出的“气韵”意义大致相同。不过谢氏提出的“气韵”是就人物画而言,而荆浩则指的是山水画,“山水的骨体以及所流露出的美感不同于人物,无法像人物画那样取其气韵,只好以笔取气,以墨取韵,以笔取其山水的大体结构得其阳刚之美,以墨渲染见其仪姿得其阴柔之美。”[21]232具体言之,荆氏所说的“气”与张彦远的“意气”有着极深的渊源,意思即画家在作画时,其主观精神作用于画笔时心灵手敏、意到笔随,且一气呵成的表征,这是得山水“真”的首要条件。反之,心手不应,取象迟疑,则必然无生气,无生气即无“真”矣。“韵”指用笔的表现与物象刻画妙合一体的艺术效果。荆氏曾评吴道子和项容画作时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22]326这即是说,在荆氏的心目中,吴道子的画“气”胜于“韵”,而项容的画则“韵”胜于“气”。“思”和“景”就是构思(即张彦远之“立意”)和取象,大约和谢赫的“经营位置”和“应物象形”相对应。“笔”指的是用笔法则,要如飞如动,不能受到物象形体的束缚,这正和“气”相贯通。最后一要“墨”,即用墨要领——用干湿浓淡不同的墨色皴染出物象各尽其态的审美效果,亦即荆氏所言的“文采自然”,这正和“韵”相联系。换言之,即“墨”是“韵”的实现手段,而“韵”是“墨”的呈现效果。所以,清代恽寿平指出:“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30]368-369“墨”之“要”,诚如笔者所言,这是唐末五代时期时代风尚给予荆氏的理论创新。“墨”的概念在谢赫时代没有提及,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绘画多以丹青赋彩。直至唐、五代之际,人们发现了水墨的乐趣,画史记载王维始用水墨渲染。水墨画既兴,所以“墨”色之趣味在唐代开始被大家关注,杜甫不是有“元气淋漓障犹湿”的诗句吗?这正是在赞美“墨”色在艺术传达中所产生的独特审美效果⑥。
除了“六要”之外,荆浩在《笔法记》中根据“真”的程度(即“气韵”效果)提出了评鉴绘画作品优劣的“神、妙、奇、巧”四个品第。在荆氏心目中,做得最完美的是“神”的境界——“亡有所为,任运成象”[29]4,即无所用心地任意刻画物象,此时技巧和精神完全融合为一体。这和张彦远“五等”说的最高品第“自然”相同,此乃最“真”的作品,故称为神品。后面的“妙”(“思经天地,万类性情,文理合仪,品物流笔”[29]4)、“奇”(“荡迹不测,与真景或乖异,至其理偏,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29]4)和“巧”(“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29]4)三个品第,又依凭技巧和精神不能完全融为一体的程度(亦即“真”到“不真”的程度)而有了高低之别。
此外,荆浩还提出画之“二病”说,即“有形病”和“无形病”。“有形病”即“花木不时,屋小人大,或树高于山,桥不登于岸,可度形之类是也。”[29]4“无形病”即“气韵俱泯,物象全乖,笔墨虽行,类同死物。”[29]4所以,“有形病”一般是“形似”的问题,问题出现在“景”上,而“无形病”,乃气韵全无,不可删修。若“有形病”是肌肤之病,那么“无形病”则是膏肓之病。此“二病”说,应该对北宋苏轼的“常形常理”说造成一定影响。
总之,荆浩是一位在绘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具有颇高成就的大家。他的《笔法记》在继承顾恺之、宗炳、王微的“传神”论和谢赫的“气韵”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较有创见的“图真”论。围绕“图真”论,他又阐发了“六要”“四品”“四势”(筋、肉、骨和气)和“二病”等较具原创性的主张见解,这无疑开启了他之后一千多年中国山水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如元代的黄公望、倪云林,明代的文征明、唐伯虎等大画家,都尊崇荆氏是山水画的大宗师。另外,兴于盛唐和中唐之际的水墨山水画,到了唐末有了更大发展。山水画自五代始居中国绘画艺术之首,而水墨山水画又能居山水画的主流地位,荆氏之理论见解实乃起到重大作用。
(三) 郭若虚:崇“气”说之最后一位中坚人物
宋代是绘画美学理论甚为昌盛的一个时代,不仅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论画,而且文人在诗词之余、官员在为政休闲之时也论画。在画家或绘画理论家论画方面,此时有郭若虚、刘道醇、郭熙和韩拙等人。
作为书画鉴赏家的郭若虚,在继承和发展谢赫“气韵生动”说的过程中,堪称是主“气”说全盛时代最后一位中坚人物。郭氏在中国绘画理论这一主“气”的最后坚守中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郭氏提出“气韵非师”说(此说宣告“气韵”由谢赫时代的画面效果明确转向画家的主观精神层面)。郭氏在对谢赫“六法”论的认识上,从理论的高度强调了画家主观精神在艺术传达中的作用。他在其著作《图画见闻志》中言道:“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22]316他认为“气韵”是一个画家先天的禀赋,不可能通过师传和学习而获得。清代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亦曾指出:“笔墨可知也,天机不可知也。规矩可得也,气韵不可得也。”[30]365此处的“天机”即可理解为“气韵”。因此郭氏的“气韵非师”说与恽寿平此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诚然,郭氏“气韵非师”说的提出也不是偶然的。早在谢赫《古画品录》的文本里,谢氏品评姚昙度时就指出:“画有逸才,巧变锋出。魑魅神鬼,皆能妙绝。同流真为,雅郑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31],这里的“天挺生知,非学所及”可看作“气韵非师”说的发端。到了唐代,张彦远进一步强调:“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22]106-107张氏首次提出了画家的身份以及由此身份引起的个人素养上的不同对画作风貌的影响。到了郭氏这里,他继承了张彦远的思想,明确提出:“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22]316-317在中国绘画史上,郭氏第一次指明了画家人品(人的生命精神境界)与画作的品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气韵非师”说一经问世,对其后的中国绘画理论发展,特别是文人论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清之际,董其昌、王时敏诸家曾大谈人品与画品的关系。王时敏在《王奉常书画题跋》中言:“烟云逸致,俱从胎骨中带来,非习学所能企及。昔人所云,胸中读万卷书,足下行万里路,自然脱去尘俗,浚发灵机,洵非虚语。”[32]先天人品和后天学养积淀决定着画品,此语不虚。
其二,郭氏认为笔病问题(或用笔质量)直接关乎作品气韵生动之效果。早在谢赫时代,谢氏所言“六法”之第二法“骨法用法”就已经看到了用笔的巧拙与画作格调的关系。到了唐代,张彦远把用笔问题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再到了五代,荆浩则专门对用笔进行了阐释。而且,唐宋之际“画品”(或“画格”)的出现,某一层面上,也可看作是绘画理论家从用笔的优劣上来评判画作所达到的不同境界。而到了郭氏这里,他在《图画见闻志》之《论用笔得失》中明确提出了“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22]317的论断,而且专门讨论了用笔表现的“版”、“刻”和“结”三种弊病,这些笔病都关涉作品气韵生动效果的实现。此外,由于郭氏“笔病”问题的提出,也引发出后人对此相关其它画病问题的探讨,如元代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提出了作画要去除“邪”、“甜”、“俗”和“赖”四字大要以及明代李开先在《中麓画品》中又提出了“僵”、“枯”、“浊”和“弱”的作画“四病”。总之,郭氏提出的用笔“三病”说,可谓表明了中国绘画发展到宋代绘画理论家等对笔墨表现之重大价值的深刻认识,因为他们体察到了有无生气力量的笔墨所形成的画作风貌是大异其趣的。无疑,这种对笔墨表现效果的深切关注使得中国绘画的笔墨语言愈加显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对自明代开始的绘画进一步突出笔墨表现的独立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三,郭氏十分推崇北宋以“气”胜出的“三家山水”。逮至北宋,中国水墨山水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风貌,一是以荆浩、关仝、李成和范宽为典型的表现雄健的北方峻岭的风格,二是以董源、巨然为典型的表现秀丽的江南风光的面貌。因此,两宋山水画论的美学思想,无论是画家论画,还是文人论画,都集中体现在对这两派山水画风格的品鉴上。那么,郭氏对以气势胜出的“三家山水”的推崇,则彰显了宋代绘画理论家和画家的审美格调。无疑,郭氏对李成、关仝和范宽三家山水画推崇至极,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在《论三家山水》篇开门见山言道:“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前古虽有传世可见者,如王维、李思训、荆浩之伦,岂能方驾近代。虽有专意力学者如翟院深、刘永、纪真之辈,难继后尘。”[22]320接着,他对三人的画风进行了具体评述:“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22]320从其评语不难看出,三家山水在物象刻画和笔墨运用上可谓达到了妙合一体的高妙境界。物象和笔墨的“妙合一体”,代表了宋代画家的审美理想,换言之,即既要有笔墨表现的审美趣味,同时又能生动地传写出物象的形质。有学者指出,此种“妙合一体”即是“以笔墨来应物象形,达于形神兼备的表现。”[4]134然而,郭氏对董源的评价是:“善画山水,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兼工画牛虎,肉肌丰混,毛毳轻浮,具足精神,脱略凡格。”[22]340对巨然的评价是:“工画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但林木非其所长。”[22]352郭氏的后两则评语相比于三家山水,高低轩轾自不待言。具体言之,即郭氏虽然看到了“董、巨”那种以秀润之笔墨状写江南烟岚气象的妙处,但是其心中嘉许的仍是“石体坚凝”、“势状雄强”以“气”胜的劲健山水画品格。诚然,在宋代绘画中,虽然有画家和“院派”们追求描绘精谨、色彩浓艳和笔墨雄健等特点的院体画风,但是,这种风格终究没有成为中国绘画发展的主流。而滥觞于唐代、发展于五代两宋的文人画,却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自元代起一跃而统领整个中国画坛。因此,以郭氏为代表的“主气”论者,在笔者看来,其角色也仅仅只是在文人画开始以“尚韵”论为主调的时代大潮中坚守“主气”说的最后一班岗。
(四) 苏轼:尚“韵”说的肇端者
诚如前文所言,宋代绘画理论有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论画,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文人论画,如欧阳修、王安石、沈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晁补之等。由于文人多有“万卷书”的沾溉,并且注重内在精神的陶养,他们对绘画问题的体悟最终成为主导性的绘画理论,对元明清时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从美学精神和时代风尚而言,整个宋代三百余年是一个“尚韵”的时代。虽然早在魏晋时代“韵”就被广泛应用在人物品评上,但真正在绘画领域将“韵”的美学理论展开的实乃为宋代。有学者分析其原因时指出:“这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倾向有关,而在此发展过程中,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宋代开始,中国文化由外拓型转向内省型,原来以武功、拓边为特点的文化逐渐被以文治、守边的文化所取代,文官制度充分完善,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伴随着这一发展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气’的衰减——或者说阳气的衰减,阴气的上升,而‘韵’却越来越得到生长。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职责不再是仗剑闲游,任侠使气,而是躲在书斋中皓首穷经,修身养性。……这就使得更多的人都痴迷于琴棋书画这类精神的游戏中而无须受社会的现实义务和责任的责难,而在评价人物时这种对事功的疏远得到的是一个非常高的赞誉,这种赞誉最常用的语词就是‘韵’。”[33]此番见解立论深刻,分析透辟。
那么,“韵”在宋代文人论画中的意思是什么呢?笔者以为,“韵”即涵义隽永的余味之意。这种“余味”,再结合文人画的审美理想(或美学品格),可理解为富有诗意(或意境)的画面效果⑦。比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十分赞赏“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绘画审美趣味。他在《鉴画》中曾云:“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34]苏轼在欧阳修的影响下,也非常欣赏“萧散简远”以及“清新”和“简古”等画面意境。此外,米芾还提出了“平淡天真”和“高古”的绘画理想。受两宋时期整个文化氛围的影响,此时期文人画追求的这种诗意(或意境)不是雄浑阳刚,而是偏向于秀丽阴柔的。可以说,这种秀丽阴柔奠定了文人画的审美总基调,无论是以后的元代,还是明清,甚或现当代,虽然出现了“萧条淡泊”等以外的诗意追求,但文人画偏向于阴柔秀丽的总的审美理想没有改变。下面,笔者兹以苏轼和米芾为例,考察他们对“气韵”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苏轼对前代和同时代人的画作写的题跋,构成了其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陈传席曾有这样的评价:“宋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绘画理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能像苏轼画论一样深为文人所知晓。没有任何一种画论具有苏轼画论那样的统治力。”[21]297应该说,这一评价较为公允。综观苏氏的文人画见解,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画面效果而言,苏氏推崇在形似基础上有神韵且有诗意的绘画作品;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来看,文人“有道有技(或艺)”之画是苏氏的绘画理想(第二条不属于对发展“气韵”说的贡献,暂不讨论)。关于第一条,我们可从《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和《王维吴道子画》知其大概。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苏氏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35]的高论。很多人没有根据苏氏所言之语境,认为他论画不要形似,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王主簿的绘画技术性和写实功夫在苏氏看来是毋需多言的,因此,对于王主簿画作的评判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他于是很自然地提出了“天工与清新”的绘画评判标准和审美理想。真正理解了苏氏的本意而加以阐述的要数他的学生晁补之,他在《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中言道:“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36]203另外,结合苏氏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37]和《王维吴道子画》中“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28]4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王维和吴道子的绘画,苏氏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就其个人的审美偏好而言,苏氏或许更加钟爱王维“清且敦”与“得之于象外”的具有诗意偏于阴柔型的绘画风格。
苏氏之后,北宋另一位甚有影响的文人论画者要数米芾。他不仅在绘画实践上开辟了“米氏云山”(亦即“米点山水”),而且在绘画理论上,接续沈括的主张,高推“董、巨”式山水,十分注重“自然”的表现,于是提出了“平淡天真”“高古”等绘画美学思想。
对“董、巨”山水的推崇,第一人当为沈括。他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38]从这则言论看,沈括以褒奖的语调赞美了董源和巨然的山水画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这与绘画理论家论画的郭若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究其原因,因为“董、巨”山水中的物象和笔墨在郭氏眼中是相分离的,没有达致“妙合一体”的圆融境界,但是,这种“用笔甚草草”的笔墨表现,在沈括等文人画家眼中,实为画家主观精神的自然流淌。到了稍晚于沈括和苏轼的米芾那里,他把“董、巨”山水推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因此,米氏对“董、巨”山水和“三家山水”的看法刚好和郭若虚的相反,即米氏甚赞“董、巨”,而郭氏力推“三家山水”。米氏言“董、巨”的作品是“董源峰顶不工,绝涧危径,幽壑荒迥,率多真意。巨然明润郁葱,最有爽气,矾头太多。”[39]166“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39]147“余家董源雾景横批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39]149而米氏对“三家山水”的评语却有些不恭,谓“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多巧,少真意”[39]166,“范宽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39]166,“关仝粗山,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39]166。由此看出,“董、巨”山水之所以受到米氏等文人们的推崇备至,关键一点就在于,他们的作品表现中“从笔墨间流露出人的自然天性,一种活泼的生气”[4]138,而“三家山水”则因笔墨表现的“奇峭之笔”和“多巧,少真意”,且过于拘泥“应物象形”而失去了笔墨的自由表现力。
总之,宋代绘画理论家郭若虚论画和文人画家苏轼、米芾等论画主张的反差,鲜明突显了中国绘画美学品格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自宋代开始,占据主导的绘画风貌由唐代绘画表现中的那种气势雄强以及用笔表现中的应物象形,逐渐转变为借以抒发胸中意气的、用自由灵活的笔墨状写而成就的且偏于“韵”的秀丽绘画样态。从美学品格上言之,即由阳刚雄浑转为了阴柔秀美。而在以赵孟頫开启的元代文人绘画的发展中,特别是随后的“元四家”,四人无不推崇“董、巨”山水画范式,并且以此为正宗。黄公望“师法北苑,汰其繁皴,瘦其形体……自成一体”[40]293,吴镇“师学巨然,俨然一体”[40]294,王蒙“少学其舅,晚法北苑,将北苑之披麻皴,屈律其笔,名为解索皴”[40]293,更不用说倪瓒的画法了,据《画旨》载:“黄、倪、吴、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双行海内”[30]222。《画旨》又云:“元季四大家,独倪云林品格尤超。早年学董源,晚乃自成一家,以简淡为之。”[30]235到了明代,董其昌辈更是把董源推上了“南宗”画祖的地位。如前所述,后人对“董、巨”画风的赞许至极,追根溯源,无疑和整个中华民族崇尚内敛中和、温润文雅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五) 赵孟頫:尚“韵”说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人
元代,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民族和用人政策等,导致了元代绘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人画上。就文人画自身的发展轨迹而言,在历经了唐代的滥觞期以及五代两宋的发展期后,元代可谓是文人画的成熟期。如果说五代两宋文人画的成就体现在理论的建构上,那么,元代的文人画成就则体现在继承五代两宋文人画理论基础上的创作实践中。元代的文人画理论虽有元初钱选的“士气”说,以及中后期黄公望“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说和倪瓒的“逸气”说,但从对谢赫“气韵生动”说的继承和发展上言之⑧,都不如赵孟頫的“作画贵有古意”说和“书画本来同”的观点影响深远⑨。
探究赵孟頫的绘画主张,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倡作画贵有古意;二是力主书法入画;三是提倡师法造化。然师法造化在南北朝和唐代早已有之,所以前面两则影响最大。
“古意”说可谓是赵氏绘画理论的核心。他曾言:“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41]160在这段文字中,赵氏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绘画评判准则和审美理想,认为作画贵在有古意。接着,他指出了元初画坛的绘画弊病“用笔纤细”、“傅色浓艳”。这种弊病可能直接受南宋院体风格的影响。众所周知,南宋院体画发展到后期,刚劲的线条、猛烈的皴法以及渐趋程式化“一角”“半边”的构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最后,他对自己的作画风格作出了“似乎简率”的评价。但是,结合赵氏的众多绘画作品以及绘画言论,笔者以为,赵氏崇尚的是具有一定造型基础且有文化性的简率而非简单的绘画风格。而这种文化性,像他的性格和审美偏好一样,追求的是一种清新淡雅的阴柔之美。“古意”的核心内涵,应该正在于偏阴柔的中和之美里面。
在绘画具体实践中,赵氏力主书法入画。如果说赵氏的“作画贵有古意”是其绘画的审美理想,那么,“书画本来同”则可看成是如何实现其绘画理想笔法上的具体要求。赵氏在其画作《秀石疏林图》卷后自题一诗,有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36]93全诗意思不难理解,即是说,为了表现出石头的质感和特性,可以用书法中飞白法加以诠释;为了画出林木的韵致,可以用书法中写篆书的方式加以表现;同样,要描绘出竹子的神态,则可以利用书法中写楷书“永字八法”的要领来实现;如果有人真能领会其中真意,须要知道书法和绘画的用笔方法是相通的,并且是可以相互借鉴的。随后,柯九思在赵氏的启发下,进一步丰富了画竹石的言论。柯氏曾云“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42]关于书法和绘画的用笔关系问题,早在唐代,张彦远首次提出了书法和绘画用笔相同之论。到了北宋郭熙,他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郭氏曾言道:“故说者谓:王右军喜鹅,意在取其转项,如人之执笔转腕以结字。此正与论画用笔同,故世人之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22]301以上三家书画用笔相同之言论,张彦远针对的是人物画,郭熙针对的是山水画,而赵孟頫则扩展到了竹石花卉画中,但论其对后世的影响,赵氏的无疑最大。某种程度上,赵氏以书入画的主张开启了元代书法性绘画的门径,使得元代文人(士大夫)画家开始关注笔墨自身的审美价值。诚然,这一新的动向,使得文人画的绘画性绘画审美标准发生了向非绘画性绘画审美标准的倾斜,从而亦更加符合文人画托物言志、寄情遣兴的内在要求。
总之,元代绘画,一方面就绘画技法言,以书入画是元代文人画创作实践中的一个普遍特征。虽然早在唐宋时期书画用笔同法的主张已经出现,但很少付诸绘画实践,而到了元代,由于元初赵孟頫的积极倡导,以书入画成为整个元代乃至后世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以前,笔墨主要是用来服务于造型的,而到了元代,文人(士大夫)画家已普遍认同笔墨,除了服务于造型之外,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应该说,这一新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文人画绘画性绘画审美标准向非绘画性绘画(书法性绘画)审美标准的转变。如果说此时这一转变还带有过渡性质的话,即元代文人画还兼顾造型和笔墨的双重标准,那么,到了明清时期,文人画的审美标准已经几乎完全滑向了笔墨的非绘画性标准。另一方面,就内在审美追求来讲,元代文人(士大夫)画家普遍崇尚和大力践行萧散简远和平淡天真的画面意境。如果说在五代两宋时期,由于受欧阳修、苏轼和米芾等文人(士大夫)绘画美学观的影响,萧散简远和平淡天真仅仅是绘画理想,还没有普遍将理想化为实践的话,那么元代文人(士大夫)画家对萧散简远和平淡天真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实践,已不是个别文人画家所为,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元初,赵孟頫因其审美偏好,自觉实践简率而有“古意”的画风。到了元代中后期,“元四家”成为了画面求简之楷模,极力追求画面萧散、寂寞和简远之意境。清钱杜曾云:“宋人写树,千曲百折,惟北苑为长劲瘦直之法,然亦枝根相纠。至元时大痴、仲圭,一变为简率,愈简愈佳。”[30]651在元代以前,南唐董源平淡天真的画风虽深受沈括和米芾的推崇,但客观而论,其画风在五代两宋时期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到了元代,董源的平淡天真画风十分切合文人(士大夫)心境抒发之需要,因此“被推上了元代文人画风格的首席宝座。”[43]毫不夸张地说,元代文人画诸位大家,没有不受董源平淡天真画风影响的,而在元代以后,亦几乎没有一个文人画家或理论家不是言必称松雪道人和“元四家”的。
(六) 董其昌:文人画尚“韵”理论全面且系统总结之殿堂级人物
明清之际的绘画理论,和前代相比,没有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绘画实践命题,其特点仅是集前人之大成,特别注重对传统绘画思想的整理、阐发和总结。而此时期文人画在理论上最显著的贡献,即是在明末万历年间,董其昌正式提出的“文人画”概念。文人画虽滥觞于盛唐、中唐之际,并与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相区别,但直到北宋中后期,才由苏轼首次提出“士人画”的概念,但确切地讲,文人画在唐宋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即与该时期文人画理论内涵相伴随的艺术实践还没有普遍实行开来。之后,文人画历经南宋及元代两百多年的发展,其实践和理论都渐趋成熟,可以说,元代文人画创作才真正实现了宋代文人画的审美理想。到了明清时期,文人画艺术达到极度的繁荣,进而统领了整个画坛。面对文人画的发展盛况,从明初开始,就有一些画家或艺术理论家开始从源流考辨、风格特征及美学追求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脉络。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氛围下,董氏顺应时势,提出了“文人画”的概念。当然,早在董氏之前,宋濂、文征明、王世贞、王肯堂等已经做了一些对画史演变的总结性工作,而且颇有见地。这无疑对董氏提出“文人画”的概念和山水画“南北宗”论铺平了道路[44]。
考察董氏的文人画主张,被他推崇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南宗”绘画审美理想是以王维为鼻祖,以董源为实际领袖,以“米家父子”和“元四家”为中坚。有学者指出,董氏的“南宗”绘画,“是以自娱为目的,以抒情为手段,以柔润为形式,以不为皇家服务和他人服务为原则,又以文人士大夫、高人逸士以及虽居官位而心存隐逸又非贵族的画家为主要阵营。”[45]437相反,董氏所认为的“北宗”绘画,“它是皇族的产物,以刚性线条为形式,而缺乏柔润和平淡天真的韵味。又以贵族和从属于贵族的画院画家(高级工匠)为主要队伍。”[45]437董氏“崇南贬北”,他大力倡导柔、润、淡、清、静的艺术,并把这种风格定为正宗,这直接对整个清代绘画面貌向着柔润的美学格调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与之相反,刚性的、躁动的、具有激烈情绪的艺术,乃至于雄浑的、气势豪纵的艺术视为非正宗,其追随者称之为“邪学”,皆在不可学之列[39]478。我们再将董氏的“南北宗”论与莫是龙、陈继儒和沈颢等人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知“南北宗”论的提出并不是董氏一个人的偏执见解,而是明代出现的一种带有很大普遍性的新的审美趣味或审美理想。这种审美趣味(或理想)即是对“南宗”派系那种“虚和萧散”、“裁构淳秀”、“出韵幽淡”艺术风格的充分强调和推崇,而对“北宗”派系那种“粗硬”、“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艺术风格的贬低和否定[46]。诚然,董氏勾勒下的“南宗”和“北宗”绘画风格的形成,一方面缘自北方自然景象和南方江南山水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另一方面则由于文化上的强烈影响,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重心以江浙为主导地位,从而导致“南宗”那种柔淡秀雅的笔法成为文人画家的审美理想。进一步,从更为深层的文化角度分析,董氏和同时代以及稍后的信奉者们为何要崇倡“南宗”?这应该归结为他们对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文化的高度认同。“南宗”的笔墨深刻体现出儒家文化之温文尔雅、怨而不怒,以及道家文化之法天贵真、不拘俗套的美学意蕴。
总之,董氏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文人画”观点与“南北宗”论,对明末和整个清代乃至近现代数几百年的中国绘画美学品格的陶养和塑造起到了一种主导性的作用。正如清初王士祯评价宋荦《论画绝句》所言:“近世画家,专尚南宗。”[47]亦如清末叶德辉所论:“自思翁持论尊南而抑北,自是三百年海内靡然向风。”[48]两则言论鲜明地表明了这种影响之深远。结合诸位专家贤达的观点⑩,笔者此处对“南北宗”论的价值影响试作一个简短归纳。第一,它旗帜鲜明地确立了“董、巨”“元四家”为系统的“南宗”画的正统地位。第二,董氏的同时和之后的画论大多以“南北宗”为据,如清代的王原祁、唐岱、华琳、沈宗骞、布颜图等人阐述的赞同“南北宗”观点就颇具代表性。考察这些观点,一方面,它们对董氏“南北宗”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修正,或阐述“南北宗”,或发挥“南北宗”,或重新排列“南北宗”人物等;另一方面,明清两代对“南北宗”论的斟酌完善,亦对近现代艺术家和理论家对“南北宗”问题的认识大有助益。第三,由于董氏“南北宗”论的强大影响力,此时期诗文、书法等艺术门类也分“南北宗”,甚至连体育中的武术也分“南北宗”(譬如拳术,柔性的太极拳为“南宗”,刚猛的少林拳则为“北宗”)。此外,董氏的“南北宗”论不仅在国内盛行,而且在日本也广为流传。日本画界受董氏“南北宗”论的影响,他们亦“崇南贬北”,后来日本人干脆把中国的主流绘画统称为“南画”。这虽和董氏之论大有出入,却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受董氏的影响之甚。
结 语
清初之后,关于绘画理论探讨的著作浩如烟海,不计其数,但是大多数理论见解均以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和“四王”的守法、仿古论为基调,然后加上一些阐述和补充而已。稍后虽有“扬州八怪”能承继石涛的思想,但却被目为“恶习”和“狂怪”,他们的影响在当时可谓微乎其微,不足挂齿。而真正使中国画出现新机的思想主张,实始于近现代,如康有为的“变法”论、陈独秀和吕澂的“革命”论、金城和陈师曾等的“国粹”论、徐悲鸿的“改良”论、林风眠的“调和”论,等等。但是,在对传统绘画和美学命题“气韵生动”的继承和发展上,似乎到明末董其昌那里就无出其右了。
考察从东晋顾恺始至清末民初众多有识之士论画为止的一千五百多年的绘画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文人画的美学品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由“重气”到“尚韵”的变迁理路。而在发生转折的关键点上,郭若虚和苏轼二人的贡献是可圈可点的:前者如果说是崇“气”说之最后的中坚人物,那么,后者则是尚“韵”说的肇端者。因此,二人各自在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变迁的转捩点上担负起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后来,在米芾、赵孟頫和“元四家”等人的努力下,中国文人画“尚韵”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稳定发展起来。再后来,到了明末董其昌,因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对以“董、巨逸轨”[41]259为中国文人画范型的图式语言赞叹至极,并且对中国文人画“尚韵”理论作了有史以来全面、深刻且系统的总结。所以,从某种层面而言,中国文人画“尚韵”的理论主张始于苏轼而成于董其昌,的确是有道理的。
注释:
① 关于此部分的内容,请参见笔者刊发于《美苑》杂志2013年第2期第95-97页的论文《谢赫“六法”原义新考》。
② 上述十条,笔者参阅了陈传席的《中国绘画美术史(上)》一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③ 《世说新语任诞》有“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这里的“风气韵度”是作为风气和韵度两个词语使用的。除此之外,关于“气韵”还有两处:一是河南荥阳出土的刻于公元522年(北魏正光三年)的《郑道忠墓志铭》,见有“气韵”一词,其铭云:“君气韵恬和,姿望温雅,不以臧否滑心,荣辱改虑……”(参见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二是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亦见有“气韵”一词。其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参见陈洪、张峰屹等人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④ 关于此处摘录的“气”和“韵”的原文,笔者参阅了谢赫的《画品》(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六朝-元)》,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6-23页)。
⑤ 对“风骨”的理解,笔者赞同陈传席的看法。他认为气、风、骨三字常是同义,风骨即气骨。参阅陈传席的《中国绘画美术史》(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⑥ 其实,早在战国中期的《庄子·田子方》中就有“舐笔和墨”的记载,还有战国晚期的帛画中的墨色勾染,也说明距今两千多年前,墨色就已经在绘画中占据重要地位。只是此时期人们还未赋予“墨色”以独立审美内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制墨技术有了新发展。而到了晚唐,美术理论大家张彦远有了“运墨而五色具”之高论。他正是在看到了“墨”的丰富变化和表现力的基础上,从而肯定了“墨”色在艺术表现中的独立地位。
⑦⑨本部分内容,可参阅拙作《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历程及其美学特征》(载《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92-94页)。
⑧ “气韵生动”这一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典绘画命题,传承到元代,受到道家和禅宗思想的强烈影响。从外在形态上讲,元代绘画以淡和秀雅的阴柔美为主要特征;而从画家内在精神上言,元代绘画更加偏重状我情和表我意的自我精神的抒发。
⑩ 关于论述董其昌“文人画”主张与“南北宗”论的影响,可参阅陈传席的《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485页),以及樊波的《董其昌》(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202页)两书的内容。
即使是在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的鉴画准则之始,在“气”和“韵”不能兼善的情况下,其审美倾向仍是“重气”的。
[参考文献]
[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 刘义庆.世说新语选译[M].徐传武,注释.济南:齐鲁书社,1991:318.
[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36.
[4] 钟跃英.气韵论[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5] 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277.
[6] 老子.老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72.
[7] 刘安.淮南子[M].阮青,注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2.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452.
[9] 柏青.后汉书·三国志[M].刘正平,刘起,何德张,等,译编.通辽: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199.
[10] 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9.
[11] 刘邵.《人物志》校笺[M].李崇智,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15.
[12] 杨成寅.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先秦魏晋南北朝卷[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114.
[13] 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14] 袁昂.古今书评[G]//张彦远.法书要录.洪丕谟,点校.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59-61.
[15]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59.
[16]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3.
[17] 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61.
[18] 王巍.历代咏物赋选[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45.
[19] 刘勰.文心雕龙[M].郭晋稀,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4:332.
[20] 萧涤非,刘乃昌.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诗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92.
[21]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术史:(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22] 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六朝—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
[2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4] 阮璞.中国画史论辨[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25] 张锡坤.“气韵”范畴考辨[J].中国社会科学,2000(2):154.
[26] 韩刚.谢赫“六法”义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2-13.
[27] 金刚经·六祖坛经[M].杨帆,译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68.
[28] 于景祥,徐桂秋,郭醒.苏轼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29] 荆浩.笔法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30] 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明—清).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
[31] 谢赫,姚最.古画品录·续画品录[M].王伯敏,标点,注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12.
[32] 王时敏.王奉常书画题跋[G]//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44.
[33] 张黔.中国山水画审美理想的演变:从“神品”到“逸品”[R].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4:81.
[34] 欧阳修.欧阳修散文全集:(下)[M].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96:617.
[35] 徐培均.苏轼诗词选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67.
[36] 周积寅,史金城.中国历代题画诗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
[37] 屠友祥.东坡题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61.
[38] 沈括.梦溪笔谈[M].刘尚荣,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96-97.
[39] 黄正雨,王心裁.米芾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0] 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G]//于安澜.画论丛刊(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41] 张丑.清河书画舫[M]//李来源,林木.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42] 徐显.柯九思传[G]//宗典.柯九思史料.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4.
[43] 林木.论文人画[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132.
[44] 曹贵.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历程及其美学特征[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8(03):95.
[45]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术史:(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46] 樊波.董其昌[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190.
[47] 宋荦.西陂类稿:第13卷[G]//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37.
[48] 叶德辉.叶德辉诗文集: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0:882.
(责任编辑 文 格)
From “Emphasizing Qi” to “Advocating Rhyme”: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Aesthetic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CAO Gu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After studying the 1500 years of painting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Gu Kaizhi’s discussion of painting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o the end of the discussion of painting by many people of insight such as Kang Youwei,Chen Shizeng and Xu Beiho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we find that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is not unchangeable.It ha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emphasizing Qi” to “advocating Rhyme”.And at the key turning point of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Gu Kaizhi,Xie He,Zhang Yanyuan,Jing Hao,Guo Ruoxu,Su Shi,Mi Fu,Zhao Mengfu and Dong Qichang,all of them have shouldered the sacred responsibility and glorious mission given by history.Especiall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Dong Qichang praised the painting style language of “Dong and Ju”,and made a comprehensive,profound and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theory of “advocating rhyme” in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Therefore,to some extent,the theory of “advocating rhyme” in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began with Su Shi and matured with Dong Qichang.
Key words:literati painting; aesthetic character; emphasizing Qi; advocating rhy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