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里“看不见的人”
2024-12-05谈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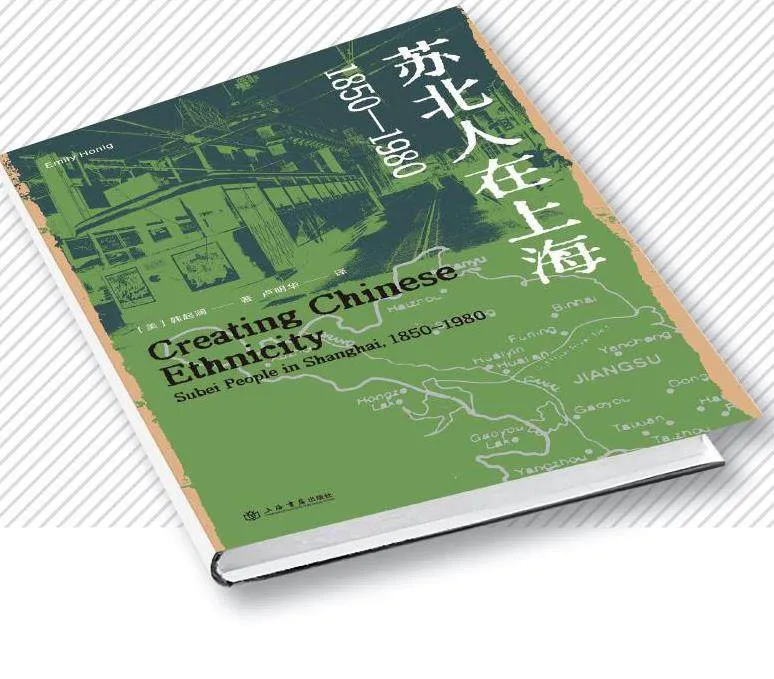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 美] 韩起澜 著
卢明华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10月
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生前唯一出版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以这样一段独白开场,当主人公回忆起自己遭遇的种种“社会性隐形”时,他得出结论:“别人看不见我,那只是因为人们拒绝看见我。在马戏的杂耍中,你常常可以见到只露脑袋没有身体的角色,我就像那样,我仿佛被许许多多哈哈镜团团围住了。人们走近我,只能看到我的四周,看到他们自己,或者看到他们想象中的事物——说实在的,他们看到了一切的一切,唯独看不到我。”
和美国一样,任何移民社会,都会形成一个又一个如同血痂般坚硬的族群。黑人以其肤色的“高可见性”,悖论般地沦为了“看不见的人”。肤色,是从作为主体的我们之中剥离出作为客体的他们的关键。但若没有这殊异的肤色,我们依旧会寻找那些所谓外来者身上不同于我们的地方,可能是口音,可能是文化风俗,可能是饮食习惯,我们必然要高傲地在这些方面划分出高贵与低贱、文明与野蛮。
近代以来,之于移民城市上海,苏北人正是这样一个被构建出来的他者。
在流行文化有关旧上海的想象中,苏北人至关重要,却又常常缺席。上海是摩登的现代都市,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黑暗迷宫,站在上海这一舞台上的,是来自江南与广府的资本家、买办,是流氓大亨、暗杀者与革命家。苏北人被卷入他们的厮杀时,或是扮演打手,或是充当看客,但很少成为主角。他们的命运有时被看成20 世纪苦难中国的象征,可他们没有自我拯救的能力,只能沉沦下去,或者等待着被拯救。
美国历史学家韩起澜出版于1992年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以下简称《苏北人在上海》)是英语世界中第一本将目光聚焦于在沪苏北族群的学术著作。其考察的时间段,正好落在上海开埠与改革开放两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之间。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落败,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以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五市为通商口岸。
翌年11月8日晚间,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爵士一行乘坐“麦杜萨”号抵达上海,在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反复磋商后,中英双方议定11 月17 日,上海正式开埠。
从此,曾经以纺织闻名,“衣被天下”的松江府,逐渐成长为承载着殖民的屈辱与现代化的绮梦的远东国际都会,而来自各个周边省份的移民纷纷拥入上海,国内国外的异质文化,如同各色颜料交织在上海这张巨大的画布上,融合成所谓的海派文化。
江南在地理上切近上海,太平天国起义又迫使江南资本进入上海租界,寻求庇护。江南精英于是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原始股东之一,他们的语言、风俗与娱乐习惯,深深影响上海的市民社会,江南文化成为海派文化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方言正是在吴地诸多方言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嗜甜的本帮菜,亦时常承袭江南浓油赤酱的风味。
由此,韩起澜发现,江南文化在上海的优势地位,无意间塑造出了作为他者的苏北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海话和江南各地吴方言中,“江北佬”都是一个极具羞辱性的詈语。在江南农村中,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外来者,陷入了一种颇为典型的排外反应。移民,即使是季节性的短期移民,也会被视为滋生一切反常现象的他者,主体透过塑造他者,把自身纯洁化了。因此,讨论作为镜像的苏北人,也即是在叩问江南人何以在后殖民语境下构建出一种主体性,而此种主体性又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不过,在进入具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苏北人”这一概念。在吴方言中,更经常出现的是“江北人”的说法。初看,这两个词似乎指涉出一片非常明确的地域,即长江以北。江北人就是来自长江以北的人。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譬如,扬州位在长江以北,可在明清时期,这座城市是江南的代表。而如今被称为苏北的这片区域,古时候并不落后于苏南。尤其是在京杭大运河尚未丧失其作用的时代,这条运河如主动脉般贯穿起苏北的一座座城市,漕运带来的海量财富,让扬州一度成为地区枢纽般的存在。
然而,随着19世纪海运兴起取代漕运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苏北迅速没落下去,黄河改道后的连年水灾,加上长期的战乱,严重破坏了苏北的经济基础。因此,每逢荒年,便会有大量难民自北向南拥入上海。
而当我们用“苏北”一词指代这些难民的故乡时,仿佛从扬州到徐州的这一片土地,都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相似的习俗。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徐州自秦汉时,就已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城市,从他们那坚硬的方言、粗犷的性格便可窥知,扬州则说江淮官话,与南京及安徽相近。
在旧上海,方言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是苏北人的重要方面。尴尬的是,若将所有讲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地区视作苏北,那么显然,彼时的首都南京也应属于苏北,这就与另一个对苏北人的刻板印象相悖。
在江南精英眼中,苏北人是来自苏北黄泛区的难民,进到上海以后,便从事一些低贱的重体力劳动,他们往往聚居在棚户区里,他们的头顶,是只要刮风下雨,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的茅草,身下也是同样的茅草,不防风,不防水,不防火,细碎的草屑粘在他们身上,仿佛也粘在他们粗笨的口音里。一个苏北人的典型形象由此得到显影,仿佛隐形墨水在烛火的烘烤下现出真身。
旧上海的苏北人获得了某种不亚于黑人的“高可见性”,纵使其在外貌上与那些蔑视他们的江南精英别无二致,但他们始终是与摩登上海格格不入的隐形人,只能出现在市井生活的背景中,作为一个擦鞋匠,一个黄包车夫,一个码头搬运工,一个搓澡工或一个理发师。他们总是在服务于人,像空气般持久地存在着,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他们似乎的确在动摇着这座城市的清洁与文明。若是你放眼望去,在这不亚于纽约的国际都会的深处,竟看到一丛丛如坏疽般涌现出来的茅草屋,它们像霉菌一样环绕着租界里的欧式建筑。
可我们不去看他们,就像我们不会注意空气的颜色一样,唯有缺少空气时,我们才察觉到呼吸的必要性,唯有缺少他者时,我们才发现自身的主体性是如此脆弱。
江南精英选择与苏北人割席,很大程度上,亦是殖民文化影响的结果。在租界中,中国人始终处于下位,所以,要想在这样一个变形的文化体系里获得尊重,就必须突显自己与其他中国人的不同,更开放,更西化,愿意拥抱现代文明,讲法律,讲契约精神。
这一切让人联想到法农笔下的殖民地黑人,一旦这些人去过巴黎,便会将他们从巴黎学来的纯正法语口音呵护终身,时常缝缝补补,穿戴在年久失修的声带上。混血文化自然有它的精彩之处,但文化修养若是将人导向某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且那个自恃有修养的人,仍需以弱者因处于弱势而形成的诸多习惯作为参照,印证自身的修养,那么在这所谓修养背后支撑它的,只是傲慢与偏见。他们推崇现代文明,讲自由,讲人性,却唯独忽略了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平等,那不是作为概念的平等,而是作为行动的平等。
不幸的是,对苏北人的傲慢与偏见仍存在于1980年代的上海。而这正是韩起澜写作《苏北人在上海》的时期,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基于一手采访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示出,在去殖民后,歧视苏北人的积习仍然隐藏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之中。
例如在婚恋上,由于缺乏其他选择,70%以上的苏北人最终与苏北配偶结婚。在沪的第二第三代苏北人,很多都会强烈地否定自己的苏北背景,他们在上海土生土长,出门在外时能讲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却仍因那个遥远的祖籍而遭受偏见。其实,到1980年代,苏北早已摆脱贫穷与战乱,因此,他们的祖籍在除上海以外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令人艳羡的存在。
如今,在千禧年一代口中,“苏北”似乎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无公害的地域梗,这个词仿佛是语言的活化石,很少有好事者愿意敲开它,细察其中蕴含的上海城市史,而这段历史久已矿化了的骨骼,就藏在“苏北”这个词所唤起的爱与憎,痛苦与纠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