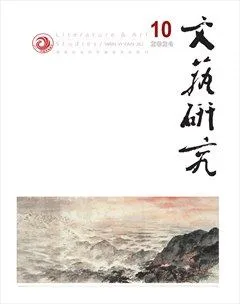“凌驾”与明代制义文风之嬗变
2024-10-25陈维昭
明代制义的理论范畴、修辞手法和批评范式大多借鉴传统诗学和古文理论,但在近三百年的科举实践中,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科举制度环境又使制义范畴、修辞手法和批评范式具备了自身的规定性,拥有新的文章学内容,从而与传统诗学和古文理论区别开来。“凌驾”就是一个典型的制义修辞范畴。在诗、古文传统中,它是一个褒义词,意即超越。当其被挪用于制义理论与批评时,既葆有原先的内涵,又发展出更为丰富多样、更具写作范式意义的特征。在特定历史时期,它又与时代文化思潮交融而成为其表征。从明代制义理论和批评的实际情况来看,“凌驾”指涉两种写作现象:一是才情、思想超越同时代乃至千古,甚至突破主流价值体系;二是在写作修辞上突破时间顺序(如预叙、倒叙),在空间关系上改变形状与位置(如剪裁、嫁接)。后者至今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拟作详论。
一、语意浑然与变序凌驾
文章修辞本应千变万化,既可简朴严整,也可绚烂多彩,要之,贴题为上。然而,在古代文章学传统中,崇雅黜浮、崇简古而抑丽辞,成为主流倾向。比偶俪辞,本为文事之必有。刘勰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尚书》《周易》已多有偶对,而诗人抒怀,大夫联辞,奇偶适变,自然妥贴。但是,唐、宋道学家持“文以载道”观念,重道轻文,宋代理学家尤其强调“作文害道”。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把“辞达而已”注为:“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富丽是道学的天敌。有人问:“作文害道否?”程颐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他所谓“文”,指的是“词章之文”。在程颐眼里,富丽词采成了“道”的对立物。制义为理学文章,对俪辞艳句自然持否定态度,不过,明代科举官方功令规定,制义的主讲部分要采用比偶形式,这导致制义在文体上始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
《左传》被视为文法之祖。后世的很多叙事技巧,在《左传》中已被广泛使用,比如打乱时间顺序、空间关系进行预叙、倒叙、详写、略写等。其中,倒叙被明代中后期的制义继承下来,由此形成一种迥异于明初以来正统制义写作的新理念。明代前期的制义写作多是根据题目的语序渐次展开论述,此即铺叙,而中后期变换题目语序的倒叙、逆叙则被视为“凌驾”。清代康熙间戴名世曾这样概括这两种写作理念:“今之论经义者有二家,曰铺叙,曰凌驾。铺叙者,循题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为此成化、弘治诸家之法也。凌驾者,相题之要而提挈之,参伍错综,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以为此《史》《汉》、欧、曾之法也。”对于“铺叙”与“凌驾”这两种写作理念,历来存在争议。
强调“铺叙”者往往持“以道论艺”立场,把儒家经典神圣化。方苞说,在四书中,“圣人于虚实本末之序,层次推究,语意浑然”。此语可以代表明代、清代正统派制义论家讨论制义理论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四书中圣贤的话语以及对圣贤言行的记述,都有确定的秩序,其虚实本末的秩序、行文层次的推究,形成了浑然一体的语意,不容割裂颠倒,因而制义写作必须按原典语序依次展开。如果不按原典语序展开,就会被视为“驭题凌驾”,冒犯了儒家经典的浑然一体性,在义理上也破坏了程朱理学的正统性与纯粹性。他们认为,阐述四书的经义文,最合理的修辞方式就是顺题挨讲,运用挑剔钓挽等技巧,有损于经典的“语意浑然”。缘此,正统制义文论家坚决反对机法、机局、凌驾等。如明万历二十年(1592) 壬辰科会试被吕留良斥为“格用断制,调用挑翻,凌驾攻劫,意见庞逞”。这十六字断言被后来学者广泛引用,我们可以通过该科程墨来探究其含义。此科首艺题为“知及之章”,选自《论语·卫灵公》第三十二章:“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孔子这里谈及为官的三层境界:第一层是智能及之,但不能以仁守之,则虽得必失;第二层是智能及之,仁能守之,但以不庄莅之,则民不敬;第三层是智能及之,仁能守之,以庄莅之,但不能动之以礼,则仍未尽善。朱熹指出,“此一章,当以仁为主”,“大抵发明内外本末之序,极为完备,而其要以仁为重”。但该章论及“智”“仁”“庄”“礼”四个范畴,写作制义,应该自“智”开始,然后是“仁”“庄”“礼”,顺题挨讲。该科会元吴默之文即依朱注而作,以“仁”字统摄“智”“庄”“礼”,其中两股曰:“人之心,非必独知之境,所当操持,即一威仪,一振作,皆吾心出入存亡之会。人之学,非必本原之失,乃为人欲,即失之威仪,失之振作,亦此心理消欲长之时。”把该章第二节的“庄以莅之”和第三节的“礼以动之”俱摄入“仁”字之中。这一修辞法为万历制艺家击节称赏,但方苞却提出批评:“立义虽本朱子,但圣人于虚实本末之序,层次推究,语意浑然。独括‘仁’字,联贯前后,乃时文家小数,机法虽熟,体卑而气薄矣。”他认为,此文没有按题目语序将“智”“仁”“庄”“礼”四项逐项论述,而是独括“仁”字,并以之联贯前后,虽机法圆熟,但凌驾题序,使八股文的文体卑下。
而崇尚“凌驾”者则持“以艺论艺”立场,强调读经不能拘泥于形迹。汤宾尹说,四书中有些话,虽属“圣贤心曲,托于言而亦外,脱于口而已陈,第令六经、《语》、《孟》圣贤复说一过,亦必有另出一局、再开一新者”。如此,则变序凌驾不应被视为侮经叛圣。从作法修辞的角度看,制义是一种论体文,此体以恃才使气、力压众说为贵,所以凌驾本来就符合论体文的禀性。此等立场视制义为一种“艺”,应“相题之要而提挈之”,根据科举考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题型而提出优良的修辞策略。这样看来,不仅凌驾之法可用,一切文之修辞法均可用,关键要看是否切题。清代乾隆间倪承茂云:“论文者宗化、治则主挨讲,宗隆、万则主逆提,各分途径,二者交讥。不知行文次第,当视义理何如;篇法顺逆,当视语气何若。挨讲、逆提,岂容胶执?如‘天命之谓性’,‘性’字宜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字何缘先见?此逆提不可概用者也。况化、治合作,挨讲中题义实亦贯通;隆、万名篇,串插中语气未尝倒置。文当以理为准,初无偏主,昌黎云:‘惟其是尔。’”该顺该提,相题而为。这种以艺论艺的立场在明代隆万时期大为流行。
二、题型变化与驭题凌驾
对于明代制义流变史,人们往往强调成化、弘治的里程碑意义,认为八股文体定型于成化,有所谓“成弘法脉”之称。然而,八股之体式、技法之强调与文风之变异,早在成化之前就出现了。钱禧说:“今学士家未得见国初文字,故溯源成、弘耳。”的确,文献的缺失使人们做出不符合实际的论断。
明代制义于正统间即已出现命题求变、文风诡怪的情形。正统十二年(1447) 丁卯科福建乡试出了一道俗题“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鸡豚、牛羊等俗物毕竟不宜出现于崇尚典雅的制义中。正统十三年戊辰科会试题“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乃比兴题,前一分句只是一个比兴,主旨在下一分句的“学”,题目的比兴结构召唤着修辞上对“机局”的考虑。至景泰二年(1451) 辛未科会试,则出现截搭题“百世以俟不厌”,钱禧称此题“题似求新”,指出该科考官命题已经有“求新”的意识。
虽然制义的题目选自四书五经,但当题目只是选取其中的几句话甚至一句话时,题型就会变得十分多样,相应地,考生应对的修辞法也会变得非常复杂。
随着科举的发展,顺题挨讲的修辞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题型。面对长题、偏正题、截搭题,顺题挨讲就不太合理。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各直省多出长题,如顺天首题为“子贡问师也全章”,应天首题为“子曰管仲之器全章”,浙江第三题为“夫人幼而玉哉”,湖广第一题为“子曰鄙夫全章”、第三题为“有楚大夫为善”,山东第三题为“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全章”,山西第三题为“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全章”,广西第三题为“孟子见齐宣王慎与”,贵州首题为“尝独立学礼”。出现这种情形,究竟是由于考官为了提高题目的挑战性,还是纯属偶然,有待考证,但长题的命题方式对制义的修辞形态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元臣说:“凡长题,依文讲则题役我,凌文讲则我御题。”“依文”者,顺题挨讲也;“凌文”者,凌驾驭题也。左培说得更加具体:“题目既长,作者当自出一机轴,令题为我驾驭,不可令我为题牵制。题情漶漫,我约之以剪裁;题句错综,我当之以凌驾。擒龙捉虎,扼要争奇,如整衣挈领,金针暗渡,任千条万绪,可一索而穿矣。”他又说:“一曰摄神驾局。或头绪多端,旨义涣散,作者于起处,须总摄其神,凌空驾局,则血脉钟聚在前,下便走瓴破竹矣。二曰击首应尾,如弄丸承蜩。三曰参字贯意,使文机联络。”钱禧虽然对颠倒经典文序的做法极力反对,但他仍然承认凌驾法在应对长题时的必要性。一方面,他说:“是科直省多出长题,一时程墨皆以穿插凌驾为能事,先民步骤荡然无存矣。”另一方面,他在万历三十七年己酉科乡试首题文之后又评道:“长题势必用凌驾,然亦须有体裁,轻重、宾主,毫不可乱。”可以说,是长题的命题方式诱发了制义之凌驾。长题如此,截搭题更是这样。
截搭题被视为与冠冕正大命题背道而驰的歧途,不过,其出现,也基于科举制度本身。由于明代八股文命题范围限于四书五经,那些冠冕正大的语句容易成为考生押题的对象。明清时期,坊间即有“拟题”一类的书籍售卖,如署名张鼐编撰的《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一书,预拟科举考试中可能出现的题目,并提点相应的作文法。如果考生拟题而获售,则不能考出考生的真实水平。袁黄说:“近来每科建议只用平正……甚至题目只出旧者,使人人得以揣摩,而帖括饾饤之徒,尽记旧文以入彀。科场本以网罗豪杰,而今反为浅庸易售之地,非法也。”于是,改变命题的常规形式就成为必然,截搭题应运而生。清代路德说:“国家取士,师儒训士,不能变而更之,岂崇尚时艺哉?正所以杜剽窃也。试之以策论,则怀挟者滥登;试之以表判,则宿构者易售;惟时艺限之以题,绳之以法,一部《四子书》,离之合之,参伍而错综之,其为题也,不知几万亿,虽有怀挟弗能赅也,虽有宿构未必遇也。”所谓“离之”,即是截题(包括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虚冒题、承上题);所谓“合之”,即是搭题(即一般所说的截搭题),其结果则是“其为题也,不知几万亿”。这种命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备考中的拟题、押题之风。
但是,从以道论艺的立场来看,考官命题时对经典又截又搭,冒犯了经典的神圣性,于是有官方的科场条例对考官命题作出规定,禁止割裂命题。嘉靖十一年(1532),礼部尚书夏言条奏科场三事,“乞令考官今次会试所命三场题目俱要冠冕正大,有关理道,不许截裂牵缀”。既要防止考生拟题宿构,又不许考官出截搭题,这个矛盾一直到清末科举废止都没能真正解决。
明代中期以来,截搭题逐渐出现于乡、会试中;在地方府、州、县的小试中,截搭题更是提学官用以训练士子八股文写作的常规手段。既然截搭题不可避免且普遍存在,那么,由其催生的修辞技法也越来越成为制义修辞的常规。清代道咸间高骧云说:“书有全章全节,题止数句或一句半句,命题者不过令发明此句之旨,并非断章取义。”截搭命题并非蔑视经典的完整性,而是以特殊的方式诱发士子对经典完整性的领悟。它截取四书五经的某半节或语意不能自足的句子为题,如果按题文顺序敷衍注疏,显然不成文字。作者必须对题目的上下文乃至对全章、全节的义旨成竹在胸,构思时首重机局,行文时不粘滞于题目字面,才能取胜。左培说,巧搭题“语虽若判,旨实相同。其中词有顺逆,意有重轻,得力全在接缝过脉处,绾合有情,方称巧手……近日搭题,亦以凌驾为主”。只有如此凌驾,方能在修辞上驾驭好截搭题。
可见,题型对制义修辞和文风具有一定诱导、形塑作用。正因为明代正统以来有求新变异的命题倾向,才有险怪奇崛的文风。成化间丘濬针对当时出现的奇诡文风说:“统、泰以前,士大夫制行立言,以质直忠厚、明白正大为尚,而不为睢盱侧媚之态、浮诞奇诡之词。”成化二十三年(1487) 会试同考官赵宽也指出:“近日作者竞以险怪奇崛相高。”正德二年(1507) 丁卯科浙江乡试出“子路有闻有闻”题,邵宝的墨卷抓住“恐”字发意,这已不是先民苍浑之风,而是后世(尤其是隆万) 挑逗、挑剔文风的滥觞。总之,成化文风的凌驾变异,与截搭题的出现有直接关系。
三、老释思想、心学思潮与义理凌驾
在明代中后期那类“以我驭题”的凌驾修辞中,作者的写作个性得到张扬。当这种凌驾之风蔓延到义理阐释领域时,就可能严厉冲击程朱理学,这必然会受到官方的围剿。
作为一种经义文体,明代制义并非如方苞所说,仅仅要求士子“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它还要求士子在体认圣贤义理之后抒发己见,在小结之后设计一个大结。制义的这种文体结构及其功能来自宋代王安石的大义。钱基博说:“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王安石奋笔为之,存文十篇;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眉山苏氏父子,亦出其古文之余,以与安石抗手;然皆独摅伟论,不沾沾于代古人语气;其代古人语气者,自南宋杨万里始。此则四书文所由昉也。”他指出,“独抒己见”“独摅伟论”是宋大义的文体特征,这源于宋代文人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情怀。在明代制义中,此种独抒己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大结。左培说:“文至大结,时文中古文也。文已说尽,又自我评断一番,使有归结,须凌空驾驭,死中求活,有断制而调古,方是家数。”可见,大结为思想上凌驾程朱提供了空间。嘉靖十六年丁酉科广东乡试,已出现考官所撰“词义荒谬”的“诡怪”程文,受到言官弹劾,于是才有十七年的正文体、禁《庄》《列》之议。该年官方功令规定,会试文字务必醇正典雅,“其有似前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文,必加黜落……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将试卷送出,以凭本部指实奏请除名,不许再试”。嘉靖十六年广东程文应该是引用了《列子》《庄子》的语句或思想,故被视为“诡怪”、大坏文体。而要求独抒己见的大结,恰好为道、释思想的抒写提供了空间。万历十年壬午科应天乡试副主考沈懋孝所作程文之大结说:“盖闻太上,知有之,次亲之、誉之。人亲誉我者,我投以迹也,无意则忘,忘则人亦忘我焉,而天下化。斯治古之极,而养之至乎?然在所自养矣。”这实际上是引述《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帝王之治天下,最高的境界是百姓不知其有上;其次则是百姓亲之、誉之,其下者则是百姓畏之、侮之。王锡爵主试万历十四年会试,声称制义“不必避二氏百家”,而常常非议程朱、专事凌驾的考生袁黄也在其主试下中式。
明代制义的大结在明末大多被删,崇祯间杨廷枢、钱禧编《同文录》所录明文已是如此。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科场条例即以防作弊为由,不许制义作大结。因此,在清人编的明文选本中,很难看到明人张扬主体意识的大结。对于制义大结或正文中的独抒己见,持道学立场者视为洪水猛兽。清乾隆间四库馆臣批评明代隆万启祯时期的文风,即说:
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
可见,当凌驾不仅发生在修辞层面,也发生在义理阐释层面时,就会被视为“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从而危及专制体制。
明代中叶,以我驭题的凌驾意识也得到过王阳明心学思潮的哺育。嘉靖十一年壬辰科会试前夕,夏言上疏请变文体以正士习,责主司以定程式,简考官以重文衡。嘉靖帝说:“文运有关国运,士子大坏文体,诚为害治,宜明禁谕,务醇正典雅,明白通畅。仍前勾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则主考具奏处治。”但是,就在该科,桑惟乔应“大哉尧之全章”题而作的墨卷被视为“开凌驾之端”。罗念庵说:“此科之后,大变厥初,风藻如许、弘丽如薛,岂不斐然,终伤大雅。”嘉靖二十年辛丑科会试,由于礼部尚书温仁和的主试衡文,那种超越结构修辞意义上的凌驾文风更为盛行。此科首题“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取自《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夫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以博施济众求仁,孔子让其返求诸近。温仁和的程文前半部分即借用《易经》“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而凌空发论:“不知仁道至大,有自其一端而言者,有自其全体而言者。如一念之善,仁也,推而言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亦仁之极功耳。如一事之善,仁也,极而言之,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亦仁之大用耳。”对此,杨廷枢觉得“颇快人意”,钱禧却认为是“凌驾法”,感叹“民怀(温仁和字——引者注) 弘治间人,何破坏古法也”!这种凌空发论已有一种挣脱约束、放飞文思的倾向。
那位为文“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的归有光,也追随着心学的潮流。归有光曾写过三篇《物格而后一节》题文,题中隐含着“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等“八条目”。吕留良指出,对于此题,若顺题挨讲,则空衍无奇,于是嘉靖间的作者“但于局阵求异。好新者为凌驾破碎”。归有光同题文第二篇并不在语序上“凌驾破碎”,而是在义理上以王阳明的“致良知”进行阐释,其提比曰:“诚能于典学之始,而启之以格物之功,于天下之理无不穷,而于天下之物无不格矣,则物者,吾之知之所资也。外缘无穷之象,而内识自然之心,理明义精而可以扩其天聪明之尽,良知自此以不蔽也。知既至矣,则知者,吾之意之所因也。内极昭旷之原,则几分善恶之介,机融神朗而可以致其纤毫之必察,独知自此以不欺也。”吕留良批评此文为阳明学说所“惑乱”,比如:“‘外缘无穷之象,内识自然之心’,都似是而非。圣贤所谓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请求体会,到贯通彻尽处,便是格至,不分内外。若谓缘解外物,以求试内心,正是分内外。圣贤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识心则甚,识以自然之心,尤属邪异之旨,如此说,则‘外缘无穷之象’一句已早契阳明痛棒了也。既见得万象属外,要内识自然之心,又要缘象以识,那得不契他痛棒?”指出归有光以心分内外去解释孟子的良知,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对科举文章的影响,这显然是在义理阐释上凌驾官方悬为标准的程朱理学。
四、考官旨趣与凌驾风尚
面对从儒家经典中选取的题目,究竟是顺题挨讲,还是变序凌驾,是恪守程、朱的诠解,还是引用阳明学或释、道二氏作别解,其间有多种影响因素。而对制义文风的形成与流变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考官。从制度设计角度看,朝廷人才选拔理念是通过考官的命题、衡文、录取等实现的。明代乡、会试的考官聘任制度一直处于调整中,从明初的由朝官与地方教谕组成考官群体,逐步发展到由阁臣主持会试、由京朝官主试各省乡试。阁臣、翰林、詹事官等成为考官,不仅提升了人才选拔质量,也引导、塑造着天下的文风士习。宋濂、董伦、杨溥、杨士奇、金幼孜、黄淮等先后成为洪武至宣德间的主考官。这些人也是明初的文章领袖、台阁体的创作主体,其台阁文风引导、塑造着景泰之前质朴忠厚的制义文风。这主要是通过命题、衡文与选编《考试录》实施的。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有些考官的经学思想和文章旨趣不一定与朝廷一致,这是明代制义文风嬗变过程中的最大变数。
明代考官中,在制义修辞方面影响天下士子文风转变的典型个案是王锡爵。王锡爵一般被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倡导者,但他在会试衡文中讨厌平庸,专取峭削。这种修辞取向在诗、古文传统中是合理的,但在制义语境中却被视为导致凌驾文风的始作俑者。万历五年,王锡爵以詹事掌翰林院,负责庶常馆馆课。何宗彦说:“嘉靖末季,操觚之士嘐嘐慕古,高视阔步,以词林为易与。然读其著述,大都取酉藏、汲冢、先秦、两汉之唾余,句摹而字敩之,色泽虽肖,神理亡矣……二十年来,前此标榜为词人者,率为后进窥破,词林中又多卓然自立,于是文章之价复归馆阁,而王文肃先生实其司南也。”把“操觚之士”与“馆阁”对立,视王锡爵为重建馆阁文章之价的司南。
然而,王锡爵的文章并非只有纡徐庄重一路。冯时可说:“其为文章,穷变极化,削涤卑琐,振挈高华,有驾鸾凰捕虬豹之势,而天窍自发,神理自标,上不为古人束,下不为今人拘,所谓竖立三界,非与?”万历元年癸酉科顺天乡试,王锡爵任主考官,他为“诗云不愆节”题所作程文,在论述题面的遵先王之法而得保治之道的义理之后,于大结里说:“然使三代以还,人必里居,地必井受,舞必韶夏,服必邹鲁,能以治乎?要之,谨任人,持大体,而王者躬明德于上,虽玄黄异饰,子丑殊建,不害为继述也。夫周官月令试之而不效者,岂法弊哉?故曰王道本于诚意。”对于此文,后人多有不满,王世懋说它一味凌驾,苏浚认为属于程文变格,王锡爵之子王衡则说:“识见高,笔力高,故锋芒四出,不复可掩,而遂为后世疾行怒视者开一法门。”所谓“疾行怒视”,或许是指该文的束股由于采用反问句式而呈现出咄咄逼人的声气:“故诗之言‘不愆’也,则守法之一效也。何也?法立于先王而天理顺焉、人情宜焉。其在后世,但一润色间而画一之规模自有四达不悖者,何愆之有?诗之言‘不忘’也,则守法之又一效也。何也?法立于先王而大纲举焉、万目张焉。其在后世,但一饰新间而精详之条理自有咸正无缺者,何忘之有?”这种姿态与语气显然有别于先民的质直忠厚。清代康熙间汪份编《庆历文读本新编》收录此文,并对王世懋等人的“一味凌驾”论断表达异议,认为王锡爵此文写得“议论精实”。这或许是因为汪份所看到的王锡爵程文已经被删去了大结。
万历十四年,王锡爵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主试丙戌科会试,视陶望龄七篇制义平淡无奇而予以黜落,又以袁黄“七破七承,皆刻意求新”而予以录取。这是明代制义史上的一件标志性事件。俞长城说:
隆庆改元,去繁芜而归雅正。至于癸未,冲淡极矣。石篑乡试尚仍其旧。丙戌遇太仓,目为七作平常,有激而归,力求遒炼,己丑遂冠天下……己丑后,尚凌驾者为俗法,尚斫削者为俗调,是皆石篑开之。然癸未之习不改,其弊亦同于此。
“太仓”即王锡爵。陶望龄追随癸未科倡导的雅正冲淡文风,但在丙戌科会试中,其七作被王锡爵认为平庸而黜落,而袁黄的作品因求新而中式,于是他盛称王锡爵“乃今日取士之指南,百世语文之标准也”。这或许给了陶望龄启发,他随后作文“力求遒炼,己丑遂冠天下”。从此,凌驾等制义新风尚开始盛行。
在通过担任主考官衡文、录取,从而以心学、老释二氏之学影响天下文章方面,徐阶、李春芳、焦竑、杨起元等人最具代表性。艾南英说:“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这里的华亭执政,指嘉靖末首辅徐阶,他推崇阳明心学,有姚江弟子之称,嘉靖三十二年任会试主考官;而兴化执政,指隆庆间首辅李春芳,此人曾是阳明后学王畿的学生,于隆庆二年(1568) 继徐阶为首辅,同年任会试主考官。李春芳将自己所写的程文编置于该科《会试录》首篇位置,对当时以及其后数十年的举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破题是“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矣”,顾炎武明确指出,这个“真知”是典型的道家用语。这篇八股文出现于《会试录》首篇,无疑是个信号,向天下应试士子宣布,在制义中引用道家思想或语句,将得到鼓励,正如顾炎武所说:“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会试被后人视为明代文风士习走向衰颓的一个转折点。高嵣说:“万历自壬辰而降,宣城以穿插纤佻为巧,同安以排叠凌促为工,一时靡然从风,真气销亡。”隆万间理学家杨时乔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儒学独尊,唐宋虽崇信不纯,权术虚无杂用,但仍然是首孔子、次佛老,“未始凌驾独宗”。至明嘉靖以来,心学盛行,阳宗孔子,而实阴用佛老,又凌驾独宗,这就危及儒学统序了。此等制义,在隆万时期比比皆是。
“凌驾”作为明代制义写作与批评的高频范畴,不仅指涉与儒家原典语序相关的写作修辞,也包括义理上的程朱理学与阳明学、老释二氏之学的纷争。而参与命题与衡文的考官之儒学思想、价值观念与文章旨趣等,也会对科举文风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使得“凌驾”之意涵变得更为丰富。通过对“凌驾”范畴及现象的历史、制度、文化、文章学等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明代的文风士习,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责任编辑 陈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