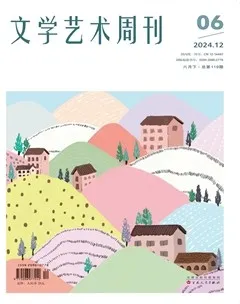论元稹诗歌对《庄子》生死观的接受
2024-10-23马李茗
中唐多数士人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倾向,往往儒释道兼修,以儒家的济世情怀为立身之本,以佛道作为困顿中的自我调节,元稹同样如此。据学者统计,现存元稹诗歌中对《庄子》典故化用多达87处,远超其他来源的典故[1],可见《庄子》对元稹思想价值体系的建构有重要影响。生死观是《庄子》哲学体系中极为重要,也极具特色的模块,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元稹诗歌中对于《庄子》生死观的接受,也是他在对《庄子》的接受中体现得最为显著的部分之一。
一、人生苦短,浮生若梦
元稹诗歌中呈现出的生死观自始至终都铺着一层相对悲观的底色。综观其现存诗作,不难发现《庄子》中人生苦短、浮生若梦的思想 频繁出现。
关于人生苦短,《庄子 ·逍遥游》中有“朝菌不知晦朔”,元稹诗中也以“菌生”抒发人生短暂之叹,如“菌生悲局促,柯烂觉 须臾”。又如元稹诗中“生物固有涯,安能比金石”,化用《庄子 ·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感叹生命之有限,无法似金石那般长久。
关于浮生若梦,早在校书郎时期,二十余岁的元稹便写下“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异少何为”,认为人生百年皆是梦幻,年老年轻并没有什么区别,借此安慰比自己年长的友人不必为年华逝去伤怀,这其实是以一种更为消极的思想去宽慰消极的情绪,流露出少年老成 之感。而当他经历了近十年的贬谪,几番病重,蹉跎半生后,他又一次写道:“渐觉此生都是梦,不能将泪滴双鱼。”此处浮生若梦的悲叹相较年少时,是更为深刻的痛苦与叹息。《庄子 ·齐物论》中有言:“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人生便如一场大梦,但是在醒来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其实身在梦 中,而醒后也许会面临与当下完全不同的处境。这样的思想虽然显得虚幻消极,但在人生极其艰难之时,或许确实能给人以些许希望与慰藉。
二、死生有命,命途多舛
《庄子》有文:“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一切事物的生灭就像日月交替一样,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自然现象,人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坦然接受大道的安排。元稹诗亦有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诗人写生死由命,兴衰付天,似乎契合《庄子》的思想,但庄子敬重自然之道,接受其一切运转变化,而诗人显然对所谓“命”与“天”心存不满。王粲与屈原的幽愤被历史埋没,平生之志最终也未能实现,而天道是无情的,并不会因此对他们特殊眷顾,就如江流始终奔涌向前,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此处元稹既是在为先贤申冤,也是在为自己遭遇的排挤迫害而愤懑不平,他虽 然借用了庄子生死由命的思想,但最终想要表达的意趣却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的不平其实是元稹对于天命的一贯态度。他在《酬别致用》中就直言自己“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绝不会因为所谓“命”与“时”的不顺便轻言放弃。在《人道短》一诗中他更是指出:天道不能惩恶,违背道义的奸佞之人依然可以安享一世富贵,并不曾遭到任何惩戒;天道不能扬善,圣贤之言皆是仰仗人而代代流传,是人使道无穷;天不及人有创造力和判断力,人更能有针对性地促进社会发展。最终他得出“天道短,人道长”的结论,认为世间还是要依赖人力治理,一味仰仗天道并不会使人间变得更好。他的思考相较于《庄子》, 显然多了一些属于儒家的积极进取的部分,而不再是一味地消极顺应。
除却生死由命,《庄子》中还指出人生中的各个阶段同样是由遵循着自然规律不断推进的。《庄子 ·大宗师》中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道的阴阳造化就如同一切生命的亲生父母,它赋予人形体,让人生存,且在庄子看来,生是一种劳碌,衰老是逐步走向安闲的过程,而死亡才是最终的安歇。元稹诗中也常常流露出对生之劳苦的感慨,并多处化用《庄子》, 表达因世事缠身、命途多舛而产生的厌倦疲惫之感。如“一世营营死是休,生前无事定无由”,“营营”化用《庄子 ·庾桑楚》,感叹人的一生都 无法免除奔忙劳碌,唯有到死才能真正安息。又如他在一场重病稍减后,百无聊赖中写下“世间除却病,何者不营营”,他有感于自己此刻因病而得的闲暇与旁人的忙碌,不由感叹世间除去自己这病人,还有谁不是疲于奔命呢?再如“我受簪组身,我生天地炉。炎蒸安敢倦,虫豸何时无”,“天地炉”亦出自《庄子》,抒发了诗人被困于仕宦生涯中,在贬谪之地恶劣的环境里深感倦怠,却又无法解脱的痛苦。
人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难免会感到身心俱疲,即使入世之心强烈如他,有时也会生发出退隐之意,想要顺随自然,不再执着地追求或是改变什么:“况兹百龄内,扰扰纷众役。日月东西驰,飞车无留迹。来者良未穷,去矣定奚适。委顺在物为,营营复何益。”诗人自问“营营复何益”,《庄子》中也有劝诫世人的句子“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但是就其进入仕途所抱有的济世的初衷而言,这里流露出的甘于淡泊,“委顺”以求个人的安闲,其实依然潜藏着一份对于蹉跎岁月、平生之志无从施展的难言悲慨。这份退隐之心,说到底是元稹郁郁不得志时情感取向的一时偏移,对于立志要“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氂”的诗人而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他都无法真正做到不问世事。
三、彭殇无异,生死齐一
《庄子 ·齐物论》中讲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道观之,万物齐一,生与死本质相同,长寿与短寿也没有绝对的区分。元稹的生死观中,也有《庄子》齐物思想的体现,如“天地为一物,死生为一源。合杂分万变,忽若风中尘”。
元稹对于生死关系的探求,主要出现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且由于其自身思想体系的复杂性与人生经历的特殊性,许多时候他对《庄子》的接受会与其原意存在差异,使《庄子》的内容在诗作中呈现出新的内涵。
第一种情境是面对死别之痛时。庄子妻死,他却并不哭泣,反而“鼓盆而歌”,因为于他而言生死通为“一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是“气”的一种呈现形式,死只是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已,正所谓“大道周流”,为死而悲,反而 是“不通命”的表现。[1] 在《六年春遣怀》中元稹写道:“小于潘岳头先白,学取庄周泪莫多。”面对发妻韦丛的逝世,一年多的时光也未能冲淡他的悲痛,此句正是他试图通过学习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来缓解丧妻之痛的体现。
第二种情境是自己病重时。元稹在通州时,曾在病中写下《遣病十首》, 其中有这样 一段:“为生信异异,之死同冥冥。其家哭泣爱,一一无异情。其类嗟叹惜,各各无重轻。万龄龟菌等,一死天地平。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惊。借如今日死,亦足了一生。”诗人身体欠佳,时常生病,再加上多年贬谪荒凉之地,其间路途颠簸、心绪郁结、水土不服、缺医少药等因素叠加起来,更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摧残。在通州时,他不幸患上疟疾,病情之沉重令他自己都已不抱生还的希望,甚至已托人给远在江州的挚友白居易送去了一封近于绝笔的信。诗人此时还未到四十岁,可谓正值壮年,却已在这一次次病痛中被迫去思考生死之事——他不得不设法自我宽慰,以面对那不知何时便可能突然降临的死亡。“万龄龟菌等,一死天地平”便是他用以开导自己的话:有着万年寿命的神龟与不知晦朔的朝菌都逃不过一死,当死亡降临之时,天地万物皆是平等的。因而不论生命长短与人生境遇如何不同,世间所有人最终都会走向同样的归宿,生前种种在死后也都不再作数,那么,即使过早地逝去,也不必惊慌难过了。诗人以此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从而能够豁达地面对自己的生死。
不过此处元稹虽然接受了《庄子》的观点,将长寿与短命等量齐观,但其中的逻辑仍有不同。《庄子》中的“齐”是通过相对主义的视角得出的。《庄子 ·齐物论》中道:“天 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不是从外形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比较出的结果,而是从天性是否得到圆满 的角度来看:“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虽大山亦可称小矣。”[2]因而只要衡量标准转变,同样的事物对比起来便可以有全然不同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便无所谓大小,无所谓寿夭,彭殇自然也可以是“齐一”的。相较而言,元稹的“齐”则是通过更为世俗化的诠释路径,以及更贴近日常的思维达到的——死亡面前,众生平等,这是所有生命共同的结局。同时期的白居易在《赠王山人》中写道:“闻君减寝食,日听神仙说。暗待非常人,潜求长生诀。言长本对短,未离生死辙。假使得长生,才能胜夭折。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彭生徒自异,生死终无别。”松树与槿花虽然生命长短差异巨大,但最终都难逃一死,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人也不必因恐惧死亡而乞求长生。他对《庄子》这一观念的接受大体也是通过与元稹相似的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庄子》的理解方式。
第三种情境是困顿失意之时。此种情境下诗人往往是借《庄子》生死观中的齐一思想来书写自己对朝堂黑暗的不满与抗争,相较于前两者,与《庄子》原意的差异会更分明。如《思归乐》中:“浮生居大块,寻丈可寄形。身安即形乐,岂独乐咸京。命者道之本,死者天之平。安问远与近,何言殇与彭。”诗歌作于810年元稹被贬江陵时,在此之前他在河南御史台任职,因弹劾房式不法事被罚俸回京,回京途中在敷水驿又因争厅一事遭到宦官殴打,最终以“轻树威,失宪臣体”[1] 为罪名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此事对于元稹的打击极大。《思归乐》全篇言语锋利,情绪强烈,表达了自己的坚守,也表达了对朝中小人的不屑。上面这段中,诗人认为殇与彭是一样的,长安与江陵也是一样的,但他并非真正认可这点,而是要以此向打压他的奸佞小人宣言,这样的贬谪于他而言不算什么,他也绝不会因此妥协,所谓“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又如《放言五首(其一)》中:“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这虽似酒后狂言,却是诗人面对政治中的艰难处境时的真实情绪反映。“死是等闲生也得”一句表面是阐发自己对于生死的态度,实则是以“放言”的形式向政敌表明自己无所畏惧、绝不低头的立场——自己连生死都无所谓,那其余的事更算不了什么,朝中那些敌视自己的人就算百般刁难,又能如何呢?
四、结语
《庄子 ·让王》中将脱离世俗的人分为三类,认为“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元稹正符合其中“养志者”的形象,可以为了平生之志将生死置之度外,但终究未能到达“致道者”这种理想境界。但这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在《和乐天赠樊著作》中他直言其志:“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解悬不泽手,拯溺无折旋。神哉伊尹心,可以冠古先。其次有独善,善己不善民。”他情愿舍弃自己百年的安逸,换取万物安生,以此在有限的人生中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而不愿独善其身。就事实而言,无论是前期的“直躬律人”还是后期的“权道济世”[2],他确实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道”,即使因此在生前身后遭到了诸多误解。
《庄子 ·骈拇》中指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 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在庄子看来,“利”“名”“家”“天下”等皆是外物,而“殉”则意味着为这些外在之物牺牲个体的生命,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元稹平生的所作所为与《庄子》的“养生”思想可谓全然相反。但不可否认,从元稹流传的诗作看,《庄子》对其生死观的塑造确实有着诸多影响,只是由于他的人生经历与个人的价值判断,最终形成的观念保有其独特的生命底色,与《庄子》终有差异。
[作者简介]马李茗,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1] 出自胡遂、尹芳丽《试论元稹诗中的〈庄子〉典故与诗人心态》,《求索》2015年第6期。
[1] 出自吴迪《庄子“齐生死”的逻辑理路及其思想特质》,《理论界》2017年第6期。
[2]出自(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
[1]出自(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中华书局出版。
[2]出自(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典藏本),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