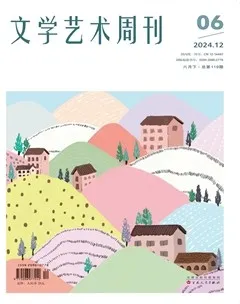真实•多义•群像
2024-10-23上官艳艳
叙事一直是纪录片绕不开的话题,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纪录片的故事性越来越强。范俭导演的纪录片《活着》便以纪实化的影像讲述了叶红梅夫妇做试管婴儿的故事。本片以独特的微观叙事打开宏大的历史视角,将镜头聚焦平凡而又特殊的“失独”家庭,用多维度的人物刻画重新审视历史灾难;影片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倒叙和多线索叙事的方式,以点代面;在矛盾的设置上,多种矛盾使得影片更具故事性,同时将影片的主题延伸,完成影片的主题升华。
一、真实:现实人物与历史事件
由于纪录片真实性的特质,要求被摄对象和事件的真实。在范俭导演的纪录片《活着》中,影片将镜头聚焦特殊人群——地震后“失独”家庭。影片开头,出现“谨以此片献给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们”字幕,在这里, 导演将影片的人物延伸,指代屏幕之外更多的人。在真实事件的呈现上,作品以汶川地震为背景,聚焦叶红梅及其他家庭做试管婴儿的故事。汶川地震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大事,范俭也不例外,但是“2008年的环境过于混乱,很难冷静下来”[1],所以他选择了滞后,在经过走访之后,他通过志愿者与这些家庭建立联系,用地震中失去的生命和震后生命的延续作为参照,将生命的无常和有常通过影像表达出来。
在范俭的纪录片《活着》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存在一个特殊群体,即那些已经逝去的孩 子,导演分别从影像和声音两个角度来呈现。在影像表达上,多为孩子的旧物件,这里面包括衣物、生活用品等,但是最直接的呈现方式还是旧照片。摄影术诞生的神话起源中,有“木乃伊情节”[2],照片和影像是最容易将人的容貌和肉身封存的方式。
(一)三重维度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刻画通常分为三个维度,生理维度、心理维度和社会 维度。生理维度及人的身高、体重、外貌等自然生长条件,对于这部分的影像呈现,无疑照片和视频是最好的选择。照片和视频作为影像资料,在还原已经逝去的人物时,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一点吻合了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保障了人物真实的特点。
在心理维度的表现上,主要手段是人物的采访。这些逝去的孩子们的心理特征多通过他们的父母的访谈来表现。在纪录片的发展史上,采访和访谈是纪录片的主要表现手法。在拍摄前期,纪录片导演往往需要和被摄者建立良好的关系,通过采访的方式介入,创作者更好地走进被摄者的内心,但是采访和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主观性较强,通过父母的描述还原人物形象还存在一定的偏颇性。
社会维度也是建立这群在地震中逝去的孩子的形象的重要表征之一,他们的社会形象首先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孩子,在提倡计划生育的年代,大部分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在家庭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其次他们的身份还是一个学生,影片所聚焦的叶红梅的孩子祝星雨是在新建小学上学,影像中出现了灾后的校园遗址,以及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影片中有一个重要的场景,就是部分家长都来到新建小学的旁边,对逝去的孩子进行怀念和祝福,车水马龙的街道人潮拥挤。这段影像中,范俭导演在拍摄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坚持用影像呈现社会问题和不同的声音。
(二)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
2008年5月12 日,汶川地震的消息快速 传播,地震造成的破坏性和对生命的摧残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活着》中有相关历史影像的插入,在开篇的4分50秒处,通过声音转场,插入地震时的真实影像资料,黑白色代表过去和历史,快速、晃动的镜头是地震发生时的真实记录,哀号声与深沉哀痛的背景音乐充斥耳朵。
范俭对地震灾难现场的拍摄是富有诗意的。在关于都江堰新建小学旧址的纪录中,前景是破旧的黑色铁门框,后景是夷为平地的荒地,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紧接着镜头对准墙壁上学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这背后仿佛就是 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钢琴教室三的微黄色的木质门框,里面却是挖掘机和地震过后的破败景象。在影像处理上,范俭用门框式构图去展现震后的现场,揭开历史的伤疤,《活着》也是一扇窗口,展现地震带给普通人的生活的影响。
二、多义:倒叙、多线、隐喻
(一)倒叙:人物自我成长的完成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影片开头是叶红梅和丈夫将孩子的衣物扔到河里的情节,这也是影片的结尾,是叶红梅夫妇不断释怀过后所采取的行为,而《活着》用摄影机记录了这一切。在纪录片中,“一般都按照顺序纪录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因为这比较符合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但有时纪录片的作者会出于叙述、美学、文化意义的考虑,会‘竭力改变自然的序列’”,如“通过倒叙与预叙造成悬念,吸引读者对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事件的结果牵肠挂肚”[1]。
《活着》采用倒叙的方式,除了设置悬念外,更重要的是对人物完成自我成长的外化。叶红梅夫妇往河里扔衣服的行为如果只在开头出现,可以理解为怕睹物思人而做出的行动;如果这个情节出现在高潮之后,可以表现为夫 妻二人与孩子的告别仪式;如果出现在影片结尾,在叶红梅夫妇生下二胎之后,但这种假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得知生下的二胎是个男孩子的时候,父亲祝俊生与女儿祝星雨的诀别是满怀愧疚和遗憾的。导演让这个情节出现两次,叶红梅夫妇在经历了试管婴儿手术的折磨之后,仍然与孩子无缘,于是他们跟自己和解,扔掉了女儿祝星雨的衣物,准备迎接新的生活,完成人物的自我成长,结局的出现也顺理成章,他们通过自然受孕生下二胎。
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说“纪录片是对自然素材的创造性使用”[1],倒叙在影像的处理方式上其实是对叙述时间做出的调整。在《活着》中,有清晰的时间标记,表现在人物的服饰、植物的生长变化、天气等信息中。同一情节不同的出现顺序和出现次数能够改变影片的整体效果,倒叙在这里不仅仅是结构上的调整,同时承担了铺垫和过渡的功能。
(二)多线叙述
《活着》的叙事始终以叶红梅做试管婴儿手术为线索,其高潮是叶红梅夫妇最后一次做试管婴儿手术。在设计上,导演并没有把关注点聚焦在叶红梅一个人身上,还包括与她同行的好友高国英夫妇。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做试管婴儿的过程充满了紧张感和未知,不同结果对他们的人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悬念设置很好地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主动积极地参与影片的叙事。
《活着》的结局是出人意料的,最后一次试管婴儿手术失败后,影片开篇的场景再次出现,镜头跟着叶红梅夫妇回到他们地震前的旧居,整理祝星雨的旧衣物,扔进河里,代表叶红梅夫妇真正的释怀。当一切都要落下帷幕的时候,影片打出字幕“叶红梅夫妇在三个月后意外自然受孕成功”,相比之前的等待和被宣判的过程,最后这个结局反而令人感到一种平静。叶红梅夫妇在2011年5月12 日生下一名男婴。下一个镜头,在叶红梅的家,父亲祝俊生在女儿祝星雨的照片前挥泪倾诉。
在叙事结构上,《活着》以叶红梅一家做 试管婴儿手术为主线,穿插了几个相似家庭的情况。影片还采用了隐喻蒙太奇和交叉蒙太奇。影片的拍摄地是震后的棚灾区,影片开篇,摄影机对准了棚灾区前面的菜园,绿意盎然的颜 色和棚灾区的灰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绿色在影像表达中还代表着生命和希望,影片将蔬菜的生长过程和叶红梅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交叉剪辑,蔬菜遭遇的虫灾和地震的天灾有双关的语义。
三、群像:多层矛盾叠加
(一)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制度
《活着》的矛盾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 是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 自然即汶川地震,天灾让这群人失去了至亲骨肉,社会层面即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家提倡优生优育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政策,震后国家支持和允许“失独”家庭做试管婴儿同样也是。天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新的问题,它推动国家重新做出相应的调整政策,范俭导演用镜头语言默默地记录下了一切,比如祝俊生到社区去领补助,叶红梅通过电话向医生建议增加试管婴儿手术机会的诉求等。《活着》的叙事情境是地震后“失独”家庭的生活日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被浸润在一个个细小的情节中。
(二)家庭的破碎与重组
矛盾的第二个层面是人与他人的矛盾。在纪录片《活着》中,有很多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探讨。第一个是如果这些夫妻没有孩子,婚姻是否应该继续。在影片中,叶红梅的一个朋友在聊天中说,她愿意离婚,但是还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还可以帮忙带孩子。第二是是否应该抱养一个孩子。叶红梅关于抱养孩子也表达了自己明确的态度,抱养的始终跟自己的不一样。多个场景和谈话都表明了这些家庭在失去孩子后经营婚姻的处境。
在人与他人的矛盾中还包括男性与女性的矛盾。首先体现在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上, 从祝俊生和叶红梅的谋生方式中体现,男性可 以靠体力劳动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而女性多 考虑体力较轻的工作;其次体现在家庭分工中,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男性多承担抚养家庭的重任,在影片中,祝俊生去青海打工,他们的女儿从小就懂得爸爸赚钱辛苦,所以要求自己和妈妈节约用钱;最后体现在生育观上,我们能看到叶红梅因为做试管婴儿所承担的苦痛和祝俊生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能为力。
(三)非理性的自我要求
矛盾的第三个层面是人与自我的矛盾。在纪录片《活着》中,叶红梅和祝俊生的内心经历着巨大的矛盾。叶红梅与祝俊生的第一个孩子祝星雨是一个女孩,所以他们强烈地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这样就可以认为是祝星雨重新回到他们身边了,这样的美好夙愿从情感的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又是存在问题的。比如在影片最后我们看到祝俊生含泪和女儿告别的场景。在范俭关于地震的同题材的纪录片《十年:吾儿勿忘》中,导演记录了试管婴儿的成长,能明确感受到这些家长将二胎看作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的替身,所以他们的情感寄托和 要求对新生的孩子来说是种伤害。
群像原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一群 人物的形象”[1],在电影艺术中,群像表示人物在三者及以上,范俭在访谈中谈道,一开始他聚焦的是三组家庭,一个是很成功地怀孕,另外一个是不想怀孕却意外怀上了,而叶红梅是比较曲折的,所以“他将着力点放在了这家人身上”[2]。在纪录片《活着》中,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矛盾贯穿全片,牵引着叶红梅、高国英、刘江琴等这类“失独”家庭的故事。此外,在影片中,叶红梅出现的场所都是人物较多的,比如棚灾区、医院病房、公共交通、震后纪念园等,在这些场所中,叶红梅获得了讲述自己故事的契机,并且也成了一个倾听者,多个人物的声音共同完成了该片的摄制,最后将情感凝结,献与所有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
四、结语
范俭在采访中就谈到过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审视,他对媒介事件拥有敏锐的嗅觉,能够透过表象看本质,并且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转换到影像的表达中。在纪录片《活着》中,范俭用独特的视角展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将叙述视角对准了叶红梅夫妇,用倒叙和多线叙述的方式结构影片,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提出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共同辅助影片完成了真实、多义、群像的人物塑造,传递出生活、生命、母爱的伟大力量。
[作者简介]上官艳艳,女,汉族,山西阳城人,西安培华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
[1]出自《纪录片〈活着〉记录生活新希望》, 《中国妇女报》2012年1月21 日。
[2] 出自范俭访谈《在生命的无常与有常中坚韧〈活着〉》,凤凰网文化频道2011年12月5 日。
[1]出自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
[1]出自景秀明《纪录的魔方:纪录片叙事艺术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
[1] 出自范俭访谈《在生命的无常与有常中坚韧〈活着〉》,凤凰网文化频道2011年12月5 日。
[2]出自安德烈 ·巴赞《电影是什么》,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