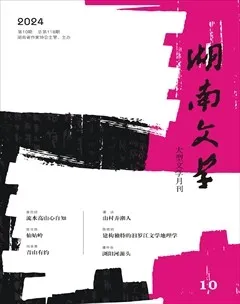在汨罗江流域发现“文学中国”
2024-10-22佘晔
“楚人肚量大,湖南好汉多。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这是著名作家莫言先生给韩少功文学馆的题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给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赞赏。亲爱的读者,如果您不是在湖南生活、写作,您对汨罗江及汨罗江流域作家群有怎样的认识或想象?反之,如果您就是土生土长的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中的一员,您又如何看待自身并期待获得怎样的业界评价?
一
汨罗江,千百年来静谧流淌的自然之河,因屈杜之魂而成文化之江,浩浩汤汤。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条绵延千年的华夏文脉源流至此,汨罗江流域文化因“蓝墨水”的衬托而更加丰富、多元、具象。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单一与封闭强化了人们对水、水系、水域的依赖和崇拜,有水的地方才有耕作,才有文明孕育和碰撞的可能。我想,相较于文明、文化、文学的演变与衍生,汨罗江流域如何进入这一历史视野并对接当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会是我们解锁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密码。
在百年乡土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地域作家群体的发散式涌现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京派、海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东北作家群等作家群体皆因鲜明的文学主张和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闪耀文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被人们知晓但只在有限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地域作家群,如湖南益阳茶子花派作家群、江苏里下河作家群、贵州乌江作家群等。时间是最伟大的魔术师。这些不同类型的地域作家群也经历了文学史的洗礼和自身的更新迭代,有的渐渐消隐,有的慢慢转型,有的发展壮大,正是在这样一种此起彼伏、沧海桑田的时代变幻中,汨罗江流域作家群在新世纪的文学长廊中逐渐浮出地表,逐渐进入主流文学视野,逐渐被人们关注和谈论。这一群体到今天仍在持续发力,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实力和潜力,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一是这一群体有着“顶层作家”和“基层作家”共同助益的人才梯队和成长环境,这对整个群体气候的形成和作家独特气质的培养至关重要,上有顶层引领,下有坚实根基,汨罗江流域作家群所需的文学供给和养料在这片底蕴深厚的土地上基本可以自足。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一群体的累累硕果,与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从2000年开始的“候鸟式”定居汨罗密不可分。韩少功先生的重返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他对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影响广泛、深刻而持久,作家韩少功与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与这片他曾经奉献过青春的土地相互馈赠,相互成就。我想,这也是一位作家除了创作出优秀作品之外的另一重要成就和价值了。二是这一群体携带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中西与内外等种种二元对立又辩证统一的文明因子。与当下“新南方”“新东北”热议背景下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相比,这一群体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明确的地域分布、经典的作家作品以及扎实厚重的群众基础和写作氛围而显得更为独立和独特。人文、地理、历史、文学在此深度交融汇通,也由此确证了这一作家群体的不可或缺。
因此,我们坚信,汨罗江的深厚历史、人文气息、地理景观、个性性格不同程度地滋养、造就、型塑着汨罗江流域作家群,没有哪一个地域作家群可以如此深刻地与一条文化大河世代相连,生生不息。汨罗江流域的文明赓续,在马桥,在山南,在水北,在坪上村,在连尔居,还在寒门,在大地,在日夜书写中,在修改过程里……汨罗江作家群应自觉呐喊,使这一方水域的神奇与韵味穿越当代文学研究的迷障,喊破时空,刺痛那些麻木呆滞的神情,找寻一种新的“汨罗经验”和“汨罗写作”新突破。
二
在汨罗江流域发现“文学中国”,首要是积极关注、研究汨罗江流域作家群,要害是如何关注、研究这一地域作家群。关于这一点,笔者建议从“地方路径”出发来探讨和观照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创作生产。
“地方路径”概念的提出最早源于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一书的启示。在这部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著作中,柯文试图在中国的历史逻辑、文化养成中梳理中国现代性的线索,其理论模式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业已形成的中心—地方格局提供了研究、反思的依据,一种着眼于地方的文学现代化进程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凸显自身价值。2020年,李怡教授在《当代文坛》开设《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栏目,可看作是中国学者对柯文“地方路径”观点的呼应。“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产点,它重新厘定了中心与地方的关系,为我们感受文学史的原始形态提供了现实路径。近年颇受学界关注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等创作现象可谓是其鲜明注脚。我们的“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视野与眼光,自觉成为中国文学“汨罗路径”的典型生发地,自动融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的布局和版图中去。
“地方路径”概念与我们日常提及的“地域文学”“地方文学”“文学地理学”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地方路径的重点在于路径,意味着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意义。借助地方路径研究,有益于追踪和挖掘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体的复杂结构和丰富面相,以及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的方式和经验。同时,地方路径更是对以往传统文学研究注重时间意识的逆反与转向,可深化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空间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于具体而微小的空间之中的,空间中隐含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感受,“地方路径”让我们重新审视“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和自恋,而是由此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引入地方视角、关注地方经验,有助于为“现代中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汨罗元素和经验。
“地方路径”研究是对新的学术领地和学术方法的重辟,引发了人们对地方文学以及地方作家、作品的重新审视,一些边缘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将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意义。李怡教授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一文中,从李劼人、郭沫若等人的创作与趣味出发,提出成都存在另外一种现代性嬗变的地方特色,这一走向现代的地方路径值得分析,它与北平路径、上海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版图。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创作实践出发,去关注这一区域不同作家、不同风格的创作,不刻意遮蔽,也不肆意夸大,重返汨罗江文学史建构和文学创作的现场,发现散落在历史深处的知识碎片及文学根须,通过这些有可能被忽视的作家、作品和材料,重构汨罗江流域文学史。从地方性视角出发去窥探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视角、方法、阐述的新突破,在汨罗发现“地方路径”的重要存在,是对中国文学既有版图认知的扩展。在地方作家如何通达现代中国这一问题上,无疑,韩少功老师在汨罗构筑起了独一无二的文学地标,也为中国文学抵达远方、抵达深处提供了丰富的汨罗资源。
三
与世界上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与运用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地方路径”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它的价值的大小和有效性的限度还有待时间来检验。引入“地方路径”来观照汨罗江流域作家群,只是让我们能更全面地关注到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位作家,打破中心与边缘的尴尬,畅通顶层与基层作家交流的渠道和机制,同时让我们更自觉地关注这个群体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发现散落在边缘地带、隐秘角落的文学元素和情绪,使跟这一群体有关的文学细节、细部之种种不被遮蔽和遗漏,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汨罗江流域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也无法重新勘定这一群体业已形成的文学史结构和格局。
另外,考虑到身体和生活方面的原因,韩少功老师决定,从今年开始不再定居汨罗。这是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文学细节,但对汨罗江流域作家群来说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韩少功老师的再度“撤离”,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创作与成长,只能交由时间来见证。
无妨,在汨罗江流域发现“文学中国”,韩少功、熊育群、黄灯的身体力行不断给我们新的文学启示和经验;“汨罗六蛟龙”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蒋人瑞、吴尚平、逆舟,以及其他汨罗文人持续发力,在国内文学刊物上的频繁亮相展示着他们创作与评论兼具的丰沛才情;未来,随着汨罗江流域文明的繁衍生息,一定会有更多文学新星从汨罗走出,为中国当代文坛的汨罗元素加持。在感性、丰富、生动、绵密的地域经验之中,生长出一支思想性、思辨性、先锋性、人民性、现实性混融的新时代汨罗文学大军,彰显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风格与特性。成为中国当代地域写作群体的重要分支,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是坚持,更是信任,是期待。
责任编辑:罗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