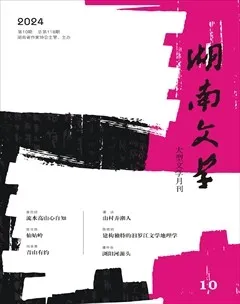陶家巷
2024-10-22杜华
路
过了石狮桥,就到谈家垄,过了谈家垄,就到石子岭,过了石子岭,下一个坡,再上一个坡,再下一个坡,就会看见一大块水田,你从水田望过去,那大山下边就是陶家巷了。小时候,我舅舅陶利斌就是这样教我和弟弟记路的。末了,他仍不放心,忍不住弯下腰来,把一双大手撑在膝头上,再问上一遍:“记住了吧?”我们便懵懵懂懂地点头:“记住了,记住了。”
其实呢,不管舅舅怎么叮嘱,这条曲里拐弯,七扭八折,掩映在杉树、枞树、杨树、柏树、楠竹和各种灌木间的黄泥路,我直到读初中时才真正记住。有回老师领我们读《桃花源记》,我脑壳里灵光乍现,回闪出舅舅的话细细寻味:经由一条神秘清幽的小道,深入大山环抱之腹地,眼前是葱茏开阔的水稻田,山山岭岭云遮雾罩,山上溪水清亮,山下屋舍俨然,天空像面银镜,映照出苍苍莽莽的青绿、灰绿、草绿、幽绿……这里若种上桃花,岂不正是桃花源?
没料到,此番遐思从母亲那里得到印证。此“桃花源”同彼“桃花源”在血缘上竟真是一脉相承。说着,我娘搭上楼梯,从柜顶上的纸箱子里搬出几部又大又厚发黄的《湖南陶氏总谱》来。细读族谱,陶氏一脉可上溯至陶姓始祖上古帝尧陶唐氏、开封侯陶舍、东晋名将陶侃。湖湘陶氏始祖陶侃,官封长沙郡公,母亲湛氏,勤俭坚贞,以德育人,与孟子的母亲孟母、欧阳修的母亲欧母、岳飞的母亲岳母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陶侃是晋南朝靖节公陶渊明的曾祖父,湘汨陶氏系出陶渊明第五子佟公之后。他们在明洪武年间迁入湘阴东关外,由此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据考证,族谱所记“湘阴东关外”,便是陶家巷。一路走来,先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600多年。陶家巷并不是狭长巷道,它由村落北边的陶家大山、唐古岭、沙婆岭、顶星峦、王思岩和南边的乾公山、下坟山围成一块贝壳状盆地。谷地两边峰峦兀立,中间地势平缓,土肥水阔。地形貌似保守的陶家巷,实则四通八达,先辈们用脚板踏出来的古道星罗棋布,犹如山之脉管,隐秘而又康衢。
一年暑假,我在陶家巷小住,舅舅讲要带我去汨罗买西瓜吃。我遥望顶星峦,深阔的蓝天下,白云悠闲地挂在山腰上,山的那一边,就是汨罗了。但山那么高,谁能爬得上去?且山上怪石嶙峋、林深树茂,除非变成鸟,张开翅膀飞过去。何况在我看来,翻过一座大山去买个西瓜,简直要把豆腐盘成肉价钱。舅舅看出了我的不情愿,就说,一两个钟头的事,打个转身就回来了。我不信。舅舅挑一担空箩筐,拉上我就走。我问舅舅走哪条路,舅舅说,走水路。我更不信了,但因为好奇,我硬着头皮上了路。
“水呢?”我问。
“在山上。”舅舅说。
果然,跟着舅舅爬上山冈后,眼前出现一面几丈高的褐色石壁,壁上挂一帘清清亮亮的泉水,捧来洗手脸,冰凉透骨。我们顺着水流走,脚下渐渐变成了铺着细密沙石的小溪。小溪前方是一片疏朗的竹林,正是午后,竹林里丝毫没有暑热,凉风阵阵吹拂过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舅叮嘱我小心蛇虫,折了一根树枝,领我钻进竹林深处,沿水迹下行。一段路后,就看见了一条横着的小路和一片水稻田。蛙鸣隐隐约约的,穿过清香的竹叶,在林间斑驳松软的泥土上跳跃,似乎为一个悬疑故事写好了结尾。顺着水田拐一道大弯,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湘阴不通火车,汨罗才有火车站呢,真的到汨罗了。我惊喜地看到,站台边有一个南杂商店,花皮西瓜就摆在门前的箩筐里。
石与水
北边大山盛产麻石,山上巨石壁立,宛如天降石盾。或站或躺的石盾,既阻挡来自北边的寒冷气流,又守护水土。春夏雨水滂沱的时节,大雨冲刷山林,石头被洗得发亮,树木吸饱了水,又肥又绿。牧牛人身披雨具,赶着一队黄牛从王思岩下来,来到山腰上的蛇形水库时,被一池烟雨吞没。他在朦胧诗意中行走,若隐若现地成为青绿山水的点睛之笔。
陶家巷人恋山,把屋舍盖在山脚边。他们把麻石运下山来,切割成石柱、石条和石礅,修房子时打基脚、搭台阶。天晴时,婆婆老倌子坐在麻石台阶上,和萝卜玉米黄豆黑豆绿豆豇豆一起,晒着太阳打瞌睡。雨来了,收走晒盘,搬把矮凳坐进屋檐下,听着哗哗流水声,也打瞌睡。陶家人信赖石头,从不担心泥石流。他们认定,石头就是天兵天将变的,下凡来护佑村庄。
南边的山是矮山,不知何时,人们在山上种满了板栗树和楠竹。秋天一到,板栗多得总也捡不完。女人们带着娃娃,提上大驮篮,个把钟头就能捡满。捡板栗时,娃娃们一路搜寻野葛。野葛藤好辨认,山里人都认得,但若想挖出它们深埋的根茎,得喊力壮的男人背锄头来。男人们按照娃娃侦察兵留下的记号挖野葛,就算慢腾腾地挖,一天也能挖上好几担。野葛根被打成浆,用清水沉淀,铺在麻石上狠狠晒几天,就变成了白白的葛根粉。葛根粉是陶家巷的山珍,用来搅糊糊,冲鸡蛋,吃了生津解渴,清心安神。
初春的水田像一面面铜镜,铜镜边上“锈迹斑斑”。它们是鱼腥草、车前草和水灯芯,都是寻常人家的珍贵草药。舅舅极少上山采药,当他从田间走过,看见田畴上肥美的药草,会通通收入篓中。药草洗净,晒干,被勤密地送到了我娘的手中。家里人若遇上感冒、拉肚子、长疖子,熬一碗喝下,次日即好。
水田霸道,一片连着一片,把山中间的空地都铺满了,菜园子只能挤在田坎上、山脚边。泉水从山上石头缝里钻出来,绵绵不绝,纵使大旱也不干涸。它们从灌木掩护的小溪沟涌向田园,欢欣而又周密地浇灌着庄稼和蔬果。水田是天兵天将布下的棋局,“棋”开就能得胜。农夫们蹲在水田边,看着谷子一颗一颗鼓起来,像看着女人怀里的胖娃儿。
菜园子葱茏又柔软,像一块块绣花手帕,针脚清新,不同凡俗。从屋舍出来,背着锄头、挑着箢箕的男人,带着石头和山的气息。他们侍弄南瓜、冬瓜、黄瓜、白菜、包菜、茄子和辣椒,如同在手帕上镶嵌珠玉。
群山呵护的陶家巷,气候温暖湿润。夏秋季节,草木疯长起来,馥郁的空气盈满山谷,仿佛一坛鲜花酿的酒。农夫们摘“珠”取“玉”,红光满面,像刚从酒缸爬出的醉汉。
村子里家家都打有石井。从晨光初上到暮霭降临,井水用去好一大截。次日晨起,又已盈满,一片幽波,在晨曦下汪汪晃荡。夏天,人们用井水冰西瓜、黄瓜、香瓜,吃进肚里,又甜蜜又解乏。云秀娭毑给我讲,喝刚打上来的井水,清凉大补,用井水漱口,还可健齿护牙。我问,要牙膏吗?她讲我们那时哪有牙膏,用草灰一擦,含几口水,咕噜几下子,就完了。她将牙齿龇给我看。九十多的老人呢,一口牙齿还没掉几颗,颗颗瓷白,如细小珍珠。
老辈儿
陶家祖上出过不少人物。如两江总督陶澍、“八千湘女上天山”之中的女将陶勇、国务院总理陶铸等等。前辈们翻看族谱,诵读《陶氏家训》:“为官不可不廉,修身不可不诚,教化不可不明,公道不可不彰,法度不可不守,诗书不可不读。”领悟先贤苦心后,立志承守家训,继扬家风。他们在祠堂开办义学,小孩读书不取分文。新式学校建立后,为鼓励求学,族中贤达捐设了氏族基金,周济弱者,奖励翘楚。我舅他们那一辈,读过老书,又上过新学堂的大有人在。
长者们知书达理,洞明世事,因而威望极高。后辈们办大事办喜事,会先向老辈儿禀明。操持的细节、礼数,持家与忠孝的规矩,由长者悉数教诲。他们如数家珍的“老话儿”,晚辈们早已烂熟于心,但每逢拜见,还得恭恭敬敬再听上一遍,全当是温习。十几年前我表哥娶亲,带了新媳妇拜望长辈,到了上屋场云秀公家。
早闻云秀公的训诫与别家长者不同些,甚至每年还有更新,便问新嫂嫂,云秀公如何说?
新嫂嫂说:“媳妇就是陶家女,公婆好比爹娘亲。”
“还有呢?”
“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盘算一世穷。”
“还有呢?”
“不吃三月鲫,不打阳春鸟。”
“还有呢?”
“祖山上头不砍柴,新竹园里怕扯笋。”
你看,年纪最长的云秀公,环保观念了然于心。
老辈儿年轻时,大都会一门手艺。男子学漆匠、瓦匠、木匠、泥匠、剃头匠,或是锡匠、皮匠、修鞋匠。女子便学绣花、纳鞋底、捕鱼虾。掌握的手艺不仅能照顾生活,还能养家糊口。但当这些技术被现代工业取代,手艺人就越发显得珍贵。云秀娭毑有三个儿子,上头两个爱读书,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南京工作。小儿子舒坨爱玩泥制陶,跑到窑上拜了一个老师傅为师。舒坨玩泥巴天赋不高,师傅让他做一个蒸钵,他做出来既不像碗,也不像盏,更不像钵。师傅就说,你不如去学泥匠,把泥巴往砖头上抹就是,到广东打工,能赚一百块钱一天。你学陶艺,只怕会饿肚子。舒坨不听,心里记着他爹云秀公的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人只要勤快,吃得苦,铁杵都能磨成针了,还怕做不成蒸钵?舒坨拉坯、上釉、烧窑,沉醉其中。师傅也就没办法了,仍旧耐心指点。一晃几十年过去,舒陀变成了舒公,也变成了老倌子。舒公做的坛子、罐子和碗盏在时光的窑火中嬗变,不仅能养活一家人,还由家庭主妇手中的寻常物变成了时兴的艺术品。舒公的孙子久坨,也爱玩泥制陶,一边干活一边搞直播,一下就成了网红。
戏
陶家巷人爱看戏,逢村里唱戏,舅舅便摇风搭信,邀我娘回娘家去看。有天吃过午饭,我开车带娘回陶家巷看戏。到了石子岭,锣鼓声从前岭滚下,咚咚锵,咚咚锵,由着惯性爬上坡,撞进我和娘耳朵里。我娘欢愉地笑了。陶氏祠堂建在乾公山旁的坡岭之上,戏台搭在祠堂前的大坪里,远远地,唢呐声在坡上乌拉乌拉响了起来。唢呐一吹,戏就要开锣了。一丘丘水稻田,陌上行人,池中水鸭,顿时安静下来。三月里,时光青嫩,屋舍里的人们笑语盈盈,三三两两出门,循着唢呐声,悠悠然往戏台行去。
一台电动摩托从身边开过,扯起一片浓郁的芬芳。低垂于稻田湿漉漉的泥腥气,如同一块春天的大布,大布在风里飘荡,向田野抛撒鼓点、插禾鸟的啼鸣和菜籽花香。
摩托车驮着住在陶家巷最北边的七叔婆。七叔婆看到娘,在前头遥遥地喊,桂庚……我娘朝风里应一声,哎……
摩托车停下来,七叔婆大声问娘:“又不上昼来?”
娘说:“路不远,来得及哩。”
七叔婆让送她的侄儿打转,她下车和我们一道上坡去。舅舅正在祠堂门口,朝唢呐声里的我们眺望。
我舅迎到坡下边,也朝娘喊:“又不上昼来?”
娘说:“路不远,来得及哩。”
七叔婆和舅舅的意思是:何不上午回,吃餐中饭,从容一点呢?巷里人好客,娘害怕给人添麻烦。但你若是上昼回来了,他们也是要殷殷相劝的:“又不昨夜来?”言语里满是恳切。
戏台前很快坐满了人,椅子不够用,坐下来的是老人和妇女。老人家的膝上抱着幼儿,外边站着的是男人,男人肩上驮着小毛坨。舅舅和舅妈自己带了长凳,摆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刚坐下来,戏便在锣鼓大镲中热热闹闹地唱起来了。咿咿呀呀……呀呀咿咿……老生登台了,透过浓妆细看,倒是个俊俏后生……午后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泰,我在沉郁的唱腔里进入梦乡。我靠着舅妈厚实的肩膀,梦见了鲁迅先生《社戏》里的老旦。“我忍耐地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地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不知睡了多久,舅舅把我摇醒过来,身边的人正纷纷起身。演员们穿着戏服在台上穿梭,锣鼓、唢呐、大筒、大镲,音响盒子被一件件搬到停在坡下的皮卡车上。戏班要撤了。
我迷糊了,问舅舅:“就唱完了?”
舅舅答:“就唱完了。”
“唱的啥?”
“沈万山焚香。”
“沈万山焚香?”
舅舅便唱:“……双脚跪在地埃尘,拜告虚空过往神,焚香非是别一个,北京城内沈万山,焚香并非为儿女,我有九子在朝廷,焚香并非为财宝,家有黄金用斗量,焚香并非求寿年,我今有了九十三,为的国正天星顺,天下黎明乐太平,为的家家出孝子,为的国家出贤臣……”
七叔婆的侄儿子早骑着电动摩托候在祠堂的大枫树下,等着把七叔婆接回家。他刚从铁牛上下来,脖子上搭着块花毛巾,黑脸膛油光水亮。听见舅舅唱戏,便问:“斌叔,您晓得唱几本戏啊?”
“我本本晓得唱。”
“啧啧啧……厉害了。”
舅舅不理他,仍自个儿唱。
舅妈扛着长凳从后边追上来,笑道:“你斌叔啊,看戏比吃饭还勤时,镲没开打,他就出了门,鸭回了,他才回,能不本本晓得唱?”
七叔婆坐上摩托,刚要走,又忍不住问:“他斌叔,三月三唱戏不?”
“唱戏。”
“唱么子戏?”
“郭子仪拜寿。”
舅舅满面红光,声音高亢。农历三月三,是他老人家八十寿诞。巷里老人过大寿,从不收礼,晚辈们请好戏班,备好果饼花生,请全村人看,图的是老人的欢心和喜庆。
七叔婆的侄儿驮着七叔婆,稳稳当当驶往田野深处,半下午的风,涂抹绚丽金光,暖洋洋的,村庄似乎还沉浸在戏文中。
侄儿在前头吆喝:“婶娘,您老后年就满八十了,咱家也唱两本戏。”
七叔婆紧挨着侄儿的背,古铜色的脸上露出甜蜜,笑眯眯地答:“好。”
七叔婆的男人在同她成亲的第二天出门经商,从此杳无音讯。无儿无女的七叔婆,在陶家巷守候了六十年,从未舍得离开。
牛屎鸟
几头黄牛在田里吃草,优哉游哉,细嚼慢咽。一大群牛屎鸟从山里飞来,像一列载着煤球的小火车,呼啸着砸向田野。
牛屎鸟绣着银花的黑翅膀,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在天上画弧线,天上被弄出许多水波样的皱褶。小黄牛眯眼看去,但风一吹,也就不见了。
牛屎鸟盘旋了一会儿,稳妥地停在牛背上,或者降在水田里。细碎的啼鸣随重力落下,像无数颗晶莹的水珠,悄摸滑入土中。牛屎鸟的啼鸣那叫一个甜润,还带着松枝上露珠的香味,是给稻田的礼物。
黄牛不犁田,就成了一道乡村物景。牛屎鸟站在牛背上,像一架架直升机。“飞机场”甩着尾巴四处走,“停机坪”比缎子还要光滑,但牛屎鸟仅凭一双巧足就能驾驭。牛背是牛屎鸟安在农田的家,虽简陋,却有温度。
七叔婆的侄儿领着小儿子陶俊,驾着一台高大威猛的“铁牛”来到了田野。漆得橙红柳绿的“铁牛”鲜艳夺目,玻璃锃亮,硕大的轮胎和宽松的锯齿引逗着牛屎鸟的目光。不到片刻,贪玩的黑鸟们便一股脑儿从牛背上飞了过来。陶俊读大专时,学的是育种专业,毕业后和父亲一起成了“种粮大户”。
陶俊是个浪漫的小青年。一块即将翻耕的圆弧形水田,田坎线从中间凹进去,大家都讲是丘“猪腰子”田,陶俊却讲是丘“爱心”田。烂漫的年轻人开着“铁牛”在“爱心”里打转,水田由外向里画着圈儿翻耕。濡湿的黑泥被犁开了“花”,灵芝样的泥花里,多的是鸟儿想要的美味。牛屎鸟“呼”地降在泥花上,追着“铁牛”屁股,热热闹闹地找食。
陶俊开“铁牛”,故意慢吞吞地,好给忙碌的小脑袋们留出富余时间,可“铁牛”的“脚步”还是太过矫健,牛屎鸟还刚找到一条蚯蚓,一颗螺头,一只蝼蛄,或几颗野果,“铁牛”已推着巨轮到了跟前。它们只好再次起飞,“呼”的一声,黑麻麻、密匝匝地落到铁牛后边。
老辈儿把牛屎鸟叫“牛屎八哥”,它们本身就是野八哥。但在娃儿眼里,牛屎鸟能驾驭崎岖的牛背,是威风凛凛的“牛背鸟”。牛背上的鸟,是老人们心中通灵的吉祥鸟。有段时间,飞鸟被四处游猎、黑洞洞的枪口瞄上了,藏在深山的树洞和岩壁里,轻易不敢来农田。这几年,村人看到猎户就赶,还给鸟喂食,鸟兽就自由了。牛屎鸟“明察秋毫”,在村子里试探着飞了几圈,就笃定地四处嬉闹了。
阵容庞大的牛屎鸟,飞起来如浓云盖顶,落下能覆盖半块水田。它们常常要在田里撑得肚大腰圆,秤砣样快飞不起了,才“呼”的一声,集体腾空,磨磨蹭蹭往北边的陶家大山飞去。这时候,陶俊便有了诗人的感觉,凝望着天空说,你们啊,都是田野的果实。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