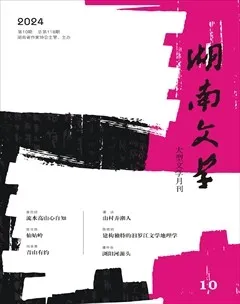丝路记
2024-10-22孙佳
加德满都,韩素音的重生之城
1956年4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一辆小轿车平缓地行驶在尼泊尔境内的尼印公路。这条公路是由印度援建的,宽敞平整,不久前才开通,两旁是连绵不断的青绿山峦。
除去司机,小轿车上坐了两人,副驾席上是一位皮肤黝黑、身材壮硕的印度男子,一副军人打扮。后座上,静静坐着一位纤瘦女子,约摸四十岁。她久久凝望车窗外的群山,山峦亦投影在她深邃的黑色眼眸。
这位黑发黑眼的女人,拿的是英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康柏夫人,她穿一件中国的高领绸缎旗袍,脸孔也颇有几分东方人的清秀。
她是一个欧亚混血女人,父亲是庚子年间留学比利时的中国铁路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名媛。
她是蜚声世界的女作家,汉语名字叫周光瑚。比起周光瑚,她的笔名“韩素音”更为人知。韩是“汉”的谐音,“素音”意为“小而平的声音”。她在1938年发表处女作《目的地重庆》时,第一次用了“韩素音”这个名字。
1951年,她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英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出版商在写给她的信中夸耀:“我在英国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几乎每人腋下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将《瑰宝》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3月底,她收到了出版商的贺电,这部电影荣获第2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三项提名。接到喜讯时,韩素音在南亚大陆上,已经旅行了两个多月。
1956年1月,时年39岁的韩素音接受官方邀请,去印度新德里度假,并被邀请前往尼泊尔,参观印方捐建的尼印公路风光。这段不短的旅途中,印度方特派了一名向导随行,正是坐在前排的文森特上校,负责修建尼泊尔铁路的工程师。
这年4月,恰逢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首都加德满都举办登基大典,韩素音也被邀请在观礼的嘉宾之列。
踏上加德满都的那一刻,韩素音不会想到,这座城市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经历过数段痛苦的恋情和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将军唐生智的侄子唐保皇。这场婚姻以唐保皇殉国东北战场而告终。唐保皇去世后,因战乱滞留香港的韩素音,和《泰晤士报》的记者伊恩产生了一段恋情。有妇之夫伊恩许诺会离婚娶她,却在不久后殉职于朝鲜战场。为了悼念这段爱情和缅怀伊恩,韩素音将两人情事写入了小说《瑰宝》,她也在小说中抒发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爱情之外,“我心里渴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或许是中国”。
1952年,韩素音再嫁英国出版商康柏,因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她曾在自传中坦言,嫁给康柏,主要是为了给体弱多病的中国养女蓉梅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
车子在尼印公路上匀速行进。春风和煦,韩素音的心,却在痛苦矛盾里挣扎。一路怡人的风景,也没有让她枯竭的心灵重新湿润,让她萌生哪怕一点点写作的冲动,她觉得自己已丧失了写作的能量。
直到踏入加德满都,韩素音心中盘桓已久的愁云迷雾,这才逐渐消散。加德满都男女老少在山泉与瀑布下洗浴、欢笑、嬉闹的自在情景,让她露出了久违的笑意。生机勃勃的加德满都人,让韩素音的心慢慢放松了,她觉察到,自己身体里某种沉重的东西,正被一步步搬走。
加德满都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天然谷地中,素有“山中天堂”美誉,四周峰峦争奇,青山叠翠。这座建于公元723年的古城,以精美的建筑艺术、木石雕刻而成为尼泊尔古代文化的象征。尼泊尔虽是个小国,却被称为“众神的土地”,这里有3亿3千万位神祇,比全国人口还要多。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的加德满都市中心,有佛塔、庙宇250多座,大小寺庙2700多座。每条街上的街头巷尾,都能看见庙宇和神龛,神龛里的铜兽头颅已被信徒摸得光亮如镜。
韩素音穿过一条古老幽深的小巷,脖子上挂着铜铃的印度教圣物黄牛,向她悠闲走来。跟在黄牛身后的,是全身抹满骨灰,腰间仅缠一布裙的苦行僧。她抬起头来,民宅上是一扇扇精细的雕花木窗,木窗之下是雕满花草动物的木门。早起的加德满都女子,用戴满红绿玻璃镯子的手轻轻推开木门,拿着娑罗树树叶做的盘子款款而行,盘子里是供神的朱砂与炒熟的谷物,还有鲜艳的金盏花。韩素音跟随她们轻盈的脚步,走到加德满都的中心——杜芭广场。
在杜芭广场的好几座寺庙里,她看到木刻的男女性爱图,逼真传神。
“印度教神话里,闪电女神是一个处女,她看见这些图案会退避三舍,所以人们在寺庙雕刻性爱图,用来躲避闪电。”文森特上校担心这些图案引起她的不适,特地解释。
韩素音非但没有觉得色情低俗,反而产生了一股对异族文化的尊敬和感动。她在书中读到过,在尼泊尔,宗教与生活水乳交融,紧密联系在一起,爱欲被认为是人生三大目的之一,在所有合法的享乐中,性爱被认为是最富于激情,也是最为完美的人生享受,也最易于被转化为宗教的热情。
不远处,一个年轻的加德满都女人,在一块石头上擦自己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又用牛奶和水来洗它,并给它戴上美丽的花环。
在加德满都,崇尚自由的韩素音不知不觉舒展了身心。这个被青山缭绕的梦之乡,治愈了她受过的创伤。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让韩素音再一次深深感到,自己的心更亲近于东方文明,并从东方的生活哲学中,找到了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
对新生活的信心,对重新写作的欲望,在作家心中复苏了。
在自传中,韩素音写下见到文森特的第一印象,“我思忖,他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呀,长相出众,漂亮极了。他确实很黑,皮肤黑得有点发蓝。可是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能引起美感的光滑的巧克力的颜色。我立即从冷淡寂寞中摆脱出来,感到一种炽热的欲望……”她毫不掩饰自己对文森特的爱,“我盯着他,两腿站不稳,感到全身的活力都在迸发出来。”
她与印度人文森特上校,在加德满都情定一生。婚后,韩素音给文森特取了个中国名字——陆文星。
1957年,韩素音出版了以尼泊尔为背景的小说《青山青》,她以英国女子安妮的经历,映射自己在加德满都获得的心灵疗愈。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安妮申请了加德满都女子学院的英文老师。安妮在尼泊尔生活得如鱼得水,加德满都让她枯萎的心灵复苏了,她重新燃起写作的欲望,也和一位印尼混血男子昂里产生了恋情。
韩素音借书中另一位人物马尔贝医生之口,形容尼泊尔的神奇之处:“在这里,人类的接触,碰一下人的手,朝人的眼睛里看上一眼,就能使人相信上帝,或众神,这一点比任何地方都灵验。”
未走入加德满都时,也许觉得这话太过夸张。但当你走入加德满都,仿佛感到空气中都飞翔着看不见的神灵。尼泊尔人的衣食住行、出生、性爱、死亡,都在神明的照拂下进行。
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早起去寺庙抹上一道朱砂,再骑了摩托车上班;寺庙台阶下,五颜六色的蔬果摊前,胖胖的妇人殷勤地吆喝;一对年轻男女,偎依在寺庙台阶上亲密低语;CD店中流行音乐与宗教音乐夹杂响起,没有半点不谐;加德满都东部的巴格玛蒂河边,供奉湿婆的帕苏帕提那神庙旁,有烧尸的,有求子的,死亡与新生彼此共处……
加德满都之外,世上还有其他地方,是神仙世界与凡人生活完美融为一体的吗?是可以让受尽苦痛的人获得身心重生的吗?
对于韩素音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嬉皮士的欢乐天堂
1962年,32岁的加里·斯奈德到达加德满都。
抵达之夜,恰逢天文奇景,加里·斯奈德笔下的加德满都,“非常安静,大多数商店都关门了,因为每个人都在里面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那天下午三点,所有可见的行星加上月亮和太阳合在一起,整个印度民族都相信世界将被毁灭。”
他入住的酒店名头响亮,名唤“喜马拉雅酒店”,却“非常肮脏,老鼠成群”。无法忍受的斯奈德,第二天搬到了一家“更好”的酒店。
斯奈德的旅伴之一,是艾伦·金斯堡,美国“垮掉的一代”中的领袖诗人。1955年11月,这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旧金山著名的地下俱乐部“六号画廊”策划了一场朗诵会,金斯堡朗诵了著名的《嚎叫》,宣告了美国诗歌新时代的开始,斯奈德朗诵的则是《浆果宴会》。
虽然和“垮掉的一代”走得很近,但斯奈德并不是他们中一员,维系他们友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东方思想的共同着迷。1953年,斯奈德随陈世骧学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了唐代诗僧寒山的诗,又去了日本京都修习禅宗和东方文化。狂热的禅宗爱好者斯奈德,也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里的人物原型,书中主角贾菲·赖德过着僧人一样的生活,打禅、沉思、冥想、素食,背着背包寻找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金斯堡和禅宗诗人斯奈德的上一站,是印度。
如果将马克·吐温那次短暂旅行排除在外的话,这是美国作家首次体验印度。
从印度前往尼泊尔的路程让人晕头转向,“坐最差的巴士,在火车上睡觉,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气味。”斯奈德将这次经历描述为,“长达12个小时的旅程,先是到达了海拔9000英尺的山区,再沿着最荒凉、最曲折的道路行走”。
斯奈德回忆当年的漫游生活时说,他们犹如苦行僧一样地游走,一点都没有想到,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样式。
他们一路漫游,最后在博卡拉停住脚步。
博卡拉,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博卡拉河谷上,四面环山,抬头可见终年积雪的安娜普纳山脉,美丽的鱼尾峰倒映在碧绿的费娃湖上。
在费娃湖畔充满异国情调的小酒馆里,艾伦·金斯堡“嚎叫”出他那著名的垮掉诗篇:
一切神圣!人人神圣!各处神圣!每个人都在永恒中!每日尽在永恒中!人人都是天使!
浪子与六翼天使一般神圣!疯人与我的灵魂一般神圣!
受到“垮掉的一代”金斯堡和斯奈德的影响,1968年至1970年间,来到尼泊尔的游客数量翻了一倍,游客的平均年龄也从老年下降到青年。
上个世纪60年代,对现实不满的欧美年轻人头戴花冠,披着印第安披风,佩戴印第安珠串,身背一把破吉他,高唱美国“银子弹”乐队的“加,加,加,加,加,加德满都”的摇滚,从嬉皮士大本营阿姆斯特丹出发,一路经过阿富汗的喀布尔、巴基斯坦的马甸、印度的果阿、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条漫长的“嬉皮之路”,最后以博卡拉作为东方朝圣的终点。
吸引嬉皮士来到尼泊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麻在尼泊尔可以自由种植,因为印度教里的湿婆大神也吸食大麻,吸大麻更是苦行僧修炼中的一部分。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右侧,有一条奇异街(Freak Street),它得名于嬉皮士年代。成千上万打扮怪异的嬉皮士曾聚居于此,鼎盛的时期,嬉皮士占了加德满都人口的三分之一。
欧美人对加德满都的特殊情结,一直沿袭至今。漫威电影里的奇异博士,为了治疗受伤的双手,只身一人来到“魔法圣地”——加德满都。
山清水秀的博卡拉更是嬉皮士心中的“麦加”,费娃湖畔到处是嬉皮士的帐篷和简陋的小旅店,街道上都是说着不同语言的长发嬉皮士。
嬉皮士们终日与雪山碧湖为伴,吸大麻,赏美景,放逐心灵,放浪形骸,在近乎原始的当地文化中完成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逃离,他们将之命名为“湖畔精神”。在尼泊尔这个遥远而隔绝的异域之地,他们潜心治愈西方文化带来的心灵创伤。
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嬉皮士运动逐步瓦解。
2007年,我到嬉皮士们的打卡圣地博卡拉时,轰动一时的嬉皮士文化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旅游书上对这座河谷城市的推荐语,除了“曾经的嬉皮士天堂”外,还多了一句,“背包客的理想家园”。
在湖畔旅馆睡个懒觉起来,推开房间窗户,触入眼帘的是令人心醉的雪山湖泊。早餐后,悠闲坐在鲜花环绕的旅舍庭院里喝咖啡,午餐是简单而地道的尼泊尔餐,浓浓的豆汤、炖煮土豆、炒蔬菜,配上一份米饭。饭后去费娃湖边的草地上晒太阳,有兴趣的话,去戴维瀑布看看水,再钻到瀑布下深不可测的洞穴里,跟随当地人在蛇神石像下放上一朵金盏花;或在碧绿如洗的费娃湖上荡起双桨,再去湖中央的瓦拉喜金庙(Varahi Temple),摇一摇神庙屋檐下的黄铜铃铛。
夜幕降临之际,灯红酒绿的酒吧响起吉他的弹奏声,乐手唱的还是披头士乐队的名曲《昨天》。短短的一瞬间,似乎加里·斯奈德、艾伦·金斯堡,以及千万万万嬉皮士们依旧停驻在博卡拉。
博卡拉的夜晚,虽然没有斯奈德诗中的“松树的树冠”,也没有“兔和鹿的足迹”,但有难忘的“蓝色的夜/有霜雾,天空中/明月朗照”。
夜间偶尔来个一小时的停电,千百根蜡烛陆续燃起,烛光与星光交相辉映,如同地面上构成了另一道星空。来电后,酒吧里响起一片欢呼,被中断的音乐声也再次响起,直至天明。踏着拂晓,驱车前往桑冉库特山看安娜普娜峰的日出,凝望银色雪山被朝阳慢慢镀金。雪山之下,晨祷的当地人已在神庙点亮一盏盏羊油灯,博卡拉也迎来了新的一天……
不少的游客只打算在博卡拉待一两天,却被美景吸引,流连忘返,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行程,签证到期后再去续签,弹尽粮绝才依依不舍离去。有的索性留在当地做起了小生意,娶了博卡拉女孩,一留就是数十载。
在嬉皮天堂里生活的博卡拉人,血脉里似乎也融汇了几分嬉皮文化的因子。我所住的天使饭店,老板Dav是个英俊高大的尼泊尔人,浅色皮肤,弹得一手好吉他,时不时在饭店庭院里自弹自唱。他做游客生意,却又不常待在博卡拉,每年有好几个月去浪迹天涯。
和他订了送我们去桑冉库特山看日出的行程,不料头一天还晴空万里,第二天早上却乌云密布。我们四个要去看日出的人早早起来,Dav还在呼呼大睡。去敲他的房门,他从充满大麻味的房间里懒洋洋哼一声:“天气坏,看不到的。”我们不死心,逼他起来开车上山。
Dav将车慢吞吞地开到山上,天气更加恶劣,我们坐在山顶小亭子里等太阳升起。有个中年男子在亭子里摆茶摊,给我们煮了热腾腾的玛莎拉茶(Masala Tea)——一种混合香料和糖的奶茶。
端来茶后,中年男子在我们身边坐下,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拿出碎大麻叶,娴熟地卷在烟叶里,静静抽了起来。他抽大麻的神情略带思索,甚至还有几分严肃,我想到了在杜芭广场漫游的苦行僧,他们在冥想中需要被大麻带入神仙世界,尼泊尔政府因此网开一面允许他们拥有少量大麻。
等了一个小时,雨依旧未停,山顶雾气弥漫,只穿了一件薄外衣的Dav冻得跑进车里。直到上午十点,天还未放晴,我们只能失望返回。与上山时的拖拉相比,Dav将车开得风驰电掣,我们每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
在自由随性的博卡拉,仿佛再拘谨古板的游客,待久了都能变成无拘无束的嬉皮士。
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与自然亲密而迅速地融为一体,漫步费娃湖畔时,耳边似乎响起斯奈德的诗篇《流水音乐(之二)》:
流动的清溪
流动的清溪
你的水对于我的嘴
是光
对于我干枯的躯体是光
你流动的
音乐,在我耳里,自由,
流动的自由!
我的内心
有你。
这一刻,你能深深体会到斯奈德的诗中世界,可以看到除人类外的其他生命,眼前的雪山、湖泊、瀑布,就和我们的生命一样美丽、睿智且充满价值。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