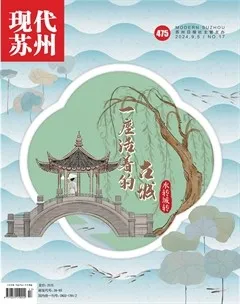以香修身跨越千年的时光,跟着苏轼学习香席
2024-10-18张蓓蕾



千百年前,深院焚香,是古人日常的优雅。而宋朝,是香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宫廷庆典,茶舍酒肆都会用香。特别是庞大的文人群体迅速崛起后,文人就成为了香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焚香也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人们对香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融合了文人特有的浪漫情愫,使香文化成为一种生活志趣的自然表达,它充满着灵性,富有诗意。
香席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余香千年。坊巷有形,纵横有序。在苏州这繁华街巷之间,有一处专注于香席的空间。在非遗与古厝的融合中,细品一缕“香”愁,馨香一盏去浮尘。
走进香稳空间,乍一看屋子里没有过多元素,非常极简。空间主人宁馨,中国社会艺术协会香学艺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苏州市姑苏区香稳空间主理人。宁馨的会客室,也是陈列香器的香室。
古色古香 淡远源长
漫步于空间内,不时能闻到独特的香味,却不见烟火。这正是香艺师在展示宋式隔火熏香。
隔火熏香,飘散的是暗香。其若有若无,舒缓柔和,虽不似烧制篆香那般香气四溢,但更加有缥缈的意境。
宁馨介绍说,中国的香学文化以及用香习惯,绝非仅仅是对某种气味的简单追求,亦非对香味表现形式和细节的过度美化。相反,它将“香”作为传递文化意境的媒介和载体,追求更为深远的文化内涵。
她边说边演示,先点燃一块木炭,把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木炭上隔一层云母片,最后在云母片上放香品,称为“隔火熏香”。
而谈起宋代的香事,就一定要说到这位香席资深玩家、男神级人物——苏轼。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
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
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同然。
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这是苏轼的《翻香令》,从这首词中看到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苏轼。
苏轼是历史上著名的和香高手。他对和香有着深入的理论研究,对和香的时节、香料的应用,甚至和香用的器具,都十分讲究。他亲手调制出“雪中春信”之香,焚烧时有满室梅花绽放之清香,它就是苏轼的登峰之作,并且流传至今。
宋朝浙江钱塘人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写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指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来品味日常生活,其实闲事非闲,四般闲事既是古时文人雅集的四个主题,也是他们缓解工作和学习压力的四种重要方式。而其中焚香文化是由嗅觉生发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香文化以熏香的形式塑造空间气味之美。在中国传统香文化中,不同的空间用不同的香,以不同的方式行香,可以说香艺的研习是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香文化最根本的基础。
香中内修 静心无虑
香艺的修习既是学习中国香文化的基础,也是香中内修的基础。香艺修习之中暗含“静”“定”“和”三个内心的诀窍。所谓“香艺之静”就是澄怀滤性:于香艺修习之中磨练自己的心性,精神内守,安于当下;所谓“香艺之定”就是见微知著:专著于香,凝神于器,察觉各种香与器配合之间微妙的变化对香气的影响;所谓“香艺之和”就是“人香和一”:如入太虚之境,“人”“香”“器”三者合一,以达“香积”之境。
宁馨表示,“香以载道”正是中国香学文化的核心所在。它涵盖了对知识的探索、道德的升华、心灵的完善以及智慧的圆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学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启迪智慧、论辩哲理、修养心灵、追求精神价值、美学理想以及思维模式上的独特魅力。
千年后的今天,与苏轼有关的“雪中春信”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几分是杜撰,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窥见宋时香席的唯美,也可以感受到苏轼爱香、惜香的品质,以及他精湛的和香技艺。
嗅觉经济借助时代浪潮,走到人们的视野中。人们渴望从香味中获得舒适和愉悦,也尝试在不同场合使用香味来塑造个人形象。
香味的疗愈力量逐渐显现,香席可能实现精神和商业价值的双重收获。香取自天然,自然的芳香植物生机盎然,将人们从繁杂的生活压力中解救出来,复归与自然的接触和融合。
点燃一支清香,沉浸在香气世界中,感受香气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