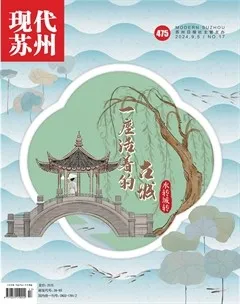众妙之理
2024-10-18王国刚

人生在世,妙理重要。
苏轼文章,篇篇哲理。
理者,前人智慧结晶,来源于经验、观察、思考或者哲学探索。
天庆观,道家场所;张易简,村间道士。
乡校中,百学间,兄者无数,置身其间,日日观察,天天思考,师、长愿讲,小小年龄,苏轼听得进。
亲眼所见,耳濡目染,从中,苏轼明白了许多人生妙理,常记心头,多加琢磨,成为营养。
一日,老师张道士动如往常,正在院子内打扫,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人,并说:“老先生快要到了。”
学长中,有人正在诵读《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苏轼疑惑:“玄妙不过是一个而已,怎么会有众多呢?”
老师笑着说:“单一已经浅陋,哪有什么玄妙之理?如果真能领悟,虽众可也。”
指着正在洒水、除草两位同学,张道士继续说:“倷看,此二人,每一动作都是一种玄妙。”
仔细观察,见学长,手若风雨,步中规矩,涣然雾除,霍然云散,苏轼惊叹,“竟然能达到这样境界!庖丁解牛,郢人运斤,确实都是真实存在。”
庖丁者,为梁惠王解牛,动作娴熟流畅,手、肩、足、膝等身体部位协调配合,发出声音如同音乐般和谐美妙。
对此,王赞叹不已,询问庖丁:“技术为何能达到如此超高境界。”
庖丁回答:“我所追求,乃世间之‘理’,而非仅仅技术层面。”
长期实践,逐渐掌握了牛之生理结构,“神遇而不以目视”,凭直觉、精神去感知、应对,而非仅仅依靠看见。
郢人者,楚国郢都一位技艺高超之木匠,善于使用斧子对木材进行精细加工。
其时,同城还有一位泥画匠人,两人之间,经常协作,频繁合力。
某日,工作中,泥画匠人鼻子上不小心沾上了一层像苍蝇翅膀一样薄之白灰,请木匠用斧子帮着削去。
毫不犹豫,挥动斧头,一气呵成,白灰被木匠削得一干二净,而泥画匠人鼻子却是毫发无损。
不动声色,一切如同没有发生,工作间里一如既往。
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道家思想,尊重事物本性和内在本质,顺应一切自然发生。
处理问题时,按照规律,避免盲目行动、主观臆断,特别强行干预和违背道义之坚决压制等。
吃喝拉撒,既进则出;学习吸收,消化输出,此乃人之本性,这个不行,那样莫说,或写,百花难放,何以万紫千红、世界灿烂?
日日操练,天天精进,郢人运斤。
大庭广众,能够根据同伴交代任务,用斧头精准地削去同伴鼻子上白灰而不伤及皮肤,充分展示出木匠高超技艺和精湛手法。
木匠技艺可以得以充分展示,除了前者自身技艺高超之外,离不了一个重要前提,即泥画匠人给予充分信任、认可和默契配合。
试想,如果泥画匠人以为自己了不起,不把天天一起之木匠当回事,甚至,如果还要阴阳怪气、口出不逊,更者,强硬阻止,那么,岂能呈现如此和谐顺畅局面?
两个故事,学之未久,苏轼印象深刻。
放下手中活计,两位学长走上前来,和苏轼说:“您还没有见到真正玄妙,庖丁和郢人并不是我们所说其人,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
技艺与道行各占一半,练习与空灵相互结合,并不是没有依据就能直接达到如此境界。
“你见过蝉和鸡吗?蝉爬树而鸣,不知止;鸡低头啄食,不抬头,各自固守自己习性,到了蝉蜕壳、鸡伏卵时,无视无听,无饥无渴,恍惚中,默默变化;细微处,等待时机,即便圣人,也无法预知,难道,这些都是技术和练习所能相助吗?”
说完后,他们走了出去。
听后,张道士对苏轼讲:“少安毋躁,等老先生到了再向他请教吧。”
回转身,两位学长又对苏轼说:“老先生也未必知道,你去观察蝉和鸡,并向它们请教,就可以养生,可以延年益寿。”
原来,在海南,苏轼已经六十有三,经常考虑、实践养生问题。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真似假,儿时天庆观之场景再现。
恰遇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道而至于妙者也,作堂,榜曰“众妙”后,写信来海南,请苏轼写一篇小文以记之。
不暇而作,苏轼独以梦境示之。
当年龆龀,此时,苏轼已经成为老先生矣!经常揣摩研究众妙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