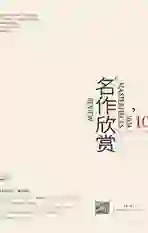从大学到田野:“历史留声机”中燕大学子与京郊村众的命运交叠
2024-10-12颜一澄
“沦陷”阴霾与田野火种:三次抉择后的人生交汇
1937年9月的北平,饱经战火后“沦陷”敌营的禁滞阴霾,时刻笼罩在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
早自“九一八事变”始,日本人便对北平城虎视眈眈。正如蒋梦麟所说:“未改名北平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易名以后则变为中日冲突的中心”。自1937年初,北平城附近便“事端迭起,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终于,“七七事变”枪响惊起,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节节败退,乃至最后弃城撤出——在这场仿若“凌迟”的“沦陷”里,日军几乎“未经抵抗即进入故都”,北平自此陷落敌寇之手。为了配合后续控制华北、驯化民众、持续侵略的方针部署,1937年7月30日,日本人设立了统管北平事宜的“治安维持会”,以酷烈手段逼迫贯彻奴化教育,一时间,在一片“易帜焚书”的悲戚喧嚣中,北平各高校人心惶惶、悲愤填膺。
覆巢之下无完卵,北平沦陷后,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大量国立高校,再无立锥之地,不得不离京外迁,辗转南方及内陆他省。唯有部分私立教会大学,凭借国际背景,留驻北平,苦苦支持,成了沦陷区学子寻求庇护、求知向学的“孤岛绿洲”——依托美国支持的私立燕京大学即是其中之一:20世纪30年代,地处西郊、与北平城之间仅“靠一条石子路连接”的燕大,不得不“极力营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氛围,以驱散战时笼罩在燕园上空的阴云”。据校长司徒雷登回忆,“在北平沦陷的危急关头,燕大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而“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此时此刻,对于“被政府丢弃在沦陷区”,“不甘心忍受‘奴化教育’,又来不及撤退到大后方”的大批青年而言,“走向燕京”成为唯一出路。而随着金秋开学日的到来,尽管战火硝烟还未清散,勉力运作以维持办学的“孤岛”燕大,仍旧强顶着日伪嫉视,迎来了新一届的学生。这批紧随着“七七事变”的脚步,于1937年正式入学,又将在1941年“一二·八”遭难,燕大被迫撤离北平前夕结课毕业的本科生们,此时或许并不清楚:为时代摆布而不得不在战乱陷落的迷局中彷徨无措的他们,四年大学生涯将完全被“沦陷”封锁、危机四伏的凝滞阴霾所笼罩,而他们的人生路径也将与燕京大学、北平城池乃至家国命运捆绑,共同在乱世兵燹中飘零沉浮。
1937年9月,燕京大学1937级的新生,历经数年寒窗苦读,穿过层层战火阴云,终于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节点,叩开了燕园的大门:这群风华正茂的少年,或从遥远的故土不无忐忑地只身赶赴北平,或自城内的家宅满怀期待地投身大学,此时此刻,他们怀着或挽救家国或求知问学的大小抱负,一齐踏入了燕大——即将就读于社会学系的邢炳南、虞权、陈永龄、方大慈、韩光远五人,便在其中。这五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本该在战火纷飞之下过着毫无交集但同样波折的一生,可与燕大、社会学以及平郊村相关的三次相同抉择,却令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交汇。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肇始于191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班的建立,彼时,“严复先生的弟子,1915年被聘至北大讲授中国法制史的康宝忠”先生,首次为学生系统地讲授了社会学。随后,燕京大学于1922年正式成立社会学系,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同时,开创了“燕京学派”,为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容忽视、影响至深的贡献。
燕大社会学成立之初,由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担任系主任,授课教师均为美国人。但从1924年开始,许仕廉、李景汉、言心哲、杨开道、吴文藻等中国学者,陆续受聘于燕京大学;1926年,许仕廉接任系主任一职,在明确提出“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宗旨”的同时,开始尝试推进实地调查工作。1928年,杨开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下,开启了对河北清河镇的社会调查,两年后,许仕廉的加入,令清河镇调查扩大为燕大“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通过数年的深入观察与细致探索,杨开道、许仕廉合著的《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ASociological Analysis),成为燕大社会学社区研究的首个典范作品。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在新任系主任吴文藻的推动下,正在国际社会学界蓬勃发展的人文区位学(humanecology)与功能人类学(functionalanthropology)理论,经由派克(RobertE.Park)、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等学者在燕大讲学的引介而备受关注。自此,深受人文区位学影响且长期聚焦“功能论”探索的吴文藻先生,带领其门下合称“吴门四犬”的四名弟子——黄迪、林耀华、费孝通和瞿同祖投入了“社区研究”理论建设与调查实践的探索之路:1930年,吴文藻“受清华大学社会学会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的公开演讲”,这份讲稿经由费孝通记录,后以《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为题,整理发表于1935年第66期《社会研究》,此后,吴文藻先生更是多次撰文,为社区实地研究鼓吹呐喊,希求“将村落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单位”,进而“以此理解中国社会”。
1938年,吴文藻离开燕京大学,系主任之职务连带着持续推进社区研究的学术重任,共同移交给了燕大社会学出身、刚刚留美归来的年轻学人赵承信。此时,战火纷争令原有的“清河试验区”调查工作被迫中断,但已然意识到社区研究之重大意义,且急于从既有经验中改良、实践新的田野方法的社会学系师生,“无不希望恢复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存续先辈学人凿取的田野火种。因此,“为了给燕大师生提供新的田野点,并对中国农村社区开展社会学调查以收集中国村庄的基本资料用以后期的比较研究,燕大社会学系于1939年将平郊村建成为‘社会学实验室’,把社会学课堂开设到了田野现场”。在赵承信设计的蓝图之中,平郊村实验室的设立,除却试验社会学新方法与搜集“中国乡村研究资料”,更为重要的意旨还在于为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并非指向简单的“社会服务抑或社会改良”,而是希望系统地引导社会学子“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切身地感知、理解、把握社会学理论的内涵与意义,以摆脱空想、脚踏实地,令燕大社会学系的“学术课程更具活力”。由此,借助这条从大学迈向田野的学术征途,燕大师生与京郊村众的人生轨迹得以逐渐贴近,社会学系1937级五位年轻学子的命运,也在他们共同决定选择入学燕大、学习社会学、走进平郊村的刹那,开始交汇重叠。
学位论文与“历史留声”:学子与民众的命运交叠
平郊村,又名前八家村,村名之由来,相传可追溯至辽太宗会同元年(937),下诏修析津府改建新城一事:当时,来自山东、山西的十六家官窑迁至此地,负责供给建城所需的一切碎瓦。这些官窑被一条道路分隔为南北两村,道南分姓韩、魏、张、杨、刘、董、龚的八家官窑,合称前八家村,即平郊村。修城工作结束后,八家皆富厚,多迁往他处,故而今日平郊村村民中已无上述八家之后人。清朝时,平郊村因靠近圆明园,受旗人及其风俗影响颇深;进入民国后,隶属北平市第十九区的平郊村,又因交通便利、有多条道路横穿村落,而与北平城、清河镇、海甸镇等多地联系紧密,保留乡村旧习的同时亦颇受城市文化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地靠清华园车站又邻近燕京大学的平郊村,凭借自身优越的区位条件与丰富的文化现象,一直是北平各高校开展实地调查工作的核心场所,据赵承信先生回忆:
早在1930—1931年,当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建立清河试验区时,我们就知道平郊村了。从清河试验区在1935年撤销了它在平郊村的剩余工作到1937年夏天(根据《清华大学创设八家村建设区》的报刊资料,清华大学当于1934年就在平郊村设立了工作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该村里建立了工作站。因此,当我们在1938年冬天的一次田野漫步而“再次发现”了这个村庄时,村民和村领导已经为外来的任何社会学调查做好了充分准备。(赵承信:《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作为一个典型的华北平原村落,平郊村占地1.7平方华里(合0.34平方千米),村内地势西高东低,无山岗亦无河流,主要为平原耕地,村民亦多以务农为生,此外还有在清河织呢厂之分厂做工者,再有极少部分人业商或入城务工。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的调查报告,平郊村共有52户246人,包括男性136人,女性110人;这一数据至燕京大学设立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室”时,更新为61户249人,其中男占140,女占109,以徐姓(燕大学子论文中隐匿此姓为“于”)为最多,占到了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1939年,在平郊村小学校长兼甲长徐志明(燕大学子论文中将此人化名为“于念昭”)的引介之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平郊村各级领袖历经多次商谈,终于结束了前期的接洽准备,敲定了正式的田野调查计划。1939年8月,社会学系在燕大理学院的帮助下,利用精密的现代仪器完成了对平郊村地理位置与内外距离的精确测量;与此同时,“一项包含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等诸多项目的专业人口普查,也正跟随着师生们紧锣密鼓、进家入户的脚步,迅速开启。这些基础性调查行动的落实,带回了真切的一手田野数据,平郊村的基本面貌由此得以在燕大学生的眼前逐步铺展、日趋明晰。而在此基石之上,更细致的专项调查与更深入的学科思考,也在学子与村众们的一回回碰面交流、一次次距离拉近中萌芽酝酿。
1940年春季,即将步入大学生涯最后一年的大三学生邢炳南,选修了赵承信开设的“农村社区”课程,出于完成课程要求之课外作业的需要,这名来自山西小镇的青年,第一次走进了平郊村,在1940届毕业班师长的带领下,开始尝试实地调查。为了同村民们联络感情,调查工作以每周一到两次的频率坚持进行,初入田野的邢炳南头几次下乡还需学长带领,三四次后,便已能独立拜访农户了。结束了一学期的调查工作后,1940级毕业生们陆续结课离校,而邢炳南同平郊村众的“联络工作也已渐成熟”,迫不及待地,他渴望进入专题性的“正式研究阶段”,此时,一门开设于暑期的“实地研究”课程满足了他的心愿。而在邢炳南再入平郊村的同时,与其同年入校的1937级同窗们也纷纷通过选修这门“实地研究”,加入了田野调查工作:虞权、韩光远、陈永龄、方大慈四人均在其列。在这次调查中,带领、指导他们的教师包括留法十年、立志投身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的杨堃,以及深研孙末楠之民俗社会学说多年的“燕京学派”代表人物黄迪。在杨、黄二人的实地引导下,正值暑假、课业轻松的学子们往往“每周下乡五六次,轮流拜访各农户,收集应用之资料”,历经两月后,已然同村民缔结了极为深厚的情谊。暑期结束、秋季开学后,在田野中辛勤工作、积累材料,并不断发现问题、深入求索的学子们,除却继续坚持每周下乡两次外,又以每两周集会一次的频率,投身于实地研究讨论班。这个以参与了暑期调查的大四学子们为核心,诸师长与三年级同学亦共同参与的讨论班,其设立不单是为了“审核暑期工作成绩”,更是希望给学生们搭建一个讨论问题、交换信息、分享看法以查漏补缺的交流平台。而也正是借助在讨论班上,与同窗、同学、老师的屡次汇报、反复磋商、推敲改进,即将毕业的1937级学子们,在指导教师杨、黄二人的帮助之下,陆续选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并开始以题为核、各自为政,进一步细化田野工作。至1940年隆冬寒假,邢炳南、虞权等六名学子甚至“又投到村内去住了十来天”,在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生活的轨迹重合中,他们的视线遍及“人口统计、性生活、死亡礼俗、村庄政治、农业管理和土地制度”等诸多议题,不但为自己的学位论文争取到了最完善、可靠的材料,也彻底织就了“学子”与“村众”间两条本无瓜葛之平行人生命途的相交和重叠。
自1939年平郊村调查项目开启,至1941年第一批系统参与调查的学生毕业,两年间,燕大社会学系围绕平郊村积累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实地材料。根据赵承信等人撰写的总结报告,系里不但高度重视对平郊村村众生活各方面材料的全面搜集采录,譬如从学校理学院获取平郊村超过800天的气象数据并记入档案#6,而且对于参与平郊村研究的师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对所有搜集到的材料与所进行的研究,全部进行详细记录并入档留存,无论是研究者前往调查前的准备、设想与期待,还是实际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自身以及村庄民众的言谈举止,甚至讨论会的每一次问题探讨与经验分享,都要留下详尽的书面材料,此类规定,除却出于保留农村社会一手资料的考虑,更是为了总结调查经验、精进田野方法,以饷后来者。在如此精密、细致的研究流程下,留存下来的材料体量庞大、难计其数,赵承信写于1941年的平郊村相关报告中,也有多处细节曾暗示这部分资料的宝贵与丰富,并表示希望在日后寻一合适时机,将材料披露于众。可惜天不遂人愿,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突袭珍珠港,美日间一宣战,燕京大学即刻被迫关停,日寇占取燕园后肆意烧掠。难发突然,燕大师生们于乱世兵隳中保全性命尚且艰难,更遑论留存学术资料,于是,平郊村所得所有田野材料全部遗失,唯有学生们的学位论文得以保存。而这十余篇“涉及方言俚语、稗话传说、灵验故事、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家族性别、组织分层、教育实践、宗教信仰、器具房舍、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庙庆市集”等众多话题的学士毕业论文,就像是一部部逃过烽烟战火、饱经时代风霜后侥幸遗留下来的老旧留声机,泛黄的纸页是锈渍的黄铜喇叭,墨色的手迹是脆弱的胶木唱片,而当今人仔细拂去其上累积的浮尘,它们仍可“吱呀”着流出历史的曲调。
在这批堪为“历史留声机”的论文中,笔者择选了其中五篇,即:邢炳南(37092)《平郊村之农具》、虞权(37250)《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方大慈(37077)《平郊村之乡鸭业》、陈永龄(37049)《平郊村的庙宇宗教》以及韩光远(37121)《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希望以之为切口,透视抗战焦灼、北平沦陷的特殊时代环境下,平凡学子与普通村众的生存姿态与命运形貌。这五篇文章都是由1937年入学燕大社会学系的同窗学生于1941年毕业之际,基于共同参与的平郊村田野调查工作完成的,它们不但文题皆以“平郊村”起头,且均紧密围绕着该村村民的生活状况展开,堪称五部为平郊村所做的专题民俗志。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篇绝非当时燕大社会学系本科生参与平郊村调查的全部成果,其外还有不少文章同样不乏学术建树,譬如李慰祖先生同样完成于1941年的学位论文《四大门》,但考虑到诸如《四大门》等文章,所探讨的议题极为广阔,平郊村在文中仅被当作北平西北郊乃至华北地区农村信仰的个案缩影,并非处于研究讨论的绝对核心,故而均不划入本文所欲探讨的主要材料。
翻阅这五篇论文,最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作者深入田野乡间而探寻得到的各类丰富、宝贵的一手材料,它们自书面实物、村众口头等多方汇聚而来,被极为认真、严谨地以或手绘图册或手写文书的方式,呈于今人眼前:决心专研村民家中农具的邢炳南与聚焦平郊村住宅设备的虞权,四处奔忙、辗转拜访各家,完成了中国最早的民具学学术尝试。邢炳南对其所见的各式农具之形制功能、购置运用、产权归属等各类细节,予以逐一探究,不仅依照耕种顺序与详细功用完成了农具分类与样态摹画,并借由对农具租借关系、技术传袭、信仰禁忌等诸社会功能的探索,留存了有关小口庙、北岭庙、妙峰山等庙会盛景及其间农具买卖的重要材料。虞权则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等社会理论的影响下,对优劣不同的各级村屋,从地理区位到外部形制再到内里设施,均予细致查考,将房屋状况同农家财务状况、村民日常生活勾连起来,以最终通向对村中社会关系、历史制度与传统习俗等深层话题的讨论。在村众大多以务农为生的大背景下,方大慈将目光汇集到了平郊村中专事养鸭的黄姓、侯姓等三户农家,以其中养殖规模最大的黄淞家为主要考察对象,兼以二侯状况辅之,文中不仅极为详细地记述了养鸭从选种到孵化到育大再到售卖的全过程,堪称一部事无巨细的“农家养鸭指南”,还不忘从家庭分工与鸭业买卖入手,引入对饲鸭之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文化议题的考察。尤为有趣的是文中记述的当地人在交易鸭货等各类商品时,使用各种表示价钱的方言俗语,并借助约定俗成的特定手势给价、还价的奇特过程。与此同时,方大慈的同学韩光远则在慎重择选之后,将目光锁定在了更小的范围以内——关注平郊村一个农家的生活状况与家庭细节,他以平郊村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赵琴甲长一家为唯一考察对象,不断登门并反复探问,终于将赵家之历史渊源、家庭关系、生业状况、社会地位等诸细节梳理清晰,并自赵家个案出发,剖解了当时北平市政府、京郊新民会、村内合作社等诸多政治力量对平郊村农家的巨大生业冲击与文化影响,以点带面地还原了平郊村于多股政治力量的角力纠缠中喘息求生的真切时代概况。而不同于上述二人,自考察议题确定探访地点,陈永龄的思路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凭借极为敏锐的学术目光,迅速发觉了平郊村内唯一的寺庙——延年寺,作为村民信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与重大意义。而借助延年寺这一村落“内核”,陈永龄得以以小见大地关注并把握平郊村历史文化源流、当代民众生活、时局政治变迁等诸多信息,并将其有机地串联、沟通起来,最终完成一篇兼具单一区域民俗志与普遍理论价值的学术佳作。
统而言之,以此五篇为代表的1941届平郊村相关学位论文,大多立足丰厚扎实的田野材料,实现了极具研究前景与时代意义的学术初探。而出众成果的取得背后,开启田野、深入乡里、贴近民众的辛酸不易,亦不应被忽视:
……因为下乡找材料不能全靠书本上的方法和学问,却是亲自去应付人事的问题。谁都知道人事是最难应付的,要见什么样人说一套什么样的话,又须尽可能地“入乡随俗”,使村人不觉得和我们太生疏和太隔膜。又为避免他们的疑心和误会,须得十分谨慎地向他们发问,注意他们的态度。有时又常被他们用言语纠缠,不但不能向他们搜得材料,反而要为他们讲些他们觉得有趣的事。这一切都要看我们应付人的手段和态度的高明与否了。(虞权:《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
出于前文所述燕大社会学调查规范的要求,从事平郊村研究的学生们往往会在毕业论文的开篇,对其研究选题缘起、所用调查方法与实地探索过程,做出“尽可能细致的交代,以便让读者明了他们是如何进人调查地点,与村民怎样建立起研究关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研究资料”。因此,纵览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极具现实应用价值乃至足以启发今日之实地调查的田野方法:直接询问农家村民的明访问法;关注客观细节、自主推断探索的观察法;不偏信一说而是并置多说、比较判断的旁证法(也叫旁敲侧击法);投入村中暂住、与村民共同生活的局内观察法;从讨论班中获取同学研究材料、共同进行议题交流的文件法;以及广泛翻阅古籍文献与中外著述,以丰满材料、提升学理的参考文献法……配合着这些方法共同出现的,还有诸多微小的细节提示:譬如下乡之前务必准备充分,“否则不惟徒劳往返,且易减低研究之兴趣,其对工作之效率,影响颇大”;调查过程中,使用明访问法时,无论身处何处,都需“看当时环境,相机发问”,并等候访问结束,再行整理材料,绝不可恣意打扰、随意记录,以免带来无谓的误会。韩光远在追踪访问赵琴及其家属时曾自述道:“作者一年来在他家里,从未作过突然的发问。谈话的态度,也尽量保持和气与自然,而使他们把他家的实情,于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此外,在获得讲述人的直接材料时,万不可忽视其他村民的叙述,同一问题应当反复多次、询问多人,以“互相补充材料,借以辨别真伪”;再有,北平沦陷之后,地方不靖、人心惶惑,村民大多心系时势、“喜探听政治问题”,依照邢炳南的经验,“在此种情形下,势须略述一二然后乘便转入正题,以免对方失望,影响感情”——而文中的每一个提示,其背后所白费的许多功夫、挣得的诸多教训,是不言自明的。赵承信曾专门述及平郊村调查过程中的一次“田野危机”,事件的起因是介绍人徐志明曾私自向一户囊中羞涩、无力处理丧仪的农户许诺,来此展开调查的燕大社会学系将为其提供一笔不菲的报酬,并借此赢得了这位村民的支持,可这一承诺并未与燕大师生提前沟通,这笔报酬自然也不会凭空出现,于是,这位村民同调查师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矛盾,田野工作不得不因此中止,最终,此事由燕大社会学系向村民提供补偿,并承诺“每月捐助一小笔经费,用于给村里购置治疗小伤小病的药品”,且最终于平郊村延年寺设立医药箱,以回馈田野村众,才得以善了——而此类涉及人情往来、权力博弈的田野伦理议题,时至今日,仍为社会学、民俗学领域的学者们津津乐道、探求不息。
而在田野探寻与学术萌芽之外,诞生于此硝烟未散、危急存亡关头的文字,自然会无可避免地染上时局危亡的隐伏阴霾,与民生多艰的悲苦血泪。事实上,在五位学子的著述之中,我们确然时时可以瞥见动荡时代的鬼魅暗影:无论是村民回忆往昔的叙述之中,极为自然地将“圆明园焚毁”“卢沟桥事变”“南口大战”作为确定某事发生时间、割断自身生活阶段的重大坐标;还是居于村落周边的民众在此不太平之时“常感不安”,哀叹每逢抢掠总是自己“首遭其难”;抑或沦陷以来,村民们或在屡次逃荒中死伤难测,或因被抓丁服役妻离子散,好不容易安顿片刻,又遇物价飞涨,劳苦终日却仍吃不上饭:从位处底层,以养鸭为生却因鸭价骤跌一夕破产,从此背负巨额欠债总是“独自默默”的侯家主事,到表面风光,实则以租地为生,家业岌岌可危、朝夕不敢懈怠的赵琴甲长……战争带给民众的从不只是生存难度的拔升,还有求生意志与生活趣味的失丧:地近妙峰山的平郊村,周边村落多庙宇香会,和平年代时,各类庙会一直是村民们慰藉农忙、放松心情的重要场所,可战争的爆发令诸多庙会不再开办,即便有一二香会勉强维持,却总归盛景不在:
惟近年二庙之香火事业,皆随政局之不安,与农民生活之苦,日趋衰落、各地游艺亦已相维停止.笔者曾亲赴比显参观,庙内杂草丛生,神像坍塌,足証信士稀少。(邢炳南:《平郊村之农具》)
以往平郊村每逢旧历四月即赴涿州广翊宫、西顶广仁宫及妙峰山朝顶进香,但后来涿州与西顶二处之盛会因故停止,所以只余妙峰山一处了……近一二年来,本村赴妙峰山进香的人减少多多,因为中日事变起后,各香会的组织多解散,且妙峰山一带时常出没便衣队,地方不靖,故乡人亦不愿冒险前去……近年因乡间地面不靖,大戏及秧歌高骄等会皆先后取消,现在只余几种卖艺者支撑残局……(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
陈永龄曾在调查中询问村众,是否有意后续恢复延年寺旧有的朝香盛会,可村中人早已对此失去了热忱,因为“本村中就是年龄最大的人,也没有赶上参加朝香盛会”——自鸦片战争以来,地处京郊的平郊村作为兵家必经之地,常于战火之中首当其冲,兵祸不断、社会动荡,令底层村落人丁凋零、经济凋敝的深切苦痛,逐步内化为心理上惊惧与焦虑层累堆叠的厚重阴影,最终让人们一步步失却了生活的信心。
而在北平市民均陷苦海的同时,平郊村众似乎更为不幸——极为特殊的区位条件,令其成为青苗会、市政府、新民会、自治坊、合作社等诸多政治力量角斗、纠缠的核心,背负多份差役的同时,还不得不忍受多重盘剥:
在政治方面,平郊村与北平是一个单位,所给与他们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复杂,他们现在要服从北平市政府的命令,办理保甲,推行自治,并要服役纳税,又要服从清水园车站的命令,看电线,守铁道,并忍受铁路,公路两旁不许种高庄稼的损失.此外新民会在北郊的活动,他们更首当其冲。(韩光远:《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
而在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权力角斗场上,以于念昭为代表的地方领袖,怀着或大义或私心的好坏念头,向日伪团体屈身献媚、打点关系,对上级命令灵活磋商、勉力维持。当历史携着沉重的时代枷锁不断下压,劳苦的底层村众总是不得不被榨干价值、流尽血汗。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这五名学子,在一次次靠近平郊村众、聆听其诉说、观察其生活的过程中,早已不自觉地因命运交叠的感同身受,而深切地怀揣起“同情之理解”,因此,在他们的文字里,我们见不到对乡民愚昧的贬低,而唯有对劳苦大众的悲悯与改造社会的决心。这五份于战火中侥幸苟全的毕业论文,正时刻不停地低吟着一支历久弥新的历史和声,借此微声,今朝学人得以跨越八十余载的时间洪流,捕捉到些许为战火淘洗的时代回响,触碰到几缕为史书忽视的小人物的血泪。
旧地焕新光:历史与今朝的共振
八十载春秋,转瞬即逝,太多的往事与悲鸣,被烽火狼烟打散于秋风之中。1941年完成学位论文,自燕京大学结课毕业的五位学子,也被时代的浪潮推涌向前:当初远赴北平的崞县少年邢炳南回到了山西故土,进入赵宗复等人筹办复校的进山中学,担任化学兼英语教师,曾因燕大庇护而求得学识的他,为了挽救更多的失学青年,给国家培养抗日和建设人才,将真理的光芒传递给了更多少年;于北平故都出生、成长的陈永龄,终于还是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下,离开了眷恋流连的故乡,追随燕大南下成都,在风雨奔波中坚持取得了硕士学位,这名胸怀抱负,在学士学位论文中野心勃勃的青年学者,后来真的在战火中实现了崇高的学术理想,成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德高望重的前辈学人。至于虞权、方大慈、韩光远余下三人,今人已无力从历史的残章断简中拾取有关其下落的只言片语——时代从来如此薄情,毕竟这些年轻学子与平郊村众,都是无力在青史之上留下些微痕迹的普通人而已。
但哪怕时移世易、人事变迁,这世间总还有可供缅怀昔日盛景的空间——当初的平郊旧地正如今日的故人旧文,在时代偶或宽容的缝隙中,保留至今:就像以岳永逸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始终在孜孜探寻着燕大社会学系诸篇毕业论文之下民俗与田野的往昔脉搏;今朝世人也从未忘记过存续至今的平郊村及其身后学理发展与政治变迁的诸多议题:他们不断重返并再探平郊村,将今昔的掌纹贴合比对,以期开拓更丰富的文化境界、回答更复杂的历史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燕大学子与京郊村众,抹平大学与田野的空间阻隔、交叠彼此命运后造就的“历史留声机”,一次次带领我们,跨越往昔与今朝的时间鸿沟,直抵八十年前的平郊村口,也令更多学人的命运与文章,共此血脉相连。
作者:颜一澄,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直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