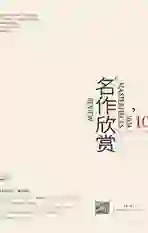隐喻的修辞才是散文的灵魂
2024-10-12丁帆高明勇
高明勇(以下简称“高”):丁老师好,一直想和您做一期对话。您这两年新作连连,每次读来总是让人“一念旋起”,仔细思索之后,却又期待下一本新书,寻找最佳时机,直到这次看到您的《消逝的风景》。一直以来,您给人的印象是笔耕不辍,佳作不断,新书不断,您为什么会说“这是出版的这么多书之中,我最满意的一本”?“最满意”主要体现在哪里?
丁帆(以下简称“丁”):像我这样的人,写作半个世纪了,形成了一种惯性,只要闲下来,不写手就痒,就这么一点爱好,如抽鸦片一样,是有瘾的。2024年我预计出版七八本书,均为这五六年来所写的学术论文结集和随笔散文集,当然,主要还是学术论集居多。除了去年底商务印书馆的那本《文学与价值》外,尚有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中的我的第一部学术书籍《中国乡土小说史论》,这是“中华当代学术辑要丛书”之一种;译林出版社的《译林评论》和团结出版社的《序跋集》(不含自己书籍的序跋)也在编辑付印中。还有一本《批评的灵感》,则是介于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之间杂交文体的文章结集,我称之为“学术随笔”,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疫情期间,困在家里,则是我以前一直在梦中设想的一种身陷囹圄、心无旁骛的写作环境,从章太炎到陈独秀,再到瞿秋白,其中自白式的自传,都是他们在牢狱里的佳作,只有在这种语境中,作者才能静下心来,深刻地反省内心深处想表达的真实情感和思想。当年我编辑《金陵旧颜》时,还责怪陈独秀的旁骛太多,耽误了真性情的写作,他的开篇之作就是那篇自传体散文《江南乡试》,语言极其生动,也极有烟火气,可惜神龙见首不见尾,多想看他的自传体散文延续下去,却再无下文了。瞿秋白则更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书写他一生做文人、写作品这一理想的破灭,一个共产党人在大义凛然就义前,说出了人性深处的思想,并非“多余的话”,堪为真正的烈士。鉴于此,我权当瘟疫这个恶魔将自己关进了囚笼,静心屏气地写了30万字的散文。
我分别给《中国作家》和《当代》杂志开了散文专栏,也给《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投了一些散文随笔,题材就是描写我一生中所看到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主要是想表达风景背后历史纵深处的人文思想,从城市到乡村,我试图寻觅到一种剖析社会和人性的入口,冀望显示出画面背后许许多多读者能看得见的隐喻。
《消逝的风景》就是我想在城市风景的历史遗迹中,试图让读得懂的读者去读到历史背后的一种呻吟,从而认识历史和今天的自我。我说是“最满意的一本”,是指在我的散文集中,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满意的一本,那是因为从编辑到装帧,从开本到纸型,再到封面设计,尤其是封面的画面色彩和设计让我一眼就想起了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黄金时代的《吻》,都是我很满意的。
当然,作为作者,都是在期待更满意的下一部作品问世,我更期待的就是在《当代》杂志专栏上发表的散文作品,结集后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乡村风景》(或曰《依昔》)。
高:您说自己起笔写这本《消逝的风景》,灵感来自伍尔夫的《伦敦风景》,具体是指哪个细节、哪个故事,或者哪句话、哪个观点吗?
丁:是的,不仅仅是伍尔夫,许多著名作家都在写“城市风景”,伍尔夫出生并生活在伦敦,她这部不长的散文随笔集虽然并不是很优秀,却很有特色。它以描写伦敦码头、牛津街、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等地理风景,作为她对英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的桥接视点,看起来是写街头风景,笔底却充满着现代哲学意味。她这本书的细节和故事并不引人入胜,所以影响不大,我只是借用她书名的寓意而已,因为此书的原名叫《南京风景》,后来我怕效颦,才改成了《消逝的风景》。其实,更令我佩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那本非虚构的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这不是他拿手的政治讽喻小说,却更有人间烟火气,故事和细节都很生动,读来受益匪浅。而现代主义大师波德莱尔所写的那本《巴黎的忧郁》,也让我感触颇深,他试图用“一种诗意的散文,没有节奏和音符的音乐”来描写巴黎这个“城市风景”中的阴暗和丑陋,可见散文的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它的灵魂所在。
高:其实这种情愫在您之前的创作中也是若隐若现。
丁:对,三十多年前,我写第一部散文随笔《江南士子悲歌录》(再版时改成了《江南悲歌》)时,是以人物肖像画为描写中心的,直到《先生素描》,我都是将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的。然而,风景描写更是我期待的描写对象,倒不仅仅是梭罗的那种具有超前意识的“生态自然”吸引了我,而是我在儿童时代开始看到的城市风景和乡村风景,触发了几十年后的回忆,从风景中寻觅到“我故我在”的主体意识,风景画面背后“自我”的发现,才是写作的真实动机。巨大的时代“隐喻”,让我时时都想动笔,虽然它们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但当时是惘然的,是没有自觉意识的。后来开始喜欢观赏西方的油画,心智有所启迪,其风景画和肖像画背后透露出来的人文意识,往往是超越画家技巧和故事的人性释放,于是,追寻风景背后人文意识中所包含的历史况味和现实意义,才是我写作最有激情的冲动。城市风景和乡村风景的描绘,便成为我近十年来散文随笔由人物素描转向风景描写的缘由。
高:您所选取的童家巷、光华门、豁蒙楼等“风景”,其实就是一些南京的“地名”,或“地理符号”,您在写作时有自己的“风景”选取标准吗?还是说主要是与自己有交集、印象深的“风景”呢?
丁:是的,我笔下的风景,都是在我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理符号”,然而,其符号背后的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却是我更看重的东西。当然,无论是城市风景,还是乡村风景,我都是按照自己生活在南京和宝应两地的时代顺序来构筑非虚构风景画面的。在《消逝的风景》中,里面提到的地名,如今依然还存在于南京的大街小巷之中,但是,它们早已成为面目全非的地名遗址了,甚至连一点旧颜都没有留下。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江城子:老南京》,该书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描写南京旧景的实录重现出来,后来南京出版社再版此书时,又加进了几篇文章,改名为《金陵旧颜》。那是再恰当不过的历史旧景的文字再现,对照南京旧时的老照片,其风景画和肖像画,活脱脱地将旧日时光里的老南京生活,用蒙太奇的长镜头还给了历史,让人伫立在风景和人的图像中,真切地体味到沧海桑田中“我从哪里来,欲到哪里去”的哲思。
风景分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两种不同的风景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绪:前者似乎是纯客观的,但其中也隐藏着不为人觉察的主观意念;后者则是纯主观的,其中却有各种各样观景的视角。这些关于风景的书籍,只是我个人对世界的一种生命的认知和体验,是我眼中城市和乡村的感官书写,也许,它们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写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景,那才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天赋和职责。
高:印象中,“风景”在您的写作中是一个高频词,比如在您的那本《玄思窗外风景》中,有《你看风景,风景看你》《风景:人文与艺术的战争》《在风景移动中的速度写作》等章节,您想借此表达什么?
丁:的确,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西蒙·沙玛在他那部皇皇巨著《风景与记忆》中所说:“只有了解风景传统的过去,才能澄清当下,启发未来。”“所有的风景——不论是城市公园,还是徒步登山——都打上了我们那根深蒂固、无法逃避的迷恋印记。”因此,“风景”一词在我所有的书籍和文章中,是一个高频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我年轻时试写小说时对乡村风景描写的眷恋。当然,这个高频词也成为一种无意识,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因而让我提出了中国乡土小说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三画”理论。其中,为什么会把“风景画”置于首位,原因就在于风景不是死去的原始和自然,而是活着的历史,意即它就是历史的见证者,所以,你看它,你就成了历史的主宰;而它看你,才是戴着历史审判者的眼镜,看着人类一切恶劣行径的最后报应。所以,风景和人,是互换的被看对象,所有的喜剧和悲剧的生成,都饱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风景巨大辐射。
高:您在“个人词典”里,如何定义“风景”?
丁:在我的“风景词典”里,我曾经说过:风景的自然属性也是有着两种形态的:其一是客观的、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这就是如今活在后现代文明生活环境中被“机械化”了的人为了摆脱文化的困扰而寻觅追求的那种情景和情境。其二是人类为了攫取、褫夺、利用大自然而对其进行改造、破坏或“美化”的风景。当一个旅游者的目光分不清这两种形态之美丑的根本区别时,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已然丧失了他们的歉疚感,麻木甚至理所当然地在风景欣赏快感中获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大自然风景之痛,人类能够倾听得到吗?即使能够听到她的哭泣,你会触摸到她的痛感吗?你会“像山那样思考”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一个人身处喧嚣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之中,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亲近后,生存的意义就少了一种原始的野性,这大概就是梭罗所要寻觅的自然野性吧!当然,另一种声音此刻就会强烈地抗议:难道大自然的美景不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吗?我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主义者,但是,我反对人类那种无节制地糟蹋自然资源与自然风景的卑鄙行径,我们要倾听自然的哭泣,擦拭山湖的泪珠,抚慰她们的心灵创伤。这也许就是人类与自然无法解决的悖论,但是不知道这个悖论的存在,无疑是人类的悲哀,因为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自然”的哭泣和呐喊了。
高:能否这样理解,您所说的“风景”,不单纯具有文学/文化的意义,更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索?
丁:任何自然的风景背后,都离不开观者“内在眼睛”的解读,如此说来,我们将用什么样的目光去看风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风景的社会属性同样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同样的景物,在不同的人群之中,她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这种差别之大,或许是与各人的生活经历与审美欣赏习惯有关,或许是与各人的世界观和生存观休戚相关。我眼中优美的风景,你看出的则是丑陋,他看出的却又是一个可利用的物体。殊不知,看风景是要怀有一颗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的,离开这个原则,你就没有资格去欣赏自然赐予你的美景,你对自然美景的占有应该只是精神层面和哲学层面的,而非物理性的践踏与侵害。
高:您似乎一直对“文体”问题非常看重,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思考,在“学术文章”与“学术随笔”之间尝试。如果说二者的“交叉点”是“学术”,您认为二者的“距离感”在哪里?或者说“创作”与“研究”本可以合为一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丁:你提的文体问题很好,试图将抽象的学术表达与形象的艺术表现融合成另一种杂交文体,正是我多年来的努力,目的就是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感”,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文体融合”的目标。无疑,僵化了的学术体制,严重制约了文学教育中的文学表述,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是文学抒写的表达能力急剧下降。所以我提倡文学教育中,要打破这种高头讲章学术文体的格局,让文学的活水流进大学课堂,流进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玄思窗外风景》序言中说:让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从文学的本质出发,才算是更加有效的批评和评论活动,否则,我们就是一个拿着手术刀解剖尸体,示范给实习医生的外科大夫而已。不融入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一个脱离了文学趣味和文学原动力的文本阐释,而非文学本质的阐释,所以,我想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中介入具象的文学体验,展现感性思维的活力——无疑,20世纪二三十年前接触到的法国“评论小说”文体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这只是一种尝试性的介入,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因为我首先喜欢的是文学,而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甚至文学理论难道不是与文学创作同属一个母系吗?虽不是孪生兄弟,却也是一奶同胞,我们没有理由离开其母乳的哺育而另找“奶娘”。
高: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意义,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思索和探索。
丁: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既是一种文体的尝试,又是一种对文学本身的尊敬,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种被称为“学术随笔”的东西就是完美的批评和评论文体,但是能够得到一些读者的认可就足矣。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大众化的书写会降低批评、评论和理论的水平,不能升华到哲学的层面,殊不知,形象思维的表达或许会以更幽默风趣的形式悄悄闯进哲学的殿堂,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审美的收获,这样的价值观植入方式也许会让人更加牢记。
我在《从瓦砾废墟中寻找有趣的灰姑娘——批评阐释与文献、文学史构成方式摭拾》一文中说过:作为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还在于他能否对文学作品保有一种“艺术趣味”——能够从作品形而下的欲望化描写形象中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理性判断上去。前者是基础,需要批评家具有一双“内在的眼睛”,用“艺术趣味”去体验有血有肉的作品肌理,只有真切地感受到作品形象的脉动,你才能进入对形象学理化和学术化的规整;而后者的理性判断,并不是给艺术作品贴上某种理论和方法的标签,它的一切判断都不应该脱离你对文本作品形而下的感受和经验性的判断,即便是援引先贤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也是那种水到渠成、不着痕迹、润物细无声的流入,这才是批评的“活水”源头。
高:这些年,“城市书写”越来越热,既有以城市生活者的视野书写城市的生活,更有将城市作为整体对象来观察和思考。以南京为例,比如叶兆言先生的《南京传》、程章灿先生的《旧时燕》等“南京三书”,张光芒先生的《南京百年文学史》,还有最近备受关注的薛冰先生的《南京城市史》《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等,您如何看待这种“城市书写”现象?
丁:是的,这是一种文体的仿写,在我的书柜里,放着一排诸如《巴黎传》《伦敦传》《瓦格纳传》《罗马》《阿姆斯特丹》《苏格兰史》《威尼斯史》《西西里史》等城市传记,这些“城市书写”的普遍现象传到中国,正是叶兆言首先开启的《南京传》写作,他从早期的中篇小说“夜泊秦淮”系列书写开始,转向了对南京的非虚构写作,开创了“城市书写”的先河。你说的南京书写作家,都是我多年的挚友和同事,正如我上面所说,除了史料的钩沉外,他们各自都是用自己“内在的眼睛”,看取南京这个城市风景中的历史遗迹、文化事件和人物肖像,各有千秋。我以为,他们都是在构建这个十朝旧都的史传,尤其是叶兆言首先打出了《南京传》这样的城市文学和文化名片,让各个城市的作家开始效仿,试图使城市风景的描写进入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文学和文化的桥接中,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南京这样的“世界文学之都”的阳台上,没有这些盆花装点,似乎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恰恰正是这种“城市书写”,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散淡的市井烟水融为一体,点缀出了城市靓丽风景线中五颜六色的斑斓色彩。王振羽先生出版的《南京乎》,也是这类题材的佳作,带有巨大的历史隐喻。
高:您笔下的“城市风景”,我的理解,属于另一种“城市书写”,个体的成长与城市的成长两种“书写”交互,在个体层面体现为消逝的个人时光,必然交织经历、记忆、情感等因素;在公共层面,表现为消逝的城市风景,则多了一些文学、文化和文脉的考量。您如何界定自己的这种“书写”?
丁:是的,你抓问题很准,“个体的成长与城市的成长两种‘书写’交互”,正是我将个体成长中的生活经验,融入每一个时代变迁中的企图,所以,我尽力将自己的童年视角、少年视角、青年视角、中年视角和老年视角,客观地代入写作中,把各个时代风景的成长史客观中性地折射出来,明智的读者就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原始风貌。当然,作为一个叙述者,我有时也抑制不住自己情感的冲动,跳出来评说几句,这不仅破坏了历史客观呈现的“包浆”,而且也从叙述的层面破坏了艺术留白的技巧。我明知“胆汁型”的冲动对文学创作是不利的,但忍不住,我的抽象思维的结果总是想让读者知晓,这就是我长期被学术学理文章熏烤的“弊端”——总要将形而上的逻辑哲学思考代入散文写作中,而不管文学形而下的描写特质。这也是我谈到的应该让学术论文从概念化写作中走出来,融入文学趣味性元素主张的反弹与反射——散文随笔创作也应融入形上的哲思,提升其文化哲学的含量。所以,文体的多样化,也就是文无定法的古训,才是散文存活长久的理由。
高:记得之前有人将类似的创作定义为“学者散文”,您怎么看?
丁:有人将它归类为“学者散文”,我不予评判,但我深知,我要克服的问题则是:尽量少发议论,多加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描写,让文章活起来,即便是议论,也须得采用云波诡谲的“曲笔”技巧。我想,这也是散文创作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悖论,那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模式,就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尽管它有许多弊端。
高:以“乡土文学”做参照,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城市文学”?如何理解“历史文脉”?
丁:“乡土文学”是“城市文学”的对应参照物,前者是农耕文明的奏鸣曲,后者是现代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乡村风景”是正在“消逝的风景”,而“城市风景”也是在不断变迁中“消逝的风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淘汰了前工业文明留下来的“城市风景”,比如那些城市风景中一度引以为豪的大烟囱、大锅炉、大厂房、大机械,如今都变成了城市的污染源,逐渐消逝在“城市风景”的地平线上,这就是“历史文脉”的风景变化。然而,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基因遗传下来了,作家的文学描写,就成为这种基因火炬的传递者,当然,许许多多曾经走过那些时代的人,也在不折不挠地追逐着旧日的时光,这样的题材,在我即将于《花城》上发表的一篇散文中有所描写。这就是写我看到的那些住在公寓,甚至别墅里的老人,在缺水少雨的山地里开垦处女地,种植各种各样农作物的情形,这不是“历史文脉”,而是“历史血脉”的传承,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深刻眷恋。它隐喻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高:写一座城市,不同身份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作为作家,作为学者,各有其兴趣,有其侧重,以“一位吹毛求疵的批评者”来写南京,您的兴趣、灵感会侧重在哪里?
丁:其实,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涉及,我以为,每一个人看风景的眼光都是不同的,因为个体的差异是巨大的,同一风景,有人看到的是喜和乐,有人看到的是悲和苦。那是缘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的差异,从而让自己眼中的风景呈现出了色差、落差和反差,而我作为一个具备了批判意识的学人,当然寄希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形而下的文学作品中去,但不是那种强行的植入,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观点越隐蔽就越好”的艺术技巧下的“曲笔”表达。
高:我留意到在您这里,“批评家”和“评论家”似乎有着不同的界定,您认为有哪些区别?
丁:所谓“批评家”,其原意特指在文学领域中,善于采用批判哲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批评性的指责,被称为“吹毛求疵的人”。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批评家”就是采用某一种理论作为武器,对文学思潮、流派、社团和现象进行高屋建瓴批评的文学理论家,其文章讲求逻辑性,往往带有指导性和引导性,而非单纯狭义的批评者。在百年文学史上,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个是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如恩格斯和别林斯基那种);另一个就是20世纪强行植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苏式”批评方法(如毕达科夫等传播者),他们强调的是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作用。
而中国的“评论家”,也与西方“评论家”和“批评家”合体的称谓内涵不尽相同,那是专指从事作家作品评论分析的人,其职业性和专业性很强,分工很细,甚至有的“评论家”一辈子只专注一个作家的作品研究。这一类评论家被人诟病的原因,大多数是命题作文,概念化文气较重。
高:以前我围绕《知识分子的幽灵》写过一篇书评,写到从一个学者的批评家经历到一所大学的批评家谱系,再到一座城市的批评家群落,既有研究与批评,又有构建与传承,背后是若隐若现的“批评家本色”的精神谱系。其实,像南京这样,一个批评家群落云集一座城市,在城市中是很罕见的,您怎么理解这种批评家与城市/大学的关系?
丁:你的问题很深刻。一个城市的风格,与它的教育史是有密切关系的,也与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著书人、教书人,乃至一般的市民阶层都血脉相连——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精神谱系”才是最重要的城市价值资源。南京作为旧都,尤其是中央大学的所在地,其所形成的精神地标性的血脉,并没有被时代的洪流冲垮淹没,所以,那种特立独行的文风仍在,自由之意志仍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飘浮着,虽然只是风轻云淡的一现,却也是一个时代可以观看的一道风景。这些有点本色的批评家虽也是极少数,各自为政,“荷戟独彷徨”,且散落在南京的各个高校里,但他们的文章,也算是从这个“世界文学之都”里发出的一声声呐喊。
高: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对您来说,南京意味着什么,另一种“乡愁”?如果在您生活过的苏州、扬州、南京之间做个比较,各意味着什么?
丁:南京是我半个世纪长于斯、活于斯的城市,我对她的感情是最深切的,这在我编写《金陵旧颜》时的序言中,就说得很清楚了:“我爱这方热土,不仅仅是一种故园的眷恋,更是因为在这山水城林之中埋藏着我一生的读书梦和生活梦。”我喜欢“此地甚好”(瞿秋白语)的金句,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是读书写作的好去处。
苏州是我的出生地,那里埋藏着父亲的眼泪,以我的名字纪念那段岁月,是我摇篮里的梦魇。苏州是一个吴侬软语的温柔乡,在那里,却并不缺少文化的刚性,从东林党人的历史背影中,我们看到了大写的城市人格。
扬州甚好,那是古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销金窟,是人类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而在这个城市下辖的宝应县,留下了我最宝贵的青春记忆,当人们在批评“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仍然不后悔那段苦难岁月的磨练,它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中国”这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常识问题——一个没有看过“乡村风景”中苦难悲剧的人,他就无法看见中国的本质,也就看不见“城市风景”对于一个乡下人的奢侈。高晓声笔下的苏南农民(《陈焕生上城》)对于生活在偏僻水乡里的农民来说,那也是奢靡的行状,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旧时代里,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这些我都写在《乡村风景》里了,最让我不能释怀的就是那篇发表在《随笔》上,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的《老屋手记:梦里不知身是客》,那才是我至死难忘的“乡愁”,它让我终生铭记。
至于扬州市,那是我“十年一觉扬州梦”读书工作的地方,几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闲话扬州〉的闲话》,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七八年前,我写的《先生素描》,其中就有当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教我为人为文的先生们,那也是我的读书“乡愁”。如果有闲,我还是要续写扬州瘦西湖畔旧梦篇的。
高:您的《消逝的风景》其实也是《江苏新文学史》的一部分,或者在“江苏新文学史”的延长线上,从历史文脉看,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里的身份认同问题?
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逝的风景》也是我在80年代研究中国乡土小说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中所说的“地域文化”对作品的影响,主要是“异域情调”对读者的影响,也就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对“乡土文学”概念的定义,即地方色彩是作品的灵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对这种“异域情调”的一次文学创作实践,无论是乡村风景,还是城市风景,都不可能离开这种风格的抒写。其“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是融化在作品之中的。
作者:丁帆,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知识分子的幽灵》《消逝的风景》等。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