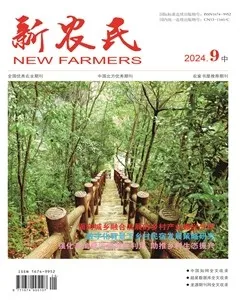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基层治理的新实践
2024-10-12葛传宇
摘要:基层治理现代化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一个部分,随着国家资源下乡、项目下乡、政策下乡等一系列的治理变革,基层治理的重点与乡镇政权的特性也发生改变。本文以河南省H县为例,总结了其党建统领基层治理路径,并从基层空间构建的组织边界、村民自治体系的功能再造、村干部行政化与选择性行政三方面提出新的思考,表明要抓党建统领基层治理,重构党建治理新格局,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
关键词: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压力型体制;组织架构;乡村振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三农”问题日渐突出,村民自治越来越不能担负起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尤其进入后税费改革时期,随着国家资源下乡、项目下乡、政策下乡等一系列的治理变革,基层治理必须抓住什么?乡镇政权的特性是什么?一时间,目标多维条件下的乡镇政权运作变得不知所措。于是,相关学者在没有搞清楚乡村体制运行的基本逻辑前提下,面对基层现代化治理的各种约束条件,盲目地开出所谓的“药方”,使得乡村“何去何从”“乡村政权是什么”这个基本的前提变得暗淡不清[1]。基层政府也意识到,要想出色地完成上级政府压力型和运动型的重大政治任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系统是行不通的,而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就是这种合理的政策选择。在基层自治的空间中嵌入党的主体性,抓党建促进基层治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基层政府通过抓党建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避免口号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惰性、推诿、低效率、自保自利、裹足不前等治理难题,使得基层治理有了“主心骨”“当家人”。但这种“主心骨”“当家人”的角色不应成为万事包办的家长,而是应通过集中各方面资源,千方百计地释放市场的潜能和效率,从而达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这一制度的落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可行性的实施路径[2]。
1 国家推进基层治理实践的历史逻辑
围绕着我国国家治理的模式,学界提出很多模型,以下对各种模型的来龙去脉和研究的道路进行梳理。
1.1 锦标赛体制与行政发包制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都在进行市场经济的大实验,地方政府展开激烈的竞争。锦标赛理论认为,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的激励,就要冲业绩发展地方经济实力,于是各地方展开类似于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竞赛。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逐渐“法团化”,像市场上盈利的公司,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财政包干制实际上是以财政分权的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展开竞争”[3]。基层政府也是在这种“驯化”中不断成长并且适应市场经济中自身角色的新的定位。
行政发包制是从基层政府治理的失序方面展开的论证,即锦标赛制在强调地方官员晋升的同时,也看到竞争导致了市场的分割、重复建设等相互的、盲目“攀比”“较劲”和“拆台”,因为官员之间无法像商人之间那样实行利益合作,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因此,中央政府为了调节地方政府在竞赛中的发展失序,在采取经济激励的同时,也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了必要的控制。正如学者周黎安指出“如委托人的管理和监督成本,财政约束,激励代理人的成本,平民百姓的权利保障和合法性预期,等等,使得官僚制的现实版本偏离其理想类型,向行政发包制转型”[4]。
1.2 压力型体制与运动式治理
具体而言,压力型体制表现为“上级政府通过将确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任务等‘硬性指标’层层下达,由县而至乡(镇),乡再到村庄,并由村庄将每项指标最终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5]”。在目标管理上,采取“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5]。这种考核机制就是压力型体制下的产物。周雪光认为,“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点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其常规机制,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6]针对这种治理方式,周雪光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中,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运动式治理则是针对这一矛盾及其组织失败和危机而发展起来的应对机制之一,反映了国家治理的深刻制度逻辑”[6]。
2 河南省H县党建统领基层治理路径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基层治理逻辑也在不断地转换,这背后凸显的是不断变迁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逻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在逐渐走向融洽,国家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基层,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下乡”到脱贫攻坚中的“政策下乡”和“资源下乡”双管齐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近年来,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等治理都采取了大部门体制,地方政府也意识到,要想出色地完成上级政府压力型和运动型的重大任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是不行的,而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就成为目前比较合理的政策选择。
2.1 重塑组织架构,优化机构设置
河南省H县为了破解县乡权责不清晰、条块关系不融洽、乡镇统筹没权力、条线压责到属地等突出问题,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构建权责明晰、治理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基层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构建“王”字型基层治理架构。改革前(如图1),乡镇分工形式比较灵活,乡镇在分配工作时要考虑干部能力的因素,除了职位本身规定的职能外,还可以在统筹乡镇总体工作的基础上来分工。本文在调研中发现,一个乡镇所有副职领导并非能力大小都一样,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另外,有些新提拔的年轻副职干部在本职工作上也有一个需要历练的过程。但是,这种除本职工作以外的灵活分工,即“能者多劳”的分工往往没有界限,导致边界不清带来工作上的推诿扯皮、无人负责的现象时常发生,因为每人对自身工作边界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乡镇在分工上往往是靠非正式的情感因素来支配,靠乡镇主要领导的政治统合能力来实现。政治的统合能力是结合各个副职能力的大小来进行分工,能力强的副职多承担任务,当然也多担责;能力弱的副职少承担任务,当然也就少担责。干部的晋升往往是和主要领导的赏识有关,能为主要领导分担的副职更有上升的可能。
改革后(如图2),乡镇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按照职能分工,具体划分了工作职责。从县到乡,各个职能定位清晰、目标明确,打破了过去“大锅饭”的职能分工,乡镇在总的工作格局建构上实现“人人有责、事事具体”的大工作格局。在考核上,也能比较具体地量化各自分管领域的工作成效,实行年度排名,对工作落后的干部采取多种方式安排其进一步的工作。这种压力传导会在整个干部制度中产生深远影响,压力是通过层层传导机制逐级往下的。除正常的分工安排外,这种模式还衍生出一种专班工作制,即对于各个分管工作,尤其是很难具体实施的中心工作、涉及多个联合主体的工作推进的任务,还是按照乡镇的政治统合能力来实施,建立各种中心工作的专班工作制。但其中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即干部的能力的不一致导致这种分工往往难以人尽其才,因为在管理中“人”这个要素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是有能力大小之分的,这必然导致工作存在短板,而且在固定分工的格局下无法弥补,在各司其职的状态下,工作的固定性不会迁就人才的不确定性。
2.2 推行科学考评,强化组织领导
在治理考评方面,推行乡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年度排名、“双向换岗”制度,全面推广“三评两比一综合”考核方法。“三评”即单位全体(代表)人员对班子成员进行评价、中层干部对班子成员进行评价、班子成员之间互评;“两比”即上级业务主管领导对下级同业务分管同志排序,本单位“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排序,进行“纵”“横”双向比较;“一综合”即综合考量领导干部在日常“抓项目促发展”“抓治理解难题”的表现和业绩。通过“三评两比一综合”,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科学分析研判,实现考评精准化,真正树正导向、传导压力、推动工作。
3 结论与思考
新时代,在全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但是,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3.1 基层空间构建的组织边界问题
百余年来,中国的国家权力持续渗透乡村社会,政府的组织边界也在不断发生重构。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是要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如何激发基层组织活力是当下改革的重点,如“在组织维度,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上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它有法定义务协助政府的相关工作;在人事维度,村干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部,但他们的报酬又由国家财政负担,基层政府亦以乡镇干部的角色和要求来对待他们”[7]。
3.2 村民自治体系的功能再造问题
基层自治实施以来,对于构建乡村治理空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整合了乡村的公共资源。但随着新的形势不断变化,在国家大批的政策、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原有的组织体系不能承接大规模的改造,在社会转型期中,我国旧有的规范和秩序形成的文化权力网络在逐渐丧失,而新的规则和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现代行政科层制最大的缺陷是难以预知因社会急剧变迁所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由此容易留下许多‘规则空间’和‘治理空白’”[8]。
3.3 村干部行政化与选择性行政的问题
基层治理的末梢靠非正式的村干部运作,可以说村干部是县政府的“腿”,没有腿便不能走路。随着近几年来国家的资源和政策的双重下乡,乡镇干部往往需要靠前指挥工作,这导致村级干部行政化问题日益突出,村级组织承担着越来越繁重的行政任务,各种报表、汇报、检查、督查等纷至沓来,使得村干部成为乡镇运作的“神经末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是给基层治理格局打了一剂“强心针”,整合了乡村资源,凝聚了乡村共识,提升了乡村面貌,使乡村成为留住“乡愁”情怀的根。
参考文献
[1]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
[2] 欧阳静.简约治理: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2(3):146.
[3] 周飞舟.锦标赛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9(3):57+56.
[4]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6):7.
[5] 王汉生.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9(2):63.
[6] 周雪光.运动式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106+107.
[7] 景跃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J].治理研究,2018(1):56.
[8] 欧阳静.政治统合制及其运行基础——以县域治理为视角[J].开放时代,2019(2):195.